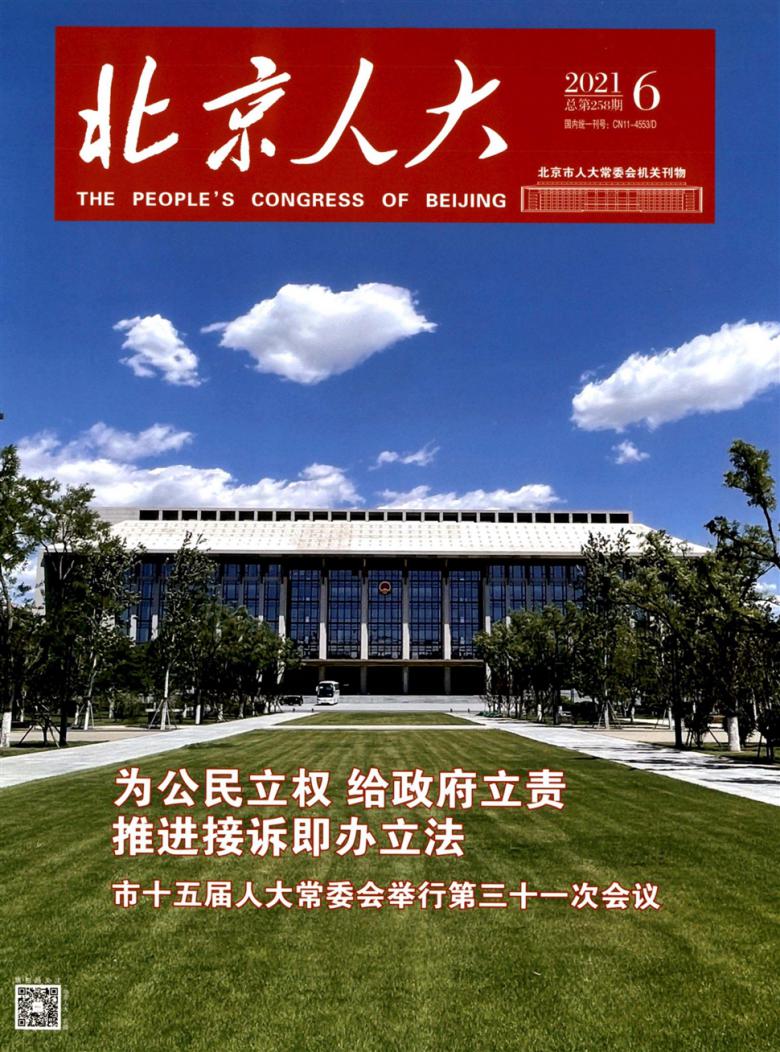對我國20世紀散文的“真情實感”探討
佚名
關鍵詞:散文 真情實感 客觀生活 主觀感受
前 言
中國20世紀文學及其囊括下的中國20世紀散文、詩歌、戲劇、小說的學術概念,最早由北京大學錢理群教授等學者在20世紀80年代提出,莊漢新教授在《中國20世紀散文思潮史》一文中也明確提出了“中國20世紀文學及散文”的理論,該理論針對有關中國20世紀文學,一直沿用中國近代文學、中國現代文學、中國當代文學的約定俗成的概念來分別表述其段落,卻忽略了時間的無窮順延性和區別歷史分期的相對性的現象,提出“中國20世紀文學及散文”的理論,讓中國20世紀文學及散文的劃分表述更為合理、正確、科學。同時為我們進一步研究中國20世紀散文的“真情實感”提供了有力的學術理論支持。
在中國歷史文化的長河中,散文始終占有重要的位置,散文發展呈現“波浪式前進,螺旋式上升”的特點,其間幾次繁榮時期比如“五四”新文學發展初期、60年代初期,新時期等極大地促進了散文的發展。尤其進入90年代,散文呈現出熱烈而繁榮的局面,形成一股“散文熱”,一直持續至今,其市場前景越發讓人看好。但在繁榮的背后,我們冷靜思考后就不難發現,當代散文研究相對匱乏,根本無法和小說相比較,而且散文研究相對雜亂,沒有形成一整套統一被學術界廣泛認可的理論體系。在有限的研究中,散文的“真情實感”又是散文界討論的重點話題,眾說紛紜,莫衷一是。文章參考借鑒了散文界權威觀點,來探討散文的“真情實感”。
綜觀中國20世紀散文思潮的主流風格,是寫實主義、現實主義,是與中國現實社會生活和民眾真實心緒息息相關、血肉相連,具有強烈的反對封建主義、專制主義、蒙昧主義,爭取個性自由、人民民主和階級解放的思想內容。從20世紀初, 站在散文思潮潮頭前的魯迅先生,高擎紅旗,對中國20世紀散文做出的種種開拓性的貢獻,《野草》的問世直至王實味《野百合花》的出現、鄧拓《三家村雜文》的異軍突起,都無不貫穿在中國20世紀散文嚴格寫實主義、現實主義的紅線中,從來沒有間斷過。雖然其間各種倒行逆施的政治勢力,憑借其強力、暴力,殘酷打壓、迫害,但中國20世紀以魯迅為代表的一大批寫實主義、現實主義散文作家,始終忠實于社會生活和人們內在心靈的真實,執著于對現實人生的真實描寫,說真話,抒真情,敢于書寫人民群眾的心聲,表現了一代散文作家應有的干預生活的主體精神和高尚人格,其勇氣、膽識、風范,驚天地、泣鬼神。同時,關于散文的理論及其批評也曲曲折折,尤其是關于散文的“真情實感”問題歷來是散文界作家及文學批評家討論的重點。魯迅的散文批評經典之作《怎么寫》,對散文抒寫“真情實感”進行了認真的探索。他提出了散文的重要審美命題——散文的幻滅“不在假中見真,而在真中見假”。周立波在其主編的《散文特寫選》(1962年)序言中, 便寫下一段頗具權威的話:“描寫真人真事是散文首要特征。散文特寫絕對不能仰仗虛構。它和小說、戲劇的主要區別就在這里”。1980年前后, 巴金連續發表了《說真話》、《再論說真話》、《寫真話》等文針對17年某些散文滿紙的假話、空話、套話和藝術上單一、封閉的創作傾向, 倡導散文要說真話, 抒真情, 要“當作我的遺囑來寫”, 要“把心交給讀者”。這些無疑都是發自一個有良知作家的肺腑之聲, 因此巴金的“真話論”一出, 立刻獲得散文家和散文研究者的廣泛認同。20世紀80年代, 在散文研究方面頗有影響的林非先生在《關于當前散文研究的理論建設問題》一文中比較全面探討了散文的范疇、本體、創作、鑒賞和批評等問題,其中反復強調“散文創作是一種側重于表達內心體驗和抒發內心情感的文學樣式, 它對于客觀的社會生活或自然圖像的再現, 也往往反射或融合于對主觀感情的表現”,他從“真情實感”和文化本體的角度追問散文,使散文的創作、鑒賞和批評等理論發展更進一步。林非不僅強調散文的“真情實感”的重要性, 而且將其定位為散文創作的基礎, 甚至將其提升到散文本體的地位。加之他還從散文美學, 從整個民族文化建設的高度來思考散文的本質特征, 如此散文的“真情實感”論自然便成了80年代初期和中期理論話語匱乏的散文界的一個熱門話題,引起文學界的廣泛討論。時至今日,“真情實感”仍然是一個廣泛用于散文創作、研究、批評的重要概念。閱讀所及, 幾乎每篇每部研究批評散文的文章書籍, 都對其津津樂道。然而,究竟何謂散文的“真情實感”,一篇散文應不該應該遵循以及如何遵循“真情實感”,各家眾說紛紜。
在中國漫長的古代社會中,古人對散文的理解一直比較寬泛。通常包括:一是指與韻文相對而言,泛指除詩、詞、曲以外的一切不押韻的文章;二是指與駢文相對,指句法不整齊的散體文字。就連“散文”這個名稱在古代也不流行。直到“五四”新文化運動,一批文學革命的先鋒們大膽吸收、借鑒國外的散文樣式,對中國傳
文學作品都是帶有感情的,散文自然也不例外,且散文更有“美文”的稱號。我們通過與其它文體相比較,就不難發現散文自身所具有的優勢,彰顯散文“真情實感”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散文作為一種文體本身就決定了它的“散”、“淡”和“閑”,使其必然成為一種“家常文體”,在西方稱之為“Familiar style”。因而,散文也不會成為時代的主流話語。如果說,詩歌、小說、戲劇更多的像書法的“中鋒”行筆,那么散文更多的是“側鋒行筆”。散文與其它文體相比,散文是最早成熟的。新文學的小說、詩歌形式上較多地借鑒國外,戲劇更是典型的外來品,它們都需要一個模仿、探索、理解、消化吸收的艱難而漫長的本土化過程。因此,它們成熟地也較晚,以至今日仍然免不了模仿的痕跡。而散文不同,雖然也借鑒了外國散文創作中的優點,尤其較多取法英國的隨筆,但由于中國古代輝煌燦爛的散文成就做積淀,以及作家們深厚的中華傳統散文的個人修養,都往往決定著他們自覺從中華傳統中汲取養分,并與外國散文創作方式與理念相糅合,在“散”、“淡”、“閑”這片屬于自己的文學園地中展示散文本來面目——真實,讓散文的生命力不斷傳承下去,這是其它三種文學體裁所不具備的。形式上,散文短小精悍,也最為自由活潑、靈活多樣,便于抒發感情、表達感觸,容易成文,也方便閱讀,在傳播思想、反思社會和自身及開展批評等方面有不可替代的優勢。更獲得了文藝戰線上“輕騎兵”的美稱。魯迅就在《怎么寫》中指出:“散文的體裁,其實是大可以隨便的”。散文所具有的這種自身優勢,也就決定了它是抒真情、表實感的;是靈魂的袒露,個性的抒發;是一種人格的張揚。敘述視角上,嚴格意義上散文的敘述視角僅局限于第一人稱,遵循“我”即作者的書寫模式。也正是散文本身文體的這種約束性限制,決定了散文“真情實感”的必須性和重要性。第一人稱“我”,沒有真實的現實生活經歷,沒有“真情實感”的流露,何以打動讀者,何以繁榮不衰?而其它文體則自由。但在散文的演變發展過程中,尤其是自20世紀90年代以來,散文創作中“虛構”與“想象”的成分與日俱增, 使得散文的敘述視角也發生了變化。許多散文的敘述視角已不再局限于第一人稱, 也不再遵從作者是一切寫作素材的來源的法則,而且普遍運用了第二或第三人稱的敘述視角。截止今日,這種現象依然存在。這便給作家的創作和讀者對作品的審美帶來了混亂和困惑。但透過散文發展史,我們可以清楚看到,散文自身不斷在變化完善,但散文的敘述視角必須局限于第一人稱,這樣才能確保散文“真情實感”的可靠前提。詩歌、小說和戲劇等文體是可以虛構的,像科幻小說等甚至可以完全虛構,且備受廣大讀者的親睞,這或者就是它們的特性,但散文則完全不同,散文必須真實,散文不是靠動人的情節吸引讀者,不是靠虛幻故事來迷惑讀者,而是靠實實在在的“真情實感”。如果我們所讀到的不是一個真實的作家的真實的事件敘述、情感流露或心靈告白,我們還不如去讀小說。因為要講虛構,散文就遠遠比不上小說的魅力。散文的魅力在于全篇“真情實感”的流露。而小說的魅力在于有完整的故事情節,有血肉豐滿的人物形象,有高度集中的矛盾沖突便,因此牢牢揪緊讀者的心,“欲知后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電視劇也大多根據小說改編而來。戲劇則主要是通過矛盾沖突,通過具體的舞臺形象再現社會的斗爭生活,能激起觀眾強烈的情感反映,達到社會教育的目的。小說、戲劇的作者,往往把自己強烈的感情傾注在人物形象的塑造上,作者對生活的感受、對人物的愛憎褒貶,一般是通過間接的方式表現出來的。而散文則不一樣,它常常像詩歌一樣,每每用直接抒情的方式抒寫胸臆,不僅使讀者知其理、曉其事,而且悟其心、感其情。散文寫人,它可以是自始至終地比較全面地寫一個人,也可以寫一個人的片斷,還可以寫一個人的某種思想閃現,或者寫一個人的一件或幾件事,甚至是寫一個人的一瞬間活動,以小見大。有人因此認為,散文篇幅短,也不是專門刻畫人物,不要求有完整的故事,因而沒有豐富堅實的生活基礎也可以寫出散文,甚至可以寫出優秀的散文。我們須知要把散文中的人物等寫真實寫活,讓讀者感到這就是現實生活的真實反映,沒有作家對現實生活的仔細觀察品味是根本辦不到的。因此,通過與其它文體的比較發現,散文作為一種文體本身就決定了它必須要表達“真情實感”。真情是散文的生命,只有直抒胸臆,把真實生活中的人物原汁原味的呈現給讀者,把真情實感捧給讀者,才會贏得讀者的喜愛。
散文的“真情實感”,首先表現在客觀生活的真實。散文題材的選擇、內容的篩選、素材的積累必須以現實社會生活中的真人真事為根據,決不能憑空胡亂想象,肆意虛構。散文的內容必須來源于生活,而且是對客觀生活的真實反映。作者要做生活的有心人,善于捕捉生活中細小的點點滴滴,以小見大,將現實社會生活原汁原味反映在文學作品中。散文的描寫力求細膩,同時也需要有豐富的生活知識,作者要注意生活積累,特別是注意細致的觀察生活,日積月累。要做到這一點,一方面要從實際生活中積累各種知識,另一方面也要從書本上積累各種知識。不論社會科學知識,還是自然科學知識,都要注意學習。沒有生活,沒有積累,只靠胡編硬造,靠個人的想象和虛構,如同高樓大廈沒有堅實的地基,是永遠寫不出好散文。秦牧指出:“一篇小小的散文也許寫作時間僅僅是一兩個小時,但卻要求作家深厚的素養,而且不斷擴大和豐富這種素養。把散文當作是‘小功夫’,‘掉以輕心’的寫作態度,是很不利于我們散文創作的繁榮發展的。即使是怎樣熟練的名作家,我們也要求他們在寫作一篇小文章時,采取‘大象搏獅用全力,搏兔也用全力’的態度”。
散文的“真情實感”,不僅表現在客觀生活的真實,而且表現在主觀感受的真實,以真誠的心態,以“真情實感”去打動讀者的心弦。著名作家莫言說過這樣一句話:“關于散文的寫法、說法很多,如果讓我說,那就是一個‘真’字,真心真情真感覺。有真乃大,有真乃美”。郭沫若對此概括有一句很精辟的:“散文不是寫出來的,是流出來的”。確實,一片好的散文,定是建立在生活積累感悟之上的思想結晶,作者必有豐富的人生閱歷,對現實生活有真實而強烈的愛憎感受,才能真誠地直面人生,體味人生, 反思自身,觀照生命。這一方面,巴金、孫梨等都以自己的作品向世人們展示真實的自我,不論是億悼親友,還是追思過往,反思自我,反思社會,都真切地傳達著自身的真實生活體驗、感受和思索。散文的靈魂也在于此,抒寫自己的真情實感,以情動人,寫真人真心真事,是對生活的真實記錄和表達,而它的內容也與人們的內心世界、真實性情和現實生活最為貼近,袒露生活的真實和表達情感的率直受到廣大讀者的普遍喜歡。散文應該也必須通過真情實感,以從內心深處迸發出來的真情實感打動讀者,而不是單純依靠語言的華麗、美艷,更來不得半點虛情假意,嬌揉造作。如果不動真感情,不寫真生活,不抒真心緒,散文何以安身立命?何以能在廣大的人民群眾心中生根、發芽、開花、結果?例如魯迅的散文集《朝花夕拾》,冰心的《往事》、《寄小讀者》,朱自清的《荷塘月色》、《背影》等之所以成了膾炙人口的名篇,無不是因為“真情實感”。劉增山的《我凝望著祖國的版圖》、禾子的《長城,留在我們身后》、王英琦的《大唐的太陽,你沉淪了嗎》等散文,飽滿的熱情,深情的眷戀,傾訴了對祖國命運的關注,對民族命運的憂思,拳拳之心,無不以其“真情實感”而感人。朱自清代表作《背影》,是一篇著名的紀實散文。它以至誠、至真的父子之愛,感染了一代又一代讀者。《背影》全文不足1500字, 寫的是普普通通的生活場景和瑣事,且無華麗的文字,那一幕幕真實的生活情景“我那時真是聰明過分,總覺他說話不大漂亮,非自己插嘴不可,我心里暗笑他的迂肥胖的身軀……,父親穿著黑布大馬褂,深青布棉袍,步履艱難,蹣跚地爬過鐵道為兒子買橘子,我的眼淚又來了……”,作者將自己真情實感融入平淡的生活細節中,善于捕捉特定情景中最富有表現力的細節, 以具體細膩且凝聚著濃烈感情的筆觸, 向我們展示了一個摯愛兒子的父親的形象,他對即將離別的兒子的無限的憐惜、體貼、依依難舍的深情都包含在他那臃腫而樸實的背影里,抒發了人們所共有的思親之情, 同時表達了作者的懺悔,對父親深深的懷念,從而撥動人們的心弦, 產生感人的力量,深深打動了讀者。朱自清先生1947年曾談到過《背影》創作原因,“我寫背影就因為文中所引的父親來信里的那句話。當時我讀了父親的信,真的淚如泉涌。我父親待我的許多好處,特別是背影里所敘的那一回,想起來跟在眼前一般無二。我這篇文章只寫實,似乎說不到意境上去。”這也就是“真情實感”。朱自清沒有刻意的去追求散文的結構藝術,沒有多么華麗的辭藻,而是讓自己的真情實感樸樸實實地表現出來,筆之所至,情之所至。無夸張,雕琢,做作,掩飾,如山間潺潺而流的清泉,讓人感到自然。
回顧中國20世紀文學一百年來的發展歷程,其它文體,如詩歌、戲劇等,曾一再出現不同的斷裂、蕭條、冷落,但散文卻一直能較穩定地吸引讀者,占有讀者,走進讀者的生活和心靈,這于散文文體的解放較為徹底有關,但最重要的是散文的“真”和“實”,散文立足于現實,扎根于大地和民間,反映最低層人的苦難與不幸,成為他們心靈的代言人,用“真情實感”來吸引打動讀者,散文經久不衰的藝術魅力,也蓋源于此。然而這種“真情實感”在實際創作過程中卻是難能可貴的,受政治、經濟等各種各樣的需要所左右,散文作家的“真情實感”創作道路舉步維艱,但以魯迅、鄧拓、等為代表的一大批散文作家,始終忠實于社會生活和人們內在心靈的真實,執著于對現實人生的真實描寫,說真話,抒真情, 敢于書寫人民群眾的心聲,表現出了一個散文家所應該具有的操守。“五四”時期的現代散文剛剛起步,卻呈現了強勢的發展勁頭,散文創作是同一時期其它文體無法比擬、望塵莫及的,產生了一大批膾炙人口的名篇佳作,如魯迅的《朝花夕拾》,朱自清的《背影》、《匆匆》等等。作家將真實的社會、真實的自我、真實的內心感受通過作品真實反映在作品中,讓廣大讀者看到了一個真誠、真實的作家的人格,而絕不是帶著虛假面具去迷惑欺騙的偽君子。尤其上世紀五六十年代,在極“左”路線的高壓下,片面強調文學為政治服務、文藝為工農兵服務,要求全部展現生活中陽光的一面,“頌歌式”的散文,誰要是敢抨擊現實的弊端、揭露生活的矛盾,就認為是“歪曲”生活,“丑化”社會。到“四人幫”橫行時期,散文界更是充斥著“假大空”、“滿和騙”,完全是為“四人幫”陰謀而服務的工具,不少作家因此受到極其殘酷的打壓迫害,甚至付出了生命代價。但老一輩作家依舊堅持散文“真情實感”這塊圣潔園地,為了恢復“五四”以來散文現實主義的傳統,表現客觀真實的生活,表達作者的“真情實感”而不懈奮斗。
當然,關于散文中所描寫的真人、真事、真景物、真歷史等究竟要不要“絕對真實”,一直是散文界爭論的重點,至今也沒有明確定論。尤其面臨現在情感泛濫,題材假、人物假、感情假、表達方式和語言都假,而有的散文雖然寫真人真事,但在市場利益驅動下不抒真感情,沒有心靈的感動,虛假、矯情、造作的作品充斥著散文界,這些都對讀者的文化導向和審美品位提出了嚴峻的挑戰,更不利于散文的健康發展。作家賈平凹在回答“散文創作要不要絕對真實”的問題時說:“這個問題爭論很多,又都沒有一定結論。我個人的體會,還是傾向于‘絕對真實’四個字。所謂真實,主要是指在感情以及運用環境和事件上。古人寫的散文,題材也是很廣泛的,但古人寫散文,都是有感而發。今人寫散文,多多少少存在著一些為寫而寫的現象,所以在絕對真實問題上就出現了所謂‘理論與實踐上的不一致。’
時代在發展,尤其我們今天處于一個理性的時代, 反思社會、反思人自身成為社會潮流。真正的文學作品是對人類深層次的思考, 是賦予啟迪的,反思性的,閱讀后能給人一種啟迪,給人一種反思,給人一種思想,給人一種意境,給人一些知識,讓我們的精神世界不斷充實。而散文是社會生活的紀錄, 時代精神的折射,這讓它的思想性反思性就顯得格外重要,散文也正是適應了這種反思的需要,以“真情實感”立足,透過字里行間的“真情實感”,發出一個有良知作家的肺腑之聲,讓人們通過閱讀散文能夠有所收獲,引起廣大讀者內心世界的共鳴,對現實社會生活有更深入的反思,這才是一位優秀散文家的職責使命所在,也是我們廣大讀者所期望的。我們看到中西方社會的散文大家魯迅、朱自清、羅曼·羅蘭、羅素、丘吉爾等,他們的散文作品能夠影響一個時代, 就是因為他們的思想總是走在時代的前面,文章包含“真情實感”,用真情實感去打動讀者,去贏得讀者的喜歡。近年來,散文與小說、詩歌、戲劇、影視等文學樣式結合,增添了散文的活力,愿散文在秉承其生命力“真情實感”的前提下為廣大讀者奉獻更多優質文學作品。
1、莊漢新.《中國20世紀散文思潮史》[M].學苑出版社,2005.12
2、莊漢新.《中國20 世紀散文思潮史》前言[J].廣播電視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6.1
3、金明生.情真意切、感人至深——朱自清散文名篇《背影》再認識[J].書刊評介,2002.4
4、洪珉.《“散文熱”原因解析》[J].殷都學刊,2005.4
5、楊安翔.《20 世紀中國散文繁榮期略評》[J].新疆師范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