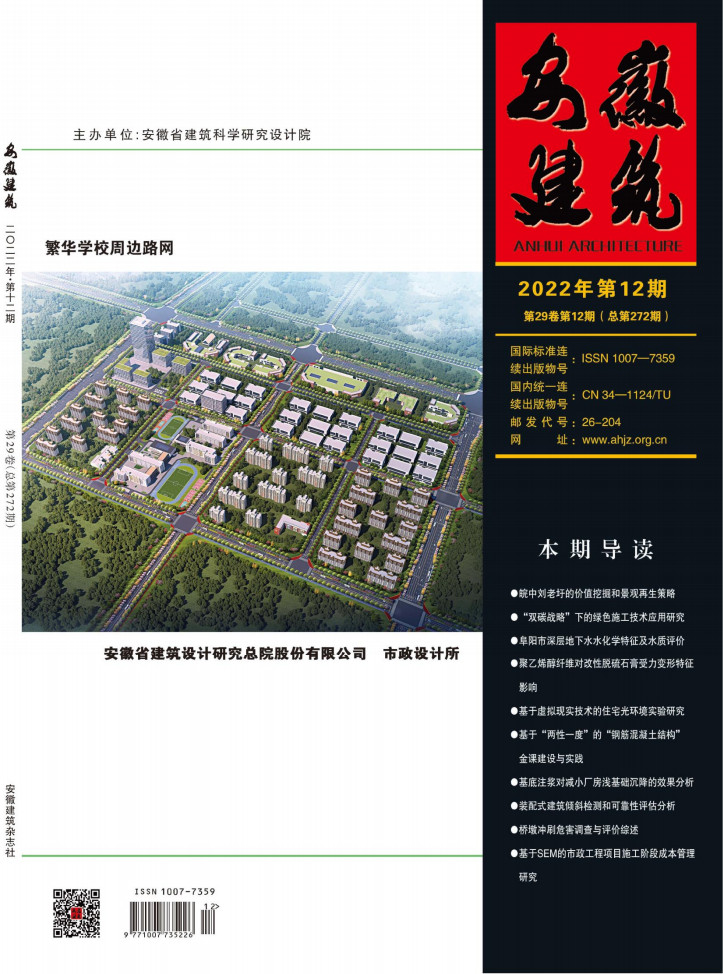王雱的《老子注》探微
尹志華
王雱(1044—1076),字元澤,北宋著名政治家王安石之子。他才華橫溢,惜因病早逝,年僅三十三歲。“其學術廣泛涉及儒釋道三家,不但是《三經新義》的主要作者,又作策論三十余篇,極論天下之事,而且著有《佛書義解》及《老子訓傳》、《南華真經新傳》等,從時事政治到思想學術,發表過一系列的議論。”[1]然而,由于變法反對派對其人格的抹黑、詆毀,致使其學術思想長期被忽略。但是,只要是認真讀過其著作的人,即使是受到負面宣傳影響,對其人格不以為然,也不得不佩服其著作特別是解注《老》、《莊》之作的精辟深刻。生活于明末清初的王弘撰在其所著《山志》中說:“注《道德》、《南華》者,以予所見,無慮百家,而呂惠卿、王雱所作頗善,雱之才尤異。”他還嘆惜王雱:“使當時從學于程子之門,則其所就當不可量。”不過,他又因為受到關于王雱人格不佳的宣傳的影響,而懷疑王雱的《老》、《莊》注解非自己撰著,“或倩門客為之,亦未可知也”。[2]這當然是毫無根據的懷疑。
關于王雱的學術思想,當今學者漆俠、盧國龍皆有精當論述。[3]本文只就王雱的《老子注》作一些探討。[4]該書現無單本傳世,其內容主要保存在北宋太守張氏所輯《道德真經集注》(明《正統道藏》洞神部玉訣類)中。李霖《道德真經取善集》、彭耜《道德真經集注》、劉惟永《道德真經集義》均有征引,可資校刊。筆者曾對王雱的《老子注》作過輯校,作為附錄刊于拙著《北宋〈老子〉注研究》一書(巴蜀書社2004年11月出版)中。
關于王雱的《老子注》,北宋梁迥在為太守張氏《道德真經集注》所作《后序》中曾作過高度評價:“近世王雱,深于道德性命之學,而老氏之書,復訓厥旨,明微燭隱,自成一家之說,則八十一章愈顯于世。”[5]
本文試從以下幾個方面闡述王雱《老子注》之特點:
《老子》主張以道治天下,批評儒家的仁義禮智等綱常名教。受三教融合的時代思潮的影響,北宋人在注釋《老子》時,紛紛致力于調和儒道之間的矛盾。王雱在調和儒道矛盾方面,提出了獨特的“孔、老相為終始”的循環論。
王雱對老子充滿崇敬之情。他認為老子與孔子一樣都是圣人。他感嘆“末世為學,蔽于前世之緒余,亂于諸子之異論,智不足以明真偽,乃或以圣人(即老子)之經與楊、墨之書比”[6]。他批評世儒只知孔、老之言有異,而不識其道為一。他說:
“圣人雖多,其道一也。生之相后,越宇宙而同時;居之相去,異天壤而共處。故其有言,如首之有尾。外此道者,皆邪說也。然而道一者,言固不同;言同者,道固不一。而世儒徒識其言,故以言同者為是;不知其道,故以道一者為非。”[7]
圣人之道是一致的,但其所處時代不同、考慮問題的角度不同,因而其言相異。其言雖異,但因同出于一道,所以又如首尾一樣是可以互相銜接的。由此,王雱提出“孔、老相為終始”論。他說:
“道,歲也,圣人,時也。明乎道,則孔、老相為終始矣。”[8]
王雱形象地把道比作歲,把圣人比作四時。四時不同,但四時相繼而成歲。孔、老之言不同,但也是“相為終始”的。何謂“相為終始”呢?讓我們聯系他在《老子注·序》中的一段話,就比較容易理解了。他說:
“道,歲也;圣人,時也。自堯舜至于孔子,禮章樂明,寓之以形名度數,而精神之運,炳然見于制作之間。定尊卑,別賢否,以臨天下,事詳物眾,可謂盛矣。蓋于時有之,則夏是也。夏反而為秋,秋則斂其散而一之,落其華而實之,以辨物為德,以復性為常,其志靜,其事簡。夫秋豈期于反夏乎,蓋將以成歲而生物也。”[9]
自堯舜至于孔子,建立了完備的典章制度,不正如夏季之燦爛與榮華嗎?但盛極則弊生,禮樂形名在現實社會中逐漸變成一種形式主義,甚至被嚴重異化,所以老子要否定它們,以期人們復歸于素樸之本性。王雱說:“老子于四時當秋,其德主金,靜一復性者也,故其尚如此。”[10]老子并不是要跟孔子對著干,就如秋天不是為了反對夏天一樣。夏天必須發展到秋天才能成歲,禮樂文明也必須向人的本性復歸才能合道。
可見,王雱認為孔、老代表兩種不同的治世方法:孔子致力于禮樂文明的建構,希望以社會制度的不斷完善來規范人們的行為;老子則認為人們的本性是純樸的,只要不擾亂人們的純樸之性,則社會不治而自治。自三代以來,禮樂文明不斷繁富,但在此過程中,禮樂文明不可避免地要受到異化,從而變成虛偽的形式,甚至走向它的反面,成為社會動亂的根源。在這種情況下,必須提倡老子的返樸歸真之說,使人們恢復純樸的本性,以消除異化現象。復性之后,社會要向前發展,又必須致力于禮樂文明的建設。因此,王雱說,“孔、老相為終始”[11],圣人之道循環相接。
王雱指出,“圣人之教,時而已矣,何常之有?”[12]社會淳樸未散,則用道德治世;社會已亂,則以禮匡世;禮治出現弊端,則又提倡復性說。因此,“孔、老相為終始”說,實際上是要表達圣人治世之方因時而變的道理。
具體聯系到北宋時代,王雱主張“以老氏為正”[13]。因為,“三代之后,民無不失其性者”[14]。這樣,在三代之后,就都應該提倡復性之說。故他認為“歸本之言,于學者為要矣”[15]。
王雱主張“以老氏為正”,并不表明他有“老高于孔”的傾向,而是說,當時的問題不是如何使禮樂刑名等制度更加完備,而是如何克服禮樂刑名等制度在現實社會中的流弊,用現代語言來說,也就是如何克服禮樂刑名的異化。王雱認為,方法只能是提倡復性說,使人們返樸歸真,不去追求外在的事物。
王雱認為,按照老子的復性說治理現實社會,是能夠取得成效的。他注《老子》第80章說:
“竊嘗考《論語》、《孟子》之終篇,皆稱堯舜禹湯圣人之事業,蓋以為舉是書而加之政,則其效可以為比也。老子,大圣人也,而所遇之變,適當反本盡性之時,故獨明道德之意,以收斂事物之散,而一之于樸。誠舉其書以加之政,則化民成俗,此篇其效也,故經之義終焉。”[16]
《老子》罕言心性,五千言中無一“性”字。戰國秦漢以至魏晉南北朝的眾多《老子》注,也很少涉及心性問題。唐代雖有成玄英和陸希聲在《老子注》中探討了復性問題,但總的說來,以心性之學解說《老子》仍非普遍現象。
北宋儒學復興,心性問題成為儒家學者所探討的核心問題之一。重視心性之學的時代思潮,在北宋人的《老子》注中,也得到了充分的反映。北宋學者普遍認為,《老子》一書講的便是盡性、復性之學。王雱更明確認為:“老子之言,專于復性。”[17]
王雱以復性之學解《老》,在《老子》注中探討了人性的來源、本質、失性之由與復性之方法以及盡性與窮理之關系等問題。
先秦時期的孟子和荀子雖然分別提出了性善和性惡兩種對立的人性論,但他們對人性的來源問題,即人性的本體論依據,沒有進行探討。朱熹就曾對孟子的性善論未能在性與天道之間建立起一種直接聯系提出批評。他說:“孟子亦只是大概說性善。至于性之所以善處,也少得說。須是如說‘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處,方是說性與天道爾。”[18]又說:“孟子不曾推原源頭,不曾說上面一截,只是說成之者性也。”[19]這里“繼之者善”指天地之理,“成之者性”指人物之性。朱熹認為孟子的性善論沒有闡明性的本體論來源和根據,理論上“少了上面一截”。[20]
孟子曾說過“盡心知性則知天”,可見他認為性與天是有一致性的。但是,畢竟缺乏直接的論證。這也就是朱熹批評他的原因。在先秦儒家典籍中,直接論述天(或道)與性的關系的有兩處:一是《中庸》開篇就提出“天命之謂性”,一是《易傳》中的“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然而當時和以后直到隋唐的儒者并未根據這一提示,將性與天道貫通起來。直到宋儒才對這一提示予以充分重視,據此建立其人性論的本體論證明。
北宋儒家學者對性與天道的貫通,學界最熟悉的例子就是程頤的“性即理”說。然而,正如陳來先生指出的那樣,程頤雖然將性與天理(天道)統一起來,但這種統一“只是一種自然的天人合一,還沒有后來那種稟受天理為性的實體說法”。[21]錢穆先生亦指出,伊川講“性即理”主要是闡發孟子之義,在伊川思想中性理“非從宇宙界落下”,亦即不是從形而上的本體而來。[22]錢、陳二先生認為,只有到了南宋的朱熹,才從本體論的高度進一步論證了性即是理。筆者通過考察北宋的《老子》注發現,其實早在二程時代,一些儒家學者在注釋《老子》時,便已明確提出了“道于人為性”的說法,認為本體之道落于人身即為人之性。
北宋學者中,最早在《老子注》中將道與性聯系在一起的是王安石。他在注釋《老子》第48章“為學日益,為道日損”時說:“為學者,窮理也;為道者,盡性也。”[23]既然盡性即是為道,性與道顯然具有同一性。但是,因為王安石的《老子注》已大半散佚,我們尚無法知道他是否明確提出了“性即道”的主張。而王安石的兒子王雱則在《老子注》中明確提出了“道乃性之常”[24]、“道,民之性也”[25]等說法。他還認為,“物生乎道而各得于道,故謂之性。”[26]這就是說,萬物之性都是由道所賦予的。
王雱在人性的本質問題上,主張性素樸論。
性素樸論起源于莊子。莊子認為,“性者,生之質也。”[27]性是人生而具有的自然資質。《莊子·馬蹄》云:“彼民有常性,織而衣,耕而食,是謂同德;一而不黨,是謂天放。”這就是說,人之“常性”就是指人追求溫飽的生命本能。因而,超出生命本能以外的東西,如仁義、嗜欲等等,都非人性所固有。莊子指出,儒家揭仁義于天下,“天下莫不奔命于仁義,是非以仁義易其性與”[28]?同時,莊子也反對把情欲說成是人的本性,認為“盈嗜欲,長好惡,則性命之情病矣”[29]。
由于莊子認為性中既無仁義,也無嗜欲,因此,性的本質是素樸的。他說:“同乎無知,其德不離;同乎無欲,是謂素樸。素樸而民性得矣。”[30]
王雱繼承了莊子的性素樸論,但對“素樸”的理解則又與莊子大不相同。
王雱注解《老子》第19章“見素抱樸”說:“不見物而見自性也。素者,性之質。人生而靜,不染諸物,故無文而素。……樸者,性之全,以樸為本,以器為末。”[31]
這是把素與樸分開來講。素是指性本清凈,就像一塊白布,沒有任何玷污。這顯然是吸取了佛教的“性本凈”說。但王雱又把它與儒家的“人生而靜,天之性也”[32]之說揉合在一起,實際上是把“靜”與“凈”混而為一了。因為“靜”是對“動”而言,而“凈”則是對“染”而言,二者本來不是一回事。王雱雖然引用了儒家經典《禮記》中“人生而靜”的話,實際上卻是按佛教觀點,把“靜”曲解為“凈”。
王雱說“樸者,性之全”,是以“樸”來指稱性體全而未分的狀態。而據《老子》第32章“道常無名,樸雖小,天下莫敢臣”的說法,樸也就是道。因此,王雱既說“道乃性之常”[33],又說“樸在人為性”[34]。王雱以樸喻性,其目的是為了說明“性能成萬法,而不主一器”[35]。“樸散則為器”,若性體全而未分,則同于道而非器。同于道則無所不能。可見,王雱關于“樸者,性之全”的說法,其用意是強調保持性體本來全而未分之狀態的重要性。
可見,王雱雖然繼承了莊子的性素樸論,但其內涵已明顯不同。莊子所謂的素樸即是樸素的意思,是指人性中除了包含人的生命本能外,并無仁義、嗜欲等東西。仁義即是善,嗜欲即是惡,仁義、嗜欲均非性所固有,所以性是非善非惡的。而王雱的性素樸論,則是從主客關系的角度來看問題。他所謂的人性素樸,主是要指人性本來與外物是分離的。受外物污染乃是性之蔽,而非性之“素”,隨物而遷乃是性之散,而非性之“樸”(即全)。因此“性中無外物”就是王雱的性素樸論所要表達的主要意思。這顯然是受佛教“心性清凈,離客塵垢”[36]思想的影響。
王雱認為,人性雖然稟自天道,本來是素樸的,但現實中的人們,大多已失其本性。他繼承莊子的觀點說:“三代之后,民無不失其性者。”[37]那么,人們失性的原因是什么呢?王雱也繼承了莊子的觀點,認為原因就在于“以物易性”。所謂“以物易性”,就是指人們因追逐外物而喪失本性。王雱說:“失性之人,忘其不貲之有,而貪逐外物。”[38]
既然人們由于逐物而失性,那么人們為什么會不守本性,而去追逐外物呢?王雱認為,根本原因就在于人們認為萬物實有:“種種色相皆以為實,因生妄情,與接為搖,窮萬世而不悟”[39]。
王雱認為,實際上萬物都是虛幻的,唯一真實的就是人的本性。明白萬物皆妄后,就應該做到對境無心,雖萬物紛呈于前,而自己心中不起一毫欲念。王雱強調,無欲是復性的關鍵。但是,讓人完全沒有欲望是不現實的。人作為一個生命體,至少要有生存的欲望。王雱對這一點也是肯定的。他認為,復性并不排斥人的生存欲望:“飽食暖衣,性所不免,欲此而已,不為有欲。”[40]生存欲望是性所固有的,它并不導致人們失性。超出生存需要的各種欲望,如追求難得之貨、馳騁田獵等等,才是人們復性的障礙。
王雱所闡述的復性論,其積極意義在于引導人們提高精神境界,淡化功名利祿之心,從而減少紛爭,使社會臻于和諧。但其理論基礎卻是“萬物皆妄”,即否定客觀世界的真實性,這樣的觀點顯然是錯誤的。
王雱在《老子》注中不僅提出了復性的主張,而且根據《易傳》和《中庸》的盡性說[41],大力倡導盡性論。
盡性論與復性論都是著眼于保全人的真性,二者只是論述角度不同而已:復性是指恢復曾經喪失的天性,盡性則是指順著人的天性發揮其功能而不使之受到傷害。
王雱根據《老子》第59章“治人事天莫若嗇”的觀點,認為只有“嗇”才能盡性。他所謂的“嗇”,是指不以外耗內。他說:“葆其精神,不以外耗內,嗇也”[42]。外,指外物;內,即人之性。不以外耗內就是不要去追求外在的東西而使自己的天性受到傷害。因此,他的盡性論就是要人們明于內外之分。
王雱繼承了孟子關于“萬物皆備于我”的思想,認為“性分之內,萬物皆足,窮居不損,大行不加”[43]。他說,人們如果明白了這個道理,就應該安于性分,而不向外貪求。不向外貪求,也就是要做到無為。他認為,人們的天性受到損害,都是有為造成的:“人之本真,充塞六極,無所不遍,而終至于不足者,侈有為而輕自用故也。”[44]因此,只有“不多費于妄作”[45],才能盡性。
王雱又根據《中庸》關于“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的說法,認為只要統治者做到了盡性,則天下之民皆能盡性。他說:“吾(指最高統治者)不敗常失性,則天下亦盡其常性矣。”[46]“上不自厭其生而盡性,故民亦得盡性也。”[47]為什么上盡性則下亦盡性呢?這是因為統治者若能盡性,則自然清靜無為,而不以事擾民。“民不擾,則得盡其性”[48]。
王雱的盡性論還跟窮理、復命問題聯系在一起,這是因為《周易·說卦傳》有“窮理盡性以至于命”的說法。那么,他是如何看待盡性與窮理、復命之間的關系的呢?
王雱實際上將“窮理”歸結為“盡性”。他說:“欲觀物理者,必先致一也。”[49]致一就是要體悟到萬物一致之理。而萬物一致之理就是道。因此,要窮理,必先體道。他說:“萬物由道以出”,“得道,則萬物之理不待識而知。”[50]而道也就是人之性,因此,只要能盡性,也就能知萬物之理。他解“不出戶,知天下,不窺牖,見天道”說:“天下之眾,天道之微,其要同于性。今之極唯盡性者,膠目塞耳而無所不達。”[51]
王雱認為,如果不從盡性入手,而從感官知覺入手,則只能認識萬物各自具有的特殊之理,而不能通達萬物一致之理。他說:“茍唯見而后識,識而后知者,是得其萬殊之形,而昧于一致之理。然則所謂識知者,乃耳目之末用,而非心術之要妙矣。”[52]
王雱進而指出,“窮理”不是為了增加對萬物的具體知識。他解“為學日益”說:“方其窮理之時,物物而通之,凡以求吾真,非以為博也,故日益而無害。”[53]所謂“物物而通之”,就是要以萬物一致之理來貫通萬物。所謂“凡以求吾真,非以為博也”,就是說,窮物之理,是以萬物來驗證自己由盡性而體悟到的一致之理,而不是為了增長自己的見聞。
王雱還從性真物妄的觀點出發,認為對萬物之理也不能執著,否則就會妨礙盡性。他說:“夫見理之后,逐理不返,則妄作為兇,失道遠矣。”[54]故對萬物之理應該觀之以空。他說:“至人雖殫窮物理,而知理無實相,故雖知之,而不逐理離道。”[55]
對于性與命的關系,王雱說:“有生曰性,性稟于命,命者在生之先,道之全體也。”[56]這就是說,命即是道,它是性的來源。王雱認為盡性的極致就是復命。他解“歸根曰靜,靜曰復命”說:“歸根,盡性也;復命,至于命也。至于命極矣,而不離于性也。”[57]因為性即來源于命,故復命不離于盡性。
王雱關于盡性才能窮理的觀點,實際上就是將對事物本質的認識活動與認知主體的精神修養聯系起來。其運思理路為:一個人的精神境界越高,他對本體之道的領悟也就越多。而本體之道乃是萬物之理所從出的源泉。故窮理可歸結為盡性。
王雱的這一觀點,就其理論本身來說,是圓滿自足的。但是,由于他所謂的道(或萬物一致之理),只是由主觀的精神體驗所設定,而不是來源于客觀實踐,故顯然沒有多少實際意義。
王雱將“道”區分為“常道”和“可道之道”。他認為“常道”乃“萬物之所道,在體為體,在用為用,無名無跡,而無乎不在者是也”[58]。對于“常道”,“雖圣人之言,常在其一曲”[59]。也就是說,即使是圣人,也無法語其全體,而只能表達它的某一個方面。常道的某一個方面即道之用,也就是“可道之道”。王雱認為,“可道之道,適時而為,時徙不留,道亦應變。蓋造化密移,未嘗暫止,昔之所是,今已非矣。而曲士攬英華為道根,指蘧廬為圣宅。老氏方將祛其弊而開以至理,故以此首篇。明乎此,則方今之言猶非常也。”[60]在這里,王雱形象地以“蘧廬”來比喻可道之道。蘧廬語出《莊子·天運》篇,意為旅店。可道之道就像旅店一樣,只可暫止,不能常住。王雱以此比喻突出強調了可道之道的暫時性。“可道之道”是否有某種實指?聯系王雱的其他論述,可知他所謂的“可道之道”,主要是指具體的政治措施。他認為,任何政治措施都屬于可道之道的范疇,因而不能固定不變,而應隨時代的變遷作出適當的調整。王雱指出:“唯體此不常,乃真常也。”[61]只有認識到“可道之道”的變化無常,才算是真正掌握了永恒不變的真理。
王雱是王安石之子,他對“可道之道”之暫時性的論述,顯然包含有為變法作理論鋪墊的政治意圖。按照王雱的理論,宋初制定的政治措施,雖然是“祖宗法度”,但它并不是“常道”,而只是“可道之道”。既然是“可道之道”,就必須因時而變。可見,王雱區分“常道”與“可道之道”的用意就是為了論證變法的正當性。
王雱關于先王之法必須因時而變的觀點,可能也是淵源于《莊子·天運》篇。該篇認為“夫三皇五帝之禮義法度,不矜于同而矜于治。……故禮義法度者,應時而變者也。今取猨狙而衣以周公之服,彼必龁嚙挽裂,盡去而后慊。觀古今之異,猶猨狙之異乎周公也。”這就是說,古今時勢不同,禮義法度應該根據不同的時勢而作出相應的變化。三皇五帝的禮義法度各不相同,但都是根據當時的實際情況而制訂的,因此都取得了天下大治的效果。如果只追求與前代的禮義法度相同,就好比是把周公的衣服強加給猿猴一樣可笑。
王雱對《莊子》作過深入研究,著有《南華真經新傳》一書,因而其思想受《莊子》的影響是很自然的。
王雱在《老子注》中,對“因時順變”的觀點作了反復闡述。如他解釋《老子》第五章“天地之間,其猶橐籥乎”說:“橐籥虛以應物,物感則應,應而不藏。天地之于萬物,圣人之于百姓,應其適然,而不系累于當時,不留情于既往,故比橐籥之無窮也。”[62]王雱強調圣人“不留情于既往”,與王安石強調“不仁乃仁之至”[63]一樣,其用意均在說明對前代政治不能礙于情感而不作變革。
王雱大聲疾呼“大運不留,當時者為是”[64],希望帝王“不先物動,亦不失時”[65],認為圣人“唯變所適,故無不能也”[66]。
王雱還把“因時”與“乘理”結合起來,提出“因時乘理”的主張。他說:“至人因時乘理,而接之以無我,則其出無方而所應不窮也。”[67]“君人體道以治,則因時乘理而無意于為,故雖無為而不廢天下之為,而吾實未嘗為也。”[68]“(圣人)于立言垂法,亦因時乘理,適可而已,非為辯也。”[69]他所謂的“理”,主要是指事物發展的客觀規律。如他說:“夫萬物各得其常,生死成壞,理有適然。”[70]因此,“乘理”就是掌握事物發展變化的客觀規律而順應之。他說:“虛己而應理,緣物為變,而不與物迕”[71]。
王雱提出“乘理”說除了強調帝王應順物之變外,也有防止帝王從主觀意志或情感出發而施政行事的意思。他注《老子》第73章說:“天任理而不任意,其禍福也付之自為。”[72]這是說帝王不能憑借自己的權力意志而行事,而應尊重客觀情況,最好是任物自為而不加干涉。他注《老子》第8章“政善治“說:“任理而不任情。”[73]注《老子》第77章說:“天道任理,故均,人道任情,故不均。”[74]這就是說,帝王只有擺脫情感因素的影響才能保證政治的公正性。
王雱的《老子注》完成于熙寧三年(1070年)。熙寧五年(1072年),王安石在與宋神宗對答時也強調要“任理而無情”[75]。由于王安石的《老子注》已佚失大半,我們現在難以判斷王安石的“任理而無情”的說法究竟是受其子的影響,還是他本來就有這樣的思想。
道與陰陽的關系,是北宋學者所關注的重要理論問題之一。理學家程頤解釋“一陰一陽之謂道”說,“道非陰陽也,所以一陰一陽,道也。”[76]又說:“所以陰陽者是道也。陰陽,氣也。氣是形而下者,道是形而上者。”[77]程頤認為,陰陽的對立轉化運動只是氣的運行規律,這種運行規律不能稱之為道。只有形成這種規律的原因,即陰陽之所以然,才是道。與程頤的觀點形成鮮明對照的是,王雱明確認為,陰陽就是道。他說:“陰陽,道也。”[78]這兩種觀點看似對立,其實只是二人對道的內涵作了不同的理解。程頤將道之體與道之用作了明確區分,只有道之體才可稱之為道,道之用(如一陰一陽的運動變化規律)不能稱之為道。而王雱則認為,道之體與道之用都是道的表現方式,因而都可稱之為道。王雱說:“道者,萬物之所道,在體為體,在用為用,無名無跡,而無乎不在者是也。”[79]又說:“道有二物,自形而下,則陽尊而陰卑;自形而上,則陰先而陽后。”[80]可見,王雱認為形而上的道體與形而下的道用,都是道。這樣一來,王雱所說的“道”,其內涵就比程頤所說的“道”的內涵寬泛了許多。
王雱跟其父親王安石一樣,對佛教經典很有研究。王安石作有《金剛經注》,王雱則作有《佛書義解》。王雱在解《老》時,明顯摻入了佛教的思想。如前文所述,他主張“萬物非實”,就是受佛教“緣起性空”思想的影響。他還將《老子》的有無與佛教的色空對應起來,認為有與無的關系就是色與空的關系。他解《老子》第1章“常無,欲以觀其妙;常有,欲以觀其徼”說:
“《易》之陰陽,老之有無,以至于佛氏之色空,其實一致,說有漸次耳。世之言無者,舍有以求無,則是有外更有,安得為無?故方其有時,實未嘗有,此乃真無也。有無之體常一,而有有以觀者,但見其徼。欲觀其妙,當知本無。而本無之無,未嘗離有也。既曰常無,又曰常有者,以明有無之不相代,無即真有,有即實無耳。”[81]
可見,王雱所謂的“無”,既不是指無形的實體,也不是指非存在,而是以佛教的“空”來理解之。按照佛教的觀點,萬物都是因緣和合而成的,故無自性,無自性就是空。空乃是對萬物(“色”)之本質的說明,故《心經》中說“色不異空,空不異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王雱認為“色不異空”、“色即是空”也就意味著有不異無、有即是無,“有無之體常一”。因為無就在有中,所以不能“舍有以求無”。無不是與有相對立的某一事物,而正是對有的本質的說明:“無非有對,因有有無。”[82]所以說“有無本一,未有二名。”[83]“無不離有,有亦真無。”[84]有的本質就是無,無就是對有的本質的說明。故不能把有與無對立起來,也不能在有之外去尋找無。
值得注意的是,王雱還以佛教的思想對《老子》的“道法自然”說進行了重新審視。他根據《楞嚴經》“非因非緣,亦非自然”之說,認為“自然”非終極真理。他釋《老子》第25章“道法自然”說:
“自然在此道之先,而猶非道之極致。……《莊子》曰:‘季真之莫為,接子之或使,在物一曲。’佛氏曰:‘非因非緣,亦非自然。’自然者,在有物之上,而出非物之下。此說在莊(即莊子)、佛之下,而老氏不為未圣者,教適其時而言不悖理故也,使學者止于自然,以為定論,則失理遠矣,不可不察也。”[85]
老子推崇“自然”。王雱受佛教影響,認為“自然”之說不高明,“非因非緣,亦非自然”之說才是真理。王雱的觀點與《老子》原文出現了沖突。王雱既要抒發己見,又不想批判老子,于是斷言“自然”之說并非老子的定論。這顯然是以王雱自己的見解來改造老子的原意。
綜上可見,王雱的《老子注》內容豐富,思想深邃,頗多理論創新,如“孔、老相為終始”論、“因時乘理、唯變所適”的與時俱進思想等等,在老學史上有著重要的意義,值得我們加以研究。
[1] 見盧國龍《宋儒微言》,華夏出版社2001年版,第140頁。
[2] 王弘撰《山志》初集卷五,中華書局1999年版,第129頁。
[3] 漆俠:“王雱:一個早慧的才華四溢的思想家”,載《中國史研究》2000年第4期,又見其所著《宋學的發展和演變》(河北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盧國龍:“王雱‘任理而不任情’的政治哲學”,見其所著《宋儒微言》(華夏出版社2001年版)。
[4] 近見臺灣學者江淑君撰有“王雱《老子注》‘性論’發微——兼論‘援儒入《老》’之詮解向度”(載《東吳中文學報》第八期,2001年5月),研究角度與本文有同有異,互看可也。
[5] 太守張氏《道德真經集注》,《道藏》第13冊第105頁。
[6] 太守張氏《道德真經集注·序》,《道藏》第13冊第2頁。
[7] 太守張氏《道德真經集注·序》,《道藏》第13冊第2頁。
[8] 太守張氏《道德真經集注》卷三,《道藏》第13冊第27頁。
[9] 太守張氏《道德真經集注·序》,《道藏》第13冊第2頁。
[10] 太守張氏《道德真經集注》卷二,《道藏》第13冊第15頁。
[11] 太守張氏《道德真經集注》卷二,《道藏》第13冊第27頁。
[12] 太守張氏《道德真經集注》卷六,《道藏》第13冊第53頁。
[13] 太守張氏《道德真經集注》卷三,《道藏》第13冊第27頁。
[14] 太守張氏《道德真經集注》卷一,《道藏》第13冊第7頁。
[15] 太守張氏《道德真經集注》卷六,《道藏》第13冊第53頁。
[16] 太守張氏《道德真經集注》卷十,《道藏》第13冊第103頁。
[17] 太守張氏《道德真經集注》卷一,《道藏》第13冊第13頁。
[18] 《朱子語類》卷二十八,中華書局1994年版,第2冊第726頁。
[19] 《朱子語類》卷四,中華書局1994年版,第1冊第70頁。
[20] 參見陳來《朱熹哲學研究》第二章,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3年。
[21] 陳來《朱熹哲學研究》第131頁。
[22] 轉引自陳來《朱熹哲學研究》第131—132頁。
[23] 蒙文通《道書輯校十種》,巴蜀書社2001年版,第699頁。
[24] 太守張氏《道德真經集注》卷一,《道藏》第13冊第8頁。
[25] 太守張氏《道德真經集注》卷五,《道藏》第13冊第47頁。
[26] 太守張氏《道德真經集注》卷六,《道藏》第13冊第52頁。
[27] 《莊子·庚桑楚》。
[28] 《莊子·駢拇》。
[29] 《莊子·徐無鬼》。
[30] 《莊子·馬蹄》。
[31] 太守張氏《道德真經集注》卷三,《道藏》第13冊第27頁。
[32] 《禮記·樂記》。
[33] 太守張氏《道德真經集注》卷一,《道藏》第13冊第8頁。
[34] 太守張氏《道德真經集注》卷五,《道藏》第13冊第45頁。
[35] 太守張氏《道德真經集注》卷四,《道藏》第13冊第41頁。
[36] 《舍利弗阿毗曇論》卷二十七。
[37] 太守張氏《道德真經集注》卷一,《道藏》第13冊第7頁。
[38] 太守張氏《道德真經集注》卷六,《道藏》第13冊第63頁。
[39] 太守張氏《道德真經集注》卷三引王雱注,《道藏》第13冊第24頁。
[40] 太守張氏《道德真經集注》卷九,《道藏》第13冊第88頁。
[41] 《周易·說卦傳》說:“窮理盡性以至于命。”《中庸》說:“唯天下至誠,為能盡其性。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能盡物之性,則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則可以與天地參矣。”
[42] 太守張氏《道德真經集注》卷八,《道藏》第13冊第81頁。
[43] 太守張氏《道德真經集注》卷五,《道藏》第13冊第47頁。
[44] 太守張氏《道德真經集注》卷八,《道藏》第13冊第81頁。
[45] 太守張氏《道德真經集注》卷八,《道藏》第13冊第81頁。
[46] 太守張氏《道德真經集注》卷九,《道藏》第13冊第88頁。
[47] 太守張氏《道德真經集注》卷八,《道藏》第13冊第82頁。
[48] 太守張氏《道德真經集注》卷八,《道藏》第13冊第82頁。
[49] 太守張氏《道德真經集注》卷三,《道藏》第13冊第23頁。
[50] 太守張氏《道德真經集注》卷七,《道藏》第13冊第71頁。
[51] 太守張氏《道德真經集注》卷七,《道藏》第13冊第65頁。
[52] 太守張氏《道德真經集注》卷七,《道藏》第13冊第65頁。
[53] 太守張氏《道德真經集注》卷七,《道藏》第13冊第66頁。
[54] 太守張氏《道德真經集注》卷七,《道藏》第13冊第71頁。
[55] 太守張氏《道德真經集注》卷七,《道藏》第13冊第71頁。
[56] 太守張氏《道德真經集注》卷三,《道藏》第13冊第24頁。
[57] 太守張氏《道德真經集注》卷三,《道藏》第13冊第24頁。
[58] 太守張氏《道德真經集注》卷一,《道藏》第13冊第3頁。
[59] 太守張氏《道德真經集注》卷一,《道藏》第13冊第3頁。
[60] 太守張氏《道德真經集注》卷一,《道藏》第13冊第3頁。個別文字據劉惟永《道德真經集義》校改。
[61] 太守張氏《道德真經集注》卷一,《道藏》第13冊第3頁。
[62] 太守張氏《道德真經集注》卷一,《道藏》第13冊第9—10頁。
[63] 蒙文通《道書輯校十種》,巴蜀書社2001年版,第681頁。
[64] 太守張氏《道德真經集注》卷八,《道藏》第13冊第80頁。
[65] 太守張氏《道德真經集注》卷二 ,《道藏》第13冊第12頁。
[66] 太守張氏《道德真經集注》卷二 ,《道藏》第13冊第12頁。
[67] 太守張氏《道德真經集注》卷二,《道藏》第13冊第13頁。
[68] 太守張氏《道德真經集注》卷五,《道藏》第13冊第51頁。
[69] 太守張氏《道德真經集注》卷十,《道藏》第13冊第104頁。
[70] 太守張氏《道德真經集注》卷一,《道藏》第13冊第9頁。
[71] 太守張氏《道德真經集注》卷三,《道藏》第13冊第33頁。
[72] 太守張氏《道德真經集注》卷十,《道藏》第13冊第97頁。
[73] 太守張氏《道德真經集注》卷二,《道藏》第13冊第12頁。
[74] 太守張氏《道德真經集注》卷十,《道藏》第13冊第100頁。
[75] 據《續資治通鑒長編》卷二三六記載:熙寧五年閏七月辛酉,王安石對宋神宗說:“陛下正當為天之所為。……所謂天之所為者,如河決是也。天地之大德曰生,然河決以壞民產而天不恤者,任理而無情故也。”
[76] 《河南程氏遺書》卷三,《二程集》第1冊,中華書局1981年版,第67頁。
[77] 《河南程氏遺書》卷十五,《二程集》第1冊第162頁。
[78] 太守張氏《道德真經集注》卷十,《道藏》第13冊第100頁。
[79] 太守張氏《道德真經集注》卷一,《道藏》第13冊第3頁。
[80] 太守張氏《道德真經集注》卷一,《道藏》第13冊第5頁。
[81] 太守張氏《道德真經集注》卷一,《道藏》第13冊第4頁。
[82] 太守張氏《道德真經集注》卷二,《道藏》第13冊第17頁。
[83] 太守張氏《道德真經集注》卷一,《道藏》第13冊第4頁。
[84] 太守張氏《道德真經集注》卷二,《道藏》第13冊第17頁。
[85] 太守張氏《道德真經集注》卷四,《道藏》第13冊第37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