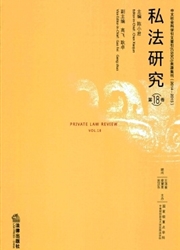從《紅樓夢魘》看《紅樓夢》對張愛玲的影響
毛燦月
摘 要: 《紅樓夢魘》是文學家張愛玲情節化操作之外的特例,這部關于《紅樓夢》的考據和評點專論,是她窮畢十年精力的后期作品。張愛玲對《紅樓夢》及研究的“瘋狂”是其這部學術專論的表征,而她與《紅樓夢》及其作者之間的文化傳承關系是這部專論的非學術隱義。張愛玲與曹雪芹文人品格的共性,源于他們共同的末世之感;張愛玲繼承了《紅樓夢》對悲劇本原的演繹方式,將《紅樓夢魘》作為自己的間接訴情文本。《紅樓夢魘》的完成過程,是張愛玲消解其對時代與人性的悲劇感,表達情感最后歸宿的過程。同時,《〈紅樓夢魘〉自序》為審視張愛玲與《紅樓夢》及作者的情感淵源,考察她與曹雪芹在精神特質、審美傳達等方面的契合,深入研究張愛玲的創作意識和文本意義,提供新的考察視角。
關鍵詞:紅樓夢魘;張愛玲;紅樓夢;曹雪芹
《紅樓夢魘》是張愛玲豐厚作品系列中唯一的學術著作,意在評點和考證《紅樓夢》。紅學大家周汝昌為此專作《定是紅樓夢里人》一書,從學術層面對該書進行過再評點和詳解。但筆者認為《紅樓夢魘》的價值并不在其學術范疇。目前,我國大陸的研究注意力聚焦于張愛玲的文學作品,疏淡于她為之傾注了10年功力和心血的著作,這也可算是它的價值真的不在學術范疇的佐證。《〈紅樓夢魘〉自序》(以下簡稱《自序》中是張愛玲真實再現自己與《紅樓夢》情緣的寫實之作,它為我們解構張愛玲與《紅樓夢》淵源關系提供了重要視角。 一、訴情文本:情感歸宿的同向度 真正的學術研究當是心境清雅醇正其間全無雜念,既不受世局與外緣的影響,也不被內心情態所支配,即所謂“惟偏蔽之務去,真理之是從”[1]的審慎,但張愛玲并非如此。她移居美國后,沉潛10年于《紅樓夢》文本及版本繁瑣考據,自設疑點,多版本比較,校勘辨偽,大膽假設加小心求證,以“一個字看得有笆斗大”的辭簡義豐用字完成了她的“張看”。關于書名,她在《自序》里寫道:“我寄了些考據《紅樓夢》的大綱給宋淇看,有些內容看上去很奇特。宋淇戲稱為Nightmare in the Red Chamber(紅樓夢魘),有時候隔些時就在信上問起‘你的紅樓夢魘做得怎樣了?’我覺得這題目非常好,而且也確是這情形——一種瘋狂。”在1967年秋天丈夫賴雅去世前,她已經著手于《紅樓夢》的考證,1972年,臺北幼獅文藝研究社出版的“幼獅月刊學術叢書”《紅樓夢研究集》第30卷40期上發表了她的最早成果“紅樓夢末完”,接下來幾年,各專論陸續問世。這些論作均各有所得,各臻其妙,直至結集而成《紅樓夢魘》。張愛玲是將經年癡紅的“瘋狂”情愫,轉嫁到“學術研究”的特殊形式中。如果說曹雪芹將《紅樓夢》原創作為直接訴情文本,那么張愛玲則是將《紅樓夢》考證作為間接訴情文本。 張愛玲的學術研究具有明顯的“作家之學術”特征,她以作家的氣質與才情感受作家與作品,在抉幽探微之中獲得“詩眼文心”“莫逆暗契”[2]的藝術感應。在任職加州柏克萊大學的中國研究中心的1969年之前,張愛玲曾在哈佛燕京圖書館與柏克萊的加大圖書館借書時,她看到“脂本紅樓夢”,對近人的考據,《自序》中披露“都是站著看——來不及坐下”。這說明兩個問題:一是她考證的著迷入神、緊迫焦渴,二是她能找到的考核和例證資料相當有限。第二個問題事關學術真偽深淺,她解決的辦法是“唯一的資格是實在熟讀紅樓夢”,用這樣最單純的方法直奔第一手材料,反倒使她有“采銅于山”的意外清新收獲。張愛玲對《紅樓夢》文本的熟悉,達到了“不同的本子不用留神看,稍微眼生點的字自會蹦出來”的境界。《自序》是我們解構張愛玲與《紅樓夢》的淵源的重要視角,對這3 000字啟篇語的釋證,正是陳寅恪先生的“以詩證史”的文學研究的另一面——以史證詩。我們在通解《自序》的研究基礎上,得其寫作的真相,這與旨在學術范疇的考察立場是完全不一樣的。 《紅樓夢》研究和《紅樓夢魘》寫作,兩者之于張愛玲的意味非比尋常。《紅樓夢》是她凡俗世界之外的別樣境界,一個令她“確實什么都不管”的“真喜歡”的境界;“偶遇拂逆,事無大小,只要‘詳’一會紅樓夢就好了”,《自序》里所寫到的“詳”《紅樓夢》,是她暫時擺脫世俗煩擾,享受精神安寧愉悅的生活內容和方式。她在《自序》里所說的“在已經‘去日苦多’的時候,十年的工夫就這樣摜了下去,不能不說是豪舉”,既有完成某個壯舉的富足和自豪,更有了卻某樁宿愿的超脫和快慰。“十年一覺迷考據,贏得紅樓夢魘名”,她用這兩句詩為《自序》作結,再恰當不過了。 張愛玲家學深厚,自幼酷愛文學,對《紅樓夢》癡迷有加。據說她12歲時讀《紅樓夢》,讀到80回以后,只覺得“天日無光,百般無味”,可見她對此書的藝術感覺之了得。她在《存稿》一文中,追憶自己14歲那年,寫了個純粹鴛鴦派章回小說《摩登紅樓夢》,還像模像樣地擬訂共計五個回目。在《紅樓夢魘》第一部分“紅樓夢未完”的開篇,張愛玲寫道:“有人說過‘三大恨事‘是’一恨鰣魚多刺,二恨海棠無香’,第三件不記得了,也許因為我下意識的覺得應當是‘三恨紅樓夢未完’。”從她“下意識”將《紅樓夢》作為生命最強烈情感的歸宿,到“有意識”地為之沉潛十年理性考證,可以說,《紅樓夢》這部作品里的藝術元素與張愛鈴的生命元素融結為一體了。對《紅樓夢》的研究,考據的名義下的是她對《紅樓夢》的詩藝淵源、審美情趣、風格意蘊等“詩眼文心”的入迷,甚至影響到她自己作品的敘事模式。張愛玲創作中的愛情婚姻題材選擇,飲食男女瑣事鋪陳和心理描寫、形象塑造和語言風格等文本構成因素,都可以確證她和它之間的千絲萬縷聯系。所以,周汝昌先生盛贊《紅樓夢魘》,也用了一句性情中語:“只有張愛玲,才堪稱雪芹知己。” 二、末世情懷:文人品格的共同構型 “縱觀史乘,凡士大夫階級之轉移升降,往往與道德標準及社會風習之變遷有關。當其新舊蛻變之間際,常呈一紛紜錯雜之情態,即新道德標準與舊道德標準,新社會風習與舊社會風習并存雜用,多是其是,而互非其非也。”[3]陳寅恪先生關于“士大夫階級”與時代社會的關系的論述,照應了曹雪芹和張愛玲共同精神氣質的種種現象。 曹雪芹對頹敗了的貴族世家感情復雜,“滿紙荒唐言,一把辛酸淚”與“都云作者癡,誰解其中味”共享《紅樓夢》的情感空間,同情、無奈的末世喟嘆與悲憤、質疑的否定批判共存于文本中。曹雪芹沒落貴族的宿命思想和深刻的悲觀主義,訴之于這部家族史和情愛史中。甚至有學者認為,曹雪芹“對沒落貴族的哀嘆和惋惜要大于其對沒落貴族的批判和諷刺”。[4]張愛玲于20世紀40年代橫空出世,以女性命運的多種形態和生命的欲望為創作視覺,對女性時代人生的境況進行深度自省和反思。研究者習慣把張愛玲的《金鎖記》與《紅樓夢》放在一起審視,并對前者給予過極高的贊譽:“我們的文壇最美的收獲之一。”[5] 張愛玲感性與理性經驗里所獲得的末世之感,是她和《紅樓夢》及其作者形成精神氣質契合的淵源。她的末世之感主要是從這兩種經驗中離析出來的。一是早期經驗里的失敗感與沒落感。根據弗洛伊德還原式的解夢法,追根溯源的童年創傷是夢的隱義,對她產生重要影響的是早期經驗里充滿失敗沒落感,即便是1952年避居香港后的多種經歷,也與她的早期經驗構成連帶關系。1937年17歲那次逃離父親家,是她第一次迎受生命冷酷真相;1939年因太平洋戰爭爆發將英格蘭求學之夢改到了香港,是她對命運的委曲求全;1942年從淪陷的香港退回到出生地,是她人生至此最無選擇的選擇。1940年《西風》雜志刊出了她的應征作品《天才夢》,其中很出名的一段話是:“……可是我一天不能克服這種咬噬性的小煩惱,生命只是一襲華美的袍,爬滿了虱子。”這樣的句子,出自一位19歲少女的筆下,不能不說她性格里有著與年齡不相稱的敏感、憂郁、成熟、世故,過早涉入悲涼的世事已給她的心靈鋪上了灰暗、蒼涼的底色。二是對日漸式微的社會的危機感和憂患感。經過“五四”的掃蕩,舊生活方式和文化形式已經沉淪,新的生活軌道并未完全形成,這是一個新舊之際的“末世”和亂世。加上世界范圍內的戰爭危機,普通人的生存已面臨嚴重威脅。張愛玲曾在《五四遺事》一文中說:“像‘五四’這樣的經驗是忘不了的,無論湮沒多久也還是在思想背景里。”香港和上海是張愛玲生活和書寫的兩個重要場景。作為新舊社會轉形期的都市,這里是自由經濟與傳統文化共同產生作用的地方,交織著現代化的喧囂和傳統的沒落多種元素。她曾在《傳奇再版序》中表述過自己的困擾和恐慌:“如果我常用的字是‘荒涼’,那是因為思想背景里有這惘惘的威脅。”張愛玲以這樣“末世”創作心理,審視文化敗落時期的人生狀態和情感心理,表現人性在危機時代的扭曲變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