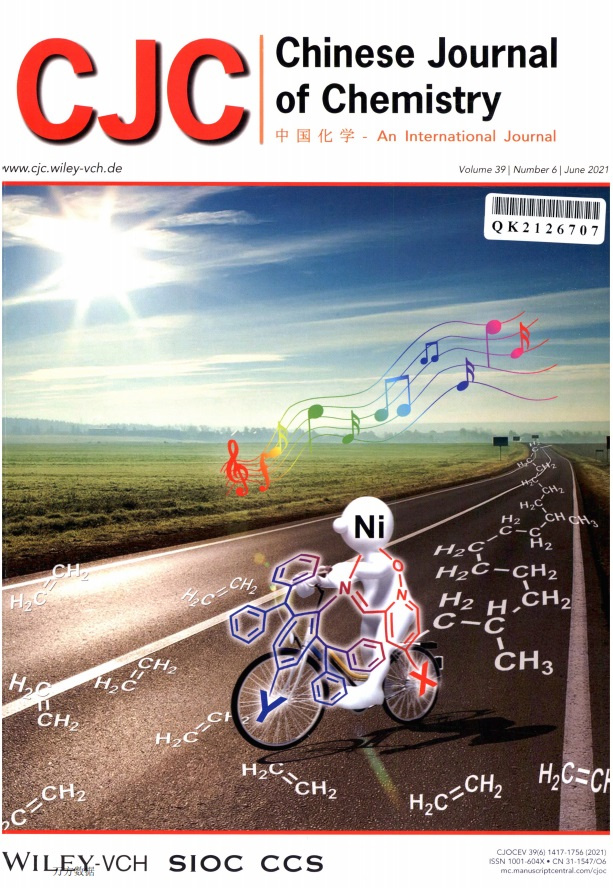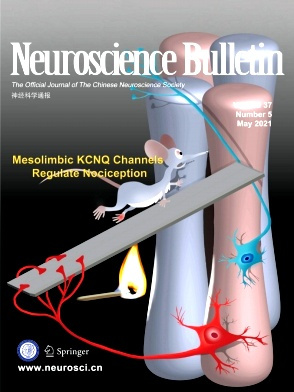比較兩種新時期出版的《紅樓夢》評點本
李 潔
摘 要: 王蒙和王志武都采用評點型的文學批評研究《紅樓夢》,二人都重視文本的閱讀,研究都具有一定的創新性。王蒙的創新之處是試圖將《紅樓夢》置于當代的語境之下,運用比較現代的話語對其進行新的解讀。王志武以小說文本研究為基礎,主要提出了王夫人與賈寶玉圍繞著婚配對象的選擇而產生的矛盾沖突是《紅樓夢》的中心矛盾沖突的觀點。但二人在研究眼光、研究方法、評點風格和主要觀點等方面表現出很大的不同,體現了各自的特色。
關鍵詞:《紅樓夢》評點;研究眼光;研究方法;評點風格;主要觀點 評點,作為一種兼有文學欣賞與批評功能的短捷的批評形式,既記錄了評點者閱讀作品時的審美心理過程和審美體驗,也為讀者的閱讀提供了參照。評家可以根據實際的需要靈活地選用不同的形式,如眉批、旁批、側批、回首總評、回末總評等來對作品進行評點,發表自己的看法;讀者對于評家的評點,可以然其然,也可以不然其然。這種靈活、自由的批評形式為很多人所青睞,被廣泛地使用。作為著名作家的王蒙先生和作為學人的王志武先生都不約而同地選用這一批評形式來研究《紅樓夢》。1994年漓江出版社出版的《〈紅樓夢〉王蒙評點》和2005年上海文藝出版社出版的《〈紅樓夢〉王蒙評點(增補版)》,1997年陜西師范大學出版社出版的《〈紅樓夢〉王志武評點》,代表了二人這方面研究的成果。雖然二人都重視《紅樓夢》文本的精讀,研究都具有一定的創新性,但無論是在研究眼光、研究方法、評點風格,還是主要學術觀點等方面,都表現出了很大的不同,具有各自研究的特點。 二位評家都重視文本的精讀,王蒙也好,王志武也好,他們的研究都是以《紅樓夢》文本為出發點,把《紅樓夢》當作小說來看,并以此為基礎來談自己的發現和獨特心得的。這不同于以闡釋小說本事為旨歸,過于關注小說的政治命意,捕風捉影、強拉硬扯,以“奇”眩人的“索隱派”;也不同于處處以材料說話,過于求實,忽視小說的虛構性特征,以“實”服人的“考證派”和將《紅樓夢》作為“自序傳”的“新紅學”;更有別于將《紅樓夢》作為集陰謀、愛情、政變、仇殺、情義、宮闈秘史于一體的所謂“紅學分支”之“秦學”。 同時,二人的研究都具有一定的創新性。王蒙的創新之處是試圖將《紅樓夢》置于當代的語境之下,運用比較現代的話語對其進行新的解讀。他使用了很多現代性的語言,如“人才危機”、“姨娘文化”、“主流派”、“青春烏托邦”、“青春片”、“董事長”、“秘書長助理”等。他試圖構建一套新的語碼釋義系統,將《紅樓夢》的研究從傳統的現實主義、反封建、階級斗爭、四大家族等一套機械性的政治熟語和研究框架中解放出來。另外,他還用自己對社會、人生的感受、認識、體悟來評價《紅樓夢》,不像是搞學術研究,更像是與讀者暢談人生、交流經驗,希望將之從以往相對狹隘的理論研究中解放出來。王志武提出了王夫人與賈寶玉圍繞著婚配對象的選擇而產生的矛盾沖突是《紅樓夢》的中心矛盾沖突的觀點,“王夫人從自己的家長地位出發,要通過給賈寶玉選擇婚配對象給賈府選擇一個符合封建大家庭要求的德(封建階級之德)、才(管家之才)、體(身體)、錢四者兼備的管家婆,寶玉則從婚配主體出發,要通過給自己選擇婚配對象實現與黛玉的知己愛情,于是母子倆圍繞這一關鍵問題發生了曲折復雜、牽動全局的矛盾沖突”,[1]1這與過去流行的看法(認為《紅樓夢》的主要矛盾沖突是賈政與賈寶玉圍繞走不走功名仕進之路而展開的矛盾沖突)截然不同,學術觀點新穎。 兩位評點者雖然都選用了評點這一文學批評形式來研究同一部《紅樓夢》,但二人在研究眼光、研究方法、研究術語和風格以及主要觀點等方面,表現出了很大的差異性,具有各自的特點和研究建樹。 二人研究眼光不同。王蒙是以小說家的身份和眼光來看《紅樓夢》的,表現出了很強的“作家意識”,這種“作家意識”主要表現在對《紅樓夢》文學性研究方面。王蒙以自己的創作體會來驗證、評價《紅樓夢》,利用此優勢和特長,他往往能發現很多被紅學家們所忽略的問題。比如他從小說結構學的角度認為第七十四回“惑奸饞抄檢大觀園 避嫌隙杜絕寧國府”是前八十回的終結,底下幾回是余波,“抄檢大觀園,從精神上說(即不是從考據上說),乃是曹氏‘紅’著的結束。具體的終結,應是終結在芙蓉誄上”。[2]830作為一位作家,王蒙說這樣的話是比較有資格和分量的。在談到《紅樓夢》中大量詩詞時,他認為“加點詩詞歌賦,一為賣弄才學,二為調劑節奏、調劑閱讀興味,……三為刻畫、補充敘述,四為審美化,間離化”。[2]46這融入了他自己的創作體會、創作經驗。另外還談到《紅樓夢》某些情節、人物、事件的非情理化、非邏輯性的問題,這些認識都是出于一個小說家的獨特領悟。雖然王蒙的評點缺少邏輯上的嚴密性,但他是以小說家來理解《紅樓夢》,以一個作家的身份來談自己的看法的,因此很多說法都具有一定的合理性。王志武以紅學家的眼光來看《紅樓夢》,將之作為一個統一的整體,提出了很系統的觀點,并且從文本中尋找到了具有說服力的證據,論證過程具有很強的邏輯性、嚴密性。他提出了“王夫人與賈寶玉圍繞婚配對象的選擇而發生的沖突是《紅樓夢》的中心矛盾沖突”這一觀點,并通過對小說故事情節的分析(“作者在前五回概括揭示了這一沖突的成因、矛盾雙方的大致情況、斗爭結局、小說主人公寶玉以及作者對此結局的態度;第五回以后作者通過金釧之死、晴雯之死以及未寫之寫的黛玉之死等高潮表現這一沖突,用一系列的情節故事貫穿這一沖突”[1]1)和對各種類型矛盾沖突的比較(“其他矛盾沖突圍繞這一沖突”[1]1)來論證此觀點,很具說服力,令人信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