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評《三國演義》中的“英雄史觀”
竺洪波
《三國演義》中貫穿著“英雄史觀”,是作品的客觀存在,有目共睹。問題是:應(yīng)褒?應(yīng)貶?功歟?過歟?對此問題的研究和爭論,與對這部名著的主題論、人物論、藝術(shù)論、版本論等方面的熱烈程度相對比,可說顯得死氣沉沉了。但是,據(jù)我了解,長期以來,“英雄史觀”主要是被視為《三國演義》的一大詬病的。一種有代表性的觀點(diǎn)認(rèn)為:《三國演義》的主要思想缺陷在于“歪曲事實(shí),把歷史說成是少數(shù)剝削階級的‘英雄’人物創(chuàng)造的”,它對三國歷史現(xiàn)實(shí)的反映建立在英雄至上的思想基礎(chǔ)之上,其歷史觀是唯心主義的。盡管他們也注意到作品對封建階級的各類英雄人物也持有明顯的不同態(tài)度,特別是“擁劉反曹”,一褒一貶,涇渭分明,但又認(rèn)為這僅僅是對英雄人物道德評價上的差異,所以無論是對正面英雄的歌頌,還是對反面奸雄的詆毀,作者都宣揚(yáng)了“英雄史觀”。(1)其實(shí),這種評述雖不能說事出無因,但以此來評價《三國演義》這部偉大藝術(shù)名著的思想價值,或恐也嫌絕對,不夠全面和公允。時至今日,對“英雄史觀”在作品中的表現(xiàn),也應(yīng)作實(shí)事求是的具體分析,對“英雄史觀”本身是否構(gòu)成作品的“罪名”也可議論一番,因此,很有必要作新的評說。 一 所謂“英雄史觀”,即是認(rèn)為英雄是歷史的創(chuàng)造者和推動者,將英雄視為人類生活的中心,而把人民群眾排斥在政治舞臺的邊緣,忽視他們對歷史的創(chuàng)造和推動作用。《三國演義》描寫自東漢末年至三分歸晉的百年歷史:三國紛爭、群雄割據(jù)、中原逐鹿、波及全國,但說到底,這是一場由各個政治集團(tuán)之間為爭奪政權(quán)而展開的大角逐。伴隨著政治、經(jīng)濟(jì)、文化的全面抗衡,其斗爭的直接方式是軍事力量的對抗。而各個政治集團(tuán)之間的斗爭,又主要表現(xiàn)為其中的杰出人物即英雄霸主之間才識膽略的較量,其最后的勝負(fù)或成敗也取決于各路英雄人物自身的命運(yùn)。杜甫歌頌諸葛亮“伯仲之間見伊呂,指揮若定失蕭曹”,蘇軾贊揚(yáng)周瑜“雄姿英發(fā),羽扇綸巾,談笑間檣櫓灰飛煙滅”,又何嘗不適合于其他的三國英雄。“得人才者得天下,失人才者失天下”,這是人人皆知的道理。因而英雄人物無庸置疑地會成為作品描寫的中心,占據(jù)主體的、至上的地位。 與這種英雄至上和英雄中心論相一致,《三國演義》又不可避免地顯現(xiàn)出對人民群眾的疏遠(yuǎn)和輕視。曹操的名言“寧教天下人負(fù)我,休教我負(fù)天下人”,在道出了他的極端利己主義的“奸雄”本質(zhì)的同時,也顯露了天下黎民在所謂英雄眼中草芥不如的地位。無獨(dú)有偶。作品第六回?cái)⒍颗c袁紹、曹操等十八鎮(zhèn)諸侯交兵不利,為避其鋒,決定遷都長安,群臣苦諫若劃率遷棄,百姓騷動不安,董卓大怒道:“我為天下計(jì),豈惜小民哉?”無論是曹操,還是董卓,人民群眾都是任人擺布、宰割的羔羊;他們哪里把“天下”“小民”的利益放在眼里。 在疏遠(yuǎn)、輕視人民群眾的同時,作為社會政治生活中心的英雄,理所當(dāng)然地充當(dāng)了“天下人”的救世主。曹操討伐徐州,百姓將遭禍殃,后陶謙三讓徐州給劉備,徐州百姓擁擠府前哭拜:“劉使君若不領(lǐng)此郡,我等皆不能安生矣!”陶謙雖有仁慈愛民之心,但庸才無能,無力興邦安民;而劉備仁德之君,諸葛亮?xí)缡榔娌牛瑒t百姓澤恩得以“全身”。所以,禽相木而棲而人擇主而安,便成了作品倡導(dǎo)的一種人生處世態(tài)度。劉備治新野的時候,新野百姓作童謠歌曰:“新野牧,劉皇叔,自到處,民豐足。”曹操奔襲新野,劉備、諸葛亮巧施妙計(jì),擊退曹操大兵,終于保持了一方平安,于是新野百姓遮道而拜:“吾屬全身,皆使君得賢人之力也。”可見,廣大的人民群眾非但沒有成為政治生活的主體,反而常常成為政治生活的受害者,他們只有把自己的命運(yùn)安系在少數(shù)英雄人物身上。天下不是“天下人”之天下,而是少數(shù)英雄人物的天下,英雄成了“天下人”的救世主,“天下人”則是英雄的附庸。所謂“天下事在我!”(董卓) 在曹操、董卓那樣的奸雄那里,人民成為草芥;那么在劉備這樣的仁慈明君那里,人民群眾也許可以顯示其自身的力量和價值了?不是的。他們之間的關(guān)系只是一種賜與和接受的關(guān)系,人民群眾仍是一種消極的存在。而且在一定的條件下,這種關(guān)系的表面和諧就被打破了,人民群眾仍然是多余的累贅,甚至妨害了英雄人物建功立業(yè)。第四十一回?cái)鋽y民渡江,燒新野棄樊城,入襄陽,敗走江陵,裹挾民眾十萬迤邐而行,終于被曹兵趕上。雖因趙子龍一身是膽,于百萬曹兵中縱橫馳聘,力斬?cái)硨⑽迨鄦T;張翼德聲若奔雷,于當(dāng)陽長坂橋頭喝退曹兵;但劉備畢竟慘遭損兵折將、妻離子散的敗績。顯然,劉備慘敗的原因,正在于十萬民眾的負(fù)擔(dān),沒有這一巨大的牽累,劉備完全可以順利突圍;而如果他們具有一定的力量,人自為戰(zhàn),共抗強(qiáng)敵,則劉備完全可以反敗為勝。后來赤壁大戰(zhàn),諸葛亮出使東吳,聯(lián)吳抗曹,東吳謀士即以此敗為笑柄,譏諷諸葛亮;諸葛亮便以“有數(shù)十萬赴義之民,扶老攜幼相隨”,劉備“不忍棄之”,“甘與同敗”云云,振振有辭,舌戰(zhàn)群儒。雖然作品的目的是在以劉備的敗績來顯其“寬仁厚德”的品質(zhì),諸葛亮敏銳犀利、善于反敗為勝的辯才,但其中對人民群眾的歷史作用的基本看法已昭然若揭了。人民群眾成了不折不扣的“惰性物質(zhì)”,與曹操、董卓把人民群眾視為“小民”、群氓,其實(shí)沒有本質(zhì)的差別。 《三國演義》中的“英雄史觀”V不僅表現(xiàn)在對英雄的歌頌,對人民群眾的輕視,更主要的還表現(xiàn)在對黃巾起義的態(tài)度上,東漢末年的黃巾起義是中國歷史上的大事變,提供了歷史發(fā)展的大契機(jī),也是《三國演義》得以展開的歷史大背景。因?yàn)橼w個三谷的歷史,都是在黃蕉起義有力地打擊、瓦解了東漢王朝的廢墟上建立起來的;然而作品無視了黃巾起義的歷史必然性和推動歷史進(jìn)程的巨大作用,把起義的原因,歸結(jié)為大平道人的個人欲望,所謂漢室暗弱,“若不乘勢取天下,誠為可惜”,也無視黃巾起義軍的浩蕩烽火,只憑一紙朝廷文書、各路王師舉兵征討,紛紛告捷,黃巾雖曰“賊兵勢大”,“官軍望風(fēng)而靡”,但畢竟是烏合之眾,無帥之兵,一觸即潰,很快便被斬盡殺絕了。 凡此種種,都說明《三國演義》中的“英雄史觀”是客觀存在,由此更顯示出這也是評價作品的一個不可回避而又事關(guān)宏旨的關(guān)鍵問題。 二 一般來說,如果將《三國演義》中的“英雄史觀”作為一種歷史觀,那么,其思想上的偏頗,便被認(rèn)為是不言而喻的。普列漢諾夫在《論個人在歷史上的作用問題》中明確指出:只有生產(chǎn)力才是人類歷史運(yùn)動的終極原因,生產(chǎn)力的發(fā)展決定了人類社會歷史的演變,英雄人物受生產(chǎn)關(guān)系的制約,只能改變“歷史事實(shí)的個別外貌以及各個事變的某些局部后果,但他們終究不能改變由別的力量決定的事變的一般方向”,“不能隨意撥快歷史的鐘表”。(2)然而,問題分明在于:藝術(shù)作品不是歷史,《三國演義》中的“英雄史觀”,不能完全等同于歷史觀。藝術(shù)作為認(rèn)識世界,掌握世界的方式,是對一定現(xiàn)實(shí)生活的審美反映,而不是某一單純的思想觀念和直接的傳聲簡。《三國演義》中的“英雄史觀”固然與歷史觀有關(guān),但也有著與其相對獨(dú)立而又更為廣闊的思想意蘊(yùn),從中寄寓著作者對一定社會歷史、現(xiàn)狀的獨(dú)特理解。過去,有提出“曹操是了不起的民族英雄”,《三國演義》把曹操寫成這個樣子,成了一部名副其實(shí)的“曹操的謗書”,這“實(shí)在是歷史的一大歪曲”,因而聲稱要為曹操翻案。(3)這是以歷史學(xué)來匡定文學(xué)。胡適也因作品把周瑜這樣的風(fēng)流倜儻、英俊儒雅的英雄豪杰,寫成一個心胸狹窄,“妒忌陰險的小人”而大為不滿,并為周瑜在藝術(shù)作品中的命運(yùn)憤憤不平,并因此斷定《三國演義》是一部“平凡之作”。(4)這是以道德標(biāo)準(zhǔn)來品評藝術(shù)形象。對此,小說研究界在尊重他們的一家之言、學(xué)術(shù)個性的同時,大多持不以為然的態(tài)度,因?yàn)閺臍v史真實(shí)來看,這確實(shí)是“小心求證”的結(jié)果,但從藝術(shù)科學(xué)的角度說,這種批評就不顯其高明了。曹操、周瑜作為藝術(shù)形象、是藝術(shù)創(chuàng)造的結(jié)晶,根本不存在用藝術(shù)以外的尺度來作重新認(rèn)定,進(jìn)行翻案的問題。同樣,把《三國演義》中宣揚(yáng)的“英雄史觀”等同于歷史觀,這是以哲學(xué)來匡定文學(xué),一樣是不恰當(dāng)?shù)模粯邮怯秀K囆g(shù)科學(xué)的。所以,我認(rèn)為它不僅不足以構(gòu)成作品的思想性缺陷,而且還以其歷史的必然性、合理性和卓越的藝術(shù)成就顯示了作品獨(dú)特的思想性價值。 《三國演義》所表現(xiàn)的“英雄史觀”,主要是由作品的對象形態(tài)的特點(diǎn)決定。文學(xué)是對現(xiàn)實(shí)世界的藝術(shù)再現(xiàn),它必然與它所反映的時代的社會特征密切相關(guān)。三國時期是我國歷史上最為動蕩不寧的時代,也是最富有英雄色彩的時代。東漢末年,政治昏暗,農(nóng)民與地主階級的矛盾日趨尖銳,土地兼并日益嚴(yán)重,戰(zhàn)亂頻繁,終于迫使人民于水火中揭竿而起,引發(fā)了轟轟烈烈的黃巾大起義。于是,世事飄搖,風(fēng)云際會,英雄輩出,逐鹿中原,從何進(jìn)、董卓、李傕、郭汜擾亂京都,到曹操、袁紹、呂布、孫堅(jiān)、劉備等擁兵割據(jù),誠可謂各領(lǐng)風(fēng)騷,“一時多少豪杰”,走馬燈似地在三國歷史舞臺上登臺亮相,最后曹魏集團(tuán)以司馬父子之力飲馬長江,滅蜀吞吳,問鼎中原,三分歸一。這種歷史時代便是變革和轉(zhuǎn)型的時代,往往是產(chǎn)生杰出人物和英雄人物的時代。恩格斯在評論歐洲文藝復(fù)興時說過:“這是一次人類沒有經(jīng)歷過的最偉大、進(jìn)步的變革,是一個需要巨人而且產(chǎn)生了巨人——在思維能力、熱情和性格方面,在多才多藝和學(xué)識淵博方面的巨人的時代。”(5)三國時代與之相比無疑有著許多共同點(diǎn),所以也是一個產(chǎn)生“巨人”的英雄時代,各個政治集團(tuán)出于問鼎逐鹿的目的,奮發(fā)圖強(qiáng),銳意變革,唯賢是舉,招攬人才,使有識之士,英雄豪杰,得以在轟轟烈烈的政治舞臺上,施展抱負(fù)和才華,從而形成了英雄輩出、俊才云蒸的局面,成為中國歷史上最有利于英雄涌現(xiàn)和成長的時代。與歷史現(xiàn)實(shí)的特征相適應(yīng),《三國演義》成了文學(xué)史上首屈一指的英雄傳記,它的思想和藝術(shù)成就,只有后來的《水滸傳》,才能媲美,此外無出其右者。故而明人編《英雄譜》,即為《三國》、《水滸》之合璧;揚(yáng)明瑯《英雄譜敘》并稱“《水滸》以其地見,《三國》以其時見”,說明水滸英雄是梁山的地理特征造就的,而三國英雄則是時代特征孕育的。可見,《三國演義》之所以成為一部偉大的經(jīng)典性巨著,恰恰是由它將英雄作為對象主體的特征決定的。在作品中,各類英雄如星漢燦爛,美妙絕倫:有成功的英雄,有曇花一現(xiàn)的英雄,有失敗的英雄;有雄才大略、氣貫長虹的英雄,有謹(jǐn)重慎細(xì)、綿里藏針的英雄;有運(yùn)籌帷幄、決勝千里的儒雅英雄,有戰(zhàn)無不勝、攻無不克的威武英雄;有面對強(qiáng)敵大義凜然、不辱使命的英雄,有忠義至誠、殺身成仁的英雄;有仁君、賢相、良臣,也有名醫(yī)、高士、神卦。總之,作品把英雄人物從整個人類社會生活中凸現(xiàn)出來了,只要是杰出的人才,無論尊貴貧賤,不分長幼男女,都得以充分的顯現(xiàn)。對于這一光照千秋的群英譜,《三國演義》的整理者毛宗崗曾予以娓娓評點(diǎn):
注釋: (1)何磊《三國演義·前言》,人民文學(xué)出版社1973年版。 (2)普列漢諾夫:《論個人在歷史上的作用問題》第30頁,生活·讀書·新知三聯(lián)書店1961年版。 (3)參見《三國演義學(xué)刊》第一期。 (4)胡適:《三國演義·序》,《胡適古典文學(xué)研究論文集》第747頁,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 (5)恩格斯:《〈自然辯證法〉導(dǎo)言》,《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論文藝》第113頁,人民文學(xué)出版社1980年版。 (6)轉(zhuǎn)引自徐君慧《中國小說史》第147頁,廣西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 (7)《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三卷第42頁。 (8)馬克思:《哲學(xué)的貧困》第41頁,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 (9)《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三卷第42頁。 (10)引自托馬斯·卡萊爾《英雄與英雄崇拜》,轉(zhuǎn)引自《中國社會科學(xué)》1994年第1期胡為雄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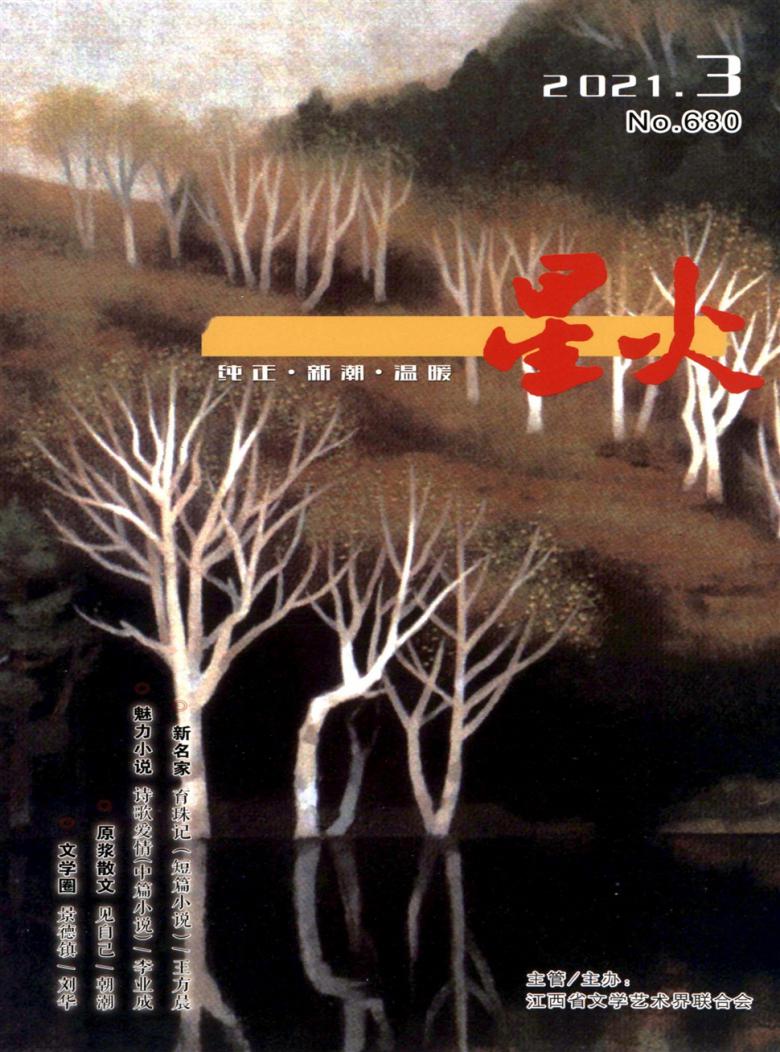
傳染病電子.jpg)
院學(xué)報.jpg)
學(xué)報.jpg)
院學(xué)報.jpg)

于我們.jpe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