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高等職業教育課程改革的基本策略
未知
高等職業教育的課程改革是一項十分復雜的系統工程,因而在我們明確了改革的背景、現狀、目標、任務、趨勢等一系列問題之后,對于改革策略問題的思考就變得十分重要了。這里所說的策略,包括改革應該走什么樣的道路、選擇什么樣的進程、采取什么樣的管理方式等多方面。只有選擇了明智的改革策略,才有可能確保改革取得成功,或者使改革少走彎路。也只有在基本策略選定之后,才談得上設計或推行具體的改革方案。
一、“移植”,還是“借鑒”
在美國等經濟、技術比較發達的國家,高等職業教育的課程改革早在本世紀60年代就開始了。到現在雖然他們的高職課程仍在不斷的改革之中,但無疑已在課程領域的各個方面積累了豐富的經驗。我國的高等職業教育課程改革如果從80年代算起,在起步上就比發達國家晚了近20年。由于人們看到在科技和生產管理領域內,發展中國家常常采用技術引進的策略,以便越過漫長的實驗與探索過程,直接將發達國家先進的科技成果轉化為生產力,這種“移植”成功的例子是很多的,故而我國的職業教育界也有這樣一種觀點,認為可以仿照技術引進策略,直接“移植”發達國家的高等職業教育課程模式和課程開發模式,甚至引進全部的高職課程材料。這種主張并非全無道理,事實上一些高職院校在移植國外先進的課程模式后也確實嘗到了一些甜頭,至少對以往一成不變的單一傳統模式產生了積極的沖擊。
但是我們認為,對于高等職業教育課程來說,“移植”并不是一種明智的策略。其原因之一,高等職業教育不同于職業培訓,它作為正規高等學歷教育中的技術教育,是國家學制體系中的一個重要的有機組成部分。由于各國各地區的學制體系不一樣,“移植”進來的高職課程很難保證能與其他各類教育的課程,乃至與初、中層次的職業教育課程之間合理銜接。其二,高等職業教育是直接面向勞動力市場的,而由于各國各地區的勞動就業制度不一樣,尤其是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的勞動力市場發育程度和社會化職業分工程度不同,因此發展中國家的高職課程在體系結構上就很可能不宜照搬發達國家的模式。其三,各國各地區對技術型人才所制定的具體規格要求不盡一致,例如同樣是培養技術員,有的國家用初中后的學制,有的國家用高中后的學制,有的國家則干脆規定為是在培養技術工人基礎上進行的繼續教育學制;對技術員所應具有的知識和技能結構差異也很大,相互間很難比照對應,容易在人才使用和評價上產生不合理和不公正的現象。其四,高等職業教育作為一種教育,其目標的確定和為實現目標所需的手段的選擇必然帶有一定的價值傾向和傳統習慣上的特點。由于西方發達國家在教育文化傳統和社會價值觀等方面與我們的巨大差異,因而他們的高職課程中的某些內容、結構以及課程觀方面的價值傾向就不一定適用于我國。
總之,高等職業教育的性質雖然是技術教育,但技術教育畢竟不能等同于技術,技術教育的課程也不能等同于技術成果。高等職業教育與各國獨特的社會體制、文化傳統及其國民普遍奉行的價值觀念、思維方式等社會環境因素密切相關,因此高職課程缺乏在國與國之間,尤其是在發達的西方國家和我們這樣東方的發展中國家之間的可移植性。從另一個角度來考慮,隨著社會經濟和科學技術的迅速發展,高職課程在內容、結構和觀念上都經歷著一個不斷演變和發展過程,而這種過程往往是有連續性的、不可跨越的。如果我們在空間上直接去“移植”發達國家的課程,意味著割裂了發達國家已經走過的一段連續的課程發展歷史,這一方面可能造成“移植”過來的課程與我國這樣的發展中國家的社會經濟和科學技術發展狀況不相符合,另一方面導致高職教育工作者在課程觀念和教學方法等方面的不適應,而且造成在教學設備等方面的“瓶頸”制約,最終在課程的實施中產生許多問題和困難。在這方面,50年代初我國全盤照搬蘇聯經驗的教訓,相信人們至今仍記憶猶新。
根據以上的分析,我們主張采用“借鑒”而不是“移植”的策略。所謂“借鑒”不同于“移植”之處在于它不是全盤照搬,而是吸取國外高職課程中的合理成分加以改造,以適合本國的國情。當然,“借鑒”并不排斥直接采用原型中的某些具體方法。這種“借鑒”策略包含兩層意思:一是借鑒發達國家在高職課程改革過程中關于改革本身的成功做法;二是借鑒發達國家現行的高職課程模式和考察開發模式中的合理成分。前者可以使我們的改革少走彎路;后者則可以優化我們的改革方案設計。
事實上,“借鑒”不同于而且優于“移植”之處還在于:“移植”只能照搬某國的某一種模式,從而既照搬了它的優點,也照搬了它的缺點;而“借鑒”則可以廣為吸取各國的各種模式課程的優點和長處。從這個意義上來講,借鑒本身就是一種創新,而創新正是高職課程為迎接未來技術更高、更快發展的唯一源泉。目前我們已經看到在我國高職課程改革過程中,一些學校已成功地采取了“借鑒”策略并取得了初步的成效。如成都電子機械高等專科學校主要借鑒了加拿大的CBE/DACUM模式,上海電機技術高等專科學校主要借鑒了英國的“課程單元”模式,上海市儀表電子工業職工大學則主要借鑒了德國建立在“雙元制”職業培訓一級培訓基礎上的技術員培訓二級培訓課程模式。
二、“突變”,還是“漸進”高等職業教育的課程改革,當然歸屬于教育改革的范疇。
美國學者馬克·漢森在《教育管理與組織行為》一書中將教育改革分為兩種類型:一種是“地震式變革”,另一種是“漸變式變革”。所謂“地震式變革”選擇的就是“突變”的策略,這種策略試圖全面、迅速地推行一項既定的改革方案。換言之,“突變”策略就是追求“一步到位”,企圖在較短的時間內和在較大的空間范圍內實現理想的改革目標。運用這種策略所實施的改革風險是很大的,如果改革成功,其收益當然就很大;但若是失敗,則損失將十分嚴重。而高等職業教育的課程改革由于涉及面相當廣,不僅要涉及課程設計、教材編選、教學設備,還要涉及教師和學生的接受心理。因為長期以來,師生雙方都習慣于在一種根深蒂固的傳統課程模式下進行教與學,如果一下子改變傳統而代之以彼此都比較陌生的新東西,容易在心理上產生恐懼感進而形成排斥感。在實踐中,可以說沒有什么比人們心理上的排斥感更加阻礙改革的進程了。
因此,我們認為高等職業教育的課程改革應該采取“漸進”的策略。這種策略的特點,一是在時間上“分步到位”地達到最終的改革目標;二是在空間上“由點及面”地逐步推廣改革的方案和成果。理論與實踐都已經證明,在教育改革中采用“漸進”策略是比較適合教育領域中的具體情況和特點的,比較容易使改革取得成功。美國學者史密斯和基思在《教育革新剖析》一書中曾精辟地闡述了“漸進”策略,認為“這種策略包含:①較低層次的不確定性和極少脫離本意的結果;②減少時間方面的壓力;③拉大重大變革的間距;④限制有關變革的決定;⑤減少對資源的要求。這種策略會使最初的目標作為成功的可能性逐漸增長的自然結果而實現。這樣反而增大了造成有利形勢的機會”。
歸根到底,高等職業教育課程改革能夠采用“漸進”策略,還是由它所培養的技術型人才具有的職業適應性和高技術發展在一定時空范圍內的漸進性所決定的。試想,如果技術型人才缺乏對特定高技術職業領域的適應性,他們就必須在學校里接受全新的高技術課程學習后才能從事高技術職業崗位的工作;而如果高技術在一定的時空范圍內得以迅速地普及和推廣,就更加迫使技術型人才全部要接受高技術課程學習,那么這樣“漸進”策略可能就行不通了。
三、“自流”,還是“調控”
當前,高等職業教育辦學熱潮方興未艾,高職的課程改革更是成為熱中之熱。但由于各高職院校實施課程改革的動因并不都是源于自覺地意識到這是高技術發展的必然要求,有的動因可能來自于各校為了提高一般意義上的教育教學質量的需要,有的動因則可能來自于學校的一些功利性的目的,因此高職的課程改革往往處于“自流”的狀態。這樣的改革,從目標制定、方案設計到組織實施、工作評價等一系列環節,可能都是屬于自發性質的。當然從理論上講,“自流”也不失為一種改革的策略,它至少可以減輕教育行政管理部門對于改革的工作責任與壓力;而在某種利益機制的驅動下,這種“自流”還會對調動各校改革的積極性起到有效的作用。然而“自流”策略的最大弊端,一是在新課程的開發、設計等方面會造成低水平重復,浪費人力和物力資源;二是在舊課程更新方面,由于縱向缺乏理論指導和咨詢服務,橫向缺乏信息交流和相互合作,使課程更新帶有一定的盲目性和缺少創見;三是因新課程實施后缺乏可靠的質量監督和評估,很可能會忽視實效而使改革流于形式,甚至反而造成教育質量的下降,更談不上適應高技術發展這一更高的目標與要求了。
我們主張,在高等職業教育的課程改革中宜采用“調控”策略。這種策略要求教育行政管理部門在規劃、組織、監督、協調和控制各高職院校的課程改革方面承擔起不可推卸的責任,還要求行政管理部門協同有關高技術企業集團為課程改革提供必要的信息服務和資金、設備方面的支持。發達國家在這方面的做法值得我們借鑒。例如在美國,技術教育的課程改革始終是由其教育局USOE領導和組織的。USOE在簽訂合同的保證下,組織專家不斷開發適應高技術發展要求的新課程方案計劃、課程材料,或者不斷修訂原有的“課程指導”;一些如IBM公司這樣的大型高技術企業財團,也在資金、設備方面對改革試點院校予以大力支持,從而使改革穩步發展,真正取得實效。
高等職業教育的課程改革之所以采用“調控”策略,在很大程度上是由這種改革在操作上的復雜性和成本上的昂貴性所決定的。這是因為,如果在課程內容改革方面實施詳細的價值分析,在課程結構改革方面全面實現模塊化,在課程觀念改革方面真正做到吸取各課程論流派之長,那么在課程方案設計和教材編制等方面的工作可想而知將變得異常復雜,加上因要有效地推行全新的課程需添置更多的教學設備而使得改革成本變得十分昂貴。因此,有關教育行政管理部門在宏觀上作適當的調控是完全必要的。有了調控,就有利于避免或減少各高職院校不必要的重復勞動,并實現有限教育資源的合理配置。至于采用什么樣的具體“調控”策略,在全國教育科學“八五”規劃重點課題“關于職業和技術教育課程體系改革若干問題的研究”成果中所提出的實施校際聯合改革、宣傳和信息服務、校長和教師培訓、資源共享、配套改革、課程研究、交流和推廣、獎勵性推動、行業牽動等9個子策略,完全適用于當前和今后一段時間內對高職課程改革的調控。
綜上所述,高等職業教育的課程改革必須根據我國的國情、高等職業教育本身的特點和課程改革所應遵循的基本準則,選擇正確而有效的改革策略,使改革走上有領導、有計劃、有步驟的比較穩妥的發展道路。
主要
1沈勤:“面向高技術發展的技術教育課程改革”,《現代職教課程論研究》,中國科學技術出版社1995年12月版。
2黃克孝、嚴雪怡、沈勤:“關于職業和技術教育課程體系改革若干問題的研究課題總報告”,《職教課程改革研究》,科學普及出版社1997年11月版。
3薛喜民:“上海市職業技術教育課程改革與教材建設的基本思路”,《職教模式實驗研究》,科學普及出版社1999年5月版。
4黃克孝:“21世紀中國職教課程發展目標與模式選擇”,《面向21世紀的職業教育教學改革》,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年2月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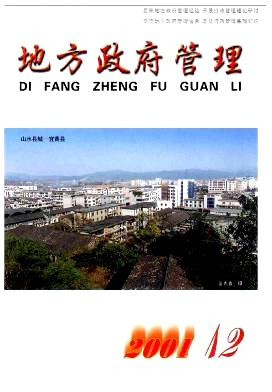
.jp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