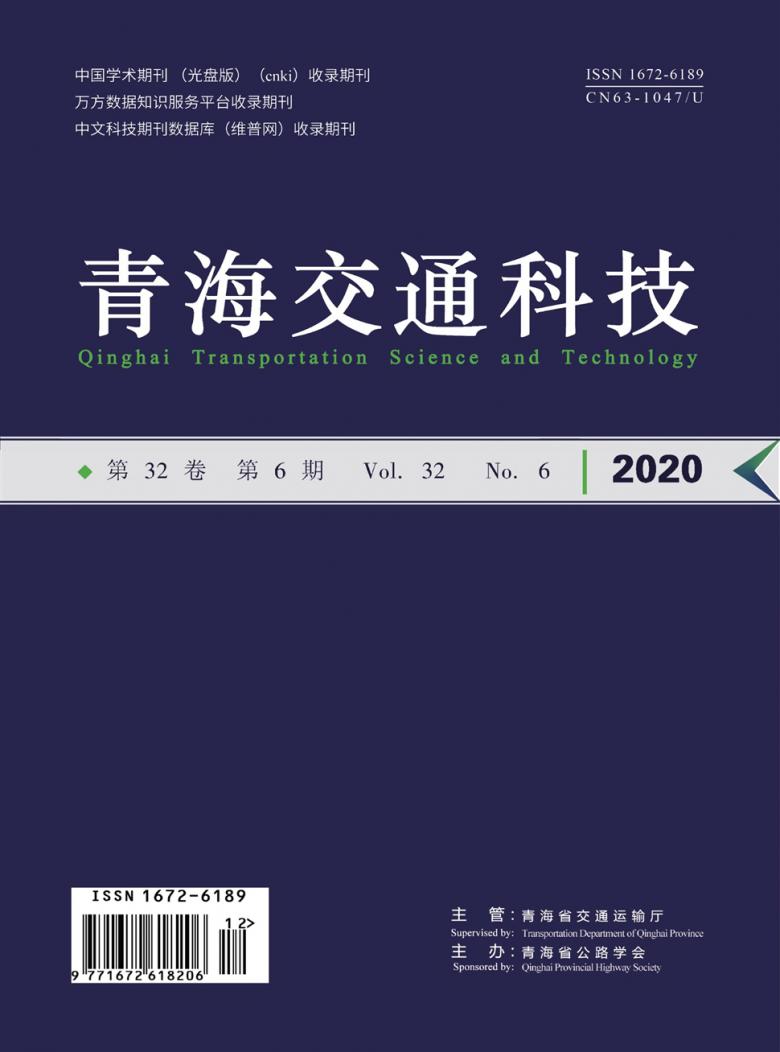自尊:心理健康的核心
佚名
作者:叢曉波 田錄梅 張向葵
[論文關鍵詞] 自尊 心理健康 心理健康教育
[論文摘要] 自尊是人格的核心,也應該成為心理健康的核心。本文試圖以人生命適應的根本源泉為出發點,解讀自尊的生命性意義;進而分析與探討自尊在人的生活中尤其是心理健康中的地位與作用,并在此基礎上提出相應的教育理念,以期為當前的心理健康教育提供一定的參考和依據。
自尊(self-esteem)屬于自我的情感成分,是個體對一般自我或特定自我積極或消極的評價,也是人對自我行為的價值與能力被他人與社會承認或認可的一種主觀需要,是人對自己尊嚴和價值的追求。這種需要與追求如能得到滿足,就會產生自信心,覺得自己有價值等;否則就會使人產生自卑感、軟弱感、無能感。自尊是個體人格的核心因素之一,對人的生活來說“自尊是你能夠給予孩子們的最好禮物——也包括你自己。對于獲得健全的頭腦、豐富的學識及幸福的生活來說,自尊至關重要。”[1](P4)
一、自尊:生命適應的心理根源
人并非一生下來就是有自尊的,正如人類并非一開始就有自尊一樣。在人類漫長的進化史上,自尊乃是人在對各種環境壓力(包括生態學壓力和社會壓力)的反應過程中獲得的,是生存適應和社會適應的必然結果。對于個體而言,自尊同樣也是其自身適應生存、適應社會環境所必需的一種基本需要,是人生命適應的心理根源。
首先,自尊是個體適應社會環境、適應基本生存的心理資源。根據有關研究,兒童在3歲左右產生較為清晰的自我尊重情感,如犯了錯誤感到羞愧,怕別人譏笑,不愿被人當眾訓斥等。①這種社會性情感的產生是重要的,因為在自尊產生之前,兒童基本上還處在生物人的階段,盡管語言和一些初級的認知能力已經發展起來,兒童可以進行初步的社會交往,但還不會主動地、自覺地修正自己的認識和行為去適應社會和他人的要求,還不會在體驗自我的情感指導下進行有效的自我保護和自我發展。兒童在這一時期除了生理需要、安全需要和一些初級的社會需要(如依戀)外,并沒有清晰地自覺自己人之為人的榮辱和價值,其發展基本上還是一種生物人的發展,這與動物的生活仍然具有較大的相似性。換言之,如果沒有自尊,沒有對自我的一種自覺的情感判斷,即使兒童具一定的自我認識的能力,也很難去調整自己的認知和行為以更好地適應社會,成為一名真正意義上的社會人。就像一個不知道疼痛為何物的人終將會被傷痛致命一擊,一個不“知道”自尊的人同樣會因不知道自我保護而失去做人的資格和價值,失去基本的心理和諧,甚至失去生命。在自尊被自覺后,兒童就可以很好地解決這個問題。如果說情感是人作為種的存在所具有的心理現象,那么有關自我情感的有效判斷則是人作為類的存在所特有的心理品質。人在犯錯誤后的羞愧感、遭到失敗的恥辱感、成功后的自豪感以及對自己的滿意感等由自尊而引起的情感體驗無疑會成為一種前提性暗示,決定著行為的取向。所以,如果說食物和水是維持人的物質生命的基本所需,那么自尊就是維持人的心理生命的基本所需。
也正是在這個意義上,人本主義心理學家馬斯洛認為,自尊是人類的基本需要之一,它具有類似本能的性質。一個人自尊需要的產生雖然晚于其它基本需要如生理需要、安全需要等,但它一旦產生并被自覺,就會以勢不可擋的力量發展起來,并逐漸成為深植于人心靈當中最為根本和最為重要的需要,成為一個人生命的心理根源。
其次,自尊是文化適應和社會適應的一種機制,可以有效緩沖人類的基本焦慮。人,不僅能意識到死亡,而且由于自我意識的反省能力,還能意識到死亡包括自己的死亡是不可避免的。這樣就不可避免地產生死亡焦慮。這種死亡焦慮是潛在的,只有當死亡意識被喚醒時才會深切地體驗到它的存在。而且,死亡的含義是廣義的,并不局限于真實的死亡,死亡焦慮會泛化到生活中的方方面面,比如人們懼怕失敗、擔心冷遇、害怕被拒絕、被否定、被排斥等,因此,筆者把這種焦慮通稱為基本焦慮。為了減緩這種焦慮,人就需要一種緩沖機制來維護自身的身心健康和生命存在。而自尊就是這樣一種機制。因為,自尊本身是一種強大的動力,當人面臨威脅和沖擊時,它會策動一定的社會行為,去補救和防御,使自己重新獲得意義感和價值感;只有當沖擊和威脅過于嚴重、時間過長時,自尊的社會適應機制受到損害,這時就會引起適應不良和心理障礙,導致各種心理和生理的健康問題,人的生命尤其是心理生命也就失去了最根本的保障。這也是社會學家Becker等人提出的恐懼管理理論(Terror Management Theory, TMT)的內涵所在[2](P39-40)。
因此,自尊對于一個真正意義上的社會人是必不可少的一種需要,一種情感體驗,一種適應機制。自尊在一定程度上起著維系社會正常運轉、潤滑人際關系并保護自我的重要作用,使人能夠在適應社會和他人要求的前提下保持自己的本真和尊嚴,保持良好的心理狀態,保持自己的生命完滿。簡言之,自尊乃是人類生命的心理根源所在。
二、自尊:心理健康的核心
如前所述,自尊是人類生命的心理根源,它可以保持一個人生命的健康發展和完滿。在自尊作用于人的過程中,首當其沖的是人的心理健康。也就是說,自尊最初對一個人起作用,是從其心理反應和心理健康開始的,而生命(尤其是人的社會生命和心理生命)的殘缺或完滿直接來源于心理健康的是與否。
在社會生活中,社會總會對人提出這樣那樣的要求。但不管何種要求,也不管何種社會,要求基本都是一致的,即人應該是健康的、積極的、發展的,人應該以一種良好形象出現在公眾面前。那么,是什么在維持著人的良好形象呢?印象整飾固然是一個經常有效的手段,但只是一種很表面的手段,人維持良好形象的內在的、深層的心理機制其實就是自尊。心理學家Bednar.R.(1989)曾指出,人都有一種保持積極的、健康的、向上的自我形象的需要,這種需要既是防止與避免生存環境帶給人的傷害與壓力的有力武器,也是個體發展的基本力量[3]。這正是自尊使人更好地適應社會環境、緩沖基本焦慮的一種具體體現:自尊策動人去追求和呈現一種良好的社會形象,從而更好地適應社會環境。而良好的社會適應是心理健康的重要標志之一。
如果自尊不足甚至缺乏,人就無法正確地對待自己和他人的評價,不能適時恰當地對社會環境的要求或事件作出合理反應,無法及時緩解生活中的基本焦慮。一言以蔽之,人就無法正常地進行社會生活。因此自尊不足(即低自尊)的人呈現給社會的通常是不好的自我形象,具體表現出兩類行為或態度:一類是自傷性行為或態度,主要指向自我。其表現有自暴自棄、自怨自艾、自哀自憐、自輕自賤等,甚至可能放棄生命,自絕于世;另一類是自戀式或自我中心的行為與態度,主要指向他人與環境。可能出現不負責任、冷漠、自我中心、敵視、攻擊他人、報復社會等偏激行為和罪錯行為,甚至走上違法犯罪的道路。但無論哪類行為或態度,反映的都是心理健康問題。需要指出的是,自尊不足的人雖然沒有呈現出良好的自我形象或社會形象,并不意味其不具有維持自身良好形象的需要。相反,是這種需要與自我意象之間產生了矛盾而導致心理失調,并表現出種種不健康的態度與行為。
具體而言,自尊是人類生命的心理根源,自尊需要也就必然成為每一個個體生命都會具有的基本需要之一。自尊需要在某種意義上說也就是維護良好自我形象的需要。但是,自尊水平的高低,取決于個體與社會環境的相互作用。這種相互作用如果是良性的,自尊水平往往可以發展得較高;如果是惡性的,自尊水平往往就會較低,也就是我們說的自尊不足。現實的自尊不足和理想的自尊需要發生嚴重沖突的時候,心理問題就會隨之產生。上個世紀90年代心理學界提出的不一致模型(Disparity Models)指出,現實我與理想我之間的自我差異或現實我與應該我之間的差異將導致一種普遍的消極的自尊感覺和機能失調[4](P253-271)。也就是說,一個自尊不足的人常常會感到一方面,維護良好自我形象的需要非常迫切;另一方面,表現出的自我形象又不能令人滿意(確切地說,是不能令自己滿意),二者之間的差距和沖突促使個體主觀上愈加追求自我尊重的情感體驗。遺憾的是,在這種追求的過程中,自尊不足的個體由于“先天不足”而常常走向兩個極端:一個是由于二者之間的差距過大,個體無力彌合而產生習得性無力感,從而出現上述的第一類行為和態度,即自傷性行為和態度;另一個極端是走向自戀或自我中心。這是由于個體不是通過正常的途徑去獲取自尊需要的滿足,而是退居于目前的自尊狀態并夸大、固守這種自尊狀態,從而對外界環境的要求表現得不屑一顧甚至故意對抗。這種自戀式的貌似高自尊的自尊狀況本質上是一虛弱的或虛假的自尊現象,個體內心深處其實極度渴望他人的尊重和關懷。許多心理學家和教育工作者都曾發現過這種現象。比如Coopersmith把這種自尊稱為“偏差自尊(discrepant self-esteem)”,國際自尊心理學協會執行理事長布蘭登稱之為“假自尊(pseudo)”,而Mruk和其他一些研究者則采用“防御性自尊”這一術語來概括該現象。
真正的高自尊是一種動態平衡的自尊。也就是說,自尊需要(或維護良好自我形象的需要)與自我現狀(或當前的自我形象)之間呈現出一種動態的平衡。一方面,高自尊的人對自我現狀常常是滿意的,他們對自己的存在能力和存在價值充滿自信,即使這種能力和價值并不比別人高;另一方面,高自尊的人雖然對自我現狀很滿意,但并非停滯不前。相反,正是由于他們對自己很滿意,很自信,所以無論在生活中還是在工作中他們都恰恰表現出了社會所期待的良好形象,社會環境自然也就作出了良好的反饋,從而與社會環境形成了良性互動,進而不斷改善和提高其自尊狀況。正如Rosenberg所指出的,高自尊感不是指優越感。高自尊的人不一定把自己看得比別人好,他們只是能夠怡然自得而已,高自尊感并不包括完美感[5](P50)。布蘭登也曾指出,自信和自我肯定是自尊的內核,它們反映了自尊的最基本要素[6](P19-20)。這種自信和自我肯定使人看待自我和周圍一切的目光明顯地帶有樂觀、信賴和珍視的色彩,從而使其具備良好的心理素質和心理狀態。高自尊的人也會有失敗和落魄的時候,他們的自我意象與自尊需要之間也會產生不和諧的沖突,但是他們在與社會環境的良性互動中可以較容易地化解掉這種沖突,并很快恢復心理平衡,從而保持心理的和諧與健康。
大量的實證研究證實,自尊與心理健康的關系極為密切。這不僅包括缺乏自尊(即低自尊)與許多重要的消極可能性如抑郁、焦慮、自殺意念、機能失調、問題行為等緊密聯系在一起,而且也包括擁有足夠自尊(即高自尊)經常與積極的心理健康和一般的心理幸福密切相關。
由此可見,自尊乃是心理健康的核心,是心理幸福的根源。這個核心的狀態如何直接關系著心理健康的狀況:高自尊由于良好的社會適應而衍生出心理健康的各種表現,包括健康的認知、健康的行為以及健康的心態;低自尊由于對社會的適應不良則導致了不健康的心理狀態及其行為表現。
近年來,心理健康問題及心理健康教育越來越受到國內外教育界的重視。各種心理診斷、心理咨詢、心理療法等等都應運而生。總結起來,目前國內的心理健康教育有三種形式:一種是由正規的心理咨詢和心理治療機構開展的健康宣傳和相應的指導與治療;一種是由電臺或電視等媒體開展的心理熱線類指導;另一類就是由學校開展的常規的心理健康教育。可以說,前兩種形式主要是面對大眾的指導和教育,其重點一般針對已經產生了心理問題或心理困惑的對象,難免出現“頭疼醫頭,腳疼醫腳”的現象,很難從人自身消除類似現象的發生,尤其是在其他人的身上重復出現。所以嚴格講來,這種形式的教育只是一種治療或指導、解惑,并非真正意義上的心理健康教育。真正意義上的心理健康教育應該是一種“防患于未然”的教育,也就是第三種形式的教育。這種形式的教育更具有根本性的現實意義。
目前,我國由學校特別是中小學開展的心理健康教育已逐步走上了規范化的道路,但是目前學校的心理健康教育常常流于形式,或教育不得法。其主要的教育形式是開設心理健康課程,把心理健康作為一門課程來教,忽視了心理健康教育的特殊性。
由前所述,自尊乃是心理健康的核心。很顯然,自尊教育也應該成為心理健康教育的核心。然而,自尊教育或者說心理健康教育并不像生理健康教育,靠灌輸知識和簡單的練習就可以奏效。如果只是教給學生什么是自尊,自尊有什么特點,有哪些表現以及應如何提高或培養自尊這些死的知識以圖培養或提高學生的自尊將很難收到預期的教育效果。那么應該如何進行正確的自尊教育以改善當前的心理健康教育狀況呢?
第一,課程教學與日常生活相結合是自尊教育的正確途徑。課程教學是必要的,尤其是對于中小學生來說,教給學生有關自尊的知識可以有助于加強其對自尊的理解和重視;教給學生有關培養或提高自尊的策略則有助于其在日常生活中自我訓練和自我教育。但是,課程教學是很不充分的,因為自尊教育的一個前提就是必須認識到自尊乃是個體與社會環境交互作用的結果。這就注定自尊教育具有很強的實踐性,自尊的培養和提高必須在個體與環境的良性互動中才能有效進行。也就是說,自尊教育必須體現在日常生活中,體現在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和一言一行上。如果概括為一種教育模式的話,就是“尊重的教育”。它要求在日常生活中,教師尊重每一個學生的個性特點和成長、發展規律,尊重每一個學生的獨特需要、選擇與追求,甚至尊重每一個學生的不足之處和缺點。除了自身要尊重學生外,教師還必須做到兩點:一是自身必須自尊,二是要教育每一個學生學會尊重他人和自己。有關“尊重的教育”的論述已有另文發表,在此不再贅述。
第二,成功和愛的體驗是自尊教育的關鍵。自尊有兩個維度:能力和價值。所以,培養學生的能力感和價值感是自尊教育的關鍵,體現到教學和日常生活中就是給學生以成功和愛的體驗。前些年,挫折教育曾在中國、日本等國家風行一時,其目的在于培養學生抗挫折的能力和吃苦耐勞的精神。這種挫折教育雖然不等于失敗的教育,但其實還是沒有抓住心理健康教育的根本,即自尊教育。一個真正自尊的人,無論他是在苦水里長大,還是在溫室里長大,他的心理都將是健康的,自然抗挫折的能力都應該強。一個從小不被人尊重,自尊也不足的人縱使嘗遍了千辛萬苦,在遇到心理問題時仍然無法正確解決。前段時間,馬家爵事件鬧得沸沸揚揚,一個貧苦人家的孩子,為什么連幾句嘲諷的話這么點小挫折都承受不了?有心理專家分析說是不良情緒的長期積累致其犯罪。這種分析沒有錯,然而還不是根本所在。他為什么會有長期的不良情緒積累呢?其實,根本原因在于,馬家爵不是一個足夠自尊的人,他沒有獲得與體驗到足夠的自我能力感和自我價值感,而是要靠外界的良好評價來樹立自己生活的信心,一旦當外界給予不良評價時,他的不良情緒就產生并逐漸積累起來了。因此,成功的教育和愛的教育才是自尊教育也是心理健康教育的關鍵。教師應該針對每個學生的特點和水平給予不同難度的任務,在其力所能及的基礎上靠自己的努力去取得成功,獲得良好評價,逐步建立自尊和自信。對于學生的點滴進步,無論大小,都應及時反饋和評價。誠然,每個人都可能遭受失敗和挫折,但一個已經建立起高自尊的人完全有能力應對失敗和挫折,及時調適心理狀態,從而保持心理健康。這在前面的論述中已經得到證實。愛的教育是發展學生自我價值感的關鍵,它更多地體現在教師對學生的無私關心和無偏對待上。無論學生是否優秀,教師都應一視同仁,給予“差生”更多的關懷和愛護是尤其必要的,因為“優生”往往在能力方面容易獲得更多的成功體驗。愛的教育在兒童早期尤為重要,其重要性甚至超過成功體驗。因為在兒童早期,其能力是比較弱小的,兒童最先體會到的情感就是父母的愛。Brown & Marshall 指出,自尊在生命早期是根據生物因素與關系因素產生與發展的。就前者而言,兒童天生就有一種預先傾向,使之感受自我的方式有別,自尊具有一定的遺傳性。就后者而言,父母—子女的關系尤其是依戀關系影響自尊的發展水平。如安全依戀的兒童更敢于探索外部世界,勇于冒險等,從而發展起更高的自尊[7]。所以從這個意義上說,學校的自尊教育應該是家庭自尊教育的延伸和補充,自尊教育早在兒童入學之前就應該開始。
第三,策略指導和策略訓練是自尊教育的輔助手段。“人生不如意事常十之八九”,盡管教師可以盡量創造機會讓學生體驗成功的喜悅和自我能力感,但失敗、破壞、失意等不良事件還是會不期而遇。高自尊的學生常常可以較容易地化解問題,排解不良情緒反應,較容易地恢復心理平衡,保持良好的心理狀態。但對于低自尊的學生,這往往變得很困難,甚至可能遭受到滅頂之災。所以盡管大多數的學生其自尊水平是均等的,教師在培養和提高學生自尊的過程中,仍不能忽視低自尊學生這一特殊群體。成功體驗和愛的體驗對于任何自尊水平的學生都是適用的,但在高自尊普遍建立起來之前,必須注意低自尊學生對失敗等不良事件的反應及其疏導。必要的措施之一就是對這部分學生采取策略指導和策略訓練。研究表明,高自尊的學生在認知歸因、社會比較、自我評價、群體歸屬等等方面都存在自我服務的傾向(比如將成功歸因于自己的能力,而將失敗歸因于問題太難或運氣不佳),或者說自利的傾向,這有助于其化解不良情緒體驗或增益良好的自我體驗。但低自尊的學生缺乏這種傾向或策略[8]。因此,對低自尊的學生進行自我服務的策略指導和策略訓練是必要的,這將有助于其對失敗等不良事件以有助于心理健康的方式進行處理。至于據西方研究而提出的中國人(或東方人)的自尊水平普遍低于美國人(或西方人)一說[9](P204-205),應該與不同的文化背景及教育背景有關。西方強調個人主義和利己主義,東方強調集體主義和利他主義。所以東方人看待問題普遍不善于以自我服務的眼光來看。“謙虛是美德”的影響根深蒂固,“不居功”反“居過”的現象也被廣為提倡。所以,中國人的自尊水平偏低是毫不為怪的。甚至,“自尊”這個詞到了中國人的嘴里不再是自我尊重的原初含義而成了一種防御性手段。因此,指導學生學會自我服務式地看問題將會是一個長期的任務。還需指出的是,自我服務式地看待問題不等于自私自利。自私自利是一個道德范疇,它常常包含置別人利益于不顧甚至以損害別人利益為前提的意味;自我服務式地看問題只是一種看待問題的思維方式,它不必然牽涉到別人的利益。而且,這種思維方式和思維策略有助于保持個人的心理健康,而只有心理健康的人才可能更好地服務于社會和他人。
由此看來,以自尊為核心的心理健康教育既是當前心理健康教育的重中之重,也是整個教育界必須重視和把握的一種教育理念。
[參 考 文 獻]
[1] [美]路易絲·哈特:增進你和孩子們的自尊心[M]. 北京:學苑出版社,1990.
[2] 黃敏兒. 自尊的本質. 廣州師院學報(社會科學版)[J],1996,(2).
[3] Bednar, R., Wells, G., & Peterson, S. Self-Esteem: Paradoxes and Innovations in Clinical Theory and Practice[M]. Washington, DC: 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 1989.
[4]Wang, Y, Ollendick, T. A Cross-Cultural and Developmental Analysis of Self-Esteem in Chinese and Western Chilidren. Clinical Child and Family Psychology Review[J], 2001,(3).
[5] 張麗華. 論自尊研究的歷史發展趨向. 遼寧師范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 [J], 2003, (3).
[6] 納撒尼爾·布蘭登著,王靜譯. 自尊的力量[M]. 北京:知識出版社,2001.
[7] Brown, J., Marshall, M. Self-Esteem: It’s Not What You Think. Under Review, Psychological Review[J], 2003 Manuscript submitted for publication.
[8] Blaine, B., Crocker, J. Self-Esteem and Self-serving Bias in Reactions to Positive and Negative Events: An Integrative Review. In Roy F. Baumeister (Ed.), Self-Esteem: The Puzzle of Low Self-Regard[M]. New York: Plenum Press, 1993.
[9] 邁克·彭等著,鄒海燕等譯. 中國人的心理[M]. 北京:新華出版社,199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