試論俞樾學(xué)術(shù)思想的幾點局限
羅雄飛
【內(nèi)容提要】俞樾是晚清著名經(jīng)學(xué)家和經(jīng)學(xué)教育家,他在傳承傳統(tǒng)學(xué)術(shù)方面發(fā)揮了特殊作用,在晚清學(xué)術(shù)史上有重要地位。但是俞樾的思想立場較為保守,“守先待后”、維護傳統(tǒng)道德和文化是其治經(jīng)治學(xué)的基本宗旨。從這一宗旨出發(fā),他對西學(xué)持淡漠態(tài)度,過于強調(diào)傳統(tǒng)學(xué)術(shù)對于道德教化的“致用”功能;他還存在以疑似之見立說、以己意改經(jīng)的傾向。 【摘 要 題】近代人物
【關(guān) 鍵 詞】俞樾/西學(xué)/道德教化/疑似之見
【正 文】 俞樾(1821~1907),字蔭甫,號曲園,浙江德清人。他是晚清同光年間“最有聲望”[1] (p. 5)的經(jīng)學(xué)家和經(jīng)學(xué)教育家。太平天國運動被鎮(zhèn)壓后,清政府著力重建傳統(tǒng)文化,俞樾正是在這樣的時代背景下受到曾國藩和李鴻章的大力揄揚。他以“通經(jīng)致用”為治學(xué)宗旨、以“梯梁后學(xué)”為學(xué)術(shù)取向。在這種思想指導(dǎo)下,他一方面遍注“群經(jīng)”、“諸子”,對傳統(tǒng)典籍進行系統(tǒng)整理,并歸納出古文“文例”88例,為后學(xué)者從事傳統(tǒng)學(xué)術(shù)研究提供了重要條件;另一方面他潛心經(jīng)史教育,主持杭州詁經(jīng)精舍及其他重要書院達30多年,門生弟子數(shù)以千計,其中章太炎、黃以周、張佩倫、繆荃蓀、吳昌碩、崔適、朱一新、戴望、吳大澂、譚獻、宋恕等均在近代學(xué)術(shù)界享有盛譽。因此,在太平天國運動后的特殊歷史階段,他對于傳承以經(jīng)學(xué)為核心的“國學(xué)”起到了承前啟后的特殊作用,對晚清學(xué)術(shù)乃至日、韓學(xué)術(shù)界都產(chǎn)生了廣泛影響,在晚清學(xué)術(shù)史上有著重要地位。 由于種種原因,有關(guān)俞樾的研究長期受到忽視。1972年臺灣出版的《俞曲園學(xué)記》(曾昭旭著)是學(xué)術(shù)價值較高的一部著作,它對俞樾的學(xué)術(shù)成就進行了系統(tǒng)評介。20世紀90年代中期以后,有關(guān)俞樾的研究成果逐漸增多,但大多局限于文學(xué)、方志學(xué)、考據(jù)學(xué)、中醫(yī)文獻和中外文化交流方面,與經(jīng)學(xué)思想有關(guān)的研究成果尚不豐富(注:近年來,俞樾在傳統(tǒng)學(xué)術(shù)傳承方面的作用開始受到重視,臺灣學(xué)者、《漢學(xué)研究》主編周昌龍先生2003年制定了研究專題《清末民初儒學(xué)的內(nèi)在轉(zhuǎn)化——以俞樾、章太炎、錢玄同學(xué)脈為中心》;美國華盛頓大學(xué)歷史系華人學(xué)者麥哲維的博士論題為《俞樾、陳澧、詁經(jīng)精舍和學(xué)海堂》;浙江臺州師院一位學(xué)者已初步完成《俞樾的學(xué)術(shù)傳承》一書。但是至今還沒有看到這方面的正式學(xué)術(shù)成果。近年筆者對俞樾的學(xué)術(shù)思想進行了較為系統(tǒng)的研究,已發(fā)表論文有:“俞樾在日本韓國的影響及其與外國友人的交往”,《首都師范大學(xué)學(xué)報》2004年2期;“俞樾的‘因文見道’思想及其學(xué)術(shù)風(fēng)格”,《齊魯學(xué)刊》2004年3期;“俞樾公羊思想發(fā)微”,《清史研究》2004年3期;“俞樾:‘務(wù)求通博’治經(jīng)思想探析”,《蘇州大學(xué)學(xué)報》2004年6期;“俞樾與經(jīng)學(xué)人才的培養(yǎng)”,《山西師大學(xué)報》2005年1期。)。本文擬在筆者前幾篇論文的基礎(chǔ)上,對俞樾學(xué)術(shù)思想的局限性進行初步探討。
一、被動順應(yīng)時代潮流,以淡漠態(tài)度對待西學(xué)
俞樾作為經(jīng)學(xué)大師,其思想觀念較為保守。他特別重視中國傳統(tǒng)道德,認為施行仁政和強化道德教化乃是“自強之上策”[2] (卷六,p. 12),指出“孝悌忠信即是兵法”。教化“可使制梃以撻秦楚之堅甲利兵”[3] (《續(xù)五九枝譚》,p. 1)。但另一方面,俞樾又吸收了《公羊春秋》的“改制”思想、《周易》的“窮變通久”思想和荀子的“法后王”思想,并且在這些思想的基礎(chǔ)上,對社會變革的必要性有所認識,不僅肯定秦始皇變法等歷史上的革新之舉,而且對晚清的洋務(wù)運動亦持理解態(tài)度。然而,他對于“變”的理解是非常有限的。他說:“變也者,圣人之所不得已也。其已定之爻,無所用吾變也;未定之爻,而有可通,則亦不必用吾變也。窮而無所通,乃不得已而變以求通,此圣人所上以贊天地之化育,而下以左右民也。”[4] (《易窮通變化論》,p. 3)俞樾既站在維護傳統(tǒng)道德的根本立場之上,又以“變”為圣人不得已之舉,因此他對于現(xiàn)實社會變革必然缺乏主動精神,總是被動地隨著時代潮流而一點一點地“變通”。由于他清醒地認識到晚清社會矛盾已經(jīng)非常尖銳,清王朝已不能照舊統(tǒng)治下去,因此對舉辦“洋務(wù)”、“新政”的必要性表示理解;但他同時又敏感到“有機械者,必有機事;有機事者,必有機心”[5] (卷六. p. 20),深知“洋務(wù)”、“新政”的開展,必將沖擊乃至動搖中國傳統(tǒng)的道德觀念和生活方式,因此他內(nèi)心對“洋務(wù)”及其西學(xué)又有抵觸情緒。在他看來,“烏喙蝮蝎”之屬,雖可以治“瘤癘癰疽”之毒,為醫(yī)者“所不廢”,但畢竟是有毒之物。有見于此,他對“洋務(wù)”、“新政”雖在總體上加以理解支持,對他人乃至自己子弟學(xué)習(xí)西學(xué)亦不反對,甚至還在遺言中表示,子孫“茍有能通聲、光、電、化之學(xué)者,亦佳子弟也”[6] (p. 99),然而他自己卻“隱居放言,謹守包咸不言世務(wù)之義”,強調(diào)自己“于一切洋務(wù)、陸軍、海軍,皆非所知,亦非所欲言”[7] (卷八,p. 4)。 從這種現(xiàn)實政治態(tài)度出發(fā),俞樾雖身處西學(xué)東漸、中西交流日甚一日的時代,卻對西學(xué)從來不去主動吸取。不僅如此,他還強調(diào)西學(xué)已在“吾儒包孕之中”,只要“經(jīng)史并通,即於體用兼?zhèn)洹保蚨磳τ行涸诔Un之外別設(shè)一課,“專考經(jīng)濟有用之學(xué)”的做法[8] (卷三,pp. 5~6)。由于對西學(xué)采取這種態(tài)度,因而終其一生,俞樾的西學(xué)知識可以說是極為貧乏。在他的著作中,除介紹過熊拔三的《西洋水法》和合信所著《博物新編》外,于西學(xué)僅有幾處零星涉及。正因為他對西學(xué)茫無所知,所以直到1897年還堅持認為,如果精練20萬藤牌軍,持藤牌護身,佐以飛叉,則“破外夷之火器,有余裕矣!”[9] (卷二,PP. 19~20)對西學(xué)之盲昧竟至于此!19世紀90年代初他還聲稱:“余惟農(nóng)桑者,天下之本務(wù),不可以末務(wù)參之。古人于此二事,至纖至細,事有一定之程,器有一定之制,而便宜茍且一切之謀,皆所不用。”[10] (p. 7)他在《王夢薇本務(wù)述聞序》中亦有此說,且對“農(nóng)事、織事皆欲以機器行之”頗不以為然,并為先民樸茂之美意漸失感到惋惜[5] (卷六. ,p. 20)。但這些并不意味著俞樾對引進機器和西學(xué)的洋務(wù)運動持反對態(tài)度。在強調(diào)清吏治、嚴軍政、端士習(xí)、蘇民困為自強要策的同時,俞樾亦充分肯定彭玉麟提出的設(shè)海軍、購槍炮、練新軍的建議,認為這是“深識遠慮”[7] (卷一,p. 9);他還肯定浙江巡撫廖壽豐開繭紗廠、設(shè)蠶桑館、頒焙茶新法諸舉措,認為這些雖“從時尚,無詭經(jīng)常”[9] (卷六,p. 22)。細讀俞樾的著作,諸如此類前后矛盾之說尚有不少。這與他對現(xiàn)實政治的矛盾態(tài)度密切相關(guān),其為文勢必隨話語環(huán)境的不同而不同,前后失倨也屬正常。 還需指出的是,俞樾對于學(xué)習(xí)西學(xué)的成效亦持懷疑態(tài)度。他從維護傳統(tǒng)道德的基本立場出發(fā),對西學(xué)的“消極”影響保持高度警惕。盡管認識到學(xué)習(xí)西學(xué)特別是西方自然科學(xué)的必要性,但他反復(fù)強調(diào)“學(xué)于人者制于人”,因此要想克敵制勝,還必須在學(xué)習(xí)對方的同時另辟蹊徑。具體而言,他認為西人利在火器等剛性的一面,中國在學(xué)習(xí)那些剛性事物的同時,還必須從柔性的一面發(fā)展自己,才能最終達到以柔克剛的效果。但是,由于認識水平的局限,他認為能克剛的事物,除道德教化外,無非是“水器”、“藤牌”之類。 總之,與馮桂芬、郭嵩濤等同時代思想家相比,俞樾的西學(xué)知識是相當貧乏的,政治態(tài)度則具有鮮明的保守性;若與晚他一輩,的思想家如康有為、梁啟超、嚴復(fù)相比,則更是不可同日而語。
二、過于強化經(jīng)學(xué)的致用功能,具有以學(xué)術(shù)比附道德教化的傾向
俞樾不僅對傳統(tǒng)道德持保守立場,還特別重視道德實踐。他一生以“衛(wèi)道”自任,儼然傳統(tǒng)道德的守護神,維護、表彰和闡揚傳統(tǒng)道德,似乎已溶進他的生命之中。早在河南學(xué)政任上,俞樾就特別重視人倫教化,曾上疏奏請以公孫僑從祀文廟,以圣兄孟皮配享崇圣祠。罷官以后,他仍以人倫風(fēng)化為己任,自言不敢“默然而息”[2] (卷四,p. 1),于“名教樂地”“未肯多讓”[11] (卷五,p. 8)。他的雜文集收錄約750余篇雜文,其中關(guān)系婦女的有130余篇(含夫婦合傳),都突出歌頌“婦德”這一主題,其他雜文也以表彰忠節(jié)、孝行、義行為主,即使普通的人物碑銘亦多突出碑主德行。在他的詩集中,表彰忠孝節(jié)烈的內(nèi)容也不少。他的筆記小說則幾乎完全以“勸善”為主題,“刲股療親”、“以身殉夫”等愚昧行為都被作為正面典型大力表彰。他主持修撰的地方志,同樣是這方面的內(nèi)容連篇累牘。因此,當時人們對俞樾便有善于“寫德”的評價。 俞樾強烈的“衛(wèi)道”精神直接影響到他對經(jīng)典的校勘、訓(xùn)釋以及學(xué)術(shù)取向。他在校釋群經(jīng)時,一旦涉及道德教化,便會陷于先入為主和主觀武斷。下面略舉數(shù)例,以見一斑: 《論語》云:“求也,為之聚斂而附益之。”俞樾訓(xùn)釋曰:“季氏聚斂,乃民聚而非財聚。蓋冉子為季氏宰,必為之容民蓄眾,使季氏私邑民人親附,日益富庶。”[12] (卷三十一,p. 1) 《論語》云:“賜不受命而貨殖焉。”俞樾在訓(xùn)釋中強調(diào),子貢并非不受教命,只是“不受命于官,而自以其財市賤鬻貴,逐什一之利”。[12] (卷三十一,p. 1) 《論語》云:“四體不勤,五谷不分。”俞樾訓(xùn)詁該句時指出,兩“不”皆語氣詞,“分”為“糞”之誤,因謂“不勤,勤也;不分,糞也”。他認為此乃丈人自言:“惟四體勤,五谷糞而已,焉知爾所謂夫子!”并非以此責(zé)子路。[12] (卷三十一,pp. 7~8) 《尚書·泰誓》云:“時哉弗可失。”俞樾認為:“武王為天下除暴亂,非爭天下也。”因謂武王不可能有如此不仁之言。他斷言:“《泰誓》之偽,即此可見,若徒推求於字句之間,抑末矣!”[2] (卷二,p. 8) 以上訓(xùn)詁雖異于前人之說,卻并沒有多少確鑿的證據(jù),多為推論之言。揆其意,蓋以為前人箋注有損圣人及門徒作為道德典型的形象,故出此言。俞樾之經(jīng)說,諸如此類者尚有不少。 不僅如此,俞樾品評歷史人物亦往往從道德教化出發(fā),常以因果報應(yīng)為說。例如他論晉文公:“有陰謀者,必有陰禍”;晉祚之所以不永,實乃晉文公“譎而不正”之報[2] (卷一,p. 2)。他論馬援亦與此相仿。為了宣揚因果報應(yīng),俞樾頗佑《左傳》以成敗論人。他說:“孔子作《春秋》,微其文,約其詞,於當時諸侯大夫之罪,未嘗斥言之也。夫使當時諸侯大夫之罪而皆著於后世,則人將以天道為疑,天道不信於天下,而天下亂從此起矣!”因此,他認為《左傳》以成敗論人,于齊之陳氏,晉之韓趙魏,以及陳、蔡、江、黃諸國,皆著其所以興之之理,使善有所慕,惡有所懼,是“深得圣人之意”。他還強調(diào):“左氏不以成敗論人而務(wù)得其實,則可免后世之譏,然其為天下禍且愈以烈。”[2] (卷二,p. 5)由此不難看出,俞樾本人未必真的相信因果報應(yīng),他之所以強調(diào)因果報應(yīng),主要是為了道德教化的需要。 俞樾對東漢王充所作的《論衡》的態(tài)度,進一步表現(xiàn)出他的這種傾向。他自言:“漢人之書……獨不喜讀王充之《論衡》,以為有大謬於圣人者。”其所以然者,緣于王充不信因果報應(yīng)之說,認為世人受福佑并非行善所致,“實則遭遇使然耳”[11] (卷五,p. 8)。但是就在同一雜文集中,俞樾又有《沈懋卿事釋疑》一文,文中引王充“遭際有命”之說釋沈氏雖稱善士而不得善終之由,以“性善命兇為沈君定論”[11] (卷四,p. 8)。俞樾之“實事求是”精神,于此完全被“致用”的需要所代替。以此觀之,俞樾釋經(jīng),凡關(guān)乎風(fēng)俗道德,總以“教化”為首要考慮,即便其說有些根據(jù),主觀動機亦非純以學(xué)術(shù)為目的。 俞樾既以“衛(wèi)道”自任,其治學(xué)宗旨自然服從于道德教化的需要。但是在19世紀80年代以前,他還能夠重視發(fā)揮傳統(tǒng)儒學(xué)中的變革內(nèi)涵,提倡荀子的“法后王”思想。以后隨著洋務(wù)運動深化,西學(xué)對傳統(tǒng)的倫理道德及生活方式的沖擊漸漸顯現(xiàn)。在這種情況下,他開始更多地強調(diào)自己為孟子之徒,要求“法先王”、“守先王之意”,并以“守先待后”為己任。1881年,他作《三大憂論》和《自強論》,前者強調(diào)傳統(tǒng)文化、傳統(tǒng)道德乃至整個民族面臨的危機,后者則高揚孟子“返本”之說。俞樾一向不過問現(xiàn)實政治,這兩篇僅有的政論文章絕非隨意而作,在很大程度上,它們標志著俞樾治學(xué)宗旨的轉(zhuǎn)變,而這種轉(zhuǎn)變正是出于道德教化的急迫需要。盡管如此,直至“戊戌變法”以前,由于傳統(tǒng)文化和傳統(tǒng)道德的危機尚非十分尖銳,俞樾對“荀子之徒”的變革主張還能努力去適應(yīng)。 但是從“戊戌變法”開始,俞樾再也無法適應(yīng)時代的變化。傳統(tǒng)文化和傳統(tǒng)道德的危機以及清王朝行將崩潰的命運使他惶恐焦灼,他不僅將“憂時之淚”在許、鄭先師前灑了又灑,而且一再發(fā)出“久居人世待何如”[13] (卷十六,p. 1)的哀嘆。1900年他作“祈死”詩,又為“八十自悼文”,其內(nèi)心之絕望可以想見。然而,就在俞樾惶恐絕望之際,其弟子章太炎順應(yīng)時代潮流,毅然走上了革命道路。俞樾對此極為憤怒,斥其為不忠不孝,并發(fā)表“破門聲明”,將章太炎革出師門。章太炎毫不妥協(xié),于1901年寫作《謝本師》一文,表示與乃師決裂。從此兩人分道揚鑣。這也是俞樾不能適應(yīng)時代發(fā)展的必然結(jié)果。從俞樾對傳統(tǒng)道德執(zhí)著、虔誠的態(tài)度來看,他將章太炎革出師門是嚴肅認真的,并不是為了掩人耳目、做做姿態(tài)而已[6] (p. 72)。然而就章太炎而言,他僅僅是在政治上與乃師決裂,并不是從此不承認這位朝夕與共達8年之久的“先生”。1907年俞樾去世后,章太炎作《俞先生傳》,高度評價俞樾的學(xué)術(shù)成就,其心中仍以俞樾為師,于此可知矣。
三、以疑似之見立說,以己意改經(jīng)
學(xué)者們論及俞樾經(jīng)學(xué)之弊,最突出的莫過于“好改經(jīng)字”。此說最早由章太炎提出,他在《俞先生傳》中說:“說經(jīng)好改字,末年自敕。”[14] (p. 211)以后學(xué)者相因為說,皆謂俞樾“務(wù)反舊說,一心標異,出言太易,論斷亦近專輒”[15] (p. 647)。 俞樾治經(jīng)的確不如高郵王氏嚴謹,也的確存在以疑似之見立說、以己意改經(jīng)的傾向。如《詩·天保》“君曰卜爾,萬壽無疆”一句,舊注訓(xùn)“卜”為“予”,俞樾則謂“卜爾之‘卜’,當訓(xùn)‘報’。卜爾者,報爾也”[16] (卷三,p. 4)。此即為疑似之見。俞樾在訓(xùn)釋此條時亦多次使用“疑”、“殆”、“當”等詞。諸如此類,在俞樾的經(jīng)學(xué)著作中尚有不少。應(yīng)當指出的是,俞樾之所以以疑似之見立說,與其治經(jīng)思想和學(xué)術(shù)風(fēng)格有關(guān)。俞樾治經(jīng)喜歡“標異”,只要發(fā)現(xiàn)與舊說不符的新材料,即便其尚不足以推翻舊說,他也會本著“以疑存疑”的精神表而出之。所以后之學(xué)者常以“出言太易”病之。再者,俞樾以詞章之士轉(zhuǎn)而研治經(jīng)學(xué),且擅長邏輯思考,因此其治經(jīng)風(fēng)格傾向于從文章的整體結(jié)構(gòu)和內(nèi)在邏輯關(guān)系入手作訓(xùn)詁分析,而不是斤斤于片言只字;于是只要篇章段落乃至語句之間邏輯有所不協(xié),語意有所不順,他便懷疑經(jīng)典原文本身,并在審慎考證的基礎(chǔ)上大膽提出對經(jīng)文的改動意見。他認定,古代經(jīng)典在口耳相傳乃至輾轉(zhuǎn)傳抄的過程中,本身出現(xiàn)訛誤是完全可能的,因此他并不以改經(jīng)字為非。他在《群經(jīng)平議》序中明確指出:“或者病其(高郵王氏)改寫經(jīng)文,所謂焦明已翔乎寥廓,羅者猶視乎藪澤矣。”[12] (《序》)在他看來,高郵王氏“改易經(jīng)文”自有其深刻的思想基礎(chǔ)和開闊的眼界,而以此為病者則往往是因認識水平有限而盲目批評。 任何一種治經(jīng)思想和治經(jīng)風(fēng)格都有其長處,亦有其局限。俞樾既強調(diào)以疑存疑,其治經(jīng)自然不那么嚴謹整飭;再加上俞樾務(wù)求“通博”,對一些問題缺乏專門而精深的研究,因此治經(jīng)不準確、甚至錯誤之處亦當不少。然而他的這種治學(xué)思想和風(fēng)格往往能發(fā)現(xiàn)和提出新問題,為后學(xué)者作先導(dǎo)。所以對俞樾的這種治學(xué)思想和風(fēng)格,學(xué)界病之者固然有之,而贊成者亦不乏其人。梁啟超就從未對此加以批評,錢玄同甚而號召學(xué)習(xí)俞樾的大膽疑經(jīng)精神,宋恕則對俞樾佩服得五體投地,認為俞樾集“了真”、“洞至”、“入圣”、“極賢”、“擅鴻”、“兼文”、“踐通”、“包儒”諸優(yōu)長于一身,“學(xué)問至德清先生觀止矣!”[17] (pp. 105~108)宋恕此說雖然偏頗,但他能從“名學(xué)”出發(fā)把握俞樾的學(xué)術(shù)風(fēng)格,強調(diào)俞樾“名家之學(xué)殆過實齋”[17] (p. 90),的確可算是俞樾的學(xué)問知己。筆者以為,俞樾的這種學(xué)術(shù)思想和治學(xué)風(fēng)格,應(yīng)當說是利弊互見,對之一味批評或過度推崇都是片面的。中國的學(xué)術(shù)傳統(tǒng)歷來重接受而輕思考,讀者希望著者在書中提供精確無誤的答案,所以對俞樾的標新立異、以疑似之見立說、以己意改經(jīng)不以為然。但實際上,如果讀者同樣抱著“以疑存疑”的態(tài)度去讀俞著,發(fā)現(xiàn)他的與眾不同和標異之處,從中得到啟發(fā),引起思考,進而深入鉆研以求的論,從這個角度講,俞樾的著作還是有其特殊價值的。 俞樾學(xué)術(shù)思想的局限主要是他對中西文化和社會現(xiàn)實的基本態(tài)度使然。如果說他對于中國傳統(tǒng)文化的保守立場還含有一些合理成分的話,他對“刲股療親”、“以身殉夫”等封建道德的贊美則無疑是陳腐和落后的。此外,以“衛(wèi)道”精神治學(xué),讓學(xué)術(shù)服務(wù)于“道德教化”的目的;以及“以疑似之見立說”、“以己意改經(jīng)”的不甚嚴謹?shù)膶W(xué)術(shù)風(fēng)格,也都是俞樾學(xué)術(shù)思想和學(xué)術(shù)活動中顯而易見的缺陷,后之學(xué)者對此不可不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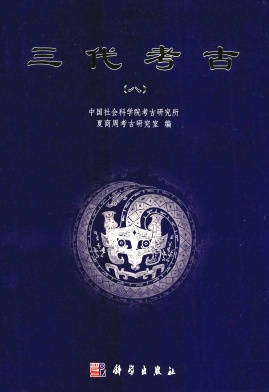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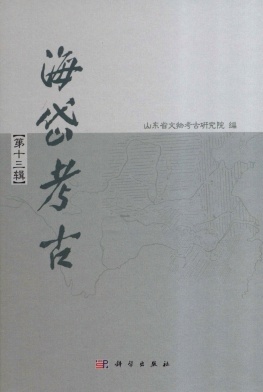
境.jp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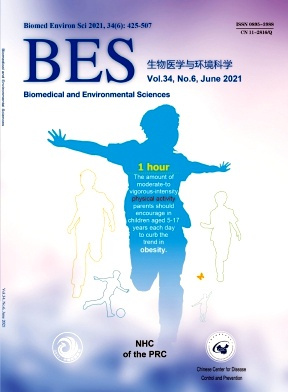
院學(xué)報.jp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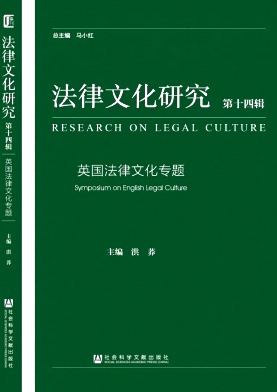
于我們.jpe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