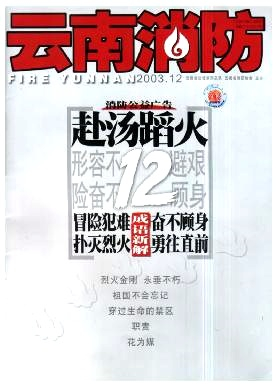傳統:給亞洲政體帶來了什么?——淺論松本三之介的思想史學研究
佚名
亞洲,具體說作為“儒家文化區”的東亞,傳統文化對這個地域的政治發生何種作用?一個民族與國家的政治特質,既被經濟形態決定,又被文化形態決定。通常討論多的是文化與經濟的關系,近年來東亞經濟進退漲跌,戲劇性地影響著“亞洲價值”的榮辱浮沉。然而,同樣是“亞洲價值”,制造與維護著一個怎樣的政治模式?文化與政體的關系如何?直面這個問題,將使我們對東亞傳統有一個建筑在合理基礎上的新認識。
日本戰前尊奉“儒教”與國學,這些學說加上其他社會經濟因素,制造出日本近代“超國家主義”、“全體主義”的專制帝國。這是戰前日本思想界一個受約束的話題,戰時更噤若寒蟬。而當日本戰敗之后,學者們終于得到一個難得的自由言說的空間。在丸山真男的首創帶動下,一股“日本政治思想研究”的學術風潮席地而起。 這是一個史學思潮、社會思想思潮,就其本質而言,更可以說是重新認識儒學、國學及一切國粹的反思思潮。參與其中的包括松本三之介等一批比較年輕,堪稱丸山弟子的學者。他們的研究都在說明,日本現代的專制政治與傳統文化及對待它的態度有關。
松本三之介寫有《國學政治思想的研究——近代日本政治思想史敘說》一書。本書內容最初發表于《國家學會雜志》。當時有一個題目是《近世日本國學的政治課題以及它的展開——關于幕末國學的考察》。 認識松本學術,或可對上面說的那個史潮的觀點理路有一個大致了解,提示我們:對民族文化的吸收與闡揚是對的,而另一方面,又要對其內在的非合理的“前現代”因素有所警戒與克服。在這方面,日本的教訓最深重,因此松本等人開展傳統研究所得的有益結論也最值得中國學界留意。
一、國學研究的前提,對朱子學的理解
日本江戶時代堪稱理學時代,以朱熹為代表的理學牢固占領思想領地,開展日本精神史研究無法繞開歷史上著實存在過的碩大理學世界,更何況它至今還在發揮影響。任何一個學術思想都不孤立存在,而與周圍思想環境密切聯系。盡管各學術派別的代表常會否定這種聯系,甚而對相關派別不惜詆毀。然而“聯系”的存在終究無法否定。再則,開展比較是進行思想研究的重要方法,既然國學與理學有著必然的內在聯系,將它們做并列比較也就很有必要。也許正是出于這些原因松本先去理學世界做一番巡游,化不少筆墨,闡述對理學的理解。
如果說孔子思想的基本特質是“政治哲學”那么到了宋明以后,儒家思想則由于受到佛教思想的影響,在闡述原有政治原理的同時,更加深對心靈世界的注目,精神內容由此改觀與擴大。 松本說,為理解朱子學的政治思想,當先窺探朱子學的人生奧里。朱子在論證人生觀時,表現出來的重要特點是突出人性論與宇宙論的連貫性與一體性。宇宙具萬物本原即“理”。由此本原,產生“氣”。理乃“絕對”,氣則回流不停,創造宇宙萬物的特殊群像與個別特征。理與氣合,以成世界。 作者引用江戶時代著名理學家林羅山的話說,天地未開,只是一個“理”,理為“太極”,一切由理而生,生于太極。
人既有作為理的善的一面,又有附著于形的,以氣的方式表現出來的惡的一面。什么是理,什么是氣呢?依林羅山的解釋:理的表現形態是仁義禮智等行為規范。氣與其相反,大體與理不合。理表現為道德原則,又可以說是善。善為一氣質,惡也為一氣質,氣質可以轉換,唯一途徑是對理的理解與服從。
因有氣的存在,引出“物欲”。如朱子論:人有本來的善良心性,只因物欲的蒙蔽,各向君子與小人的不同方向發展。人們只有依照四端與五倫的要求,對氣質做不斷的改造,將蒙蔽善良之心的物欲逐漸去掉,方有可能恢復善良本心,成為君子。
松本在進行國學研究的同時,開展理學思想研究是有原因的。松本在他的另一本書《天皇制國家與政治思想》中曾提出過“公的世界”與“私的世界”這樣兩個命題。公的世界在意義界定上說是區別于個人世界的政治社會。“私的世界”則強調個人利益,是具有獨立價值判斷的,自然、自立與自由的“個人世界”。
松本多年來在思考著:“公私未分”的前近代的社會,“私的世界”,即“個人的世界”被壓抑與泯滅。他遇到的一個問題是如何將私的世界從“公”的世界——政治與社會的世界里分離出來,具有獨有的價值與思考樣式。現代性社會的一大特點是人的“自然、自立的個人世界”的建立。一個社會倘若組成它的“個人”還沒有建立這樣的“私的世界”,這個社會不配為現代社會。
天皇制國家強調“滅私奉公”,“公的社會”(政治社會)建立在“滅私”,即消滅“個人”利益與個人自覺的價值體系之上。人們的私人世界被充分淡化與否定,而成為徒有其名的子虛烏有。因此,一旦日本戰敗,獲得精神上的解放,當務之急就是全力建立起與西方價值銜接的,個人的,獨立與自由的“私的世界”。就象一個新建筑的矗立,要有支撐它的新地基,現代性民主社會的建立急迫等待廣大人民全新意義上的“私的世界”的竣工。
戰后的日本能否建立起這樣的“私的世界”?面對這樣的問題,松本思想的深處存在著疑慮。總體上說,戰后日本人確實得到了解放,日本發生了巨大的變化,從此進入民主社會。然而面對社會“公”的激變,日本人“私”的精神狀態是不是也同時“解放”,發生變化呢?抑或以不變應萬變,以小變應大變?在松本看來,日本人經過長期的封建教育,對于他們來說在長時間的中世紀歲月里,已經建構出一個“否定私”的“私”的世界。讓日本人的思想真正獲得解放,還需要做出很大的努力。
日本在明治維新之后的一段時間,曾積極吸取西學,西方價值觀進入日本人民的心扉。然而當 19 世紀80 年代后,國粹主義盛行,日本逐漸走上“超國家主義”、“絕對主義”、“全體主義”的道路。如果說“超國家主義”這個概念表達日本專制主義政治結構的特點,那么“絕對主義”與“全體主義”則強制個人對“全體”(“國家”)的“絕對”尊崇、“全體”(“國家”)對個人的“絕對”支配。
我們要繼續研究的是日本人何以被“教化”出集體的“無私”的 “世界”?回答是在整個的德川時代,朱熹的理學思想全然占領了精神領域。 朱熹的“滅人欲存天理”的教條成為束縛日本人思想的緊箍咒。日本人的私欲受到封建倫理力量的嚴苛壓抑,而無“私”可言,絕對服從綱常禮教的失去個體靈魂的軀殼。應該說松本在研究國學與政治關系的同時,對理學思想做深刻剖析,對日本“無私”的“私人的世界”作實質性揭示,客觀上促使日本人從自我限制的思想牢籠中掙脫出來,為實現社會的現代化,及早實現人的現代化。
二、松本的國學比較論與日本古代政治特質論
國學是江戶時代的學派。其主要學術特點在于觀摩古典,提倡古道,探究由闡發民族精神。18 世紀有契沖、下河邊長流等人倡言此學,力主更新理念,發掘《萬葉集》等古典的特殊價值,從中領會日本精神的固有內涵。荷田春滿進一步發展這樣的學術思想,并糅入神道思想。賀茂真淵則說明古代精神乃日本之道,比儒學更加優越,主張恢復日本古代精神。本居宣長著有《古事記傳》,集復古思想之大成。平田篤胤繼承宣長古道觀,強化了神道與國粹色彩。明治維新時期,國學鼓吹尊王攘夷,成為維新的精神引導。
松本對幕末國學作了評價:國學發展到幕末,原有注重民間生活的思想進一步充實,而具“實用、實事、實德、實學”的特色。成員組成中的社會層面也在逐次下降,武士成分慢慢減少,如宣長門下武士只占百分之十四。學術界有“草莽的國學”的稱呼。國學倡“家職勤勉論”,勸導人民用勤敬的心情從事耕作、負擔租稅、整齊家事與維持村落生活,顯示傾心民間道德教育的思想趨向。 松本感到國學思想中有著明晰的政治論。在宣長那里政治就是“事君”,換言之是“臣的服從”。宣長說:為君者,重要的事是祭神,大臣的責任則在于服務天皇,“奉天皇之大命”,各司其職。 宣長論列他的“服務政治論”,強調對“支配”概念理解的重要:“支配”由兩個要素組成:“命令與服從”。問題的核心不在于討論支配者的意志,而在于強調被支配者必須以支配者的意志為自己的意志。這樣天皇的“大御心”就是“被支配者”的絕對行為原理。不可將天皇的 “大御心”說成是“命令”,“命令”由上而下,畢竟是客觀理念,接受命令難免有被動心態,因此應將原本是“命令”的天皇的“大御心” 視為從天皇那里領悟到的“心”,以天皇之心為本人之心。
松本將國學與理學做對比說:理學在論說“士”的精神構造時強調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而宣長突出的不是這些,是以絕對服從為基干的“被治者”(被支配者)的心情構造。理學與國學的區別、國學的特殊“實踐意義”在這里被明白突現出來。宣長塑造的是“天皇觀的政治理念”。天皇有絕對的權威,政權擔當非天皇莫屬。一切勝利與光榮屬于天皇。一切失敗與缺陷與天皇無關,也與“為政者”無關。失敗與“缺陷”之所以出現,是因為被支配者那里出了問題。 宣長還論證神道與理學的區別。理學強調教誨,神道不輕言“教”,而重視“事實”,主張以事說理。篤胤將“事實”說成“意識表現下的顯在化”,“事實才是真實的道”。宣長與篤胤思想一致,都主張以神道為依據的“無規范性格”,把理學貶斥為遠離“事實”的“空言”。宣長認為理學的空言作風其實也在違背孔子的教誨:欲載之空言,不如見之行事。總之神道是在說明一種“非規范的規范性、非政治的政治性”。它的出現與儒家思想比較,更具有政治實踐意義,與日本的政治國情況更加貼近。
在對日本政治所起的作用方面,儒學與國學仿佛各自有著自己的不同位置與分工。就象前文說的那樣,理學特別關心人的內心世界,要人從內心深處產生變化,驅逐于“公”(國家與天皇)不利的私心雜念。在治心與治人兩個方面,理學看重治“心”,可謂目光深遠。心即意志,既然把人的意志牢牢控制,即可將整個社會控制在手中。
然而在日本的國學者看來僅僅依靠理學思想還無法使日本長治久安。國學大學問家本居宣長在議論到國學的研究對象時說,國學的研究領域具體可以分為“道學、有職學、史學、歌學”。其中他特別重視“道學”。然而他又堅決反對將道理解為中國的“儒佛之道”。他說道是一種特別的“古意”,為日本所獨具。它不來自儒經與佛典,而出于《古事記》與《日本書紀》這樣兩部日本最有名的歷史典籍。他要求人們在讀這兩部書的時候特別留意神代史部分的敘述與思想。其中傳播著天皇是神的皇國史觀,反映了日本本土宗教——神道教的中心意義,說明了神道就是“天照大御神的道,天皇總攬天下的道”。這樣,國學的特殊地位就被突出起來。
與中國相比較,日本與中國皇帝(天皇)處境不同。中國自湯武革命以降,皇帝無道,可以通過“革命”驅逐下臺,從而皇運隆替,新朝開啟。日本不然,天皇“萬世一系”,推崇天皇是日本必須遵守的政治準則。這樣日本不僅要有理學來管理人民的思想,還要有一個學問來確立天皇無可侵犯的至尊地位,認定天皇神圣轉世的天道神統,編制天皇至高無上的秩序法則。這些理學做不到,國學的誕生與興隆就成了題中應有之義。理學的本質是“心靈學”,國學名稱的出現不僅是為了區別于“漢學”與“中華學”。從內涵意義理解還因為它是“國體學”與“國家政治學”。
確實,日本近世以來最大的學術為儒學與國學,兩學并存,為日本封建統治的穩定發揮了無可替代的作用,松本三之介雙管齊下,對理學與國學做并列的批判,可以說是揭示了日本封建政治的本質要害。
三、與丸山學術的關系
《國學政治思想的研究——近代日本政治思想史敘說》共分三章:第一章、國學政治思想理解的前提。第二章、國學政治思想的性質與課題。第三章、幕末國學思想。作者寫作本書的一個重要指導思想,是要通過對國學的研究尋找日本政治思想特質,及其形成的原因。應該承認,無論古代與近現代,一國歷史事件的發生與展開都與該國政治思想有著密切的聯系。日本也不例外,因此要對日本歷史特質有所了解,就要對日本政治思想特質有所了解。而在松本看來,要了解日本政治思想的特質,必須追根求源地對日本政治思想形成的特殊前提與原因作認真研究。自然,這樣的原因與前提可以從日本的社會中去尋找,然而也可以從相關的日本傳統思想境界中去尋找,松本所做的工作是跋涉日本國學的精神原野,探尋本國政治思想的意識源頭,換言之,由觀察日本國學的思想特質性,管窺日本廣義政治思想史的特殊存在。松本的國學研究就是在這樣的思想前提下進行的。
松本從事國學研究之前,學界已經有了不少國學研究的成果。這包括:明治30 年的中野虎山的《國學三遷史》、芳賀矢一的《國文學十講》(明治32年)與《國學史概論》(明治33年)、村岡典嗣博士的《本居宣長》(明治44年初版、昭和3年增補改訂)等。如果說以上的研究僅局限在資料建設方面,津田左右吉博士的《文學中的我國國民思想的研究》(大正5——10年)則指示了研究的新動向:注目國學與國民思想及社會狀況的互動關系。 這給松本留下很深刻的印象, 并啟發他將這項工作繼續開展下去。
可以說,松本在本書中所作的努力,就是實踐志愿,將國學研究與社會政治學研究結合起來,開拓日本政治思想史學研究的新視角,獲得新發現。其實,受到津田左右吉影響的不僅是松本先生。家永三郎在回憶自己的思想形成過程時也說,年輕時對自己影響最大的是津田左右吉,從他對《記》、《紀》的批判與思想史的研究中獲益非淺。特別是在畢業后讀到他的 《文學中的我國國民思想的研究》,受到的思想沖擊更為筆墨所難以形容,“由此世界的景色為此一變”。 松本的研究還與丸山真男有著密切的關系。《序言》說:自己剛開始從事國學研究的時候,還是一個研究生,論文都是在丸山真男的指導下寫作的,時間是昭和23年(1948年)及以后的2 年。他對丸山真男教授表示特別的感謝:如果沒有丸山的指導啟發,論文難以完成,觀點上的曖昧也無法克服。 松本研究與丸山真男所做的工作有著許多內在聯系,都注重運用“以思想證思想”的方法,通過對日本儒學、神道、國學等思想史的研究,做日本思想探源的工作,以尋找日本政治思想的精神源頭。丸山真男刊《日本政治思想史研究》(1952年),松本則有《國學政治思想史的研究》。相近的書題,說明相近的研究志趣與問題意識,也說明他們在學術界的師承關系。《序言》他還對遠山茂樹等學者表示謝意。因遠山茂樹的介紹認識國學研究家伊東多三郎,受到多方面教誨;又因東京大學法學部明治報章雜志文庫的幫助,有機會查閱資料,看到許多明治初年的報紙。 在研究中我們發現,丸山真男的國學、理學比較論與松本三之介發生了共鳴。丸山說:勃興期的國學,總是作為“儒學者的對立者”來確定自己的地位特征。也就是這樣的原因,它竭力否定儒學對國學體系形成的影響。國學自稱是“古學”,因此它也必然要否定自己是“來源于儒學的古學派”。國學家總是強調如何與“儒家的古學派”沒有聯系,與此同時,對儒學思想展開批判,以期從積極意義上與儒學劃清界限,進而提高自己的地位。 松本在他著作中也同樣表達了這樣的觀點。
丸山真男于1952年出版《日本政治思想史研究》,該書所討論的主題是日本江戶時代在儒學乃至國學的思維結構中,隨著歷史的推移,近代意識如何突破前近代框架而“從內部”成熟。丸山認為所回答的問題,不是分散片斷的“近代性”,而是在思想系統之中前后相續的近代意識的成長。丸山真男的視線從日本朱子學到徂徠學再到本居宣長的國學,試圖在這些通常被視為兩極對立的思想家中尋找逐漸成長、變形但又具有內在聯系的近代思想因素。 他從傳統思想內部尋找既有的現代性成分,對世俗的“西方(歐洲)中心說”有所突破,從而顯示他的思想存在。20世紀中葉之后,東亞的各國都在重新思考與確認現代化的思路,而丸山學術的價值就在于為這樣的“思考”與“確認”,提供建設性意見。松本承認自己是丸山的學生,他從事國學政治思想的研究,選從國學一門進入,窺探日本“前現代”學術原野中的“現代”根芽,取得了豐碩的學術成果。
研究松本與丸山的關系可以說明:戰后確有一個最重要的史學團體結集成陣,他們運用思想史學的批判武器,揭發明治以來日本專制主義的傳統文化根源,做了大量有益的工作。
余言:從國學到國粹學的思考
從松本對國學的研究使我們想到與國學有關系的日本國粹學說在現代的命運。當國學熱潮過后,日本在19 世紀末又出現國粹主義思潮。國粹學者考量的最大問題,乃是如何認識本國文化,導引國人尊敬民族傳統,激發愛國熱情。從這個意義上說,國學與國粹學在具有相近似的存在價值。與國學思想相同,國粹主義也是日本民族主義在文化觀上的折射。
凡一個后進民族(筆者給予密切關心的是東亞諸民族)走向現代化,必須有民族主義與國際主義的雙重關懷。現代化思想無非是民族主義與國際主義的合理配伍。從文化視角看問題,一個國家民族主義“過量”,很可能走上狹隘“自戀”,拒絕開放學習的道路;反之將國際主義做不恰當的理解,又常使一個民族盲目虛無,全盤歐化(西化)。從這個意義上說,19世紀日本國粹主義思潮曾是克服“全盤歐化”思想的良藥。然而,國粹主義發展到后來,出現與國際主義相違的傾向,導致日本產生狹隘民族主義。而狹隘民族主義勃興又必然導致國內“超國家主義”與“絕對主義”等專制思潮泛濫與對外擴張欲念的膨脹。這一切都值得人們去深思回味。時代在進步著,然而許多歷史課題,既促使19世紀的知識分子做出必要的回應,也同樣困擾當代的人們。這使得人們不得不思考,有些看來是“歷史的”提問,是否竟是“永恒的”課題。
橋川文三在《昭和超國家主義的諸相》一文表達以下的觀點:日本近代史上象德國與意大利那樣明顯的“法西斯運動”是沒有的,也可以說日本的超國家主義是漸進式的發生的,因此要找到一個日本超國家主義誕生的契機式的標志很困難。他說在這個方面丸山真男有很好的說法: 對于日本來說在什么時候,突然發生了超國家主義是說不上來的。日本的法西斯主義有著漸進式的特點,它的形成與前代傳統有著極大的聯系。
還是這位橋川文三先生要我們去注意丸山真男的一篇文章即《超國家主義的論理與心理》。因為在這篇文章中,丸山明確的說:要高度注意日本超國家主義與傳統關系的問題,當對這個問題要做最認真的分析。
松本三之介的研究成果發表于上世紀中葉,當時大戰結束,作為戰敗國的日本,西方思想一時又成為蔓延日本的精神主潮。松本注目本國傳統的挖掘與梳理,給予必要的評判,對避免可能出現的新時期的又一輪民族虛無主義的發生,有其歷史效果。而更重要的是,書中論述儒學與國學的思想特征,對日本專制思想本原鞭辟入里,注意到日本超國家主義“與前代傳統有著極大的聯系”,回應了“傳統究竟給亞洲的政治帶來了什么”這個極重要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