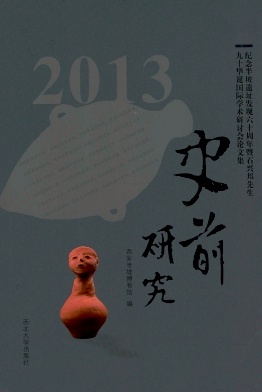《周易》古經與墨家思想
佚名
摘要:諸子之學皆源于《易》。就墨家而言,其思想的基本特征為:貴節非樂,貴兼泛愛,尚用尚齊,興利節用,尚力自苦,尚賢尚同,右鬼薄葬,非禮非命。以此為參照,考諸《易經》,不難發現,墨家思想的許多方面,如尚節、尚力、尚用、興利等,皆可在《易經》中見其端緒。
關鍵詞:易經;墨家,尚節;尚力;尚用;興利
Abstract: All of the learning of different schools of thought in the Pre-qin dynasties originated from Yi. The thought of the school of MO characterized with upholding frugality and resisting rites & music; advocating pan-love, utility, laboring, self-hardship, sages, ghosts, thrifty funeral, and promoting what is beneficial; resisting rituals and not believing fate and destiny. Basing on this, it is not difficult to discover that many aspects, such as advocating frugality, laboring, utility and promoting what is beneficial, of the thoughts of the MO school originated from I Ching.
Key words: I Ching; MO school; advocating frugality, laboring, utility and what is beneficial
臺灣學者陳立夫先生提出,儒家思想來自《周易》,道家思想來自《歸藏易》,墨家思想來自《連山易》。(見陳立夫主編《易學應用之研究》第1輯,臺灣中華書局)程迥提出:“《連山》、《歸藏》宜與《周易》數同而其辭異。”(朱彝尊《經義考》卷二.易一)這話恐有一定道理。既然同稱為《易》,三者在一些基本點必定是相同的,卦象應是三易能夠對話的橋梁。因此,我們認為,墨家和儒家、道家一樣,也同《周易》有密切的淵源關系。本文將從象數與義理兩個方面具體討論《周易古經》與墨家思想的關系。為了討論的方便,首先請允許我們從墨家思想的基本特征談起。
一、墨家思想的基本特征
1.《莊子.天下篇》論墨家
《莊子.天下篇》把墨家列為首家。其云:“不侈于后世,不靡于萬物,不暉于數度。以繩墨自矯,而備世之急。古之道術有在于是者,墨翟、禽滑肔聞其風而悅之。為之,大過;已之,大循。作為《非樂》,命之曰《節用》;生不歌,死無服。墨子泛愛兼利而非斗,其道不怒,又好學而博,不異,不與先王同,毀古之禮樂。……古之喪禮,貴賤有儀,上下有等。天子棺鑡七重,諸侯五重,大夫三重,士再重。今墨子獨生不歌,死不服,桐棺三寸而無鑡,以為法式。以此教人,恐不愛人;以此自行,固不愛己,未敗墨子道。雖然,歌而非歌,哭而非哭,樂而非樂,是果類乎?其生也勤,其死也薄,其道大觳。使人憂,使人悲,其行難為也,恐不可以為圣人之道,反天下之心,天下不堪。墨子雖獨能任,奈天下何?離于天下,其去于王也遠矣。”“禹,大圣也,而形勞天下也如此。使后世之墨者,……日夜不休,以自苦為極。曰:不能如此,非禹之道也,不足謂墨。”
綜《莊子.天下篇》所述,墨家思想有如下5個特點:(1)節用;(2)非樂;(3)泛愛兼利;(4)不異(尚同);(5)自苦。
2.《尸子.廣澤篇》論墨家
《尸子.廣澤篇》把墨子思想的特點簡要地概括為“貴兼”。其云:“墨子貴兼,孔子貴公。”梁任公解釋這句話時說:“墨子貴兼者,墨子主兼愛,常以兼易別。故墨子自稱曰:兼士。其非墨家者,則稱之曰:別士。”(見王蘧常《諸子學派要詮》第65頁,中華書局、上海書店聯合出版,1987年版)。
兼愛應該是墨家思想的一個重要特征。孟子在批評墨子和楊朱時說:“楊朱為我是無君也,墨氏兼愛是無父也。無父無君,是禽獸也。”也是把兼愛作墨家思想的特征,予以鞭撻。同時,兼愛也是與尚同(無異)緊密聯系在一起的一個思想特征,尚同是兼愛的理論基礎,兼愛是尚同(無異)在社會倫理領域中的具體表現。
3.《荀子.非十二子》論墨家
《荀子.非十二子》批評墨家時說:“不知壹天下、建國家之權稱,上功用,大儉約而鑢差等。曾不足以容辨異,縣君臣。然而其持之有故,其言之成理,足以欺惑愚眾,是墨翟、宋鑣也。”
根據以上所論,墨家思想特點又可概括為如下幾個方面:(1)上(尚)功用;(2)大(尚)儉節;(3)鑢(無)差等。
4.《荀子.天論》與《荀子.解蔽》論墨家
《荀子》之《天論》與《解蔽》把墨家思想概括為兩個特點:一是“有見于齊而無見于畸”;二是“蔽于用而不知文”。《天論》篇對第一個特點的評價是:“有齊而無畸,則政令不施。”《解蔽》對第二個特點的評價是:“由用謂之道,盡利矣。”事實上,《荀子.天論》所概括的墨子思想的第一個特征也就是《天下篇》的“不異”和《非十二子篇》的“鑢差等”;《解蔽篇》所概括的墨子思想的第二個特征也就是《非十二子篇》提出的“尚功用。”與前者不同的是,荀子在這里論述了“齊”與“用”的消極意義,認為“齊”的消極后果是“政令不施”,因為政治法律制度設置的初衷就是治理各種有差別的現象,如果像墨家那樣“尚同”、“兼愛”,那么,政治、法律制度就失去了實施的對象,因而也就沒有存在的必要了。“用”的消極意義在于“不知文”,在于“盡利矣”,也就是說只講狹隘的實利與功用,而不知文飾與形式之功用,只講物質之功用,而不知精神之功用。故梁啟超稱荀子對墨子“蔽于用而不知文”這一評價,“極得墨子之癥結”。
5.《呂氏春秋.不二篇》論墨家
《呂氏春秋.不二篇》曰:“聽群眾人議以治國,國危無日矣。何以知其然也?老聃貴柔,孔子貴仁,墨子貴廉。”
孫詒讓曰:“廉,疑即兼之借字。”(孫詒讓《墨子間詁》引《呂氏春秋》)。梁啟超先生則認為,廉是兼的刨字。(梁啟超《尸子澤篇呂氏春秋不二篇合釋》)因此,《呂氏春秋.不二篇》把墨子的學派特點概括為貴兼,這與《莊子.天下篇》所概括的“泛愛”,《尸子.廣澤篇》概括的“貴兼”,其含義是完全一致的。
6.《韓非子.顯學篇》論墨家
《韓非子.顯學》論墨家曰:“世之顯學,儒墨也。儒之所至,孔丘也。墨之所至,墨翟也。自孔子之死也,有子張之儒,有子思之儒,有顏氏之儒,有孟氏之儒,有漆雕氏之儒,有仲良氏之儒,有孫氏之儒,有樂正氏之儒。自墨子之死也,有相里氏之墨,有相夫氏之墨,有鄧陵氏之墨。故孔墨之后,儒分為八,墨離為三。取舍相反不同,而皆自謂真孔墨。孔墨不可復生,將誰使定后世之學乎?孔子墨子俱道堯舜,而取舍不同,皆自謂真堯舜。堯舜不復生,將誰使定儒墨之誠乎!……墨者之葬也,冬日冬服,夏日夏服,桐棺三寸,服喪三月。世主以為儉而禮之。儒者破家而葬,服喪三年,大毀扶杖,世主以為孝而禮之。夫是墨子之儉,將非孔子之侈也。是孔子之孝,將非墨子之戾也。今孝戾侈儉,俱在儒墨,而上兼禮之。”
由上所論可見,在戰國時期墨家已分為三,儒則已分為八,三家墨學,雖取舍不同,但從《顯學篇》的記載來看,墨家思想的特點可概括為:(1)節儉;(2)節葬。
7.《淮南子.要略篇》論墨家
《淮南子.要略篇》云:“墨子學儒者之業,受孔子之術,以為其禮煩擾而不說,厚葬靡財而貧民,服傷生而害事。故背周道而用夏政。禹之時,天下大水,禹身執鑥垂,以為民先。剔河而道九歧,鑿江而通九路,僻五湖而定東海。當此之時,燒不暇鑦,濡不給鑧。死陵者葬陵,死澤者葬澤。故節財、薄葬、閑服生焉。”
根據以上所述,墨家思想特征應概括為:(1)節財;(2)薄葬;(3)興民利。
8.《史記.太史公自序》論墨家
《史記.太史公自序》載司馬談《論六家要指》認為,“墨者儉而難遵,是以其事不可鑩循,然其強本節用,不可廢也。”“墨者亦尚堯舜道,言其德行曰:‘堂高三尺,土階三等,茅茨不翦,采椽不刮。食土簋,啜土刑,糲糧之食,藜藿之羹。夏日葛衣,冬日鹿裘。’其送死,桐棺三寸,舉音不盡其哀。教喪禮,必以此為萬民之率。使天下法若此,則尊卑無別也。夫世異時移,事業不必同,故曰:‘儉而難遵。’要曰:強本節用,則人給家足之道也。此墨子之所長,雖百家弗能廢也。”
可見,司馬談認為墨家思想之長是:(1)強本節用;(2)人給家足。其不足則是:尊卑無別(尚同)。
9.《漢書.藝文志》論墨家
《漢書.藝文志》曰:“墨家者流,蓋出于清廟之守。茅屋采椽,是以貴儉;養三老五更,是以兼愛;選士大射,是以上賢;宗祀嚴父,是以右鬼;順四時而行,是以非命;以孝視天下,是以上同。此其所長也。及蔽者為之,見儉之利,因以非禮;推兼愛之意,而不知別親疏。
可見,班固認為,墨家思想的優點在于:(1)貴儉;(2)兼愛;(3)上賢;(4)右鬼;(5)非命;(6)上同。其不足則為:(1)非禮;(2)不別親疏。
至此,我們可以依據上述九家對墨家思想的概括,給墨家畫出一個較為完整的輪廓:“節用”、“非樂”、“泛愛兼利”、“不異”、“自苦”(《莊子.天下篇》)、貴兼(《尸子.廣澤篇》)、“上功用”、“大儉節”、“鑢差等”(《荀子.非十二子》),“有見于齊而無見于畸”《荀子.天論》、“蔽于用而不知文”(《荀子.解蔽》)、貴廉(《呂氏春秋.不二篇》)、“節儉”、“節葬”(《韓非子.顯學》)、“興民利”、“節財”、“薄葬”(《淮南子.要略》)、“強本節用”、“人給家足”(《史記.太史公自序》)、“貴儉”、“兼愛”、“上賢”、“右鬼”、“非命”、“上同”、“非禮”、“不別親疏”(《漢書.藝文志》)。如果去掉了一些重復性的概括,對墨家思想的基本特征,可作如下概括:
(1)貴節非樂;(2)貴兼泛愛;(3)尚用尚齊;(4)興利節用;(5)尚力自苦;(6)尚賢尚同;(7)右鬼薄葬;(8)非禮非命。
以上八點作為參照,去檢查《易經》,我們發現上述思想中的許多內容,都可以在《易經》中找到蛛絲馬跡,尤其是尚節、尚力、尚用、興利等,在《易經》中皆可見其端緒。
二、《節》卦與墨家的尚節思想
我們認為,《節》是墨家節儉、節用、節財思想的最早淵頭,這一點,無論從卦辭,還是爻辭上都可得到說明。
就卦象來看,《節》卦為下兌上坎。兌為澤,坎為水。水入澤中,澤滿則溢,故應予以節制。孔穎達曰:“節者,制度之名。節止以義,制事以節,其道乃亨,故曰節亨。”(孔穎達《周易正義.亨》)《程氏易傳》云:“事既有節,則能致亨通,故節有亨義。”朱熹《周易本義》則云:“節,有限而止也。為卦下兌上坎,澤上有水,其容有限,故為節。”因此,“節”在《易經》中,不僅僅是一種節儉之德,也是一種社會制度和規范,還是一種體現宇宙天地變化的原理和法則。
同時,《節》之內卦兌為一陰二陽,上坎二陰一陽,故為三陰三陽卦。按照朱熹的說法,“凡三陰三陽之卦各二十,皆自《泰》、《否》而來”(朱熹《周易本義.卦變圖》)。故《節》當自《泰》來。虞翻曰:“《泰》三之五,天地交也。五‘當位以節,中正以通’,故‘節亨’也。”(李鼎祚《周易集解.節》)。意謂《泰》卦下乾上坤,下乾的九三爻上升到上坤之中位,與其互易而成《節》卦。因《泰》卦乃“小往大來,吉,亨”之卦,且成《節》之后,《節》之內卦兌外卦坎皆為剛柔得中,故節有亨通之義。
正因為節有亨通之義,因此,《彖傳》贊美“節”曰:“天地節而四時成,節以制度,不傷財,不害民。”天地宇宙因為有了節,才使得四季井然有序,生生不已。圣人效法天地之節德,建立制度以規范人們的言行,如此則不傷財,不害民。相反,如果不按照“節”的規范和要求去做事,甚至以節為苦,肯定是不行的。節作為一種美德、制度、規范和原理,其本質含義就是守持正固。正是在此意義上,卦辭說:“苦節,不可。貞。”
因此,單是從卦辭上就不難看出,在《易經》中,節無論是作為一種道德規范,還是作為一種社會制度,還是作為天地宇宙的原理法則,同后來墨家所講的“節用”、“節葬”、“節財”、“利民”思想都是相貫通的。這一點從《節》卦的爻辭中,亦可得到驗證。
初九爻曰:“不出戶庭,無咎。”《象傳》釋此爻曰:“不出戶庭,知通塞也。”《一切經音義》云:“在于堂屋曰戶。”戶庭,應為堂屋之庭,朱熹解為“戶外之庭”(朱熹《周易本義.節》),似不妥。此爻處《節》卦之始,上應六四之險。若前行,則受九二之阻塞,故宜節制慎守,不應盲目外行。如此,則無咎。尚秉和先生說:“二陽為阻,故不宜出;不出則無咎。《象》曰:知通塞,言二阻塞也。”(《周易尚氏學.節》)因此,從爻象上看,此爻意在告誡人們在做事情時,一開始就應當謹言慎行,節制自己, 見通則行,見阻則止。
金人王申子在解釋《節》之初爻時說:“陽剛在下,居得其正。當《節》之初,知其時未可行,故謹言謹行。至于不出戶外之庭,是知節而能止者,故無咎。”明人徐在漢曰:“坎變下一畫為兌,象止坎下流。戶以節人之出入,澤以節水之出入。初:不出戶庭,以極其縝密為不出,此其所以無咎。”(李光地《周易折中.節》)。
從以上所釋,可以看出,在初九爻中,“節”不僅是一種人倫道德,而且也是一種社會制度,也是一種自然之理。把這一原理落實到人,就是要求人們做任何事情,一開始就有節有度,謹言慎行,進退有止。
九二爻曰:“不出門庭,兇。”初九爻說:“不出戶庭,無咎”,但到了九二爻則成了“不出門庭,兇。”一為無咎,一為兇,似于理不通。從位置上看,門庭是大門庭院,戶庭為堂屋之庭。為什么在戶庭內就無咎,在門庭內就兇,僅從義理上難以說清,因而,關于這一爻之解釋只能求諸象數,尚秉和先生說:“二比重陰,陽遇陰則通。通則利往。乃竟不出,是失時也。故兇。”其義大致是說九二陽剛居于陰位,有過于節制之象,又因其得中,有中正之德,因而具備了外出的能力。加之又有二陰在前,陽遇陰則通,但九二仍存失正無應之憂,知通不行,可謂大失其時。正如清人李光地所說:“時應塞而塞,則為慎密不出,雖足不窺戶,可也。時不應塞而塞,則為絕物自廢。”(李光地《周易折中.節》)。《象傳》云:“不出門庭,失時極也。”說的也是這一意思。
二程認為,九二爻“處陰居兌而承柔。處陰,不正也。居說(兌),失剛也。承柔,近邪也。”(《程氏易傳.節》)。節之為道,當剛而中正,如九五爻以陽剛居外卦之中位。九二失剛不正,畏首畏尾,不愿外出從于五,懦弱茍且,乃“節”之末流,屬不正之節,其兇可知。可見,程說也是認為九二之兇,在于其過于節制。
可見,“節”原本是好事,但任何事物的存在,任何原理的應用都有一定的條件和范圍,當節時,自然要節;若阻塞已除,當進之時而又拘于節制,必然會坐失良機。
六三爻曰:“不節若,則嗟若。無咎”。該爻處于《節》之下卦兌的上位,故有“水溢澤上”之象。以此喻人耽于驕侈,不知節儉,以致窮困。但如果能傷嗟悔過,猶可無咎。
清人李道平根據虞翻的說法,從象數的角度加以詮釋。他認為,六三爻原本《泰》 之內卦乾 的上爻,由于六三失位不正,故當節當變(李道平《周易集解纂疏.節》)。如果不變不節,終當嗟若。如果變而之正,則與上坎體成坎離 。又坎為水,離為目,坎水流出離目,故為“嗟若”。因此六三失位,本當有咎。但如果能夠心嗟自悔,改過從正,自當無咎。
二程曰:“六三不中正,乘剛而臨險,固宜有咎。然柔順而和悅,若能自節而順于義,則可以無過。”(《程氏易傳.節》)。明人豐寅初也認為,六三爻“處兌之極,水溢澤上,說于驕侈,不知謹節,以致窮困。然其心痛悔,形于悲歡,能悔則有改過之幾,是猶可以無咎也。”(李光地《周易折中.節》)
可見,六三爻教人遵守節道,是從正反兩個方面來說的,節則無咎,不節則嗟。這同《臨》卦之六三爻頗為相類,《臨》六三爻亦為以陰居陽,喪失臨道,故其爻辭為:“甘臨,無攸利。既憂之,無咎。”可見,《臨》之六三雖失臨道,但既知而憂之,故云:“無咎”。《節》之六三因失節道,嗟而自悔,亦得無咎,因此,此爻立象之另一要義在于教人恪守節道,棄過從善。
六四爻曰:“安節,亨。”《象傳》釋此爻曰:“安節之亨,承上道也。”安節,乃安于節儉之意。謂人若能安于節儉,就會亨通順利。何以如此呢?從爻辭生成的角度說,這是對古人生活經驗的總結,但從爻象上看,六四爻以陰居陰,柔順得上,在其上方又承接九五君道,因而,便可做到順應自然而節制。正如元人俞琰所說,“六三失位而處兌澤之極,是乃溢而不節。六四當位而順承九五之君,故為安節”(李光地《周易折中.節》)。
二程也是從卦象的角度對此爻予以闡釋,其曰:“四順承九五剛正之道,是以中正為節也。以陰居陰,安于正也,當位為有節之象,下應于初,四坎體水也。水上溢為無節,就下有節也。如四之義,非強節之,安于節者也,故能致亨。節以安為善,強守而不安則不能常,豈能亨也?”(《程氏易傳.節》)
顯然,《易經》作者認為,水盈溢出,乃過而無節;水就下處低,乃安而有節。六四爻居《節》之外卦坎之下位,其立象旨在彰明水之下流,以喻人之安于節儉。同時,六四爻以柔處柔,其立象則旨在說明處下之水有平地安瀾之象。
因此,無論從義理,還是從象數上看,六四爻都告誡人們,節儉自制乃自然之理,人應順而從之,心安理得地恪守節道。
九五爻曰:“甘節,吉,往有尚。”甘與苦相對。“甘節”,即有以節為甘之意,九五以陽居陽,又在上卦之中位,為一卦之主,這就如同君主以中正陽剛之德居于尊位,節己節人,使中正節道暢行天下,天下太平,百姓和美,以此前往,必受尊尚。故王弼《周易注》在解此爻時說:“當位居中,為節之主。不失其中,不傷財,不害民之謂也。為節而不苦,非甘而何?術斯以往,往有尚也。”
李道平從象數的角度解釋此爻,其云:“以九居五,九為得正,五為得中。《說文》:‘甘,美也。’坎美脊為美,故為甘節吉。二應五,自內曰往。二失正,變正,上應于五,‘尚’與‘上’同,故往有尚。”(李道平《周易集解纂疏.節》)意謂九五爻得中得正,坎有美象,甘即美也,故云甘節吉。五與二相應,但九二乃陽爻居陰,是為失位,失位不正,自當之正。九二爻主動自陽之正而成陰,亦有吉節之意。又九二之正成陰后與九五陽剛和諧相應,自然和美。由于這種變化是從下卦九二爻開始的,下卦為內,上卦為外。由下而上,由內而外,曰往;由上而下,由外而內,曰來。故爻辭又曰:“往有尚。”
綜上所述,九五爻的要義在于節道之踐履,首先統治者要求從自己做起,當位以節,中正以通,正己正人。如果統治者能安于節道,甘于躬行,天下百姓自然悅而從之。
上六爻曰:“苦節,貞兇。悔亡。”此爻既言“貞兇”,又言“悔亡”,注家有不同說法。唐孔穎達認為,“上六處《節》之極,過《節》之中,節不能甘,以至于苦,故曰苦節也。若以苦節施人,則是正道之兇。若以苦節修身,則儉約無妄,可得亡悔。”(孔穎達《周易正義.節》)意謂上六之兇乃源于“苦節施人”,上六爻之“亡悔”則源于“苦節修身”。這是一種義理的闡釋,與《易經》作者之本義,似有些距離。《程氏易傳》則認為《節》卦之“悔亡”與他卦之“悔亡”“辭同而義異也”。悔,當為“損過從中之謂也”,即克服極端過中之節儉,返于中正之節道,則無苦節之兇。一句話,悔則兇無。事實上,程氏釋“悔”,只是把他卦之悔稍作引申,并未離“悔”意之大概。
結合卦象來看,該爻居于《節》卦的最上位,乃極端過中節儉之象,節而過中,必致其苦,故云“苦節”。同時,上六爻雖屬極端過中之節,但終究為節,所謂“禮與其奢也,寧儉。喪,與其易也,寧戚”,依此而言,雖有悔而終無。故宋人呂大臨曰:“上六居《節》之極,其節已甚,苦節者也。用過乎節,物所不堪,守是不變;物窮必乖,故曰:貞兇。禮奢寧儉,未害乎義,故曰:悔亡。”明人來知德則說:“無甘節之吉,故貞兇。無不節之嗟,故悔亡。”(李光地《周易折中.節》)其義與呂氏之說相類。
因此,《節》上六爻的基本含義應為:極端過中的節制,必致其苦,必致其兇。但若悔而能改,使“節”返于中正之道,自然兇無。因此,任何事情都存在一個度的問題。節原本是好事,但如果矯枉過正,做過了頭,就會違反常理,阻塞不通,從而致兇。這是《易經》作者的辯證法思想在節道中的體現。
至此,我們可以看到,節道在《節》的卦辭和爻辭中,首先是一種道德,然后才是一種規范和制度,最后,它還是物質世界的運動變化規律。節道要求人們,在一開始就應謹言慎行,中正守己,見通則行,見塞則止(初九爻);但節道正如其他原理法則一樣,亦有其特定的適應范圍和適應條件,阻塞不通時,自然須節;但若阻塞已除仍拘于節,則難免因坐失良機而致兇(九二爻);因此,節道是每個人都應遵守的原理法則,若違背了節道,其結果必定是窮困傷嗟;若遵循了節道,自然安而無咎(六三爻);節道乃自然之理,人應心甘情愿地順從于它,人之安于節道,猶水之處下而有平地安瀾之象(六四爻);節道既是自然之理和社會規范,這就是要求統治者必須首先從自己做起,節己始能節人,正己始能正人,以此而治于天下,天下百姓自然悅而從之(九五爻);正如任何事物都有自己的反面一樣,節道如果超出了自己所能夠容納的條件和范圍,也會因走向其反面而致兇,這就要求人們在踐履節道時,時刻以得正守中為原則,因為“得正”、“守中”是節道的兩個基本要素,從《節》卦六爻來看,凡得位得中者皆吉而無咎;凡失位不正者,皆兇而有咎,二、三、上三爻要么失正要么失中,故不咎則兇。一、四、五三爻皆得正之爻,故吉而無咎。而其中的九五既得正而又得中,故明人來知德稱此爻為“節之盡善盡美”,以此為規范,“立法于今,而可以垂范于后也。”(《來氏易注》)正如宋人邱富國所說:“《節》之六爻,以當位為善,不當位為不善。若以兩爻相比者觀之,則又各相比而相反。初與二比,初不出戶庭則無咎,二不出門庭則兇,二反乎初者也。三與四比,四柔得正則為安節,三柔不正則為不節,三反乎四者也。五與上比,五得中則為節之甘,上過中則為節之苦,上反乎五者也。”(李光地《周易折中.節》)
總之,《易經》作者所闡述的節道具有普遍性的哲學意義,它廣泛地存在于自然現象和社會現象之中,“季節的推移,動植物的蕃衍,人類喜怒哀樂的情狀,衣食住行的處置,均與‘節制’有關。”(黃壽祺張善文《周易譯注》,第493頁,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5月第1版)后來墨家講節用、節財、節葬、節儉,其思想淵頭當在于此。
三、《頤》卦與墨家的尚力和“興天下利”的思想
“尚力”是墨家思想的一個重要特征。盡管這一特征被《莊子.天下篇》、《荀子》、《韓非子》、《呂氏春秋.不二》、《淮南子.要略》、《漢書.藝文志》、《論六家要指》等忽略,但是,從《墨子》書的《非命》、《非樂》等篇來看,其“強力而為”的思想特征是十分明顯的。
頤,乃頤養之義,乃口中含物之象。《序卦傳》曰:“物畜然后可養,故受之以頤。頤者,養也。”因此,從字義上看,頤卦講的是與人的生存之道息息相關的養生問題,即關于如何獲取生活資料和獲取生活資料的原則的問題。
從卦象上看,《頤》 ,上為艮,下為震 。艮為止,震為動。上止而下動,猶口之嚼物以養人。故名為頤。鄭玄解釋卦辭說:“震動于下,艮止于上。口車動而上,因輔嚼物以養人,故謂之頤。頤,養也,能行養則其于事,故吉矣。二五離爻皆得中。離為目,觀象也。觀頤,觀其養賢與不肖也。頤中有物曰口實。自二至五有二坤,坤載養物,而人所養之物皆存焉。觀其可食之物,則貪廉之情可別矣”。(《周易集解.頤》)《頤》下震上艮,有動止嚼物和口中含物之象。自六二爻到六五爻四畫連互,可得二坤。坤為地,《說卦》云:“坤者,地也,萬物皆致養焉。”可見,從卦象上看,《頤》卦講的是人應如何養生的問題,也就是生活資料的索取方式問題。卦辭認為無論是自養還是養人,皆須守持正固,才能吉祥。
朱熹說:“養須是正則吉。觀頤,是觀其養德正不正。自求口實,是觀其養身正不正,未說到養人處。”(《朱子語類.頤》)應該說,朱子把卦辭概括為養德與養身兩個方面,是頗有道理的。但,他又說:“未說到養人處,”似不妥,事實上,《頤》卦中所講的頤道既包括養德、養身,也包括養人,還包括養于人。正如《程氏易傳》所說,“頤之道,以正則吉也。人之養身、養德、養人、養于人,皆以正道則吉也。天地造化,養育萬物,各得其宜者,亦正而已矣。”
以正道養人的本質,就是自求口實,自力更生。這同墨家所講的“賴其力則生,不賴其力則不生”(《墨子.非樂上》)的思想是完全一致的,也同墨家所倡導的“強必治,不強必亂;強必寧,不強必危”、“強必貴,不強必賤;強必榮,不強必辱”、“強必富,不強必貧;強必飽,不強必饑”(《墨子.非命下》)的思想相貫通。
從《頤》卦六爻的爻辭中,我們也可以看到《易經》作者所倡導的強力思想同后來墨家強力而為思想的淵源關系。
初九爻曰:“舍爾靈龜,觀我朵頤,兇。”從字義上看,此爻的基本含義是舍棄你珍貴的靈龜,卻來觀看我垂腮進食,只知羨慕我口中的食物,不知求食以自養故兇險。
虞翻從象數學的角度解釋此爻,也頗值得我們玩味。他說:“《晉》離為龜。四之初,故舍爾靈龜。坤為我,震為動。謂四失離入坤,遠應多懼,故兇矣。”(李鼎祚《周易集解.頤》)意謂《頤》卦乃《晉》卦的九四爻下降至初爻而成,《晉》 之上卦為離,下卦為坤。《說卦傳》云:“《離》為龜。”《坤》為身,為我。《離》之下爻跑到《坤》之下爻,乃舍離入坤,坤變為震,是為舍爾靈龜。震為動,故為觀我朵頤。這里,虞翻釋“爾”為四爻,“我”為初爻。即舍爾離龜之美質,羨我坤之朵頤。
但是,王弼、宋儒對此爻的解釋,與虞氏相比,其旨雖同,其辭則異。由于《頤》卦之上爻與初爻為兩陽爻,中間為四陰爻,本末剛,中間柔,猶龜之外剛而內柔,故《頤》卦取象于《離》龜。二程認為,“爾”為初九爻,“我”為六四爻。故此爻的基本含義為初九爻“以陽居動體,而在頤之時。求頤,人所欲也。上應于四,不能自守,志在上行,說所欲而朵頤者也。心既動,則其自失必矣。迷欲而失己,以陽而從陰,則何所不至?是以兇也。”(《程氏易傳.頤》)可見,在程氏看來,初九爻以陽居下,完全可以自養,但他貪求于六四,是以陽剛之實而求養于陰虛,故失養之正道。正如蘇軾所說:“養人者,陽也。養于人者,陰也。君子在上足以養人,在下足以自養。初九以一陽而伏于四陰之下,其德足以自養,而無待于物者,如龜也。不能守之而觀于四,見其可欲,朵頤而慕之,為陰之所致也,故兇。”(李光地《周易折中.頤》)
由此,我們不難看出,初九之兇在于他不知自養而求養于人。正如王弼所說:“以陽處下,而為動始,不能令物由己養,動而求養者也。夫安身莫若不競,修己莫若自保,守道則福至,求祿則辱來。居養賢之世,不能貞其所履以全其德,而舍其靈龜之明兆,羨我朵頤而躁求,離其致養之正道,窺我寵祿而競進,兇莫甚焉。”(王弼《周易注》)
李光地《周易折中》引吳澄曰:“自養于內者莫如龜,求養于外者莫如虎”,初九爻舍棄了“靈龜”,也就意味著它舍棄了自養之道。因此,《頤》卦初九爻意在告誡人們應當依靠自己的智慧和才能去創造,自養其身,自養其心,無待于人,無待于物。與其臨淵羨魚,勿寧退而結網。《易經》作者所倡導的這種自力自食的觀念,同墨家思想是完全一致的。
六二爻曰:“顛頤,拂經。于丘頤,征兇。”六二爻以陰居陰,是為得正;又為下卦之中位,是為得中。得正得中,又怎么會“征兇”呢?《程氏易傳》解釋說:“時然也。”所謂“時然”,是說六二陰柔雖居中得正,然不足以自養,故返下求養于居于其下的初九,是為顛倒常理,故云:“顛頤,拂經。”顛,即顛倒。經,即常也。六二爻與六五同為陰爻,無法應和,就只好下求于陽剛之初九,這自然與頤道相違,亦與常理(經)相悖,也就是爻辭中所說的“顛頤”、“拂經”。
既然下求違反了頤道,又悖于常理,六二爻就只好求養于上。即“于丘頤”。這里的“丘”應指上九。因六二之上,只有上九為陽爻,故求養于上九。但從六二到上九,中有三陰相阻,可謂路途艱險,加之上九本身又不中無位,極不可靠,故六二若執意前行,結果注定兇險。故爻辭云:“于丘頤,征兇”。
由此可見,六二爻之兇險并不是因為自身的能力和素質不佳,而是因為違背常理,顛倒頤道,又盲目地求養于上,顛頤則失其養,妄求則獲兇。因此,六二爻旨在告誡人們求生存、求發展必須依靠自己的力量,遵循常理,切不可違背規律,喪失原則。《易經》作者的這一思想同墨家尚力思想也是相通的。
六三爻曰:“拂頤,貞兇。十年勿用。無攸利。”該爻以陰柔居陽剛之位,可謂不正不中,又居下卦震之最上位,震為動,震之三爻可謂動之極致。以此立象,說明六三爻無中正自養之德,為求養于上九而不擇手段,其不正當的謀生行為已至極致,嚴重違反了頤道。故其結果必定是兇險的。
二程以義理釋此爻,甚得其精義。其云:“頤之道唯正則吉。三以陰柔之質,而處不中正,又在動之極,是柔邪不正而動者也。其養如此,拂違于頤之正道,是以兇也。得頤之正,則所養皆吉。求養養人則合于義,自養則成其德。三乃拂違正道,故戒以十年勿用。十,數之終。謂終不可用,無所往而利也。”(《程氏易傳.頤》)可見,二程認為,六三之兇乃源自其不中不正,而又盲動妄求于上九。宋人鄭汝諧對此爻的解釋,大致與程氏同。其云:“三應于上,若得所養,而兇莫甚于三。蓋不中不正而居動之極,所以求養于人者,必無所不至,是謂拂于頤之正。兇之道也。‘十年勿用,無攸利’,戒之也。因其多欲妄動,示之以自返之理。作《易》之本意也。”(李光地《周易折中.頤》)鄭氏在這里明確告訴我們,六三之兇乃出自其不中不正之象,又居震之極位,茍且求養于上九,可謂大失頤道。由于該爻的特點是為了求養,不惜采用任何手段,可以說已經到了無所不用其極的程度。因此,鄭氏認為,爻辭中的“十年勿用,無攸利”,就是告誡人們若處在這一狀態時,應調整心態,靜意正心,安居不動。
可見,六三爻旨在告誡人們求養應有中正之德,應自養養人,而不應求養于人;應正心靜心,腳踏實地地努力,不應貪圖捷徑,不惜采取一切手段,妄求于人。因此,該爻之要旨還是告訴人們要依靠自己的主觀努力和正當的方法與渠道解決生養問題,而不是用不正當的手段求養于人。毫無疑問,這與墨子尚力思想具有密切的淵源關系。
六四爻曰:“顛頤,吉。虎視眈眈,其欲逐逐,無咎。”居上養下,是頤之正道;居上而求養于下,是顛倒了的頤道,謂之顛頤。六二爻講“顛頤”,該爻也講“顛頤”,但六二顛頤因拂經(悖于常理)而兇,該爻顛頤則吉,原因何在?蓋因六二爻居初九之上,而又反求于初九,因二與初是相乘而非相應,不相應而相求,自然背于常道(“拂經”)。六四則不然,四與初恰為相應,四居上以上應下,固然為顛頤,但由于其以貴下賤,乃有禮賢養民之德,故為吉也。
宋人游酢認為:“以上養下,頤之正也。若在上而反資養于下,則于頤為倒置矣。此二與四所以俱為顛頤也。然二之志在物,四之志在道。故四顛頤而吉,而二則征兇也。”(李光地《周易折中.頤》)所謂“二之志在物,四之志在道”,蓋因二與初同居下卦,當為百姓眾民,百姓眾民間的求養,自然為物。六四爻居于臣位,屬于統治者階層,統治者對被統治者的求養,應為德義。故《程氏易傳》曰:“自三以下,養口體者也。四以上,養德義者也。以君而資養于臣,以上位而賴養于下,皆養德也。”因此,上之求養于下,最根本的內容乃布施德義于四方,正如《象傳》所云:“顛頤之吉,上施光也。”所謂“上施光也”,即在上的統治者一方面顛倒向下求獲頤養,另一方面又遍施德義于民眾,以貴下賤,禮賢養民。從象數學的角度解釋說,《頤》卦乃《晉》之九四爻下降至初位而成,《晉》之外卦為離為火,《晉》之內卦為坤為民,離火下降,光照萬民,猶君主遍施德義于四海,故《象傳》認為,六四之吉,是由于“上施光也”。但六四爻既以貴下賤,就須專心向下,猶虎視之眈眈;同時,還應不斷追求,不可松懈或終止。只有如此,才能不致有什么咎難。所謂“虎視眈眈,其欲逐逐,無咎”,說的正是這一意思。元人吳澄說:“自養于內者莫如龜,求養于外者莫如虎,故《頤》之初九、六四取二物為象。四之于初,其下賢求益之心,必為虎之視下求食而后可。其視下也,專一而不他;其欲食也,繼續而不歇。如是,則于人不貳,于己不自足,乃得居上求下之道。”(同上)明人林希元說得更為直截了當:“茍下賢之心不專,則賢者不樂告以善道;求益之心不繼,則才有所得而遽自足。”(同上)
因此,六四爻旨在告訴統治者向老百姓求取頤養的關鍵是廣施德義,禮賢下士之心要恒定專一;求下以養人,應汲汲不斷,如是方能養人而不窮,自養而無咎。
六五爻曰:“拂經,居貞吉,不可涉大川。”該爻處于《頤》卦之君位,以陰柔之質居九五陽剛之尊,是為失正;其所應六二亦為陰爻,是為無正應。這表明六五雖居君位,卻不能養天下,只好求助于陽剛的上九。這自然違反頤之常理(“拂經”)。但此時,六五若能之正,即由陰變為陽,卦變成《益》,《益》之九五與六二為正應,且《益》九五爻辭為“有孚,惠心勿問,元吉。有孚,惠我德。”依此看來,《頤》卦六五爻只要之正為陽,即可獲吉。這就是爻辭所說的“居正吉”的基本含義。
所謂“不可涉大川”,可以從象數和義理兩個方面作出詮釋,然其歸一也。從象數的角度說,《頤》卦六五爻只能之正(即六五由陰變為陽)。若冒然前往與上九易位,雖然該爻實現了由陰變陽的目的,但《頤》之外卦則由艮變成了坎,《頤》卦相應地也就變成了《屯》。《屯》九五爻云:“屯其膏,小貞吉,大貞兇。”涉大川乃屬大貞,其兇可知。且成坎之后,上六與六三失應,亦非吉象。因此,該爻以此立象,告誡人們處于此種境況下,不可行遠征、涉大川。這是象數學的闡釋。從義理的角度看,六五之君有陰柔之質,無陽剛之賢,故只能持中正之德,順而從上,不可行艱險,處變故,不可行遠征,涉大川。故林希元曰:“不能養人,而反賴上九以養于人,故其象為‘拂經’,言反常也。然在己不能養人,而賴賢者以養,亦正道也,故居貞而吉。若不用人而自用,則任大責重,終不能勝。如涉大川,終不能濟,故‘不可’。”(同上)
由此可見,《頤》六五爻旨在告誡統治者在陰柔無剛,不足以養天下時,應守持中正之德,順從剛賢之人,養己濟人。當此之時,若一味剛愎自用,逞強好勝,結果定難如人愿。正如《程氏易傳》所云:“君者,養人者也。反賴人之養,是違拂于經常。既以己之不足,而順從于賢師傅。上,師傅之位也。必居守貞固,篤于委信,則能輔翼其身,澤及天下,故吉也。陰柔之質,無貞剛之性,故戒以能居貞則吉。以陰柔之才,雖倚賴剛賢,能持循于平時,不可處艱難變故之際,故云不可涉大川也。”
上九爻曰:“由頤,厲吉。利涉大川。”宋人邱富國解釋此爻說:“陽實陰虛。實者養人,虛者求人之養,故四陰皆求養于陽者。然養之權在上,是二陽爻又以上為主,而初陽亦求養者也,故直于上九一爻曰‘由頤’焉。”(同上)意謂自初九爻到六五爻,皆為上九所養,故名為“由頤”。《爾雅.釋詁》曰:“由,自也。”《周易集解》引虞翻曰:“由,自從也。”爻辭稱上九為“由頤”,表明上九為《頤》卦之主,其余五爻皆宗此爻,正如王弼所說:“以陽處上,而履四陰,陰不能獨為主,必宗于陽也。故莫不由之以得其養,故曰:由頤。”(王弼《周易注.頤》)
上九身為人臣,原本無位,由于六五的依賴,竟位極人君,身當天下之大任。位高責大,任重道遠,這就要求他必須戒懼修省,常懷惕厲危懼之心,勇于濟天下之危,成天下之業,爻辭講:“厲吉,利涉大川”,正是緣此而發。二程對于上九爻的這一微旨闡釋甚詳,其云:“上九以陽剛之德,居師傅之任,六五之君,柔順而從于己,賴己之養,是當天下之任,天下由之以養也。以人臣而當是任,必常懷危厲則吉也。如伊尹、周公,何嘗不憂勤鑪畏,故得終吉。夫以君之才不足,而倚養于己,身當天下大任,宜竭其才力,濟天下之艱畏,成天下之治安,故曰利涉大川。得君如此之專,受任如此之重,茍不濟天下艱危,何足稱委遇而謂之賢乎?當盡誠竭力而不顧慮,然惕厲則不可忘也。”(《程氏易傳.頤》)朱熹的解釋甚為簡捷,但亦甚得此爻之要義。其云:“六五賴上九之養以養人,是物由上九以養也。位高任重,故厲而吉。陽剛在上,故利涉川。”(同上)
可見,上九爻旨在告訴人們,當統治者負有頤養天下之大任時,于內宜恐懼修省,常懷惕厲處危之心;于外則應盡誠竭力,勇當天下之大任,勇于成就天下之大業,決不可畏首畏尾,茍且偷安。
至此,我們可以看到,《頤》卦講的是人在各種不同的條件下應如何賴以生存的問題,即為如何獲取生活資料和獲取生活資料時應遵循的基本原則的問題。卦辭告訴人們,養生貴在守正,貴在自力自為。六爻爻辭發揮了卦辭的這一思想,主張自養、養人,反對求養于人。六爻爻辭內卦三爻皆不自養而求養于人,故初爻兇,二爻“征兇”,三爻“無攸利”;外卦三爻皆養德養人(上九專言養人,六四、六五雖也求養,但其旨在養德,賴德以養人),故四爻“吉”、“無咎”,五爻“居貞吉”,上爻“厲吉”、“利涉大川”。對此,宋人早有明察,鄭汝諧曰:“《頤》之上體皆吉,而下體皆兇。上體止也,下體動也。在上而止,養人者也。在下而動,求養于人者也。動而求養于人者,必累于口體之養。故雖以初之陽剛,未免于動其欲而觀朵頤也。”(李光地《周易折中.頤》)明人吳慎則更進一步把養人與養己提升到“公”與“私”的高度予以認識,其云:“養之為道,以養人為公,養己為私。自養之道,以養德為大,養體為小。艮三爻皆養人者,震三爻皆養己者。初九、六二、六三,皆自養口體,私而小者也。六四、六五、上九,皆養其德以養人,公而大者也。公而大者吉,得頤之正也。私而小者兇,失頤之貞也。”(同上)由此,我們可以發現《頤》卦中不但蘊含著墨家的尚力思想,而且還蘊含著墨家“興天下之利”的思想。卦辭和內卦的三爻倡導的是一種尚力思想,外卦三爻倡導的是一種“興民之利”的思想。無疑,這些思想與墨家是一脈相連的。
參考文獻:
〔1〕陳立夫.易學應用之研究:第1輯〔M〕.臺北:臺灣中華書局,1979.
〔2〕 朱彝尊.經義考:卷二〔M〕.北京:中華書局,1998.
〔3〕 王蘧常.諸子學派要詮〔M〕.北京:中華書局,1987.
〔4〕 司馬遷.史記:第10冊〔M〕.北京:中華書局,1959.
〔5〕 班固.漢書:第6冊〔M〕.北京:中華書局,1962.
〔6〕朱熹.周易本義〔M〕.天津:天津市古籍書店,1986.
〔7〕 李鼎祚.周易集解〔M〕.北京:中國書店,1984.
〔8〕 尚秉和.周易尚氏學〔M〕.北京:中華書局.1980.
〔9〕李光地.周易折中〔M〕.成都:巴蜀書社,1998.
〔10〕李道平.周易集解纂疏〔M〕.北京:中華書局,1994.
〔11〕樓宇烈.王弼集校〔M〕.北京:中華書局,1980.
〔12〕程顥,程頤.二程集〔M〕.北京:中華書局,1981.
〔13〕黃壽祺,張善文.周易譯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