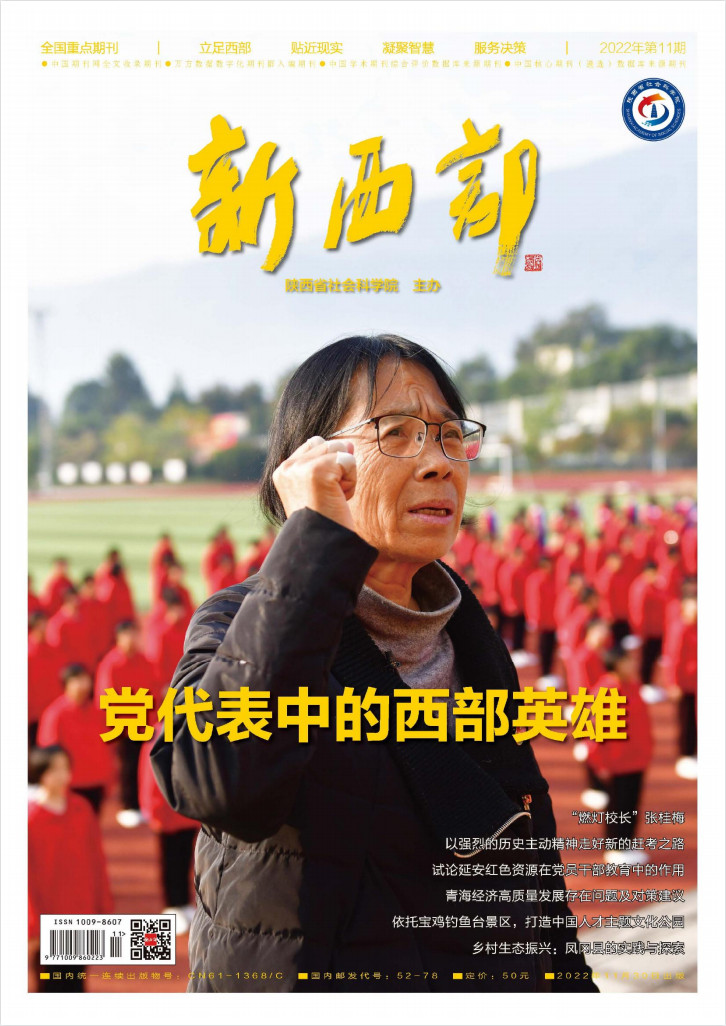漢代監獄的層次及管理
薛瑞澤
摘要:漢代的監獄分為中央級的詔獄和郡縣監獄兩種。中央級的詔獄主要處理重大政治案件,而郡縣監獄則關押地方罪犯。為了對監獄實施有效管轄,漢政府還建立了相應的管理機構。
關鍵詞:漢代;監獄;管理
監獄作為維護權力的職能部門,經過兩漢四百余年的發展,形成了自中央到地方不同系統、多種層次的監獄。其數量蔚為可觀,《漢書·刑法志》有“天下獄二千余所”之說。監獄管理也呈現出漸趨完備的態勢。
一、西漢監獄的層次
西漢監獄分為中央和地方兩大層次,中央級監獄又分為地處京城的“中都官獄”和分布在地方而直屬于中央的詔獄,地方監獄大致分為郡(國)和縣兩種。長安的監獄數目各史書記載不一,《漢書·宣帝紀》顏師古注引《漢儀注》云:“長安中諸官獄三十六所。”而《漢書·張湯傳》顏師古注引蘇林曰:“《漢儀注》獄二十六所。”《續漢書·百官志二》則云:“孝武帝以下,置中都官獄二十六所。”可能三十六為二十六之誤。先考證西漢長安的中都官獄。
1.廷尉詔獄。廷尉詔獄主要處理重大的政治案件。漢九年,趙相貫高等人謀反,劉邦逮捕趙王張敖,廷尉參與了審問。[1](《漢書·張耳陳馀傳》)漢文帝五年秋,有人狀告周勃欲造反,“逮詣廷尉詔獄”。[1](《漢書·文帝紀》)漢武帝時,杜周為廷尉史,處理案件“所論殺甚多”,到為廷尉時又效仿張湯,“詔獄亦益多矣”。史稱“詔獄逮至六七萬人,吏所增加十有余萬”。[1](《漢書·杜周傳》)漢昭帝時,河南太守魏相被人誣告“賊殺不辜”,霍光借機“遂下相廷尉獄”,后遇赦而出。[1](《漢書·魏相傳》)弘恭、石顯甚至利用漢宣帝不懂得“召致廷尉”之意,將其老師蕭望之逮至廷尉詔獄。[1](《漢書·蕭望之傳》)漢宣帝時丞相魏相誣告京兆尹趙廣漢,“宣帝惡之,下廣漢廷尉獄”,被腰斬。[1](《漢書·趙廣漢傳》)漢成帝時,王章認為外戚王鳳不可用,因此被陷害,“果下廷尉獄,妻子皆收系”。[1](《漢書·王章傳》)霍光政變時,“車騎將軍安世將羽林騎收縛二百余人,皆送廷尉詔獄”。[1](《漢書·霍光傳》)漢哀帝時,丞相朱博與孔鄉侯傅晏、御史大夫趙玄秉承定陶太后的旨意,誣陷其從弟傅喜。漢哀帝讓左將軍彭宣處理此事,彭宣“請詔謁者召博、玄、晏詣廷尉詔獄”,漢哀帝“假謁者節召丞相詣廷尉詔獄”,朱博自殺。[1](《漢書·朱博傳》)元壽元年三月,丞相王嘉因舉薦梁相而得罪漢哀帝,光祿大夫孔光乘機“請謁者召嘉詣廷尉詔獄”,雖有大臣勸諫,但漢哀帝仍然“有詔假謁者節,召丞相詣廷尉詔獄”。[1](《漢書·王嘉傳》)哀帝末年,鮑宣因制止丞相掾史行馳道,御史中丞因鮑宣“亡人臣禮,大不敬,不道,下廷尉獄”。[1](《漢書·鮑宣傳》)
2.上林詔獄。《漢書·成帝紀》載,建始元年正月,漢成帝“罷上林詔獄”。師古曰:“《漢書儀》云上林詔獄主治苑中禽獸宮館事,屬水衡。”水衡之設在漢武帝時,《漢書·食貨志下》云:“初,大農斡鹽鐵官布多,置水衡,欲以主鹽鐵。及楊可告緡,上林財物眾,乃令水衡主上林。”楊可告緡在元鼎三年,由之可知,上林詔獄存在于元鼎三年至建始元年之間。
3.司空詔獄。《漢舊儀補遺》卷上云:“司空詔獄,治列侯、二千石,屬宗正。”《漢書·百官公卿表上》“宗正”條云:“屬官有都司空令丞。”如淳曰:“律,司空主水及罪人。賈誼曰‘輸之司空,編之徒官’。”反映了司空的職能。
4.郡邸獄。《漢書·宣帝紀》載,漢武帝晚年巫蠱之禍時,漢宣帝“雖在襁褓,猶坐收系郡邸獄”。如淳曰:“謂諸郡邸置獄也。”師古曰:“據《漢舊儀》,郡邸獄治天下郡國上計者,屬大鴻臚。此蓋巫蠱獄繁,收系者眾,故曾孫寄在郡邸獄。”時丙吉為廷尉監,“治巫蠱于郡邸”,對漢宣帝關照有加。后元二年,在漢武帝病重,“遣使者分條中都官獄系者,輕重皆殺之”的緊要關頭,丙吉全力保護漢宣帝。事后就連漢武帝也認為“郡邸獄系者獨賴吉得生,恩及四海矣”。[1](《漢書·丙吉傳》)漢宣帝即位后知恩圖報,元康三年三月下詔:“吉、曾、玄、舜、延壽皆為列侯。故人下至郡邸獄復作嘗有阿保之功,皆受官祿田宅財物,各以恩深淺報之。”
5.掖庭詔獄。漢成帝欲立趙飛燕為皇后,永始四年封趙飛燕之父為成陽侯,諫議大夫劉輔上書反對,“上使侍御史收縛輔,系掖庭秘獄,群臣莫知其故”。[1](《漢書·劉輔傳》)師古曰:“《漢書舊儀》掖庭詔獄令丞宦者為之,主理婦人女官也。”故而群臣言劉輔被收于“秘獄”、“掖庭獄”。谷永也有“掖庭獄大為亂阱,榜箠憯于炮格”之說。[1](《漢書·谷永傳》)
6.共工詔獄。劉輔被送往掖庭獄后,“上乃徙系輔共工獄”。[1](《漢書·劉輔傳》)蘇林曰:“考工也。”師古曰:“少府之屬官也,亦有詔獄。”史有王莽更“少府曰共工”之說,實非鑿空之論。
7.暴室獄。漢宣帝遭巫蠱之禍,后被掖庭令張賀撫養,“既壯,為取暴室嗇夫許廣漢女”。[1](《漢書·宣帝紀》)應劭曰:“暴室,宮人獄也,今曰薄室。許廣漢坐法腐為宦者,作嗇夫也。”師古曰:“暴室者,掖庭主織作染練之署,故謂之暴室,取暴曬為名耳。……蓋暴室職務既多,因為置獄主治其罪人,故往往云暴室獄耳。然本非獄名,應說失之矣。”
8.若盧詔獄。《漢書·百官公卿表上》載“少府”屬官有若盧,服虔曰:“若盧,詔獄也。”鄧展曰:“舊洛陽兩獄,一名若盧,主受親戚婦女。”如淳曰:“《漢儀注》有若盧獄令,主治庫兵將相大臣。”成帝時,王鳳誣陷丞相王商,加之太中大夫張匡進讒言于左將軍史丹,史丹奏“請詔謁者召商詣若盧詔獄”。[1](《漢書·王商傳》)孟康曰:“若盧,獄名,屬少府,黃門內寺是也。”
9.左右都司空獄。淮南王劉安叛亂前,征求謀士伍被意見,伍被反復勸諫,有“又偽左右都司空上林中都官詔獄書,逮諸侯太子及幸臣”之語。[1](《漢書·伍被傳》)晉灼曰:“《百官表》宗正有左右都司空,上林有水司空。皆主囚徒官也。”
10.居室獄。《漢書·灌夫傳》載,元光四年夏,丞相田蚡娶妻,灌夫大鬧宴會,田蚡怒,“劾灌夫罵坐不敬,系居室”。師古曰:“居室,署名也,屬少府。其后改名曰保官”。司馬遷《報任安書》有“灌夫受辱居室”之說。李陵投降匈奴后,“老母系保宮”。[1](《漢書·蘇建傳附子武傳》)師古曰:“《百官公卿表》云少府屬官有居室,武帝太初元年更名保宮。”《漢書·衛青傳》載,衛青出身貧賤,“嘗從人至甘泉居室,有一鉗徒相青”,言其將封侯。張晏曰:“居室,甘泉中徒所居也。”居室中既然關押有“鉗徒”,為監獄無疑矣。
11.都船詔獄。《漢書·百官公卿表上》“中尉”條云:“武帝太初元年更名執金吾,屬官有中壘、寺互、武庫、都船四令丞。”如淳曰:“《漢儀注》有寺互。都船獄令,治水官也。”薛宣“少為廷尉書佐、都船獄史”。[1](《漢書·薛宣傳》)漢成帝欲毒死王嘉,派使者召至廷尉,“廷尉收嘉丞相新甫侯印綬,縛嘉載致都船詔獄”。[1](《漢書·王嘉傳》)
12.內官獄。《漢書·律歷志》云:“職在內官,廷尉掌之。”師古曰:“內官,署名也。《百官表》云‘內官長丞,初屬少府,中屬主爵,后屬宗正’。”師古又曰:“法度所起,故屬廷尉也。”漢武帝時,昭平君在其母隆慮公主死后,醉殺主傅,“獄系內官”。雖然有其母“豫贖死罪”在先,但仍被漢武帝懲治。[1](《漢書·東方朔傳》)
13.請室獄。賈誼《新書·階級》有“造請室而請其罪爾”之語。應劭曰:“請室,請罪之室。”蘇林曰:“胡公《漢官》車駕出有請室令在前先驅,此官有別獄也。”周勃被誣陷后,“征擊請室,諸公莫敢為言,唯盎明絳侯無罪”。周勃被無罪釋放。[1](《漢書·爰盎傳》)司馬遷曾說:“絳侯誅諸呂,權傾五伯,囚于請室。”[1](《漢書·司馬遷傳》)
14.導官獄。御史大夫張湯令心腹魯謁居上書告發并借機殺死異己御史中丞李文。因內情敗露,漢武帝讓廷尉處理此事。時魯謁居已死,“事連其弟,弟系導官”。張湯因故到導官獄,“見謁居弟,欲陰為之,而陽不省。謁居弟不知而怨湯,使人上書,告湯與謁居謀,共變李文。事下減宣”。減宣窮竟其事,張湯自殺。[1](《漢書·張湯傳》)蘇林曰:“《漢儀注》獄二十六所,導官無獄也。”師古曰:“蘇說非也,……時或以諸獄皆滿,故權寄在此署系之,非本獄所也。”
除京師詔獄外,地方也有直屬中央的詔獄。前文云洛陽有兩座詔獄,其一為若盧詔獄。《漢舊儀》卷下云:“(河南)府下置詔獄。”漢成帝時,定陵侯淳于長與長定貴人之姊私通,又與紅陽侯劉立狼狽為奸,“遂逮長系洛陽詔獄窮治”,被以大逆罪殺死。[1](《漢書·佞幸·董賢傳》)息夫躬得罪漢哀帝,又被誣陷,“上遣侍御史、廷尉監逮躬,系洛陽詔獄”,氣憤而死。[1](《漢書·息夫躬傳》)漢武帝時,趙敬肅王劉彭祖之子劉丹與其姐妹淫亂,被江充告發,“武帝遣使者發吏卒捕丹,下魏郡詔獄,治罪至死”,后被赦免。[1](《漢書·景十三王·趙敬肅王劉彭祖傳》)本始三年,相內史奏廣川王劉去與其妃陽成昭信濫殺無辜,“天子遣大鴻臚、丞相長史、御史丞、廷尉正雜治鉅鹿詔獄”。劉去自殺,昭信被棄市。[1](《漢書·景十三王·廣川惠王劉越傳》)史實證明洛陽、魏郡、鉅鹿有詔獄存在。
西漢時郡縣的監獄,主要關押地方囚犯。漢代長安就有郡縣一級的監獄,《漢舊儀補遺》卷上云:“東市獄屬京兆尹,西市獄屬左馮翊。”尹賞在任長安令時所建的長安獄堪稱當時最為殘酷的監獄,在監獄中建名為“虎穴”的大坑,將長安城中的“輕薄少年惡子,無市籍商販作務,而鮮衣兇服被鎧捍持刀兵者”全部關押捂死。[1](《漢書·酷吏·尹賞傳》)采取嚴厲的措施打擊地方的邪惡勢力。西漢見諸記載的地方監獄有以下幾個。
1.鉅鹿獄。鉅鹿人路溫舒刻苦自學,“求為獄小吏,因學律令,轉為獄史,縣中疑事皆問焉。太守行縣,見而異之,署決曹史”。[1](《漢書·路溫舒傳》)既然鉅鹿縣有“獄史”和“決曹史”,說明該縣有監獄之設。
2.郯獄。東海郯人于定國的父親“于公為縣獄史,郡決曹,決獄平,羅文法者于公所決皆不恨”。于定國自幼“學法于父,父死,后定國亦為獄史,郡決曹”。[1](《漢書·于定國傳》)
3.宛獄。西漢末,劉祉兄弟率軍響應劉秀起兵,王莽的“前隊大夫甄阜盡收其家屬系宛獄。及漢兵敗小長安,祉挺身還保棘陽,甄阜盡殺其母弟妻子”。[1](《后漢書·宗室四王三侯·城陽恭王祉傳》)
4.蒙獄。漢文帝時,韓安國“坐法抵罪,蒙獄吏田甲辱安國”。[1](《漢書·韓安國傳》)師古曰:“蒙,梁國之縣也。”后來韓安國官任梁內史,不計前嫌,啟用田甲,受到人們稱贊。
5.鄧獄。漢平帝時,翟義任南陽都尉,宛令劉立與曲陽侯王根為姻親,看不起翟義。翟義代太守巡視屬縣時,“以主守盜十金,賊殺不辜,部掾夏恢等收縛立,傳送鄧獄”。 [1](《漢書·翟方進傳附子義傳》)
6.定襄獄。漢武帝多次出兵定襄,使該地社會秩序混亂,“于是徙縱為定襄太守。縱至,掩定襄獄中重罪二百余人,及賓客昆弟私入相視者亦二百余人”。“是日皆報殺四百余人”, “郡中不寒而栗,猾民佐吏為治”。[1](《漢書·酷吏·義縱傳》)
7.陳留獄。建平年間,梁王劉立殺人,“丞相、御史請收王璽綬,送陳留獄”。因漢哀帝包庇,僅將其傅、相等官員正法,赦免劉立的罪行。[1](《漢書·文三王·梁懷王劉揖傳》)
8.外黃獄。西漢末,劉昆擔心禮因此而廢,率領弟子五百余人習禮,“王莽以昆多聚徒眾,私行大禮,有僭上心,乃系昆及家屬于外黃獄”。[2](《后漢書儒林上·劉昆傳》)
二、東漢監獄的層次
東漢監獄繼承了西漢的模式,既有位于京城的詔獄,也有分布于郡國的地方監獄。《續漢書·百官志三》“廷尉”條云:“唯廷尉及洛陽有詔獄。”其實洛陽的詔獄不僅這兩處。
1.洛陽詔獄。主要處理朝廷的重要案件。光武年間,外戚陰興、陰就敬重馮衍,馮衍因之官至司隸從事。光武帝“懲西京外戚賓客,故皆以法繩之”。馮衍不得不“詣洛陽詔獄”,被赦免不問。[2](《后漢書·馮衍傳上》)馬援侄女婿王磐為王莽從兄之子,不知進退,因“與司隸校尉蘇鄴、丁鴻事相連,坐死洛陽獄”。[2](《后漢書·馬援傳》)反映了東漢初年光武帝打擊結黨營私現象。楚王英謀反被發覺后,“掾史五百余人詣洛陽詔獄就考,諸吏不堪痛楚,死者大半”。[2](《后漢書·獨行·陵續傳》)經寒朗勸解,漢明帝“車駕自幸洛陽獄錄囚徒,理出千余人”。[2](《后漢書·寒朗傳》)東漢中后期,洛陽詔獄在政治生活中的作用越來越明顯。永建年間,有人向大將軍梁商誣陷霍谞之舅宋光,“以為妄刊章文,坐系洛陽詔獄”。霍谞為其舅辯解,梁商原諒了宋光。[2](《后漢書·霍谞傳》)漢桓帝初年,梁冀之弟梁不疑為河南尹,宦官單超、左惋拜訪梁不疑,因“禮敬小簡,不疑收其兄弟送洛陽獄”,二人上門謝罪,其兄弟才被釋放。[2](《后漢書·宦者·單超傳》)延熹末年,李膺為司隸校尉,宦官張讓弟張朔為野王令,無惡不作,“膺知其狀,率將吏卒破柱取朔,付洛陽獄。受辭畢,即殺之”。[2](《后漢書·黨錮·李膺傳》)延熹九年,襄楷屢次上奏為政之弊,漢桓帝怒,尚書乘機建議:“請下司隸,正楷罪法,收送洛陽獄。”襄楷被判令“猶司寇論刑”。[2](《后漢書·襄楷傳》)漢靈帝光和二年,司隸校尉陽球,逮捕了太尉段颎、宦官王甫,“送洛陽獄”,隨后將其處死。宦官又反戈一擊,“遂收球送洛陽獄,誅死,妻子徙邊”。[2](《后漢書·酷吏·陽球傳》)《蔡邕集》曰:“光和元年,都官從事張恕,以辛卯詔書,收邕送雒陽詔獄。”后經宦官呂強的請求而遷徙五原,[2](《后漢書·蔡邕傳》)蔡邕戍邊上奏章中有“臣初決罪洛陽詔獄”之語。[2](《后漢書·律歷志下》)
2.廷尉詔獄。廷尉詔獄所處理的案件也大多與政治有關。永平年間,阜陵質王劉延謀反,受到遷徙封地懲罰。建初年間,“復有告延與子男魴造逆謀者,有司奏請檻車征詣廷尉詔獄”,劉延受到降為侯的處理。[2](《后漢書·光武十王·阜陵質王延傳》)周紆任洛陽令,嚴懲貴戚的不法行為,因得罪權貴,“詔召司隸校尉、河南尹詣尚書譴問,遣劍戟士收紆送廷尉詔獄”,后被放出。[2](《后漢書·酷吏·周紆傳》)永元五年,豫州刺史梁相舉奏梁節王劉暢“不道”,雖嚴詞考訊,但劉暢不服,“有司請征暢詣廷尉詔獄”,和帝不許。[2](《后漢書·孝明八王·梁節王暢傳》)永初四年,騎都尉任仁率軍抵抗羌人的進攻,“任仁戰累敗,而兵士放縱,檻車征詣廷尉詔獄死”。[2](《后漢書·西羌傳》)漢靈帝時,黨人張儉殺宦官侯覽母親,其隨從被太山太守苑康保護,“覽大怨之,誣康與兗州刺史第五種及都尉壺嘉詐上賊降,征康詣廷尉獄”。[2](《后漢書·黨錮·苑康傳》)
3.北寺詔獄。北寺詔獄是宦官所轄的監獄,在桓靈二帝宦官勢力橫行時曾關押了大批黨人。延熹二年漢桓帝在宦官輔佐下滅梁冀,對單超等宦官寵信有加,李云上書勸諫,“帝得奏震怒,下有司逮云,詔尚書都護劍戟送黃門北寺獄,使中常侍管霸與御史廷尉雜考之”。李云死于獄中。[2](《后漢書·李云傳》)此次黨錮之禍中,李膺、范滂、陳翔都被羈押在北寺詔獄。[2](《后漢書·黨錮傳》)永康元年,竇武上書桓帝解除黨人的禁錮,“有詔原李膺、杜密等,自黃門北寺、若盧、都內諸獄,系囚罪輕者皆出之”。[2](《后漢書·竇武傳》)漢靈帝時,北寺詔獄所關押的犯人呈現出宦官與黨人交替的現象。建寧元年,陳蕃與竇武謀除宦官,將“狡猾尤無狀者長樂尚書鄭颯,送北寺獄”關押。而政變中宦官王甫也曾“持節至北寺獄收尹勛、山冰”。[2](《后漢書·竇武傳》)宦官反戈一擊,陳蕃被捉拿,“遂執蕃送黃門北寺獄”害死。 [2](《后漢書·陳蕃傳》)到了熹平二年,陳國國相師遷向靈帝誣陷前相魏愔與陳愍王劉寵,漢靈帝“詔檻車傳送愔、遷詣北寺詔獄”,派人審理,結果證明是師遷等人的誣告。[2](《后漢書·孝明八王·陳敬王羨傳附寵傳》)漢靈帝時,劉陶指出朝政的腐敗,靈帝聽信讒言,“于是收陶,下黃門北寺獄,掠按日急”,劉陶閉氣而死。[2](《后漢書·劉陶傳》)
4.若廬獄。《后漢書·和帝紀》云:永元九年十一月,“復置若盧獄官。”李賢注云:“《前書》曰,若盧獄屬少府。《漢舊儀》曰:‘主鞫將相大臣’也。”《漢舊儀》曰:“少府若廬獄有蠶室。”[2](《后漢書·陳寵傳附子忠傳》)漢和帝末年,左校令龐參“坐法輸作若廬”。[2](《后漢書·龐參傳》)李賢注云:“若廬,獄名。”永初二年五月,“皇太后幸洛陽寺及若盧獄,錄囚徒”。[2](《后漢書·孝安帝紀》)
5。掖庭獄。永元十四年夏,“有言(陰)后與朱共挾巫蠱道,事發覺,帝遂使中常侍張慎與尚書陳褒于掖庭獄雜考案之”。和帝因此廢掉陰皇后。[2](《后漢書·和帝陰皇后紀》)
6.左右都侯獄。《續漢書·百官志二》“衛尉”條云:“左右都候各一人,六百石。本注曰:主劍戟士,徼循宮,及天子有所收考。丞各一人。”劉昭補注:《漢官》曰:“右都候員吏二十二人,衛士四百一十六人。左都候員吏二十八人,衛士三百八十三人。”蔡質《漢儀》曰:“宮中諸有劾奏罪,左都候執戟戲車縛送付詔獄,在官大小各付所屬。”
東漢各郡(國)縣都設有監獄,地方監獄與東漢政治興替也有很大的關系。茲考證如下。
1.平陵獄。右扶風平陵縣的監獄。竇融之子竇穆自從失勢后,多次出言怨恨朝廷,漢明帝令其全家回到故鄉平陵縣。竇穆又“坐賂遺小吏,郡捕系,與子宣俱死平陵獄”,其子竇勛雖然與沘陽公主結婚,因受牽連,“亦死洛陽獄”。[2](《后漢書·竇融傳》)
2.槐里獄。右扶風槐里縣的監獄。《后漢書·孝靈帝紀》云:熹平五年五月閏月,“永昌太守曹鸞坐訟黨人,棄市”。李賢注云:“其言切直,帝怒,檻車送槐里獄掠殺之也。”
3.漢陽獄。漢陽郡的監獄。梁竦因其兄梁松誹謗朝廷受到牽連,漢明帝令其回本郡。建初八年,因竇氏的誣陷,漢章帝“以惡逆”的罪名,“詔使漢陽太守鄭據傳考竦罪,死獄中”。永元九年冬,漢和帝“遣中謁者與嫕及扈,備禮西迎竦喪”,改葬京師,李賢注云:“竦死漢陽獄,故西迎也。”[2](《后漢書·梁統傳附子竦傳》)
4.京兆獄。京兆尹的監獄。《后漢書·班彪傳附子固傳》云:班彪死后,班固回歸鄉里,“固以彪所續前史未詳,乃潛精研思,欲就其業。既而有人上書顯宗,告固私改作國史者,有詔下郡,收固系京兆獄,盡取其家書”。后來其弟班超上書漢明帝,方才獲釋。
5.徐獄。徐縣的監獄。漢章帝元和三年,張禹任下邳相,太尉掾功曹史戴閏,權傾郡內,“有小譴,禹令自致徐獄,然后正其法。自長史以下,莫不震肅。”[2](《后漢書·張禹傳》)
6.長平獄。陳國長平縣的監獄。陳思王劉鈞因憎恨其父的夫人李儀,“永元十一年,遂使客隗久殺儀家屬。吏捕得久,系長平獄”。劉鈞為了殺人滅口,又除掉隗久。事情被發覺后,漢和帝削除其三個封縣。[2](《后漢書·孝明八王·陳敬王羨傳附鈞傳》)
7.宛獄。南陽郡的監獄。成瑨任南陽太守時,以威嚴震攝豪強。張子禁仰仗是桓帝乳母的外親,不畏法網,“功曹岑晊勸使捕子禁付宛獄,笞殺之”。因得罪權貴,桓帝征成瑨下獄死。[2](《后漢書·黨錮列傳》李賢注引《謝承書》)
8.劇獄。劇縣的監獄。董宣任北海相時,當地大姓公孫丹濫殺無辜,董宣“即收丹父子殺之。丹宗族親黨三十余人,操兵詣府,稱冤叫號。宣以丹前附王莽,慮交通海賊,乃悉收系劇獄,使門下書佐水丘岑盡殺之”。[2](《后漢書·酷吏·董宣傳》)
9.錢唐縣獄。錢唐縣的監獄。《后漢書·獨行·戴就傳》記載,會稽上虞人戴就“仕郡倉曹掾,楊州刺史歐陽參奏太守成公浮臧罪,遣部從事薛安案倉庫簿領,收就于錢唐縣獄”。戴就受盡折磨而不誣陷太守,薛安深受感動,釋放了戴就。
10.南鄭獄。漢中郡南鄭縣的監獄。東漢初年,漢中太守丁邯,因“妻弟為公孫述將,收妻送南鄭獄,免冠徒跣自陳”。光武帝下詔免其罪。[3](《續漢書·百官志三》劉昭注補引《決錄注》)丁邯將妻關押南鄭獄是一種姿態,而光武帝免其罪是收買人心。漢中程文矩前妻所生的四個兒子對其妻李氏非常憎恨,但李氏對其則盡心撫養,終于感動四人,長子程興“遂將三弟詣南鄭獄”,并甘愿受罰。后來郡縣減免其徭役,在李氏的訓導下,四人都先后成才。[2](《后漢書·列女·程文矩妻傳》)
11.郿獄。右扶風郿縣的監獄。董卓之亂時,崔鈞與袁紹起兵山東討伐董卓,“董卓以是收烈(崔烈——崔鈞之父)付郿獄,錮之,鋃鐺鐵鎖”。[2](《后漢書·崔骃傳附孫寔傳》)
12.安邑獄。安邑縣的監獄。漢靈帝時,宦官侯覽曾派人到河東太守史弼處求假鹽稅,史弼知狀后,對侯覽所派的人“付安邑獄,即日考殺之”。侯覽知情后,誣陷史弼,“下廷尉詔獄”,后經人營救方才得免。[2](《后漢書·史弼傳》)
13.吳縣獄。會稽郡吳縣之獄。建武年間,西部都尉宰晁代行太守之職,“以微過收吳縣獄吏,將殺之”,經郡功曹彭修的勸解方免其罪罰。[2](《后漢書·獨行·彭修傳》)
14.合浦獄。合浦郡的監獄。初平年間,天下大亂,桓曄逃到會稽避難,后又渡海客居交阯,“越人化其節,至閭里不爭訟。為兇人所誣,遂死于合浦獄”。[2](《后漢書·桓榮傳附鸞子曄傳》)
15.許獄。魏都許的監獄。華佗不愿隨曹操為其治病,回到家鄉,并以妻病為托詞回絕曹操,曹操派人探驗虛實,“若其虛詐,便收送之。于是傳付許獄”,華佗死于獄中。[4](《三國志·魏書·方技·華佗傳》)
16.發干獄。東郡發干縣的監獄。《后漢書·崔骃傳附子瑗傳》記載,崔骃之子崔瑗“年四十余,始為郡吏。以事系東郡發干獄”。李賢注:“發干縣之獄也。”
17.其他監獄。《后漢書·楊終傳》載,永平以來,因大獄迭起,罪犯家屬徙邊者,“遠屯伊吾、樓蘭、車師、戊己”。章帝建初元年,楊終“以為廣陵、楚、淮陽、濟南之獄徙者數萬人,吏民怨曠”,上疏建議去掉徙邊之策,被漢章帝所采納。[3](《續漢書·五行志一》)
三、兩漢監獄的管理
漢代的監獄管理分別屬于不同系統,分為中央級的管理機構和郡縣級的管理機構。中央級的監獄管理機構由各職能部門管轄。我們這里擇其主要者作一考證。
廷尉詔獄屬于廷尉管轄。廷尉“掌刑辟,有正、左右監,秩皆千石”。地節三年“初治左右平,秩皆六百石”。[1](《漢書·百官公卿表上》)《漢書·宣帝紀》云:地節三年“十二月,初置廷尉平四人,秩六百石”。廷尉的屬官選拔還有一定的條件,衛宏《漢官儀》卷上云:“選廷尉正、監、平,案章取明律令。”即要選取熟悉法律的人充當此職。“廷尉正、監、平物故,以御史高第補之”。廷尉的屬官還有廷尉史,簡稱廷史。漢武帝掌權后,儒學大盛,廷尉張湯“決大獄,欲傅古義,乃請博士弟子治《尚書》、《春秋》,補廷尉史,平亭疑法”。[1](《漢書·張湯傳》)用儒生擔任法律機構的屬員有利于持法公允。《漢書·刑法志》載地節三年十二月詔云:“今遣廷史與郡鞠獄,任輕祿薄,其為置廷平,秩六百石,員四人。其務平之。”說明廷尉屬員有時直接聽命于皇帝。廷尉的屬員還有文學卒史、奏讞掾等。漢武帝時,兒寬“以射策為掌故,功次補廷尉文學卒史”。蘇林曰:“秩六百石,舊郡亦有也。”臣瓚曰:“《漢注》卒史秩百石。”到張湯為廷尉時,因重視儒學,“以寬為奏讞掾,以古法義決疑獄,甚重之”。[1](《漢書·兒寬傳》)奏讞掾管理疑獄的上奏。廷尉的屬官中可能還有書佐,薛宣“少為廷尉書佐”。
東漢時期,廷尉行政級別提高,屬員人數明確。《續漢書·百官志二》“廷尉”條云:“廷尉,卿一人,中二千石。本注曰:掌平獄,奏當所應。凡郡國讞疑罪,皆處當以報。正、左監各一人。左平一人,六百石。本注曰:掌平決詔獄。”劉昭注補《漢官》曰:“員吏百四十人,其十一人四科,十六人二百石廷吏,文學十六人百石,十三人獄史,二十七人佐,二十六人騎吏,三十人假佐,一人官醫。”與西漢相比,東漢省去了右監、平之職。
兩漢時期還有其他監獄管理人員。漢武帝太初元年改定的大鴻臚一職,其屬官有別火令丞。如淳曰:“《漢儀注》別火,獄令官,主治改火之事。”東漢時省去此官。宗正“屬官有都司空令丞”一職。如淳曰:“律,司空主水及罪人。”[1](《漢書·百官公卿表上》)《續漢書·百官志三》云:宗正“中興省都司空令丞”。漢代少府屬官中的若盧獄令也是管理監獄的官吏。西漢的都船獄令一職東漢時期也省去了。漢代軍隊中還有軍司空一職,昭帝初即位,大將軍霍光秉政,以杜延年三公子明習法律,“吏材有余,補軍司空”。[1](《漢書·杜周傳附子延年傳》)蘇林曰:“主獄官也。”如淳曰:“律,營軍司空,軍中司空各二人。”漢昭帝時,馮奉世“學《春秋》涉大義,讀兵法明習,前將軍韓增奏以為軍司空令”。[1](《漢書·馮奉世傳》)
郡縣級監獄管理由地方官負責,漢宣帝曾下詔“今遣廷史與郡鞠獄”。說明郡太守要親自參與監獄案件的審理。一般情況下管理監獄為普通的獄吏,路溫舒先后為鉅鹿縣的“獄小吏”和“獄史”等官。蒙獄的獄吏曾經侮辱過韓安國。公孫弘“少時為獄吏”。東海郯人于定國的父親“于公為縣獄史,郡決曹”。“后定國亦為獄史,郡決曹”。[1](《漢書·于定國傳》)魯國人丙吉也曾“為魯獄史”。河東平陽人尹翁歸年輕時也曾為“獄小吏”。涿郡高陽人王尊在十三歲時“為獄小吏”,到太守府后,“除補書佐,署守屬監獄”。后來他稱病辭職跟隨郡文學學習,“復召署守屬治獄,為郡決曹史”。[1](《漢書·王尊傳》)師古曰:“署為守屬,令監獄主囚也。”徐宣也曾為“故縣獄吏”。王霸其祖父為詔獄丞,“父為郡決曹掾,霸亦少為獄吏”。[2](《后漢書·王霸傳》)李賢注云:《漢舊儀》:“決曹,主罪法事。”《漢書·薛宣傳》還記載薛宣任職左馮翊,“池陽令舉廉吏獄掾王立,府未及召,聞立受囚家錢。宣責讓縣,縣案驗獄掾,乃其妻獨受系者錢萬六千,受之再宿,獄掾實不知。掾慚恐自殺”。反映了獄掾有可能受賄。
漢宣帝時期,允許特殊地區的地方官提高監獄管理人員待遇。本始年間,京兆尹趙廣漢“奏請,令長安游徼獄吏秩百石,其后百石吏皆差自重,不敢枉法妄系留人”。[1](《漢書·趙廣漢傳》)師古曰:“特增其秩以厲其行。”這種增吏秩以求其盡力政事的現象影響到其他地區。在勃海、膠東一帶,因糧食歉收,“盜賊并起”,張敞上書請求前去治理,漢宣帝任命他為膠東相,張敞“自請治劇郡非賞罰無以勸善懲惡,吏追捕有功效者,愿得壹切比三輔尤異。天子許之”。[1](《漢書·張敞傳》)如淳曰:“壹切,權時也。趙廣漢奏請令長安游徼獄史秩百石,又《循吏傳》左馮翊有二百石卒史,此之謂尤異也。”
東漢時地方監獄管理與西漢沒有太大差別,由地方官員管理。虞經為郡縣獄吏。[2](《后漢書·虞詡傳》)何敞的六世祖父比干,“為汝陰縣獄吏決曹掾,平活數千人。后為丹陽都尉,獄無冤囚”。[2](《后漢書·何敞傳》李賢注引《何氏家傳》)說明縣級監獄有獄吏決曹掾、都尉等。建初七年,中牟縣長魯恭為政清廉,“河南尹袁安聞之,疑其不實,使仁恕掾肥親往廉之”。[2](《后漢書·魯恭傳》)李賢注:“仁恕掾,主獄,屬河南尹,見《漢官儀》。”《續漢書·百官志五》“縣鄉條”云:“丞各一人。尉大縣二人,小縣一人。本注曰:丞署文書,典知倉獄。尉主盜賊。凡有賊發,主名不立,則推索行尋,案察奸宄,以起端緒。”說明縣級行政機構中仍然有監獄管理人員。
[1]班固.漢書[M].北京:中華書局,1962.
[2]范曄.后漢書[M].北京:中華書局,1965.
[3]司馬彪.續漢書[M].北京:中華書局,1965.
[4]陳壽.三國志[M].北京:中華書局,195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