農(nóng)村勞動力轉(zhuǎn)移及其對高等教育的需求
佚名
「內(nèi)容提要」我國農(nóng)村勞動力的轉(zhuǎn)移存在著教育壁壘。勞動力的教育文化素質(zhì)影響甚至決定著勞動力轉(zhuǎn)移的難易度、轉(zhuǎn)移后的職業(yè)及收入、轉(zhuǎn)移的區(qū)間等,勞動力有效轉(zhuǎn)移對勞動力文化知識和能力素質(zhì)有較高要求,勞動力轉(zhuǎn)移到城鎮(zhèn)、鄉(xiāng)鎮(zhèn)企業(yè)、第三產(chǎn)業(yè)以及勞務(wù)輸出等活動產(chǎn)生了高等教育需求。
「關(guān)鍵詞」農(nóng)村/勞動力轉(zhuǎn)移/高等教育/需求
農(nóng)村勞動力轉(zhuǎn)移是工業(yè)化和技術(shù)進步引起的產(chǎn)業(yè)結(jié)構(gòu)變化導(dǎo)致的農(nóng)村勞動力從一個地方移動到另一個地方的空間移動,這種轉(zhuǎn)移對文化傳播和資源的有效配置和利用起著重要作用,也是農(nóng)村現(xiàn)代化的必然選擇。從西歐和美國的經(jīng)驗來看,勞動力從傳統(tǒng)農(nóng)業(yè)中釋放出來,重新配置到城市生產(chǎn)部門,促進了工業(yè)化的發(fā)展,也促進了城市化的發(fā)展。農(nóng)村勞動力的轉(zhuǎn)移是我國農(nóng)村發(fā)展的必然選擇。我國農(nóng)村從開放的1978年到2000年,已累計向非農(nóng)產(chǎn)業(yè)轉(zhuǎn)移農(nóng)業(yè)勞動力1.3億人,但還有1.5億的剩余勞動力需要轉(zhuǎn)移[1](第6頁)。我國農(nóng)村人口在全國人口中所占比例較大,占63.91%,而1999年世界平均比例為54%,高收入國家為24%,中等收入國家為34%[2](第143頁)。另外,我國農(nóng)業(yè)勞動力占總勞動力比例1999年達(dá)50%,遠(yuǎn)低于第一次現(xiàn)代化的30%的標(biāo)準(zhǔn),而高收入國家為5%.中等收入國家為32%[2](第141頁)。所以,我國有大量的農(nóng)村勞動力需要轉(zhuǎn)移。從現(xiàn)狀來看,農(nóng)村勞動力轉(zhuǎn)移主要包括向非農(nóng)產(chǎn)業(yè)(第二產(chǎn)業(yè)、第三產(chǎn)業(yè))轉(zhuǎn)移,向鄉(xiāng)鎮(zhèn)企業(yè)轉(zhuǎn)移,向小城鎮(zhèn)及城市轉(zhuǎn)移等幾種轉(zhuǎn)移去向。大量農(nóng)村勞動力的有效轉(zhuǎn)移,對農(nóng)村勞動力教育文化素質(zhì)提出了更高要求,進而表現(xiàn)為對高等教育的需求。
一、西方農(nóng)村勞動力轉(zhuǎn)移理論述評
西方比較有代表性的勞動力轉(zhuǎn)移理論有:一是“劉易斯理論”,認(rèn)為發(fā)展中國家農(nóng)業(yè)部門所擁有的大量剩余勞動力,轉(zhuǎn)移到現(xiàn)代工業(yè)部門的關(guān)鍵在于資本家的利潤投資,隨著農(nóng)村剩余勞動力全部轉(zhuǎn)移到工業(yè)部門,發(fā)展中國家的二元經(jīng)濟變?yōu)橐辉?jīng)濟;二是“拉尼斯—費景漢理論”,特別重視經(jīng)濟轉(zhuǎn)變過程中工業(yè)和農(nóng)業(yè)兩個部門的平衡發(fā)展,指出農(nóng)業(yè)剩余勞動力向工業(yè)轉(zhuǎn)移的先決條件是農(nóng)業(yè)勞動生產(chǎn)率的提高和剩余產(chǎn)品總量的增長,農(nóng)業(yè)剩余勞動力轉(zhuǎn)移的速度取決于人口增長率、農(nóng)業(yè)的技術(shù)進步率和工業(yè)部門資本存量的增長;三是“托達(dá)羅理論”,認(rèn)為農(nóng)村剩余勞動力是否轉(zhuǎn)移到工業(yè)部門的決策,不僅取決于城鄉(xiāng)實際收入差異,而且取決于預(yù)期收入差異,如果流入城市的預(yù)期收入高于農(nóng)業(yè)的就業(yè)收入,即使城市存在失業(yè),人口也會不斷流向城市。
以上第一種理論可理解為工業(yè)化對農(nóng)村勞動力的拉力,第二種理論可理解為農(nóng)業(yè)對勞動人口的推力,第三種理論實質(zhì)上討論的是勞動者的一種心理動機。農(nóng)村勞動力轉(zhuǎn)移實質(zhì)上是個體行為,盡管歷史上存在強迫性遷移活動,但在勞動力轉(zhuǎn)移過程中個體及其心理活動起著很重要的作用。根據(jù)卡托納的經(jīng)濟心理學(xué)模型[3](第37頁),在勞動力轉(zhuǎn)移這一個體行為中,客觀環(huán)境如工業(yè)化的“拉力”和農(nóng)業(yè)的“推力”,并不直接對勞動力轉(zhuǎn)移產(chǎn)生影響,而是客觀環(huán)境對勞動力的心理過程,如愿望、態(tài)度、預(yù)期等產(chǎn)生影響,進而產(chǎn)生轉(zhuǎn)移行為。
根據(jù)現(xiàn)有對經(jīng)濟心理行為的研究,特別是把經(jīng)濟可變因素與個體(心理)可變因素互相結(jié)合起來強調(diào)行為和環(huán)境條件之間的反饋關(guān)系的研究[3](第38頁),認(rèn)為個人是以不同的方式知覺的,對環(huán)境的知覺包括對勞動力轉(zhuǎn)移后的生活氣氛、物價情況、收入情況、個人的社會地位等。這種知覺到的環(huán)境,而不是客觀環(huán)境,決定著人們的轉(zhuǎn)移行為,客觀環(huán)境和知覺到的環(huán)境之間的關(guān)系取決于勞動力轉(zhuǎn)移的經(jīng)驗和個人之間的交流,特別是大眾交流工具。個人因素對環(huán)境知覺也產(chǎn)生作用,這種個人因素包括:個人的目標(biāo)追求、價值、愿望、預(yù)期、認(rèn)知方式,收集信息的能力,對經(jīng)濟和社會發(fā)展的興趣等。勞動力轉(zhuǎn)移行為還會帶來主觀享受,這種享受包括轉(zhuǎn)移后的滿足(或不滿),對轉(zhuǎn)移后職業(yè)的參與,以及從事新職業(yè)獲得的一種認(rèn)知協(xié)調(diào)。
所以,個人素質(zhì)是影響勞動力個體轉(zhuǎn)移心理的重要因素。一是決定了對環(huán)境認(rèn)知的水平、準(zhǔn)確度和全面性,個人對環(huán)境的認(rèn)識是建立在全面把握客觀事物和全面聚集信息的能力基礎(chǔ)之上的。二是影響了個人對收入、社會地位的預(yù)期,具有較高的教育文化素質(zhì)才能較為客觀地估價自己,并有可能得到較高的預(yù)期收入和社會地位。三是影響了個人對轉(zhuǎn)移后的主觀享受,個人素質(zhì)的高低影響了這種主觀享受,教育文化素質(zhì)高的人由于容易得到更多的就業(yè)或高收入的機會而會得到更大的滿足,而教育文化素質(zhì)低的人則由于較少的就業(yè)機會或較低的收入而產(chǎn)生更多的社會問題。四是影響了個人的實際轉(zhuǎn)移質(zhì)量,個人的文化、技能水平?jīng)Q定了其轉(zhuǎn)移后的職業(yè)及收入、社會地位。不了解勞動力個人的心理要求,不完成農(nóng)村勞動力轉(zhuǎn)移的前期教育和培訓(xùn)工作,讓他們沒有充分的心理、能力等素質(zhì)準(zhǔn)備,而實行主觀性或強迫性轉(zhuǎn)移,則不會出現(xiàn)有效的勞動力轉(zhuǎn)移。
二、我國農(nóng)村勞動力轉(zhuǎn)移過程中的主要問題
1.農(nóng)村勞動力轉(zhuǎn)移難度增大。鄉(xiāng)鎮(zhèn)企業(yè)近幾年吸納勞動力的能力減弱,接收農(nóng)村剩余勞動力的數(shù)量趨于減少,如1995年到1999年5年間,鄉(xiāng)鎮(zhèn)企業(yè)接收農(nóng)村剩余勞動力的數(shù)量負(fù)增長5.1%[4](第21頁)。另外,小城鎮(zhèn)吸納勞動力的比重增幅不大,1999年農(nóng)村剩余勞動力轉(zhuǎn)向省會城市的占18.8%,轉(zhuǎn)向地級市的占18.4%,轉(zhuǎn)移到縣城的占16.7%,轉(zhuǎn)移到建制鎮(zhèn)的比重為14.9%[5](第22頁)。可見,作為我國重點發(fā)展的小城鎮(zhèn)吸納勞動力的能力還不強。
2.農(nóng)村勞動力轉(zhuǎn)入第二、第三產(chǎn)業(yè)的比例較低。有抽樣調(diào)查表明,1999年全國農(nóng)村剩余勞動力轉(zhuǎn)移到二、三產(chǎn)業(yè)的人數(shù)占農(nóng)村勞動力總數(shù)的6.4%,按可比口徑比1998年提高了0.4個百分點,轉(zhuǎn)移速度有所上升,但1999年從非農(nóng)產(chǎn)業(yè)返回到農(nóng)業(yè)的勞動力占農(nóng)村勞動力總數(shù)的比重為0.5%,增減相抵,1999年凈轉(zhuǎn)移勞動力占農(nóng)村勞動力總數(shù)的比重為5.9%,比上年上升了僅0.4個百分點[5](第22頁)。
3.農(nóng)村勞動力轉(zhuǎn)移的范圍、地域和領(lǐng)域受到限制,勞動力轉(zhuǎn)移到省外的比重較低。1999年農(nóng)村勞動力在本省內(nèi)轉(zhuǎn)移就業(yè)的占79%,比上年上升11個百分點,轉(zhuǎn)向外省的占20.9%,下降了11個百分點[5](第22頁)。而且勞動密集型行業(yè)、生產(chǎn)建設(shè)第一線和低層次的商業(yè)服務(wù)業(yè)、工業(yè)、建筑業(yè)和其它服務(wù)業(yè)仍是農(nóng)村剩余勞動力轉(zhuǎn)移的主要行業(yè),1999年轉(zhuǎn)移到第二產(chǎn)業(yè)的勞動力占54.2%,轉(zhuǎn)移到第三產(chǎn)業(yè)的為41.7%,到異地仍然從事第一產(chǎn)業(yè)的占4.1%,轉(zhuǎn)移到工業(yè)、建筑業(yè)和商飲服務(wù)業(yè)的比重高達(dá)79.4%[4](第21頁)。
農(nóng)村勞動力轉(zhuǎn)移的難度增大,難以向城鎮(zhèn)和非農(nóng)產(chǎn)業(yè)轉(zhuǎn)移,并且轉(zhuǎn)移的范圍、地域和領(lǐng)域受到限制,其原因除政策壁壘因素外,還存在著教育壁壘,即與勞動力的教育文化水平有密切關(guān)系。
三、農(nóng)村勞動力的教育文化水平與勞動力轉(zhuǎn)移的關(guān)系分析
(一)勞動力教育文化水平與勞動力轉(zhuǎn)移的難易度
教育文化水平低的勞動力通常只能滯留于依靠傳統(tǒng)經(jīng)驗生產(chǎn)的有限領(lǐng)域,很難開拓新的就業(yè)門路和工作機會,也難以適應(yīng)轉(zhuǎn)移后的工作和生活;而受教育程度高的人,往往思維開闊,易于接受新事物,具有更強的自信,更高的收入、社會預(yù)期以及更強的創(chuàng)新意識和冒險精神,更易于實現(xiàn)有效轉(zhuǎn)移。根據(jù)蓋爾·約翰遜的研究,農(nóng)村中大量低素質(zhì)的勞動力增加了向城市轉(zhuǎn)移和管理的成本,而農(nóng)村人口素質(zhì)的提高可以大大減少城市居民對于遷居城市的農(nóng)村人口的抵觸,更能使農(nóng)村人口盡快地適應(yīng)城市生活,并減少城市管理成本[6](第62頁)。我國農(nóng)村勞動力轉(zhuǎn)移的現(xiàn)實也表明,受教育程度越高,越易于實現(xiàn)轉(zhuǎn)移。據(jù)對山東聊城市的調(diào)查,在1998、1999兩年轉(zhuǎn)移的勞動力中,具有大專文化程度的勞動力由于在當(dāng)?shù)剌^為受重視,盡管轉(zhuǎn)移的并不多,但轉(zhuǎn)移起來相對容易;具有初高中文化程度的勞動力比重最大,占55.6%,接受過專業(yè)培訓(xùn)的占18.7%,高中以上文化程度的勞動力每百人中有10.3人轉(zhuǎn)移,初中文化程度的每百位農(nóng)村勞動力中有8.4人轉(zhuǎn)移,小學(xué)文化程度的每百位勞動力有4.5人轉(zhuǎn)移,文盲、半文盲每百位勞動力中有1.3人轉(zhuǎn)移。
(二)勞動力教育文化水平與轉(zhuǎn)移后的職業(yè)狀況
勞動力受教育程度與掌握和熟練運用新的工種和技術(shù)有直接聯(lián)系。我國1999年轉(zhuǎn)移到工業(yè)、建筑業(yè)和商飲服務(wù)業(yè)的農(nóng)村勞動力比重高達(dá)79.4%,說明我國農(nóng)村勞動力教育文化水平還不高。而教育文化水平越高的勞動力,越易于適應(yīng)新的工作和環(huán)境,越易掌握新的工種、新技術(shù)、新工藝、新設(shè)備,使用效果也越好,所以,教育文化素質(zhì)、技術(shù)水平與就業(yè)狀況呈正相關(guān)。美國的歷史也證明了這一觀點,美國農(nóng)村勞動力轉(zhuǎn)移高峰期的19世紀(jì)90年代至20世紀(jì)20年代,流入城市的白人和黑人在就業(yè)方面出現(xiàn)很大差距,除民族和關(guān)系網(wǎng)原因外,文化程度差異也是重要原因。
勞動力教育文化水平對轉(zhuǎn)移后職業(yè)的穩(wěn)定性有顯著作用,水平的高低是影響職業(yè)穩(wěn)定性的決定因素之一。1987年已轉(zhuǎn)移的農(nóng)村勞動力回流中,文盲高達(dá)21%,初中以下文化水平的為17.16%,初中以上文化水平的占9.46%,中專及大專以上回流的則很少[7](第29頁)。究其原因,其一便是由于教育文化素質(zhì)差,思想保守,難于適應(yīng)新的環(huán)境和條件;其二是參加技術(shù)革新的人員所提合理化建議與技術(shù)革新創(chuàng)造的價值等,與受教育文化水平成正比關(guān)系,且隨著教育文化水平的提高,事故發(fā)生率明顯減少。教育文化水平高的勞動力創(chuàng)新性越強,職業(yè)穩(wěn)定性越強,也易于完成職業(yè)或技術(shù)的轉(zhuǎn)換。教育文化水平越高,越有可能率先離開農(nóng)業(yè),長時間脫離農(nóng)業(yè),實現(xiàn)有效轉(zhuǎn)移。
(三)勞動力教育文化水平與轉(zhuǎn)移后的收入
勞動力的收入首先取決于個人的以教育文化水平為主的人力資本投資,為此有學(xué)者得出反貧困的措施是提高移民的素質(zhì)的結(jié)論。在所調(diào)查的山東聊城五個鄉(xiāng)鎮(zhèn)企業(yè)的職工月平均工資為356元,大多職工工資在200-400元之間,而工資在400元以上的有58%為專業(yè)技術(shù)學(xué)校畢業(yè)生,該企業(yè)中僅有的三個大專生的收入都在360元以上。其它相關(guān)調(diào)查也表明,越來越多的教育水平較高的勞動力參與了轉(zhuǎn)移,而且每增加一年的教育水平每年可增加匯寄款149元[8](第3頁)。原因是,勞動力的教育文化程度與勞動生產(chǎn)率具有較強的正相關(guān),相關(guān)系數(shù)達(dá)0.73[9](第58頁),教育文化水平較高的人擁有較高的人力資本,對生產(chǎn)率的提高起到促進作用,較高的生產(chǎn)率則帶來較高的收入,且轉(zhuǎn)移后的職業(yè)穩(wěn)定性也高。
(四)勞動力教育文化水平與勞動力轉(zhuǎn)移區(qū)間
農(nóng)村勞動力教育文化水平是決定其轉(zhuǎn)移方向、距離的重要因素,轉(zhuǎn)向發(fā)達(dá)地區(qū)勞動力的文化程度高于轉(zhuǎn)向落后地區(qū)的勞動力。1999年在轉(zhuǎn)向東部的勞動力中,初中以上文化程度的比重為11.5%,轉(zhuǎn)向中部的比重為10.9%,轉(zhuǎn)向西部的比重為9.1%[5](第22頁)。沒有技術(shù)特長,沒有高的素質(zhì),期望收入也就較低,而且較低的文化水平又決定了他們相對保守的思想意識,往往對自己轉(zhuǎn)移到城市缺乏信心,難以對城市產(chǎn)生認(rèn)同感,他們更多地留戀故鄉(xiāng)。
(五)勞動力教育文化素質(zhì)與勞動力轉(zhuǎn)移后的社會問題
國內(nèi)外勞動力轉(zhuǎn)移的歷史表明,社會問題的引發(fā)與勞動力素質(zhì)有關(guān)。中國近代農(nóng)民離村進城,是被迫的,既沒有充分的思想準(zhǔn)備,也不具備謀生能力,更沒有知識的積累,他們進入城市后,難以找到合適的職業(yè),多數(shù)人不得不靠出賣苦力謀生,引發(fā)了城市的無序及城市治安等問題。在歐美,農(nóng)村剩余勞動力的轉(zhuǎn)移由于太大的盲目性,不可避免地也出現(xiàn)了諸如住房擁擠、生態(tài)環(huán)境惡化、失業(yè)和貧困嚴(yán)重、犯罪率上升等一系列社會問題,德國為此實行了國家強制干預(yù),增加對教育的投入,進行了各種類型的職業(yè)培訓(xùn),促進了教育事業(yè)的發(fā)展,為工業(yè)和整個社會的發(fā)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礎(chǔ),也有效地緩解了城市問題[10](第233頁)。所以為避免引發(fā)勞動力轉(zhuǎn)移后的社會問題,應(yīng)做好農(nóng)村勞動力轉(zhuǎn)移前的素質(zhì)準(zhǔn)備,將教育和培訓(xùn)貫穿于勞動力轉(zhuǎn)移的整個過程中。
四、農(nóng)村勞動力轉(zhuǎn)移對高等教育的需求
不斷提高農(nóng)村勞動力的教育文化素質(zhì),是實現(xiàn)農(nóng)村勞動力有效轉(zhuǎn)移的前提條件之一。日本、韓國能順利完成產(chǎn)業(yè)結(jié)構(gòu)轉(zhuǎn)換和充分就業(yè)的根本條件之一,就是教育合理地超前發(fā)展,有效地提高了全國就業(yè)人口的平均文化技術(shù)素質(zhì),第一產(chǎn)業(yè)就業(yè)人口能夠適應(yīng)非農(nóng)經(jīng)濟新技術(shù)新領(lǐng)域的需要,較為順利地完成了勞動力轉(zhuǎn)移。美國在1930年到1974年間,從農(nóng)業(yè)轉(zhuǎn)移出去的人口總數(shù)達(dá)到了3280萬人,這是現(xiàn)代最大的人口轉(zhuǎn)移,而恰恰在這一時期是高等教育,特別是社區(qū)學(xué)院的大發(fā)展時期(注:美國社區(qū)學(xué)院由1930年的436所增加到1974年的1203所,增加767所。參見毛澹然。美國社區(qū)學(xué)院[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89.)。
中國解決農(nóng)村剩余勞動力轉(zhuǎn)移的當(dāng)務(wù)之急就是提高勞動力素質(zhì),農(nóng)村勞動力教育文化素質(zhì)不高是我國農(nóng)村勞動力結(jié)構(gòu)的重要特征。在我國農(nóng)村勞動力中,初中及以下程度勞動力的比重高達(dá)88.4%,高中程度的為9.6%,中專程度的為1.6%,大專及以上程度的比重為0.4%[4](第21頁)。非農(nóng)部門對勞動力素質(zhì)要求越來越高,對勞動總量特別是低素質(zhì)勞動力的需求不斷下降,所以必須提高現(xiàn)有勞動力素質(zhì)和技術(shù)水平,才能實現(xiàn)農(nóng)村勞動力向城鎮(zhèn)、鄉(xiāng)鎮(zhèn)企業(yè)、非農(nóng)產(chǎn)業(yè)等的有效轉(zhuǎn)移。
提高我國的城鎮(zhèn)化水平和農(nóng)村勞動力向城鎮(zhèn)轉(zhuǎn)移是大勢所趨,我國國民經(jīng)濟和社會發(fā)展第十個五年計劃即提出了“提高城鎮(zhèn)化水平,轉(zhuǎn)移農(nóng)村人口,可以為經(jīng)濟發(fā)展提供廣闊的市場和持久的動力”的意見。但農(nóng)村勞動力轉(zhuǎn)移到城鎮(zhèn),實現(xiàn)由農(nóng)民向城鎮(zhèn)居民的根本轉(zhuǎn)變,存在著“教育壁壘”,即農(nóng)村勞動力總體教育文化素質(zhì)較低,大多為非熟練技術(shù)人員,缺乏專門的技術(shù)培訓(xùn)和學(xué)習(xí),只能在臟、苦、累的體力部門就業(yè)。各類城鎮(zhèn)部門對勞動力的素質(zhì)有越來越高的要求,農(nóng)村剩余勞動力由于其過低的文化教育水平很難達(dá)到要求,從而增加了轉(zhuǎn)移的難度。所以,農(nóng)村勞動力轉(zhuǎn)移到城鎮(zhèn),需要提高其教育文化素質(zhì)。我國現(xiàn)有的1.5億農(nóng)村剩余勞動力,大專以上學(xué)歷的最多僅為0.4%,遠(yuǎn)低于全國平均3.6%的比例,要實現(xiàn)農(nóng)村勞動力的有效轉(zhuǎn)移,必須提高其教育文化水平,使更多的農(nóng)村勞動力接受教育,包括高等教育。在農(nóng)村剩余勞動力的轉(zhuǎn)移總量中,大約只有12%轉(zhuǎn)移到了各類城鎮(zhèn)部門,其余88%的勞動力仍是在農(nóng)村工業(yè)、商業(yè)及服務(wù)業(yè)部門實現(xiàn)產(chǎn)業(yè)轉(zhuǎn)移的,即使按目前的農(nóng)村勞動力轉(zhuǎn)入城鎮(zhèn)的比例,也將有50多萬的農(nóng)村勞動力接受高等教育以進入城鎮(zhèn)部門。
鄉(xiāng)鎮(zhèn)企業(yè)也會吸引更多的農(nóng)村剩余勞動力。制約鄉(xiāng)鎮(zhèn)企業(yè)發(fā)展的主要因素之一便是勞動力素質(zhì),鄉(xiāng)鎮(zhèn)企業(yè)將對高素質(zhì)勞動力有較大需求,吸納的將是教育文化素質(zhì)更高、思想更為活躍的高級專門人才。鄉(xiāng)鎮(zhèn)企業(yè)對農(nóng)村勞動力的吸納能力,有學(xué)者用線性外推法和生產(chǎn)函數(shù)兩種方法對今后我國鄉(xiāng)鎮(zhèn)企業(yè)的勞動力需求做出了情景性描述和預(yù)測,得出了鄉(xiāng)鎮(zhèn)企業(yè)每年要吸納200-350萬勞動力的結(jié)論[11](第25頁)。全國鄉(xiāng)鎮(zhèn)企業(yè)職工中,大專以上學(xué)歷人數(shù)比例為2.3%[12](第355頁),按這一最低標(biāo)準(zhǔn)要求轉(zhuǎn)移進鄉(xiāng)鎮(zhèn)企業(yè)的勞動力,則每年至少有4.6萬人,到2010年至少要有37萬人接受高等教育以進入鄉(xiāng)鎮(zhèn)企業(yè);如果從發(fā)展的角度,按鄉(xiāng)鎮(zhèn)企業(yè)發(fā)展“十五”計劃的標(biāo)準(zhǔn)來要求,則有更多的農(nóng)村勞動力需要接受高等教育以進入鄉(xiāng)鎮(zhèn)企業(yè)。
從吸納農(nóng)村剩余勞動力的產(chǎn)業(yè)結(jié)構(gòu)角度來分析,第三產(chǎn)業(yè)也將是吸納農(nóng)村勞動力的重要渠道。我國第三產(chǎn)業(yè)的發(fā)展還有較大空間,1998年我國第三產(chǎn)業(yè)增加值占GDP 的比重僅為33%,而全世界第三產(chǎn)業(yè)增加值占GDP的比重為61%,發(fā)達(dá)國家平均為65%,其中美國為71%;中等收入國家(人均2950美元)平均為56%,其中高中等收入國家(人均4860美元)平均為57%,低中等收入國家(人均1710美元)平均為52%[13](第93,94頁)。如果我國這一比重上升到55%,第三產(chǎn)業(yè)就業(yè)人數(shù)占全社會就業(yè)人數(shù)的比重為50%,在其它條件不變的情況下,第三產(chǎn)業(yè)將吸納16000萬勞動力。如果按既定的10年的時間實現(xiàn)這一調(diào)整目標(biāo),則平均每年有1600萬農(nóng)村勞動力轉(zhuǎn)移到第三產(chǎn)業(yè),這些勞動力如果能達(dá)到現(xiàn)在全國人口中具有大專以上文化程度人數(shù)3.6%的比例,平均每年有57萬農(nóng)村勞動力需要接受高等教育以有效轉(zhuǎn)移到第三產(chǎn)業(yè)。
勞務(wù)輸出也將是農(nóng)村勞動力轉(zhuǎn)移的渠道之一。我國勞務(wù)輸出有較大潛力,勞動力資源占世界勞動力資源的20%,而勞務(wù)輸出僅占世界勞務(wù)輸出的3%[4](第23頁)。現(xiàn)在國際上流動的勞務(wù)人數(shù)達(dá)2000多萬,中東地區(qū)有上千萬億美元的勞務(wù)市場,俄羅斯開發(fā)遠(yuǎn)東地區(qū)也需要從國外輸入幾百萬勞動力。但國際勞務(wù)輸出對勞務(wù)人員的素質(zhì)要求較高,一般是掌握一門或一門以上某種技術(shù)和外語的技術(shù)工人,甚至是高級專門技術(shù)人員,我國農(nóng)村剩余勞動力中達(dá)到要求的則很少,勞務(wù)輸出單位有時很難找到符合要求的勞務(wù)人員,故提高農(nóng)村剩余勞動力的教育文化水平是增加勞務(wù)輸出的首要條件。如果將我國勞務(wù)輸出的比例提高到世界勞務(wù)輸出的8%,則會輸出100多萬剩余勞動力,100多萬勞動力的教育和培訓(xùn)將會產(chǎn)生極大的高等教育需求。
總之,我國數(shù)量龐大的農(nóng)村剩余勞動力,要轉(zhuǎn)化為人力資源優(yōu)勢,必須實施科教興國戰(zhàn)略,需要發(fā)展教育事業(yè),以提高農(nóng)村勞動力的綜合素質(zhì),實現(xiàn)由農(nóng)民向市民的轉(zhuǎn)化。促進農(nóng)村剩余勞動力的有效轉(zhuǎn)移,一要提高農(nóng)村勞動力的技術(shù)和職業(yè)素質(zhì)。農(nóng)村剩余勞動力轉(zhuǎn)移不是簡單的地域流動、職業(yè)改變,而應(yīng)是勞動力人力資本提高的過程和結(jié)果,要通過教育和職業(yè)培訓(xùn)提高勞動力素質(zhì),提高人力資源開發(fā)水平;二要提高農(nóng)村勞動力的綜合教育文化素質(zhì)和修養(yǎng)。農(nóng)村勞動力實現(xiàn)有效轉(zhuǎn)移,不僅限于技術(shù)的培訓(xùn)和職業(yè)素質(zhì)的提高,還應(yīng)有綜合教育文化素質(zhì)和修養(yǎng)的提高,以盡快適應(yīng)轉(zhuǎn)移后的工作和生活,促進城市文明的發(fā)展。我國在實現(xiàn)城鎮(zhèn)化,及農(nóng)村勞動力轉(zhuǎn)向城市的過程中,要保證并促進城市的文明程度,形成并保護“城市的空氣”。這種“空氣”或稱“市氣”實質(zhì)上是一種氛圍,是一種自由、民主、文明的文化環(huán)境。這種氛圍的營造需要轉(zhuǎn)入城市的農(nóng)村勞動力有較高的素質(zhì)和較快的適應(yīng)能力。“人氣”足,“市氣”才旺,只有大力培育教育市場,提高人的總體素質(zhì),才會有“市氣”,不可一味地追求圈地運動,重土、重城而不重市,不重人。農(nóng)村勞動力進入城市之前,需要具備較高的綜合素質(zhì),這種基本素質(zhì)需要通過教育,包括高等教育來完成。
對農(nóng)村勞動力的教育也不僅是在轉(zhuǎn)移前,更應(yīng)該貫穿于轉(zhuǎn)移中和轉(zhuǎn)移后的整個過程中。對轉(zhuǎn)移前的農(nóng)村勞動力,要有一最低教育文化水平的要求,對未能達(dá)到最低水準(zhǔn)的人,要進行較為系統(tǒng)的培訓(xùn)和教育,提高他們的素質(zhì);要為轉(zhuǎn)移后的勞動力提供適當(dāng)?shù)慕逃h(huán)境,為他們的繼續(xù)教育創(chuàng)造條件,有針對性地提高他們的專業(yè)技術(shù)水平和文化素養(yǎng),為那些需要而又有能力接受高等教育的人創(chuàng)造教育機會。
「參考文獻(xiàn)」
[1]農(nóng)業(yè)部課題組。21世紀(jì)初期我國農(nóng)村就業(yè)及剩余勞動力利用問題研究[J].中國農(nóng)村經(jīng)濟,2000,(5)。
[2]中國現(xiàn)代化戰(zhàn)略研究課題組。中國現(xiàn)代化報告2002[R].北京:北京大學(xué)出版社,2002.
[3]俞文釗。市場經(jīng)濟中的人的經(jīng)濟心理與行為[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8.
[4]國家統(tǒng)計局農(nóng)村社會經(jīng)濟調(diào)查總隊社區(qū)處。就業(yè)與流動:從人力資源向人力資本的轉(zhuǎn)變——1999年我國農(nóng)村勞動力流動狀況分析[J].調(diào)研世界,2000,(8)。
[5]國家統(tǒng)計局農(nóng)村社會經(jīng)濟調(diào)查總隊。1999年農(nóng)村勞動力轉(zhuǎn)移有喜有憂[J].調(diào)研世界,2000,(6)。
[6]蓋爾·約翰遜。中國農(nóng)業(yè)調(diào)整:問題和前景[J].經(jīng)濟學(xué)家,1999,(6)。
[7]陳冰。農(nóng)村剩余勞動力轉(zhuǎn)移趨緩問題[J].人口研究,1989,(2)。
[8]崔榮慧。一個不容忽視的戰(zhàn)略問題:中國農(nóng)村勞動力的流動[N].中國經(jīng)濟時報,2001-07-09.
[9]譚友林。中國勞動力結(jié)構(gòu)的區(qū)域差異研究[J].人口與經(jīng)濟,2001,(1)。
[10]王章輝,等。歐美農(nóng)村勞動力的轉(zhuǎn)移與城市化[M].北京:社會科學(xué)出版社,1999.
[11]張忠法,等。我國十五及以后一個時期重點培育勞動力大容量轉(zhuǎn)移載體的歷史任務(wù)[J].社會科學(xué)研究參考資料,2001,(1)。
[12]中華人民共和國農(nóng)業(yè)部。中國農(nóng)業(yè)年鑒2000[Z].北京:中國農(nóng)業(yè)出版社,2001.
[13]李子奈。如何轉(zhuǎn)移農(nóng)村剩余勞動力[J].經(jīng)濟學(xué)家,2000,(4)。
大法律評論.jpg)
代中國文學(xué)論叢.jpg)
品安全與召回.jpg)
.jp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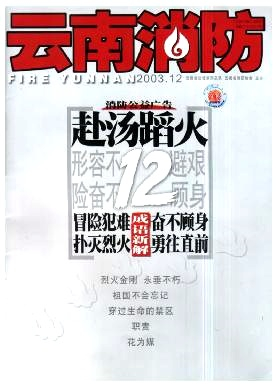
于我們.jpe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