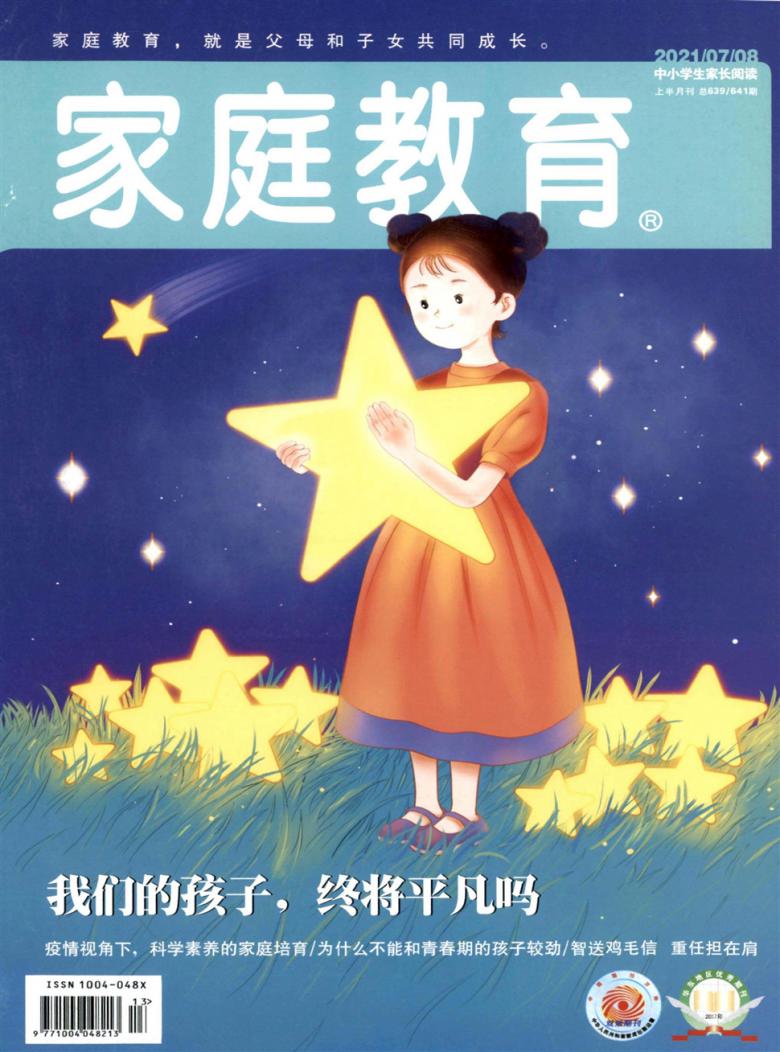帝王詩、帝王氣象及專制情結
毛翰
中國的帝王詩起于何時?第一首帝王詩系何人所作?
相傳早在三代之前,舜帝就曾彈五弦琴,唱《南風歌》:“南風之薰兮,可以解吾民之慍兮;南風之時兮,可以阜吾民之財兮。”舜帝在位十四年,禪位于禹,又作《卿云歌》:“卿云爛兮,糺縵縵兮。日月光華,旦復旦兮。”群臣進頌:“明明上天,爛然星陳。日月光華,弘予一人。”舜帝再歌:“日月有常,星辰有行。四時從經,萬姓允誠。于予論樂,配天之靈。遷于圣賢,莫不咸聽。鼚乎鼓之,軒乎舞之。精華以竭,褰裳去之。”前者出于《孔子家語》,后者出于《尚書大傳》,皆為歷史傳說,未可盡信。
《詩經·周頌》中《閔予小子》《敬之》《小毖》等篇被認為是周成王所作。其中《敬之》一篇:“敬之敬之,天維顯思。命不易哉,無曰高高在上。陟降厥士,日監在茲。維予小子,不聰敬止。日就月將,學有緝熙于光明。佛時仔肩,示我顯德行。”一般認為是周成王自勉之作。
《樂府詩集·琴曲歌辭》有數篇系于堯、舜、禹、周文王、武王、成王等名下,多為后人偽托。另有《黃竹歌》三章,相傳是周穆王所作。《穆天子傳》說,周穆王外出打獵,在風雪嚴寒中見凍餒之人,作詩憫之。詩云:“我徂黃竹,□員閟寒,帝收九行。嗟我公侯,百辟冢卿,皇我萬民,旦夕勿忘。……”相信也是后人偽托。
接下來,秦始皇有一首《祠洛水歌》,真偽莫辨。據《古今樂錄》記載,秦始皇祭祀洛水,有“黑頭公”從河中出,呼始皇曰:“來受天寶。”始皇相信此乃天意傳國于秦,遂與群臣高歌:“洛陽之水,其色蒼蒼。祠祭大澤,倏忽南臨。洛濱醊禱,色連三光。”
秦失其德,群雄起代,項羽、劉邦各有一篇絕唱留給詩史。后人眼中的中國帝王詩,往往從《垓下歌》和《大風歌》開始。不過,由于項羽的帝王身份不確,人們更為認同劉邦。“《大風》三言,氣籠宇宙,張千古帝王赤幟,高帝哉?”[①]其實,滅秦之后,項羽分封天下,共立十八王,漢王劉邦只是其中之一,而項羽自號西楚霸王,實為天下盟主。其西楚,應該視為秦漢之間的一個短暫的王朝。司馬遷作《史記》,就給了項羽一篇只有帝王才配享有的“本紀”。今之歷史年表,以漢直接承秦,未免過于粗略。而項羽《垓下歌》作于公元前202年自刎烏江之時,劉邦《大風歌》作于公元前195年東討淮南王英布途中,前后相差七年,如果略過先秦那字跡模糊的幾頁,中國帝王詩史是不妨從《垓下歌》開始的。
而帝王詩的尾聲,一般認為,當在清末帝溥儀。溥儀三歲登基,六歲退位,他的詩都是退位之后所作,包括八歲那年為師傅陳寶琛祝壽作的第一首詩:“松柏哥哥,終寒不凋。訓予有功,長生不老。”退位帝王所作的詩,應該還算作帝王詩,否則南唐后主李煜的許多亡國絕唱就都不能算數了。
但中國的帝制,到辛亥革命并沒有徹底結束。且不說后來張勛復辟的鬧劇和偽滿州國傀儡皇帝,民國四年,袁世凱還煞有介事地稱過一回帝。袁世凱的詩該不該入選?這是頗費斟酌的。從情感上說,此人冒天下之大不韙,倒行逆施,為了滿足一己無限膨脹的權欲,不惜剝奪天下人的民主自由權利,我們決不承認這家伙是什么皇上。然而,盡管只做了八十三天皇帝夢,但他畢竟在中華民國總統任上,宣布過廢除民國國號,恢復帝制,改元“中華帝國洪憲”。袁世凱稱帝固然不得人心,但歷朝歷代哪一帝王又是人民選舉的呢?民心民意算什么,只要槍桿子在握,何愁不能黃袍加身?袁世凱這個“中華帝國洪憲皇帝”的迅速倒臺,并不因為革命黨聲討,并不因為民心背棄,而主要在于他所締造和統帥的北洋軍閥的倒戈。須知民心是可以教化的,民意是可以訓導的,受過幾千年君主專制的統治和愚弄的中國人民,其時還多盼著“真龍天子”重出神州呢!(有時我想,日寇投降后,如果歷史一念之差,讓金日成入主南朝鮮,讓李承晚開赴北朝鮮,不出幾年,漢城群眾不抹淚歡呼慈父般的領袖,平壤街頭沒有反獨裁爭民主的游行,那才叫怪了。)故而,我編《歷代帝王詩》[②],就在溥儀之后,狗尾續貂式的補選了袁世凱一首。
《歷代帝王詩》該不該選***本關鍵字已替換***的詩?這也是一個有趣的問題。***本關鍵字已替換***當然不是帝王,1949年在天安門前舉行的是共和國開國大典,不是新皇登基大典。但***本關鍵字已替換***無帝王之名,卻有帝王之實;無帝王之號,卻有帝王之氣。而且說***本關鍵字已替換***是“無冕之王”也未必恰切,他不曾南面稱帝,卻欣然受用過“萬歲”“萬壽無疆”之類的歡呼歌頌。據學者考證,“萬歲”一語還在東漢就皇家化了,唐代以后,萬歲更成為皇帝的代稱,萬歲就是皇帝,皇帝就是萬歲,就是萬歲爺,其他人等是絕對不得僭越的,魏忠賢權傾天下也不過“九千歲”,慈禧太后垂簾聽政四十余年也不過“太后千秋”。況且***本關鍵字已替換***一言九鼎,“春來我不先張口,哪個蟲兒敢作聲?”他的每一句話都曾是“最高指示”,這也只能是帝王風范。故拙編《歷代帝王詩》依體例未選***本關鍵字已替換***之作,卻在前言里援引其《沁園春·雪》“江山如此多嬌”以下半闋,以為某種名實之副。
此外,曹操一代梟雄,其詩才情縱橫,睥睨千古,歷代帝王詩無出其右者,然而曹操一生并不曾稱帝。“魏武帝”曹操,以及“晉宣帝”司馬懿的帝號,都是其后代子孫奪得天下后追封的,嚴格說來,都是不大能算數的。想必朱元璋其人就對曹操、司馬懿的帝號很不滿,曾以歸謬法(即用更為荒謬的做法與之類比,以見其謬)予以否定。朱元璋一上臺,就追封自己的田舍翁爹、叫花子娘為皇帝皇后。史載,洪武元年,朱元璋追封其高祖父朱百六為玄皇帝,廟號德祖;曾祖父朱四九為恒皇帝,廟號懿祖;祖父朱初一為裕皇帝,廟號熙祖;父朱五四為淳皇帝,廟號仁祖。妣皆皇后。(百六、四九、初一、五四,聽聽這些叫花子名!朱元璋自己原名重八,屬于同一系列。)如果其幾代“先皇”中恰好有人做過幾行打油詩蓮花落,是否也要忝列《歷代帝王詩》呢?刻薄了,曹公不曾稱帝,畢竟已是魏王,挾天子令諸侯,是天下的實際統治者,絕非朱重八的叫花子先皇可比。當然,曾經稱帝與否,其詩在氣象上還是有差別的。司馬懿奉魏明帝曹叡之命出討遼東,途經故里,歌以詠懷,前面八句何等豪邁:“天地開辟,日月重光。遭遇際會,畢力遐方。將掃群穢,還過故鄉。肅清萬里,總齊八荒。”最后卻出以韜晦之語,低調結束:“告成歸老,待罪舞陽。”無奈縱有經天緯地之才,覬覦乾坤之志,一生終為人臣。
至于帝王詩篇間有御用文人代筆者,前人已有論及,如唐太宗、武則天以及清乾隆帝的某些作品。讀者心中有數就是了,一一辨析則不是本文作者力所能及的。
2
從主題和風格看,帝王詩可分兩類,一類是典型的帝王之詩,表達的是典型的帝王懷抱、志趣,洋溢著典型的王者氣象,另一類抒寫的則只是普通人的情懷,不大能看出作者的特殊身份。
“王者之氣”為人樂道。何謂王者之氣?似不外乎爭奪天下的狂氣、解救天下的正氣、一統天下的霸氣、感召天下的雅氣,以及喪失天下的怨氣。
秦始皇出巡,威儀萬千,看得劉邦眼饞:“嗟乎,大丈夫當如此也!”看得項羽心動:“彼可取而代之。”此種爭奪天下的狂氣,以詩表達,就有落第舉子黃巢的一再詠菊:“待到秋來九月八,我花開后百花殺。”“他年我若為青帝,報與桃花一處開。”就有朱元璋帶兵征戰露宿曠野時的“天如羅帳地如氈,日月星辰陪我眠。一夜不敢伸足睡,惟恐蹬倒太行山。”此輩梟雄,代不乏人,成者為王,敗者為寇。趙匡胤稱帝前,有詩《詠初日》:“一輪頃刻上天衢,逐退群星與殘月。”有詩《詠月》:“未離海底千山黑,才到中天萬國明。”登極之后,人以為詩讖。金廢帝完顏亮一向野心勃勃,奪位之前,就多次以詩明志。其詠竹詩云:“孤驛瀟瀟竹一叢,不聞凡卉媚東風。我心正與君相似,只待云梢拂碧空。”其詠龍詩云:“蛟龍潛匿隱蒼波,且與蝦蟆作混和。等待一朝頭角就,撼搖霹靂震山河。”見瓶中一枝巖桂,也慨然嘆曰:“綠葉枝頭金縷裝,秋深自有別樣香。一朝揚汝名天下,也學君王著赭黃。”可嘆天命不濟,過了一把帝王癮,就兵敗被殺,廢為庶人,徒為天下笑耳。到太平天國洪秀全,更是狂氣十足:“一張天榜蔑古賢,文王武王皆是犬。屈指盤古迄明世,風流數我洪秀全。”據史料[③]記載,洪秀全以黃緞數匹作“天榜”,上書七言韻句,上自盤古,下迄明末(“清妖”自不足掛齒),君臣史實,悉加品評。遇“帝”字一律不用,“王”字則加“犬”旁,如文王、武王,作“文狂”、“武狂”,以避其“天王”之諱。其狂傲愚妄簡直到了無以復加的地步。
解救天下的正氣,對于帝王無疑是最可寶貴的了。“白骨露于野,千里無雞鳴。生民百遺一,念之斷人腸。”曹操《蒿里行》詩中哀民救民的情懷無疑是真摯的。但這民不聊生的慘象是漢祚衰微和軍閥混戰造成的,詩人自己并不負多少責任,詩中有的只是重造時世的使命感,而非自責。后世帝王詩歌,間有憐憫百姓苦難、檢討自己統治失誤的。如果說唐玄宗李隆基登太行山,見“野老茅為屋,樵人薜作裳”,即或有自責之意,也只是虛晃一槍,那么,明宣宗朱瞻基《憫旱詩》就真誠得多了:“亢陽久不雨,夏景將及終。禾稼紛欲槁,望霓切三農。祠神既無益,老壯憂忡忡。饘粥不得繼,何以至歲窮?予為兆民主,所憂與民同……”驕陽似火,旱禾絕收,百姓饑腸轆轆,君王憂從中來。其《示吏部尚書夏原吉》更以“無道”自責,簡直要下罪己詔了:“關中歲屢歉,民食無所資。郡縣既上言,能不軫恤之?”“吾聞有道士,民免寒與饑。循己不遑寧,因請書愧詞。”可惜此種帝王襟懷古今少有,人們熟知的是晉惠帝司馬衷的故事,《資治通鑒》記載:時天下饑饉,百姓餓死,帝聞之曰:“何不食肉糜?”或者,任憑人間餓殍遍野,冤氣彌天,孤王筆下總是芙蓉滿目,鶯歌盈耳,無限風光。
一統天下的霸氣,在劉邦那里還兼有幾分憂思:“威加海內兮歸故鄉,安得猛士兮守四方?”在南朝宋文帝劉義隆《北伐詩》里還兼有幾分焦慮:“自昔淪中畿,倏焉盈百祀。不睹南云陰,但見胡塵起。”“逝將振宏綱,一麾同文軌。”到李世民貞觀年間《正日臨朝》就只拌著得意和驕態了:“條風開獻節,灰律動初陽。百蠻奉遐贐,萬國朝未央。雖無舜禹跡,幸欣天地康。車軌同八表,書文混四方。”一代女皇武則天稱霸人間久了,對司春的神靈也不改喝令口吻,其《臘日宣詔幸上苑》詩云:“明朝游上苑,火急報春知。花須連夜發,莫待曉風吹。”君主們的霸氣從何而來?來處大致有二:君權神授的理論,萬民臣服的現實。“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這種圣人之言聽得多了,不由你不驕橫悍厲,目空一切。如今有一位擅扮皇上的影視演員談表演經驗,說看著眾人口稱奴才,山呼萬歲,在他面前跪倒一大片,那份普天之下唯我獨尊的感覺就不禁油然而生了。一介戲子尚能生出如此幻覺,何況天子臨朝每日排演君臣大禮呢?是呀,帝王之所以獨霸后宮,是因為后宮男人的器官都被閹割了;帝王之所以獨霸天下,是因為天下男人的精神都被閹割了。一統天下的霸氣,表現在武功方面,就是要開疆辟土,消滅任何不臣勢力,使“耕鑿從今九壤同”[④];表現在文治方面,就是要推行教化,鏟除一切異端思想,使“天下歸心”[⑤]。最讓君王開心的是,“天下英雄盡入吾彀中”[⑥],“為王前驅”[⑦]。
此外,王者之氣也應包括感召天下的雅氣。畢竟在我們這個文明古國,人民臣服強權,更崇尚文化,儒雅的統治者更能得到人民的認同和擁戴。馬上可以得天下,馬上卻不能治天下,這句名言也應該包括文化感召這一層涵義。漢家天子自不必說,歷代入主中原的少數民族統治者,明智的,也紛紛漢化、文化起來,其漢化、文化的標志之一,就是學作漢詩。遼道宗耶律洪基《題李儼黃菊賦》:“昨日得卿黃菊賦,碎剪金英填作句。至今襟袖有余香,冷落西風吹不去。”意象之美,運思之妙,詩史為之訝異。金主完顏亮《南征至維揚望江東》:“萬里車書盡混同,江南豈有別疆封?提兵百萬西湖上,立馬吳山第一峰!”宋人就算亡國了,讀此詩,也應有不少鎮痛作用,畢竟亡于此君總比亡于化外野蠻部族要讓人好受些。“只識彎弓射大雕”的成吉思汗的子孫,幾經南風熏陶,到元文帝圖帖睦爾《自集慶路入正大統途中偶吟》,已能吟出這樣純正而不乏創意的律詩:“穿了氁衫便著鞭,一鉤殘月柳梢邊。二三點露滴如雨,六七個星猶在天。犬吠竹籬人過語,雞鳴茅店客驚眠。須臾捧出扶桑日,七十二峰都在前。”清朝順治帝以后,無一帝無詩集,乾隆帝弘歷一生作詩更達四萬多首,為古今詩人之冠,諒非涂鴉一語所能全盤抹殺。到20世紀40年代,一首“還看今朝”的《沁園春》在霧都重慶發表,讓許多潛意識里仍然寄望于救世英主的國人,讓許多有識無識之士,為之傾倒,以致有“詩人***本關鍵字已替換***贏得了一個新中國”之說。
而當“金陵王氣黯然收”時,曾經君臨天下者就只剩下一腔怨氣和無奈了。“力拔山兮氣蓋世,時不利兮騅不逝。騅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項羽兵敗烏江,于英雄末路只能作《垓下歌》這樣的悲鳴:我辜負了我的寶馬和我的美人!寶馬不肯棄我而去,我該怎么辦呀?虞姬呀虞姬,你說我該拿你怎么辦呀?“天道易兮我何艱,棄萬乘兮退守蕃。逆臣見迫兮命不延,逝將去汝兮適幽玄。”東漢少帝劉辯被董卓廢為弘農王,更被毒酒逼死,劉辯與唐姬訣別,作此最后的《悲歌》。“早晚是歸期,蒼穹知不知?”“安得有英雄,迎歸大內中?”唐末昭宗李曄被劫,登華州城樓,其《菩薩蠻》二首充斥著哀怨和悲絕。“問君能有幾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東流。”“一旦歸為臣虜,沈腰潘鬢消磨。”李煜束手就擒,南唐國史在淚光中結束,華夏詞史卻翻開了輝煌的一頁。“徹夜西風撼破扉,蕭條孤館一燈微。家山回首三千里,目斷天南無雁飛。”宋徽宗趙佶父子被金兵擄去,《在北題壁》題不盡靖康之恥、亡國之痛。“牢落西南四十秋,蕭蕭華發已盈頭。乾坤有恨家何在?江漢無情水自流……”建文帝朱允炆乃明太祖朱元璋之孫,帝位被其叔父燕王朱棣所奪,據說南京城破后,朱允炆由地道出逃,流亡西南為僧,這首《遜國后賦詩》,為野史盛傳。
在另外一些時候,帝王可能暫時淡忘了自己的至尊身份,而寫出抒發普通人情懷,與帝王氣象不大相干的詩篇。因為帝王也是人,人的情思畢竟是有共性的。
當詩的興奮點離開家國興亡、政治搏殺和種種世俗關懷,同為自然之子,帝王的詩思也會躍入生命的自然存在這一形而上層面,也不免思考生命存在的哲學意義,為人生短暫、青春易逝而感傷。例如漢武帝劉徹《秋風辭》:“歡樂極兮哀情多,少壯幾時兮奈老何!”隋文帝楊堅《宴秦孝王于并州作》:“紅顏詎幾,玉貌須臾。一朝花落,白發難除。明年后歲,誰有誰無?”只是貴為天子,擁有無盡的權力、財富和美色,面對衰老和死亡,比我輩平民百姓會有更多的悲涼絕望。
而面對生命個體的終極悲劇,人只有兩種選擇,要么及時建功立業,要么及時行樂。南朝梁武帝蕭衍《贈逸民詩》感慨:“晨朝已失,桑榆復過。漏有去箭,流無還波。”激起的是延攬人才成就大業的急切愿望。梁陳諸君的艷詩,如梁簡文帝《詠內人晝眠詩》“簟文生玉腕,香汗浸紅紗”,陳后主《玉樹后庭花》“妖姬臉似花含露,玉樹流光照后庭”,以及前蜀后主王衍《宮詞》“月華如水浸宮殿,有酒不醉真癡人”之類,反映的則是及時行樂的消極選擇。(其糜艷詩風固不足道,其坦誠做派,較之后世某些縱欲宮闈,卻要禁欲海內的偽君子,還算有幾分可愛之處。)如果既不想成就功業,也不想放浪形骸,對江山、美人都沒了興趣,那就只好學清初的順治帝出家為僧,參禪禮佛去好了:“禹開九州湯放桀,秦吞六國漢登基;古來多少英雄漢,南北山頭臥黃泥。黃袍換卻紫袈裟,只為當年一念差;我本西方一衲子,為何落在帝王家?十八年來不自由,南征北討幾時休;我今撒手西方去,不管千秋與萬秋。”
帝王詩也會吟詠愛情,但后宮佳麗三千,帝王的愛情自然沒有我輩平民的專注執著。雖也偶有動人之作,如李隆基《題梅妃畫真》:“憶昔嬌妃在紫宸,鉛華不御得天真。霜綃雖似當時態,爭奈嬌波不顧人。”帝王詩也會吟詠友誼,但其友誼無不異化為君臣之誼,如***本關鍵字已替換***《吊羅榮桓同志》:“君今不幸離人世,國有疑難可問誰?”帝王詩也會歌詠親情,但其親情不免攙雜利害關系的考量。如南唐先主李昪年少時曾借《詠燈》述懷,說若得養父善待,必將知恩圖報:“一點分明值萬金,開時惟怕冷風侵。主人若也勤挑撥,敢向尊前不盡心?”
宮中帝王有時也會體味民間疾苦,揣摩曠夫怨婦心理,以樂府舊題,弄出一些感傷主義的東西。曹操《卻東西門行》、曹丕《燕歌行》是其濫觴。前者“戎馬不解鞍,鎧甲不離傍。冉冉老將至,何時反故鄉?”代抒戍卒的鄉愁及厭戰情緒。后者“君何淹留寄他方?賤妾煢煢守空房”,空閨少婦的寂寞情懷。梁武帝蕭衍《擬明月照高樓》:“君如東扶景,妾似西柳煙。相去既路迥,明晦亦殊懸。”簡文帝蕭綱《金閨思》:“游子久不歸,妾身當何依。日移孤影動,羞見燕雙飛。”皆為這一路摹擬之作,無不英雄氣短,兒女情長。
或如隋煬帝楊廣,仿佛天地間一布衣騷客,流連《春江花月夜》,忘乎所以:“暮江平不動,春花滿正開。流波將月去,潮水共星來。”或如南唐中主李璟,沉醉風花雪月,信筆《攤破浣溪沙》,纏綿其間:“青鳥不傳云外信,丁香空結雨中愁。回首綠波春色暮,接天流。”情思淡遠處,王氣有無中,一任唯美主義的詩韻流曳。
3
有一種理論告訴我們,人類社會發展有五個階段,五種制度,依次是原始社會、奴隸社會、封建社會、資本主義社會、共產主義社會。可是,用這一理論來套中國歷史,卻發現很難套得上。中國的封建社會始于何時?夏、商、西周、春秋、戰國、秦、魏晉……史家至今各執一辭。中國上古找不到典型的奴隸社會。封建制(分封諸侯,封土建國)在夏代就已初步形成,西周達到極至,秦以后卻實行郡縣制,強化中央集權,封建制基本上不復存在。而原始社會,又稱原始共產主義社會,人們對它的描述充滿烏托邦色彩,說那里沒有階級壓迫,人人平等,共同勞動,群居生活,男人狩獵野獸,婦女采摘野果,盡管貧乏,人們分享勞動所獲,寡無所患,天下為公,沒有私有的婚姻和家庭,只有自由的愛情和浪漫……可是,人類真的經歷過這么一個童話般美好的社會發展階段嗎?人類學者拿不出實證。而直覺告訴我們,不可能。
據說人是由猴子進化而來的,那么,就讓我們來看一看相當于人類老祖先的現代猴群的社會情形吧!今天有不少影視記錄片,帶領我們觀摩原始叢林里的猴子(包括各種類人猿,和據說與人類基因有99.4%相同的黑猩猩)社會。猴子的社會有平等嗎?猴子們有平等的食物享用權和異性交配權嗎?沒有。猴子的社會籠罩著專制和強權。專制強權意志的體現就是猴王。沒有一個猴子部落是猴猴平等,沒有猴王的。這原本沒有什么奇怪,飲食雌雄,猴之大欲存焉(或曰飲食雌,雄猴之大欲存焉)。猴王的地位是靠武力征服群雄強奪而來的。居于王位,就意味著食欲、情欲的最大限度的滿足。叢林里最美味的食物必須首先貢獻給猴王,部落里所有的成年雌性都是猴王的姬妾。所以,猴王的地位是如此令人垂涎,值得用鮮血和生命去爭奪,去保衛。“殺盡江南百萬兵,腰間寶劍血猶新。”[⑧]不到衰老戰敗的那一天,猴王是決不甘心拱手讓出王位的。所謂原始共產主義社會的美妙情形,在猴子社會里是完全不存在的。因此有人推想,中華文明的源頭唐堯虞舜夏禹相繼禪讓的故事,也只不過是一個浪漫主義的傳說。古人早就懷疑過這種美妙的“禪讓制”的存在。《韓非子·說疑》斷定:“舜逼堯,禹逼舜”。《竹書紀年》也說:“昔堯德衰,為舜所囚也。”“舜篡堯位”。
從洪荒叢林的猴王,到周口店的猿人王,從紀元之初的五帝,到四海一家的秦始皇,直到上一世紀的清末遜帝,在這片廣袤的土地上,從來就是專制社會。王呀,帝呀,君主呀,一脈相傳,綿延不絕。其實,自古以來的人類社會,就統治方式和權利結構而言,只有兩種制度:君主制度,民主制度。從夏商周到元明清,四千余年所謂“文明”社會,實行的卻一直是“野蠻”的君主制度。待辛亥革命爆發,中華民國誕生,民主制度的建立和鞏固還備嘗艱辛,還一再上演袁世凱稱帝和清遜帝復辟的丑劇。
說到底,專制主義源于人的自私貪婪本性,是人類從猿猴祖先那里遺傳下來的一種頑固的獸性,民主主義則是人類試圖用以取代獸性的一種神性。獸性是與生俱來的,極難克服,極易復發;而神性是接種的、移植的,會遭遇本能的排斥,是極不穩定,極易喪失的。就像現代人還可能產生“返祖現象”,長出一條令人難堪的尾巴,現代民主社會也難免重新孳生專制主義。
這樣看來,洪秀全給帝王的“王”字加上一個“犬”旁,寫成“狂”,強調其獸性,還是有其道理的。甚至可以說,這是洪秀全的一個偉大發現。只不過這個“犬”旁,也應該給他自己加上,他這個太平天國“天王”也應該寫成“天狂”才是。同理,那位“開軒平北斗,翻覺太行低”,做了民國總統還嫌不過癮,還要做帝國皇上的袁某人,業已返祖,應該姓“猿”。而民國國父孫先生,畢其一生為結束君主專制實行民主共和努力奮斗,當然與“猻”字毫無關系了。
--------------------------------------------------------------------------------
[①]明·王世貞《藝苑卮言》卷二。
[②]花城出版社1992年4月版。
[③]清·張汝南《金陵省難紀略》,見《中國近代史資料叢刊·太平天國》四。
[④]清康熙帝玄燁《中秋日聞海上捷音》。
[⑤]曹操《短歌行》。
[⑥]唐太宗巡視殿試考場時語。
[⑦]《詩經·衛風·伯兮》。
[⑧]朱元璋《不惹庵示僧》。如果說朱元璋反元是出于民族大義,那火并陳友諒、張士誠等就純粹是王位之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