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史研究與明清檔案
韋慶遠
一、為什么要認真研究明清史
明清兩代,在中國封建社會的發(fā)展史上,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按照一般說法,在我國封建社會中,曾經(jīng)出現(xiàn)過四個最為繁榮強大的朝代,即所謂漢、唐、明、清四朝。明、清兩代都是處在中國封建社會的晚期,歷時五百多年。在此期間,史事的發(fā)展變化很大,真可謂頭緒多端,情節(jié)紛繁。如何整理,怎樣評價,確實是一個重大的問題。我們必須鄭重審慎,要作具體分析。切不可認為,既然明清兩代已處在封建社會的末期,就按此推論,得出一切都必然是在走下坡路,一概都是反動腐朽而毫無值得肯定之處的結(jié)論。必須把這兩個朝代合起來作為一個比較完整的獨立社會發(fā)展階段來考察,因為這段歷史,上承兩千多年封建制的發(fā)展,下啟半封建半殖民地社會的開端。兩個朝代都有一段往上發(fā)展的比較繁榮和穩(wěn)定的時期。清初曾有過所謂“康乾盛世”,明初也有過所謂的“洪宣盛世”。明代的“盛世”雖然沒有清代那樣持久和全面發(fā)展,但許多適應封建社會晚期的政治制度、國家典章、統(tǒng)治政策大體上是在明初打下基礎的,清朝是在明朝體制的基礎上結(jié)合滿族的特點和需要來進行治國的,即所謂“清沿明制”。
還必須注意到,清朝有一個重大特點是,由一個在各方面都比較落后的少數(shù)民族的上層;對全國進行了長達267年的統(tǒng)治,并且在相當長的一段時期和在許多方面,確實干得有聲有色,推進了社會的發(fā)展和進步,其文治武功均不遜于其他朝代。這在中國歷史上是罕見的。在明清兩代統(tǒng)治階級——地主階級和被統(tǒng)治階級——農(nóng)民及其他勞動人民中,都曾涌現(xiàn)出許多卓越的人物,積極活動在這五百多年的歷史舞臺上,譜寫過威武雄壯的篇章。歷史有情,我們將永遠不會遺忘他們。一定要嚴格按照歷史唯物主義的科學準則來正確評價這些人物的功過和得失,絕不能再肆意褒貶和“因風改史”了。
前人對明清史的研究,為我們打下了基礎,留下了許多珍貴的成果,但也難免留下一些謬誤。如何以事實為根據(jù),在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的指導下,運用歷史唯物主義的觀點進行嚴肅認真的研究,乃是擺在我國史學工作者和歷史檔案工作者面前的一項責無旁貸的莊嚴任務。
二、明清史研究和當時歷史檔案工作的密切關(guān)系
明清兩代繼承了我國封建統(tǒng)治者重視編纂史書的傳統(tǒng)。從這些王朝剛建立開始,即考慮到為本王朝留存系統(tǒng)的歷史記載。為此,從組織上、史料上作了比較周密的準備。翰林院編撰、修撰、庶吉士之類的“清貴之官”,就是代皇帝起草文件,參加修史工作的。除翰林院外,明、清兩朝都設有國史館。凡文武大臣身死而又還保持寵遇的,大體上,都要“宣付國史館立傳”。為保證編纂史書的需要,明、清王朝對其本身活動中所形成的檔案,都很注意保管整理,并制訂有各種嚴密的規(guī)章制度。如中央級的各部、院、寺、監(jiān)衙門和各省總督、巡撫等文武官吏給皇帝的題奏,各衙門之間的來往文書,在處理完畢后,都要妥慎保管起來。有些檔案更顯然是為了準備修史才形成的。例如,明《實錄》和清《實錄》,它的主要內(nèi)容就是按年代順序輯錄各個皇帝在其一生活動中所批發(fā)的諭旨、批示等。《玉牒》則是有關(guān)皇室皇族繁衍、婚娶、襲封、生死的登記冊,體現(xiàn)著當時的宗法制度和皇室皇族依其親疏所享有不同等級的特權(quán);《起居注》則更是專為記載皇帝“嘉言懿行”的史冊;而各種“史書”,就是按照吏、戶、禮、兵、刑、工等六科發(fā)抄的題本而編纂成的。不但中央如此,各級地方文武衙門的檔案也不許隨便燒毀,每隔若干年,一般是三十年左右,還要利用來編寫省志、府志和州縣志。自古以來,為適應封建宗法社會的習慣和需要,許多家族都編纂有自己的族譜和家譜。稍有名望和地位的人死后,又大都立有墓銘、行狀、傳略之類的東西,明清時期尤其盛行。這便組成了一個層次分明的相當詳細的歷史檔案編纂網(wǎng)。為各級部門修志編書準備了相當多的歷史檔案。史學因利用此一原始的豐富的史料而提高了質(zhì)量,檔案工作又因史學研究的需要獲得了提高,如車之兩輪,鳥之雙翼,起到了互相依存又相互推進的作用。我們同樣不能忽視,許多明清時期的圖書文獻,其中相當一部分也其實就是當時或其后公布的檔案文件匯編。這種源于檔案的圖書文獻,在明清史料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例如,《明大誥》三篇,原來是根據(jù)明太祖朱元璋口頭指示的記錄刊布成書的。《皇明詔全》和《皇清諭旨》等類書籍則是兩朝歷屆皇帝詔諭文件的匯編;《明經(jīng)世文編》和《清經(jīng)世文編》(及其多種續(xù)編)等則主要是匯集了明清的大臣們的奏章公牘;明清許多文武大臣都有自己的文集,其中相當一部分的內(nèi)容乃是這些大臣們在任職期間撰寫的公文。清朝有兩部重要的史料書,即乾隆時期蔣良騏編的《東華錄》和光緒時期王先謙編的《東華錄》,其所以能成書,主要因為蔣氏和王氏都曾先后在清朝的國史館任過纂修官。可以論斷,如果蔣王二氏不是因職務的方便,得以飽讀保管在宮廷之內(nèi)的皇家檔案,這兩部《東華錄》是無從錄起的。
以上是明清時期本朝的人為本朝、本地、本族、本人利用有關(guān)檔案寫的史書。還必須注意到另外一個重要的方面,就是后一朝代的統(tǒng)治集團幾乎都搜集和利用過前朝的檔案,為前朝修史。這可以清修《明史》和民國初年修《清史稿》為例。
清王朝于1644年(順治元年),開始建立了全國性的統(tǒng)治。翌年,即宣布建立明史館,陸續(xù)委任了一大批史官,下詔集中明代各官署的檔案以供明史館參考。從1679—1735年(雍正十三年),《明史》才定稿,1739年(乾隆四年)刊行。先后持續(xù)工作了近六十年之久。在舊的封建正史,即所謂二十四或二十五史中,《明史》算是較好的一種,資料比較豐富,史事的考訂比較嚴謹,也有其特點。例如,鑒于明中葉以后宦官橫行,作惡多端,專寫了《閹黨傳》;鑒子明代朱家宗藩問題已經(jīng)形成當時社會上的大災難,為諸王、公主等寫的傳記中不乏對他們貪婪昏庸的披露;有些皇帝的本紀和大臣的列傳,也寫得比較生動具體,這顯然都是參考了明人留存下來的詳細記載。據(jù)清朝官方的記錄,順治和康熙年間,都曾專門下諭,著將明朝中央各部門的檔案集中到明史館。稽考《明史》本書,利用檔案的痕跡也是極其明顯的,不少地方甚至把當時皇帝的詔令諭旨全文公布或錄引其詳細摘要,許多大臣的奏疏往往也成為本人傳記中的主要史料,試讀《李三才傳》,《楊繼盛傳》等篇,即可了然在目。
對清朝歷史的系統(tǒng)研究,也幾乎是從清王朝一滅亡就開始的。袁世凱篡位當上總統(tǒng)后, 便匆匆忙忙以大總統(tǒng)令的形式?jīng)Q定將原來清朝的國史館改名為清史館,繼續(xù)負責纂修《清史》。
此項工作從1914年(民國三年)正式開始,到1927年大致完稿,歷時共十四年,修成現(xiàn)存的《清史稿》一書。這部書因為編者們頑固地站在維護封建帝制的反動立場上,對一切革命的,或要求維新改良的思想行動都肆意進行誣陷攻擊,同時歌頌和美化了清王朝的統(tǒng)治,并鼓動復辟,存在著許多重大的原則錯誤。加以內(nèi)容比較冗雜,各篇成于多人之手而未作統(tǒng)一潤飾,彼此很少照應,體例不一,繁簡失當,往往發(fā)生年月,事實、人名、地名的差錯、遺漏和顛倒,甚至還有文理不通的地方。不論在政治上學術(shù)上,《清史稿》都不能列為好的史學著作,不符合一代信史的要求。但是,由于長期以來我們還未編出另外一部更為嚴謹完備的清史,它又仍然是現(xiàn)存的唯一一部系統(tǒng)的紀傳體清史,還可供參考利用。
《清史稿》沒有編好,其原因當然是多方面的,上文已有所述。但其中有一個因素也是很重要的,那就是,清史館在其編書的全過程中,并未能充分利用清王朝遺留下來的極其大量的歷史檔案文件,在史料來源上就存在先天不足。清史館確實接收了清朝國史館歷年搜集而來的資料,但是,反映二百六七十年清朝統(tǒng)治真實記錄的“大內(nèi)檔案”,其中的大部分在愛新覺羅·溥儀被趕出故宮以前,一直幽藏在宮內(nèi)內(nèi)閣大庫及宮中各處,清史館的人員并未參閱。當時雖然也有一部分內(nèi)閣大庫所藏檔案已移放宮外,但因北洋政府的腐敗無能,幾經(jīng)周折,遭受到難以令人置信的摧殘踐踏,發(fā)生了所謂“八千麻袋”事件。在這種情況下,當然更談不上發(fā)揮其作用了。所以《清史稿》編撰者們當時沒有,也不可能充分利用這批清代歷史檔案進行《清史稿》的編纂工作,因而嚴重影響了此書的質(zhì)量。這一事例充分說明了一旦離開了檔案這一豐富的原始史料的運用與研究,將會造成何等嚴重的后果。一部中國史學發(fā)展史,反復地說明了這一點。 三、明清歷史檔案的陸續(xù)發(fā)現(xiàn)
長期以來,我們習慣上所稱的明清檔案只是指當年在清官內(nèi)所存放的,后來保管在當時故宮博物院文獻館,現(xiàn)在則是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藏品的一部分,亦即是所謂的“大內(nèi)檔案”(其中有一小部分被國民黨政府帶到臺灣,現(xiàn)保藏在臺北故宮博物院內(nèi))。這個概念在二十年代初期大體上是正確的,現(xiàn)在則已不確切了。因為所謂“大內(nèi)檔案”,僅僅是明清兩代中央王朝在其全部活動中所形成的大量檔案中的一部份。其中明代的檔案大體上是在清初為修《明史》而搜集來的明檔的殘余部分,現(xiàn)在保存下來的只有三千余件,至于清代檔案,其數(shù)量確實很大,目前在中國第—歷史檔案館保藏的即有九百多萬件,在臺北還有三百萬件左右,所反映的內(nèi)容也極為廣泛重要。但它終究只是清王朝統(tǒng)治時期反映皇帝和宮廷各方面活動而形成的檔案,并不包括清朝各部、院、寺、監(jiān)等中央一級衙門和各省、府、州、縣等各級地方衙門的檔案。當然,“大內(nèi)檔案“是目前所知數(shù)量最大的、保藏最完整的、學術(shù)價值最重大的明清檔案。它的被發(fā)現(xiàn)和被搶救出來,一直發(fā)展為現(xiàn)在舉世知名的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的規(guī)模,在我國學術(shù)史上是一件大事。三十年代就有學者認為,殷墟甲骨、戰(zhàn)國秦漢竹簡、敦煌寫經(jīng)、明清“大內(nèi)檔案”的發(fā)現(xiàn),是當時具有極高學術(shù)價值的四件大事,它們意味著這些方面的研究開拓出新的領(lǐng)域,意味著必將出現(xiàn)新的突破。對這樣的估計,本人是完全同意的。
筆者還有一個建議,即應該編寫一部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館史。這個檔案館(包括它的前身故宮博物院文獻館)在其存在和活動的半個多世紀中,曾經(jīng)走過一段坎坷不平的道路,已為我國的歷史檔案工作和明清史研究作過重大貢獻。當年魯迅先生曾著文論述過“大內(nèi)檔案”。自二十年代初期以迄解放前,我國學術(shù)界中如陳垣、沈兼士、許寶蘅、沈士遠等有識之土,或則奔走呼號以把從宮內(nèi)流散出來的“八千麻袋”檔案搶救下來,或則竭費心力對這些檔案進行了一些分類整理,并在當時條件允許之下,編輯出版了一些專題資料。他們,以及隨同他們長期堅守歷史檔案工作崗位的許多人,甘于淡泊和默默無聞,在舊社會的黑暗統(tǒng)治下總算把這一個攤子維持下來。他們在過去的成績,雖然無法與解放后的今天相比較,但也應該說是難能可貴的,表現(xiàn)了我國學術(shù)界和檔案工作者中的識見和操守,值得我們緬懷和紀念。解放以后,從這個檔案館的物質(zhì)建設和專業(yè)人才的補充,規(guī)模的擴大,為科學研究和社會主義各個方面所提供的豐碩成果,又有力地說明了我們黨和政府對歷史檔案工作的重視和支持。當然,這個館在十年動亂期間,也遭受過許多摧殘破壞,工作受到了嚴重的損失。但浩劫終于過去,光明重照大地,在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它又踏上了健康發(fā)展的坦途。正因為它在新舊社會都有生動的事跡值得記述,有豐富的經(jīng)驗和教訓值得吸取和引為借鑒;正因為它在我國、甚至在全世界范圍內(nèi),都屬于規(guī)模很大的檔案館之列,具有重要的典型意義。這個檔案館的館史將成為中國檔案事業(yè)發(fā)展史的重要組成部分,將會從側(cè)面生動地反映出當代中國歷史檔案工作發(fā)展的歷程。
除了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保藏的明清檔案外,解放以來陸續(xù)發(fā)現(xiàn)或引起學術(shù)界注意的其他明清檔案也是很不少的。
首先,是一些地方性政權(quán)機關(guān)形成的歷史檔案。最重要的有原東北檔案館所藏的清代原東三省總督及三個省軍政衙門在其活動中所形成的檔案,其中還有一些明檔和滿族在未入關(guān)前形成的老檔:在西藏檔案館藏有自元、明、清以來歷屆中央政府給西藏地方政府的文件以及西藏地方政府在其本身活動中所形成的檔案:順天府檔案是當時首都所在的地方官府檔案;四川省巴縣舊政權(quán)的檔案是迄今所知縣級衙門檔案保留下來的數(shù)量最多的;清代直隸正定府獲鹿縣的《編審文冊》,是一套比較具體地記載該縣土地占有、變動和田賦丁銀負擔情況的系統(tǒng)資料。
山東曲阜孔府是一個大封建貴族地主莊園,它擁有封建社會最高統(tǒng)治者所授予的種種特權(quán),因此孔府形成的檔案也應該歸入明清檔案這一類。
其次,是一些具體業(yè)務部門在其自身活動中所形成的檔案。例如,清末建立并長期受外國帝國主義控制的海關(guān)總署檔案全宗里保藏有一部分清末的檔案。其他如設在廣州的粵海關(guān)及其所轄九龍、瓊崖、潮州等分關(guān)的檔案里都有一部分清末的檔案,其內(nèi)容除了有關(guān)關(guān)稅、緝私及來往公函以外,還涉及到諸如貿(mào)易統(tǒng)計、華工出洋、通商旅游、考察留學和社會政治事件等方面。又例如,近年我們從南方個別老城市的房管部門所保存的本城市的房地契約中,發(fā)現(xiàn)了一些清代自康熙、雍正、乾隆以來形成的房屋契紐,這些契約是當時的房主在房屋建成宿報官領(lǐng)契,交稅驗印時繳存在官府的。這些契約對研究各該城市的發(fā)展布局,了解各該地區(qū)人民的居住狀況、物產(chǎn)房地價格和建筑特點等都具有一定的價值[①]。在我國其它各古老城市的房管部門里,很有可能也保藏有這一類陳年的房地契,這是一筆有待于深入調(diào)查摸底,有待于發(fā)掘并發(fā)揮其作用的財富。在各級人民法院保存的檔案里,是否藏有一些清代后期遺留下來的舊案,也還有待調(diào)查發(fā)掘。希望在政法部門做檔案工作的同志能夠留心這一點,也建議國家檔案局和人大檔案系在適當時候組織人力作些調(diào)查。
再次,是明清時期各種類型的民間文書契約的被發(fā)現(xiàn)。早在五十年代初期,鄧拓同志即花了很大的力量搜集了有關(guān)京郊西山門頭溝地區(qū)民營煤窯的大批明清時期的契約文書,從中研究這些煤窯的生產(chǎn)、投資、經(jīng)營管理的特點和雇傭關(guān)系,并對其資本主義萌芽的發(fā)展狀況作了自己的估計,寫出了著名的論文[②]。五十年代中期,在安徽徽州地區(qū)及其所屬的休寧、歙縣、黟縣、祁門等縣也發(fā)現(xiàn)了大批民間契約文書、帳冊等,分別由各地酌博物館、圖書館、 高等院校和研究單位選購收藏。這些單位還分別搜集保藏了我國其他地區(qū)的許多明清時期的民間契約,其中,以中國歷史博物館、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北京大學圖書館所藏數(shù)量較多,內(nèi)容也較珍貴。
近年來,在福建發(fā)現(xiàn)了一批清代閩北土地買賣契約,在四川發(fā)現(xiàn)了一批自貢井鹽業(yè)生產(chǎn)和經(jīng)營管理狀況的契約,在北京發(fā)現(xiàn)了有關(guān)通縣地區(qū)土地買賣、人口買賣、租佃、雇工和商業(yè)合同等方面的契約,有人從蘇州的明清碑刻和北京工商行會碑刻中也發(fā)現(xiàn)了一些珍貴的契約資料。反映太平天國革命活動的文書、表冊、揮條、自述等也相繼有重要的發(fā)現(xiàn)。
以上三方面明清時期歷史檔案的相繼發(fā)現(xiàn),成了對明清“大內(nèi)檔案”的有力補充和參證。隨著祖國社會主義“四化”建設的開展,隨著社會上各方面對歷史檔案工作的重視和支持,類似這樣的明清歷史檔案文件,將逐步會有新的發(fā)現(xiàn),祖國歷史檔案寶庫將會不斷地得到新的補充。
四、明清歷史檔案在明清史研究中發(fā)揮了重大的作用
幾十年的歷史證明了,明清史的研究工作是離不開明清歷史檔案工作的。不參考利用明清時期的各類歷史檔案,而能進行科學的高質(zhì)量的明清史研究,實在是難以想像的事。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自解放以來,除了經(jīng)常接待來自全國各方面的查閱利用者外,還獨自或與其他單位合作編輯出版了諸如《江寧織造曹家檔案史料》、《李煦奏折》、《第二次鴉片戰(zhàn)爭檔案史料》、《戊戌變法檔案史料》、《義和團檔案史料》、《清末籌備立憲檔案史料》、《天地會》等等重要的明清檔案文件匯編,近年出版的《清代檔案史料叢編》也深受史學工作者歡迎。這個館正在進行著其他許多專題的編輯出版工作,必將對明清歷史的研究發(fā)揮出愈益重大的作用。
隨著明清史研究的深入,明清時期各種檔案的摸底、發(fā)掘整理和利用的工作越來越受到人們的重視并加快地開展起來了。例如: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明史研究室編纂的《明史資料叢刊》,已將明代的檔案契約,年譜家乘等列為主要的收輯內(nèi)容:近兩年來,四川省自貢市鹽業(yè)歷史博物館已經(jīng)陸續(xù)公布了該地區(qū)清代的有關(guān)鹽業(yè)的各種契約;廈門大學歷史研究所也發(fā)表了《清代閩北土地文書選編》一書;人民大學李華同志編的《明清以來北京工商會館碑刻選編》一書;南京太平天國歷史博物館編輯的《太平天國文書匯編》一書,均已出版。南京大學歷史系的明清研究室對蘇州地區(qū)工商業(yè)碑刻的編選工作已經(jīng)完成,即將出書。同時,對上述歷史檔案的研究工作也相應地開展起來了,相繼發(fā)表了一些較有質(zhì)量的論文。在我國歷史學和檔案學的領(lǐng)域里,向科學的廣度和深度的進軍已經(jīng)開始。
當然,成績還僅僅是初步的。明清史研究領(lǐng)域中,還有大量的重大的課題需要我們進行探索;現(xiàn)已查明的明清歷史檔案,在其內(nèi)容及其史料價值上,還有著大量的問題需要我們研究。這是一座剛剛在開發(fā)的寶山,許多基礎性的整理和編輯工作還有賴于我們認真去做。明清史學研究和明清歷史檔案工作本來是一雙孿生的兄弟,貴在密切的協(xié)作和相互支持。應該歡迎史學工作者進入檔案館充分利用歷史檔案文件,也應該歡迎歷史檔案工作者進入史學研究的領(lǐng)域,做一部份明清史的研究工作。在共同的進軍中將見百花爭艷,萬紫千紅。辛勤的耕耘,定會結(jié)出累累的碩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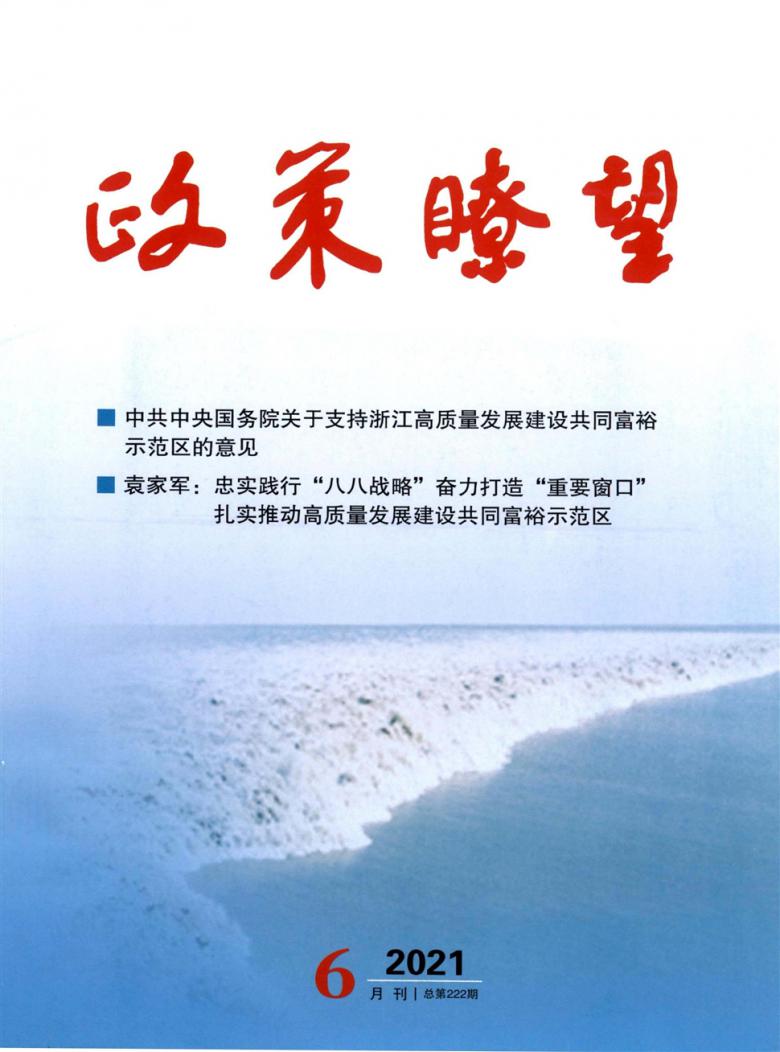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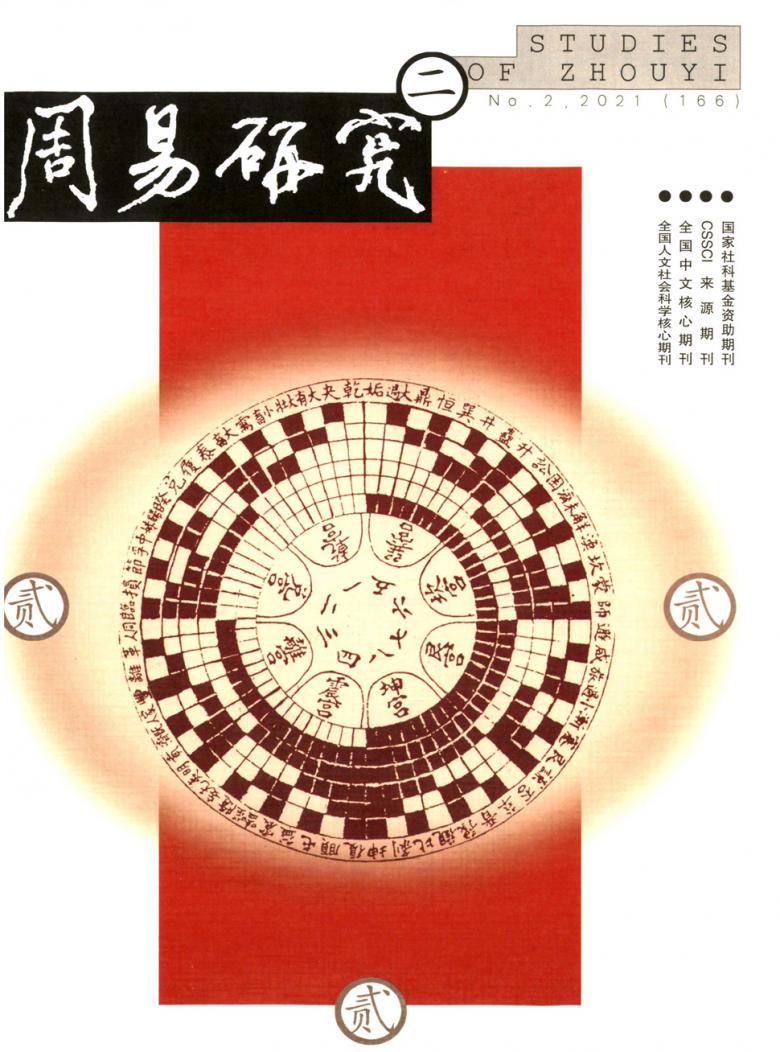
于我們.jpe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