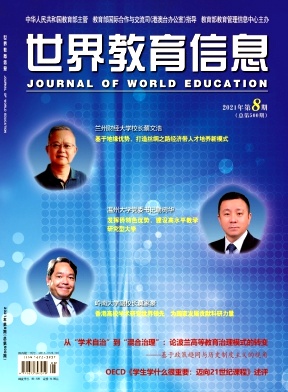理性、倫理和公民政治:哈貝瑪斯的現代性理論
佚名
在當代眾多的思想家之中,哈貝瑪斯以他對現代性的肯定態度著稱。哈貝瑪斯的大部分著作都表述了他對現代性的基本態度。他主張保存和發揚現代性具有歷史進步意義的因素,而對現代性帶有壓迫性的成分則加以批判。他對現代性的討論大致在以下四種范圍內進行:一、社會科學方法討論;二、社會理性;三、當代倫理和道德哲學;四、自由民主國家的合理性。
哈貝瑪斯關于現代性的理論不是形而上學,也不是經驗描述,而是一種文化政治闡述。他繼承了戰前法蘭克福批判理論的傳統,從實際認識論來肯定現代性。他提出,現代性最有價值的認識成分是批判和反思,而這種批判和反思之所以有價值,則是因為它們既是能動思想者尋求自我解放的條件,也是整體社會在反壓制和反壓迫中尋求自我更新的途徑。哈貝瑪斯的文化政治理論集中地體現在他的“交際行為和理性”理論中。這一理論的基本特征是以“反強制”為其價值理念,以“理性”、“倫理”和“公民政治”為其問題核心。在哈貝瑪斯的文化政治理論中,“價值”和“問題”是緊密相聯的。哈貝瑪斯把理論界定為一個有關于道德的社會概念,一個關于人們民主交往合作的概念。人們由于相互理性地陳述見解,交際協作的需要,而把自由確定為一種必須相互平等對待、相互尊重的道德關系。人們必須在這種無壓迫強制的道德關系之中,才能通過明達理性相互理解,獲取共識。話語理性和話語倫理是現代公眾領域獨立運作的條件,是現代公民政治的基本內容,也是現代民主理念合理性的根本依據。
一、從主體理性到主體間理性
哈貝瑪斯的政治文化話語理論的一個基本內容就是如何從交際(communication)來認識理性和行動。因此,這一理論又常被稱作交際行動和理性理論。在哈貝瑪斯那里,從交際來認識理論和行動有著明確的目的,那就是厘清現代性的一些正面價值和作用,并且批判現代性的一些負面表現和影響。哈貝瑪斯對現代性的二個方面作了重要的區分。一是文化現代性所包含的理性價值,二是現代性社會過程中對理性的偏面運用。這二個方面不能混為一談。我們不應當用第二個方面的偏誤來否定第一個方面的積極意義。恰恰相反,我們應當以現代文化的理性價值作為認識西方現代性某些負面作用的批判基點。哈貝瑪斯指出,現代文化之所以可貴,全在于它有助于形成“理性生活世界”。
什么是“理性生活世界”呢?哈貝瑪斯認為這個問題的答案必須在人們交際時使用的話語所包含的“正確性主張”(validity claims)中去尋找。一個人對他人表述自己的見解,他的話語之所以能被對方接受,必然是因為其中包含某種可以得到證明的理由(redeemable validity claims)。這些理由必須是可辨認的,同時也必須是可兌現的。在哈貝瑪斯那里,“交際”并不僅僅是讓某人相信某事(即“說服”),交際是與某人共同享有對某事的理解。而這種理解又必須理解為一種相當脆弱的人際間相互承認關系。人們在謀求對某事的共同理解時,不僅要提出主張,更需要澄清隱含在主張后面的前題。只有一方的前題被另一方認可,共同理解的通道才會打開。打開這一通道靠的不是強迫,而是理性的裁決。“交際理性”的關鍵是“交際自由”。交際理性指的是存在于交際行為言語之外的膠合力量。而交際自由則是對他人言語行為說“是”或“不”的基本“權利”(1984:第152頁) (文中凡引述哈貝瑪斯著作處,均在括號中直接以出版年份加以標明)。
哈貝瑪斯看到,現代理性世界有正負兩種不同的發展。正的方面是,隨著理性世界的出現,越來越多的社會互動領域擺脫了傳統或權威的擺布操縱,而通過理智協議來取得共識。負的方面是,由于社會越來越理性化,社會也越來越偏向從功能運作追求理性發展。這種偏面的理性發展表現在某些社會亞系統(如金錢或行政權力)的極度膨脹并侵入其它社會領域。哈貝瑪斯認為,現代性的病理在于其不平衡的發展,而不在于它的基本理性價值。這種不平衡的發展造成了某些領域(如政治權力和商品經濟)對其它領域(如文化、輿論、教育)的“殖民”,并且成為現代生活意義危機和自由萎縮的主要原因(1984: 第183, 239-40頁; 1987,第292-93, 422, 452, 470-88頁)。
和徹底否定現代性的后現代主義論者不同,哈貝瑪斯認為否定現代理性并非解決現代社會目前問題的辦法。他認為否定現代理性會帶來嚴重的理論和政治后果。他主張改造而不是拒絕現代理性。在80年代出版的《交際行為理論》一書中,哈貝瑪斯力圖以交際行為理論來構建一種不同于“意識哲學”的理性觀,這種理性觀包含了雙重哲學轉折,一是從意識哲學向交際哲學轉折,二是從主體理性向主體間理性,或者說,從自由理性向交際理性轉折。
這種雙重轉折的意義非常重大。意識哲學依存于以自我保護為本能的工具理性。哈貝瑪斯堅持把工具行為同交際行為區分開來。工具行為在考慮手段和目的、技術和目標間的關系時不在乎目的和目標本身的理性和正當性。工具行為是人主體控制自然(或其他人主體)的作用關系,是主體與客體間的關系。交際行為則是主體與主體間的關系。它的目的不是控制,而是共同享有理解和達成協議;不是利用,而是增進社會團結和充分發揮語言的理想潛力。
哈貝瑪斯指出,從意識哲學向交際哲學的轉折其實早在弗萊杰(Gottlob Frege)和威特根斯坦(Ludwig Wittgenstein)把意識哲學轉向語言哲學時就已經開始。但是哈貝瑪斯認為,語言哲學仍然太主體化,因為語言哲學所依賴的仍然是自我/對象模式,而并未真正轉變為交際的自我/他者模式。雖然后一種轉折在米德(George H. Mead)和德克海姆(Emile Durkheim)那里初具端倪,但這兩位社會學家卻并未能確實地提出究竟什么才是主體間互相理解和達成共識的條件,沒有能將此明確界定為交際問題。哈貝瑪斯很自信地認為,他自己的交際行為理論第一次使得哲學家得以把主體理論改造為主體間理性。經過這樣的改造,理性便不再是自我封閉的主體對自然的控制手段,而成為一種克服偏見,向其它主體敞開的交際通道。
哈貝瑪斯對現代理性的重構所針對的是韋伯(Max Weber)對現代性的悲觀評估。韋伯把現代性看成由工具理性膨脹而成為一座堅固無比的控制鐵籠,在這座鐵籠之中,因科層理性的發展,意義已經完全破碎,而自由則已完全喪失。哈貝瑪斯認為,盧卡契(G. Lukacs)、霍克海默(M. Horkheimer)、阿多諾(T. Adorno)和其它西方馬克思主義者都從韋伯那里汲取批判的靈感,這一批判更為日后福柯(M. Foucault)、波德里拉(J. Baudrillard)、德魯茲(G. Deleuze)、瓜塔利(F. Guattari)和其它后現代理論家剖析理性與現代性的內在聯系打下了伏筆。其中阿多諾和霍克海默在《否定的辯證法》中從歷史辯證對理性的批判影響最為深遠。
哈貝瑪斯不同意阿多諾和霍克海默對理性的徹底否定,他要重新喚起對批判理性的信心。哈貝瑪斯對工具理性的批判和阿多諾、霍克海默以及后現代主義者在理性問題上的立場有一個重要的區別之處,那就是他堅持這一批判必須有價值理念的基礎,并積極從理論上去建立這種價值理念的基礎。
二、從絕對命令倫理到話語倫理
哈貝瑪斯并不從西方文化傳統價值的歷史形式為批判理論尋找根據,而是轉向語言和交際的普遍特征。哈貝瑪斯認為,在語言和交際中本已存在著某種具有普遍意義的價值,這是因為交際和理解能力是整個人類在歷史過程中發展形成的。哈貝瑪斯對于價值的普遍主義和近于進化論的見解,引起過不少質疑和爭議。限于篇幅,這里不便涉及[注1〕。重要的問題是,哈貝瑪斯為什么特別強調批判理論的價值訴求和基礎?他強調的是哪些價值理念?他為什么要處心積慮地在語言和交際中為這些價值尋求某種近于經驗基礎論的來源?
哈貝瑪斯早就清楚表明話語倫理是和民主合理性理論聯系在一起的。他的批判理論的基本訴求(理性、平等、自由)是為推進民主和增強民主合理性服務的(1975)。只是在一段相當長的時期里,哈貝瑪斯的話語倫理是當作道德哲學來討論的,其重點在于一種新康德主義傳統的認識論倫理,表述的是有關“公正”(impartiality)的現代道德觀。哈貝瑪斯后來把這一倫理擴展到話語對民主政治潛在作用的討論中去。哈貝瑪斯常常強調他的話語倫理是描述性的,不是規定性的,它要描述“日常生活體制需要如何重建才能有可能對行為的道德沖突作公正判斷”(1990a:第116頁)。
在哈貝瑪斯那里,“話語”這一概念有著特殊的含義。和結構主義、后結構主義的“語言轉向”根本的不同的是,它指的不是語言自我完足的能指/所指系統,而是在不受強迫控制的環境中的交際:“(話語)是一種從經驗和行動分離出來的交際形式,話語的結構使我們確信,只有主張、建議或告誡等暗含的正確性主張才是討論的唯一對象。討論的參與者,議題和見解除了必須接受對有關正確性主張的考驗之外,不受其它約束,除了更佳論證之外,不受其它影響;因此,除了共同協力尋求真理之外,也無別種動機”(1975:第107-108頁)。
哈貝瑪斯討論話語的關鍵不在話語本身,而在如何形成理性、民主的“話語機體意志”和行動共識。參與形成話語性集體意志就必須接受理性權威,也就是說一種包含在話語中的權威,一種基于對正確性主張的證明的權威。值得注意的是,哈貝瑪斯并不認為我們用話語就可以建立起合理的社會體制來。然而,盡管話語并不是體制的構建原則,但它卻是民主體制權威的合理性原則。體制的運作并不全都通過話語,但我們卻必須在話語的層次上才能把握民主體制的運作,討論它包含的正確性主張和前題,討論這些主張和前題能否得到證實。無論是在個人交往還是在社會運作中,人們往往并不深究其話語機制,倒是情愿按老規矩辦事,或者圖眼前的效率或利益。人們往往稱話語為“空談理論”或“鉆牛角尖”。人們只是在日常的共識發生了分歧,現有的認識出現了危機的時候,才會把話語當作一種解決分歧、增強認識的交際手段。正是由于這一點,話語對于民主政治體制才特別重要。
正是從話語在民主政治中的重要作用出發,哈貝瑪斯認為民主的體制空間是“公眾空間”。以往民主理論所提出的體制性問題(權利、代表制、選票、權力平衡等等)在哈貝瑪斯那里仍具重要性,因為它們是公眾空間運作的條件(1989a,1992b)。公眾空間是一個人們討論公眾事務的場所,公眾空間必須不受脅迫和從屬等級這一類不平等關系的干擾。脅迫和從屬關系只會使個人沉默或違心服從。哈貝瑪斯對體制問題的關心,集中在如何使人暢所欲言,如何在公眾領域中防止外力干擾明達理性討論。這些外力干擾主要來自政治強權、市場和傳統觀念。
哈貝瑪斯的話語倫理(理性、平等、自由)所考驗的是對話普遍性,而不是獨語普遍性。哈貝瑪斯的倫理觀和康德的倫理觀一樣強調普遍性。它們都把道德看成是個人行為準則的普遍化。但是,在哈貝瑪斯那里,是否成功地獲得這一普遍性卻不能由這樣的問題來獲得答案:“世界是否遵守我的合乎邏輯的原則?”哈貝瑪斯要問的是一個不同的問題:“別人是否會遵守我的原則?”這個問題的要點是主體間而不是主體。在康德那里,對獨語普遍性的考驗是絕對命令倫理,在哈貝瑪斯那里,對對話普遍性的考驗是話語正確性主張,是共同分有理解的話語倫理。
哈貝瑪斯把社會行為分為兩種。第一種是策略行為,它以爭取他人的服從為目的,只要達到這個目的,任何手段,哪怕是金錢收買、權力壓制,都是合理的。第二種是交際行為,它的目的不是操縱擺布別人,也不是千方百計使別人按我的意愿行事。交際行為者是通過與別人共同分有對共同處境的理解,來和諧協調自己和別人可能不同的計劃(1984:第286,287頁)。哈貝瑪斯對“策略行為”和“交際行為”的區分包含了康德要求以他人為目的而不是為手段的道德主張。和康德不同的是,哈貝瑪斯的道德哲學有一個明確的政治目的,那就是支持現代民主理念。
理性、平等、自由是現代民主理念的基本價值。哈貝瑪斯刻意為這些價值在語言和交際中尋找一個幾乎是經驗基礎論的來源。在道德懷疑論和虛無主義喧囂塵上的今天,他這樣做,是否真能增強這些價值的合理性,實在很難說。但這不應當影響我們對這些價值的信心。我們應當看到,盡管權利必須在一個普遍的范圍內表述,才能使權利成為每個人的權利,但這種普遍性卻并不是建立在什么可以用經驗證實的基礎之上的。我們堅持權利的普遍性,并不是因為我們可以在語言、交際、或者人性等等中找到一個不容置疑的、實在的、本質的根據,而是因為不堅持權利的普遍性,平等便成為一句空話。
權利的普遍性是一種認知,一種覺悟,它本身就是人們在具體生活處境中斗爭的歷史過程中形成的。換句話說,權利的普遍性本身就是一種價值。我們堅持權利是普遍的,并不是以“事實如此”為理由,而是堅持“權利應當普遍”。事實上,每個社會中的普遍權利都是人們斗爭的結果,對民主、自由和人權的普遍價值,我們應當作歷史的,而不是本質論的解釋。我們可以把這些價值看成是人們在特定歷史環境中生存斗爭的條件和成果,社會發展的基礎和目的,而不一定要把它們解釋為某種經驗的或超然的道德命令。
其實,在自由民主思想中,理性、平等和自由是有機地聯系在一起的。自由主義的理性包括兩個方面。第一是在欲望目的既定的情況下對行動方式的選擇;第二是對欲望的重構和對目的的選擇。反對自由主義的人往往把自由理性的第一方面看作自由理性的全部,把自由理性僅僅當作實現某種目的的手段(也就是工具理性),這是不恰當的。決定論的欲望,即把人的欲望看成是完全由家庭、社會、文化或基因所決定,本是與強調自足主體的自由主義水火不相容的。自由主義認為,人不僅能選擇達到欲望的手段,還能判斷什么是于他有益的欲望,欲望是可以通過理性思考來改變和整塑的。正是人的這種按照理性調整行為和欲望的能力構成了人的選擇和行動的自由,體現了人的自由意志。從邏輯理念上說,自由主義必然拒絕一切形式的決定論(種族決定論,文化傳統決定論,歷史決定論,等等)。不相信人的獨立意志,就不可能成為真正的自由主義者。自由主義對自由的基本信仰是,人人都有自由和理性行為的能力;在一般情況下,人能夠表現出理性;如果他不表現出理性,那么就應當要求并鼓勵他表現出理性。自由主義要求把這一原則貫徹在人與人的各種社會、政治、文化關系之中,真正做到尊重每一個自足獨立的個人主體。
自由主義的自由觀念因此必須包含平等的觀念。如果理性行為和自由意志既在每個人的能力之內,又是每個人的道德價值之所在,那么人們決定如何相互對待的時候,也就必須同時考慮到自由和平等這兩個基本因素。換句話說,就理性行為者和自由意志主體而言,人人都應當是平等的。自由主義關于自由和平等的價值觀是建立在對于人的理性的信仰之上的。自由主義敘述的不僅僅是個人,而且是理性的個人,不僅僅是自我,而且是道德的自我。
在后現代思想的沖擊下,一切帶有普遍性的價值觀,包括理性、平等和自由,似乎都變得不可相信,不值得相信了。哈貝瑪斯在這種壓力下強調批判理論需要建立具有普遍意義的價值觀,也就越加難能可貴。后現代理論有理由懷疑普遍論主張后面是否隱含著某些特殊利益或權力關系,但是,只要人們還反對壓迫,反對強制,還期待有公正的社會,他們就不能不確立具有普遍意義的社會倫理價值。其實,即使反對普遍論的后現代理論本身也包含著明確的普遍性倫理,那就是,為普遍而犧牲個別是不公正的。后現代理論要求重視、理解并道德地對待個別,但它的倫理內容卻是空洞的,因為它不能確定怎樣的個別才值得尊重和保護,怎樣尊重和保護個別才具有道德性。
哈貝瑪斯的價值普遍論是以思考德國法西斯罪行的個別性為指標的。哈貝瑪斯反復強調,象奧茲維茨大屠殺這樣的個別是不能尊重和保護的,尊重和保護這樣的個別是不道德的。和抽象反對普遍論的后現代理論不同,哈貝瑪斯的批判理論有一個實實在在的歷史事件參照點。哈貝瑪斯鄭重指出,是納粹主義的“道德災難”迫使我們必須思考納粹“對普遍價值傾向的前所未有的侵害”(1989b:第210頁)。哈貝瑪斯認為唯有道德普遍論才是衡量法西斯和極權統治乖謬性的尺度。所謂乖謬就是違背普遍道德法則,就是不合普遍理性。真正的批判必須有現實的支點。80年代的中國文化批判曾經有過這樣一個支點,那就是對文革無條件的抵制和譴責。90年代的一些后現代、后殖民理論失去了這樣的支點,于是只能以道德相對論來表明自己的價值立場,從根本上取消了乖謬和個別的區別。哈貝瑪斯堅持道德普遍論,乃是因為他不能允許乖謬鉆個別性的空子而取得哪怕一絲一毫的合理性。
三、批判是以解放為目的的知識活動
哈貝瑪斯在60年代發表的《知識和人的利益》一書中,分析了人的三種利益所在以及與此相對應的知識和理性類型。哈貝瑪斯稱其為三種“知識構成的利益”類型。每一類型均可從知識對象正確性標準和利益所在來加以區分。第一種是“經驗分析”性知識,知識對象是“可以操縱的東西、事件和環境”,正確性標準是在經驗可重復條件下的假設演繹理論試驗。哈貝瑪斯指出,它并不象實證科學觀所相信的那么“客觀”,而是帶有其特殊的利益取向,那就是控制人的生存世界的“技術”利益。第二種是“歷史釋義”性知識,它的對象范圍是“說話和行動主體”,它的正確性標準是對話處境中意義的會通,它的利益則是“實踐”。第三種是“自我反思性知識”,它的對象是那些需要進一步說明和解釋的話語和行為,它的正確性標準是能否用批判眼光來進行自我審視,它的利益是從自設的和它設的壓制關系中得到“解放”。哈貝瑪斯認為,批判理論即屬解放型知識(1971,1974)。
哈貝瑪斯同意霍克海默和阿多諾,認為現代社會在這三種利益類型中過分偏重第一種:從控制和改造自然到控制和改造人類。哈貝瑪斯不同意霍克海默和阿多諾對現代社會和現代性本身的悲觀態度,他認為現代性的偏差可以糾正,關鍵在于如何可以通過認識和提高包含在“實踐”和“解放”中的理性。以此為條件,群體生活的理性基礎是能夠建立的。群體生活的理性基礎是非壓制、非強迫、無暴力的社會關系,唯此方能保證“每一種具有政治效應的原則都由無壓制的交際獲得的共識來達成”(1971:第284頁)。
哈貝瑪斯并沒有把對不同“知識構成的利益”類型的分析僅僅限制在認識論的范圍之內,而是隨后將之擴展到一切與自然語言使用者都有關的“交際能力”的視野之中。人們在使用普通語言相互陳述見解、尋求共識的時候,都必須表明話語的正確性。“交際能力”理論旨在闡述人們究竟是根據怎樣的規則來提出和表明“話語正確性”。如果討論者想在協調行動時憑信相互理解,而不是訴諸壓制、武力或其它不正當手段,那么他們自己就必須恪守他們要求于別人的“話語正確性”規則。這些包括真實性原則(話語要有根有據),合理性原則(合情合理)和誠懇原則(思想言語和心口的一致)(1979:第1-68頁,1984,第8-42頁,1990a)。哈貝瑪斯通過從認識論到交際能力的框架轉換,把批判理論的關注點由知識理性轉向交際理性,從而更加強調批判思想在民主政治中的介入。
批判性的民主介入是當今西方新型社會運動和“激進民主”的基本策略和實踐方式。哈貝瑪斯贊揚新型的社會運動(環境保護,婦女解放,和平非戰,爭取人權,等等)的解放性和民主意義,因為人們以此為手段來維護遭受威脅的生存世界,不讓它繼續受到國家權力和金錢資本的侵襲(1981,1987:第393-396頁)。這些新型社會運動成為當代西方交際行為形式和自由話語原則的體現。這些集體行為活動在對抗制度性的壓迫和專制中發揮了遠遠超過個人抗議和抵制的作用。
哈貝瑪斯所討論的不僅僅是“微觀政治”,而且是“微觀政治”的有效主體(集體而非個人),它的性質(生存世界對抗制度侵蝕)和它的道義基礎(求解放,反操控,反專制)。由于這些社會運動對分享國家權力不感興趣,由于它們關注的是如何形成更合理、更具解放性的新型集體身份,研究者便很難以傳統的政治理論或社會學概念范疇分析它們。后現代理論常常自稱為這些運動提供了思想基礎,在某種程度上,這么說也許并非為過。但是在批判理論看來,這些運動所體現的并非“后現代”觀念或價值,而是對“‘現代’價值有選擇的激進運用”〔注2〕。新型社會運動所體現的是當今西方社會內部民主化的趨向和特征,它并不以尋找替代性制度為目的,它所對抗和抵制的是國家權力對社會步步進逼的控制,它在現有體制的邊緣處展開,相互聯系呼應,形成了“激進民主”的改革浪潮。它的目的是社會的進一步民主化(“激進民主”),而不是后現代化(解構民主價值)。
“激進民主”的民主所指的不僅是一種政治操作程序,而首先是一種價值理性,一種文化。許多不同背景的思想家,杰佛遜和愛默森,馬克思和葛蘭西,約翰.穆勒和杜威,都在不同程度上對激進民主觀念作出了貢獻。他們都從不同的角度把民主參與人的自我發展和自我實現的途徑聯系起來,人民參與的機會越多,他們的民主素質也就越高。民主素質指的是對差異的寬容,對非己立場的尊重,對一己意愿傾向的檢討,對價值道德問題的關切,等等。這些素質都是民主決策所必不可少的。激進民主認為,民主并不是如自由民主者所認為的那樣,僅僅表現為權力制衡。激進民主不僅警惕權力在當權者手里過分集中,即“絕對的權力意味著絕對的腐敗”;激進民主對民眾的無權無助保持同樣的警覺,即“絕對的無權同樣意味著絕對的腐敗”。由于激進民主非常看重民主幫助民眾獲得力量,民眾通過民主自我增強的機能,它把民主當作一種生活方式,一種能自行產生理性倫理和價值的決策機能,一種促使社會和人進行自身轉化的生存形式。
哈貝瑪斯的交際理性和行為理論在當代激進民主理論中具有重要的地位。這一理論向人們展現的民主理念具有鮮明的特色,它揭示了存在于政治判斷和民主體制之間的話語關系,或者說,它特別強調政治判斷和民主制度之間關系的話語性質。他的理論把話語(話語理性、倫理和規范)擺在了民主理論的中心位置。話語不僅是解決爭端和促成集體行動的手段,更是民主制度運作的檢驗和合理性所在。哈貝瑪斯正是從民主的話語性質強調了激進民主的兩個基本命題。第一,忽略或壓制個人的自治、自我發展和自我兌現,也就無公正的政治可言。第二,民主參與有助于提高個人能力和素質,民主參與是個人的自我發展和自我實現所必需的。哈貝瑪斯對這兩點都是從當今社會的現代性來闡述的。
現代社會的特征和運作使不少人看不清為什么社會需要民主化,更對民主化的可能失去信心。現代社會高度復雜的架構、大規模的深度分工、嚴格的科層組構,加深了人的無助感,個人的日益渺小似乎使民主參與和民主評判理想越來越遙遠,唯一可能的民主似乎也就只剩下通過選舉、游說或疏通以形成利益聯盟或權力制衡。哈貝瑪斯的觀點與此不同,他認為,隨著傳統生活世界的瓦解,人們面臨著新的要求、選擇和自由(1992a:第7章)。隨著社會日趨復雜,人們發現自己處在多重無法用傳統的身份認同來說明的新的角色位置上。而在這種情況下人們就不能不自己來構建新的身份認同。一方面,復雜的體制也越來越迫使人們通過話語協調形成新的身份;另一方面,新的身份認同的出現又要求體制空間作相應的調整。例如,在失去傳統“階級劃分”,“成分”失去身份定位之后,如何為新的社會身份(如實業家,白領雇員,技術、管理人才,等等)爭取合理性和重要性,便成為一種必須在經濟、文化等多中社會體制中敘述界定(必然是話語性的)的協調過程。一旦出現了這些新的社會身份,舊的經濟文化體制也就不能不受到沖擊,隨之變更。這種雙向運作不是集中權力意志或國家政策的結果,而是體現了“民主自強”(empowerment,它是話語身份構建的條件)的運作。確立這種相對獨立的身份是復雜的、非傳統的現代社會運作的根本條件,它也是在現代體制,尤其是民間社會體制中,形成有效合作、權威和集體行動能力的唯一途徑(1990b)。
哈貝瑪斯把“民主自強”視為一種現代社會的可能性和生成功能:只要現代社會運作,就不能沒有“民主自強”,也不會沒有“民主自強”。這一觀念對民主理論具有極重要的意義 。民主轉化是解決現代社會本身的矛盾所迫切需要的。較早的參與性民主觀認為,民眾只有在有機會、有時間、有經濟能力時才會作政治參與,民主必須等到“條件成熟”時方能實行。但從哈貝瑪斯理論來看,現代民眾通過民主自我塑造,其迫切性來自他們生活于其中的現代社會本身,正是由于現代社會的復雜和差異,不通過民主,人就根本無法自我確立。政治朝民主化方向改變,不是要不要的問題。隨著社會的現代化發展,政治的民主變化是一定要發生的。所以,我們更應關心如何使民主化產生好的后果。這是民主現代自我轉化的一個重要課題,民主經驗如何產生更好的國民,素質更高的公民。
哈貝瑪斯把民主看作一種對待爭論、協調集體行動的一般方式,而不僅是以體制為所處的某種程序。在現代國家實際介入民間社會方方面面的今天,這一民主觀尤為重要。傳統民主理論強調國家和民間社會的區分,在此基礎上強調民意代表的作用和政府接受民意制限。但是現代國家的經濟調控,預算和金融政策,對工業科技發展和教育的影響,對出版、集會和社會福利的控制力,等等,使民間社會體制大大政治化了。這些體制不會自動成為與國家權力抗衡的民主機制,它們自己必須面對民主化的問題。這些體制必須從民主而不是其它協調方式(傳統觀念、市場或政治強權)去獲得權威性。民間社會體制中和體制間的民主化可以改變或阻制國家權力的進一步膨脹和集中。這樣的民主觀也和傳統的民主觀有區別,它所強調的不是人民控制國家,而是如何建立理性權威。這樣的權威所涉及的不只是政黨、領袖,而更重要的是法,尤其是憲法,公民由對憲法的認同而形成的共同身份感(公民性)以及集體一致性(國家統一和團結)。
四、公民和憲法愛國主義
哈貝瑪斯對民主場所和合理性的思考一向是粗線條的。這種思考在他1992年在德國出版的《事實和規范:關于法理論和民主散論》(1992b)一書中轉化成對政治制度更為具體的分析,其中對法的正面評價尤其引人注目。早在《交際行為理論》這一著作中,哈貝瑪斯就把現代法(包括它的普遍性和人權內容)看成是人類道德實踐學術的重大成就。但是哈貝瑪斯更強調,盡管現代法有其正面作用,但法并不能保證民主,也不等于民主;法制倒是很容易成為擴大政府行政權力的工具。因此,哈貝瑪斯談的更多的是法的兩面性和負面作用(1987:第357-363頁)。在《事實與規范》中,哈貝瑪斯關心的較多的是法的正面作用。哈貝瑪斯肯定法對于社會穩定的作用,他強調要從法在現代政治中應體現的正面價值規范去理解它對社會穩定的作用。也就是說,法有助于社會穩定。哈貝瑪斯也指出,法穩定社會也可能只是表面現象,有的法并不完全具有普遍的正面規范價值,它所起的作用只是遮掩專制和暴力。正面意義的現代法,如基本人權法和憲法,使得社會行為者在嶄新的歷史意義上獲得一種關于“合理性”和“團結”的集體意識,這是任何傳統的體制(如民族或傳統)所無法給予的。哈貝瑪斯稱這種現代的集體意識和以此為基礎的集體身份認同為“憲法愛國主義”。
“憲法愛國主義”是哈貝瑪斯長期關心的問題。在哈貝瑪斯那里,憲法愛國主義是一種道德政治的普遍規范。德國的歷史和社會現實對哈貝瑪斯形成這一理念起了重要的作用。對于歷經了納粹主義禍害,艱難地走上民主之道的德國來說,所謂“聯邦共和”與其說已經是一個事實存在,還不如說是一種有待于實現的價值憧憬。在德國,共和精神(和什么樣的國家形式才能實現這一精神)與其說已成為文化現實,不如說是一種歷史夢想的繼續,它和德國充滿變化和起伏的歷史息息相連,從19世紀的德國自由主義,到俾斯麥統一德國,德國在中歐崛起,魏瑪時期再到法西斯年代,兩德分裂,直至89年后充滿曖昧和變數的統一。德國缺乏一種象英、法、美那樣的持續而穩定的傳統民主政治文化。如何從充滿道德和政治災難的歷史中發展出真正民主的、具有普遍意義的政治文化,這是如何實現真正的德國“聯邦共和”的基本現實問題。
哈貝瑪斯認為,戰后西德的憲法,即“基本法”,體現了理性的民主政治文化的精神。哈貝瑪斯強調,憲法的基本精神是確定人的自由和平等。德國人對德國的認同(愛國主義)是以對這部基本法的規范價值的認同為基礎的:“我們的愛國主義不能否定這個事實,那就是直到奧斯維茨之后,也可以說只是在這一道德災難的震撼之后,民主才在德國公民,至少是那些年輕一代的德國公民的思想和心靈中扎下根來”(1985:第41頁)。哈貝瑪斯指出,一個民主國家的理性憲法體現了一種預先確立的、抽象化原則性的社會契約,它是一切具體共識和妥協的基礎:“在多元化社會中,憲法代表形式的共識。公民們在處理集體生活時需要有這樣的原則,這些原則因為符合了所有人的利益,因而可以得到所有人的理性贊同。這樣一種社群關系是建立在相互承認的基礎上的,每個人都可以期待別人待他如自由和平等之人”(1992b:第638頁)。
1990年,兩德重新統一后的聯邦共和國,不得不再次向自己提出國家身份認同和自我認識的問題,現代德國究竟要成為一個什么樣的民族國家?是不是要讓它的歷史來規定它的現刻?今天的德國是不是要從歷史的德國尋求它的特性?以什么來認識它作為一個文化或政治的實體?是以它的疆域或者同祖國的血緣關系,還是以一種多元文化但具普遍意義的公民觀念?德國是共有一片疆土、共有日爾曼祖先的德國人的共同體,還是具有多元文化的德國公民的共和共存的國度?作為一個有深沉社會關切的知識分子,哈貝瑪斯所思索的是如何把握與民主生活方式相一致的現代德國民族國家身份。現代德國國家的身份必須植根于現代德國公民的生活世界之中,而不能禁錮于是狹隘的“德意志性”(德意志民族性或傳統)之中。哈貝瑪斯對現代德國的民族國家性質和身份的思考對中國文化批評具有特別重要的啟發意義,因為現代中國具有類似現代德國的歷史經驗:缺乏可以依賴的民主政治文化傳統,專制政權對民主愿望的踐踏和蹂躪,以及因國家分裂和意識形態沖突而無法形成統一而穩定的國家實體。
哈貝瑪斯認為,同祖宗、同傳統文化并不是分裂國家達到統一的必然條件,既然這些因素從一開始就沒有能防止國家的分裂,那么它們又為什么一定是國家統一的條件?沒有共同政治文化的統一是脆弱的。這樣的統一也許有經濟或其它理由,但難免因經不起考驗而再次分裂(1992c:第1頁)。提出現代國家統一的價值規范問題,是哈貝瑪斯“憲法愛國主義”的精髓。哈貝瑪斯提出的問題是:非強制性的政治、社會和文化結合會是什么樣的?哈貝瑪斯認為這種結合應從政治文化的形式普遍性(即話語性)得出它的原則標準。
“形式普遍性”是相對于實體文化或實體生存世界而言的。形式普遍性承認由差異構成的多文體整體。形式普遍性的關鍵在于,一個人在憲法共和國中的公民身份(共和精神)和他對一個文化群體的親近感(民族感情)之間所存在的關系,并不具有嚴格的概念紐結,這一關系只是歷史的偶然,人們并不非要有相同的民族背景才能在一起共同提倡和維護普遍的公民權利(1992c:第7,12頁)。對于現代人來說,要緊的不是學會在民族文化中生活,而是在政治文化中生活;要緊的不是去尋根或尋回與他人同根的感情,而是學會如何批判地查視自己的利益以便進入理性的協商程序。這便是具有形式普遍性的民主政治文化。
民主的政治文化具有形式普遍性,公民性也具有形式普遍性。例如,中國公民并不必須具有“漢人”或“中華人”一類的民族實質性,也不必須信奉某種宗教或主義。正是由于公民性有形式普遍性,不同人群才能在憲法原則下團結在一起。正是由于公民性的形式性和非實質性,公民的共同性才能擺脫傳統、民族、意識形態的桎梏,奠定憲法民主的基礎,成為一種規范性的結合程序。
由于其形式普遍性,現代公民性還是當代世界范圍內民主化的重要條件之一。現代公民性適合于具有共同政治空間的多文化聯系,這個共同的政治空間的范圍可大可小,可以是民族國家,可以是國際區域,也可以是世界范圍。這樣的公民身份是一種后民族身份認同,它是民族國家范圍內公民團結和結合的基礎,同時也是世界性的,是在世界范圍內推進民主的條件。所以哈貝瑪斯說:“只有在民主法制的憲法框架中,不同的生活方式才能平等地共處。但是,這些不同的生活方式必須在共同的政治文化中才能重合,這也就意味著它們必須對其它生活方式持開放態度。只有民主公民性才能開啟世界公民性的道路,世界公民性必然不會將自己封閉在局部偏見之中,必然會參與全球范圍內的政治交際”(1992c:第17頁)。
哈貝瑪斯的現代性理論是宏觀的,然而它的理性追求和倫理原則卻是建立在實實在在的關于民主問題的關心之上。這種宏觀性和民主精神的結合成為哈貝瑪斯歷時長久、涉獵寬廣的理論工作的特殊印記。可以說,這不只是他個人的理論印記,也是我們這個現代和后現代交匯,民主和不民主爭戰的時代的印記。我們和哈貝瑪斯都生活在這樣一個時代,我們沒有理由不關心哈貝瑪斯關心的問題。
〔注1〕參見Rick Roderick, Habermas and the Foundations of Critical Theory (London: Macmillan and St Martin's Press, 1986); David Rasmussen, Reading Habermas (London: Blackwell, 1990); Alex Callinicos, Against Postmodernism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1990).
〔注2〕Claus Offe, "New Social Movements: Challenging the Boundaries of Institutional Politics," Social Research, 52 (1985): 817-68.
本文所涉及的哈貝瑪斯著作:
1971. Knowledge and Human Interests. Trans. Jeremy Shapiro (Boston: Beacon Press).
1973. Theory and Practice. Trans. John Viertel (Boston:Beacon Press).
1975. Legitimation Crisis. Trans. Thomas McMarthy (Boston: Beacon Press).
1979. Communication and the Evolution of Society. Trans. Thomas McMarthy (Boston: Beacon Press).
1981. "New Social Movements,"Telos 49: 33-37.
1984. The Theory of Communicative Action. Vol. I. Reason and the Rationalization of Society. Trans. Thomas McMarthy (Boston: Beacon Press).
1985. Die Neue Unubersichtlichkeit (Frankfurt: Suhrkamp).
1987 The Theory of Communicative Action. Vol. II. Lifeworld and system: A Critique of Functional Reason. Trans. Thomas McMarthy (Boston: Beacon Press).
1989a. The Structural Transformation of the Public Sphere:An Inquiry into a Category of Bourgeois Society. Trans. Thomas Burger (Cambridge, Mass: MITPress).
1989b. The New Conservatism: Cultural Criticism and the Historians' Debate. Ed. and trans. Shierry Weber Nicholsen (Cambridge, Mass: MITPress).
1990a.Moral Consciousness and Communicative Action.Trans. Christian Lenhardt and Shierry Weber Nicholsen(Cambridge, Mass: MIT Press).
1990b."What Does Socialism Mean Today? The Rectifying Revolution and the Need for New Thinking on the Left," New Left Review, 183: 3-21.
1992a.Postmetaphysical Thinking.Trans. William Mark Hohengarten(Cambridge, Mass: MIT Press).
1992b.Fakitizitat und Geltung: Beitrage zur Diskurstheorie des Rechts und des Demokratischen Rechtsstaats(Frankfurt: Suhrkamp).
1992c."Citizenship and National Identity: Some Reflections of the Future of Europe," Praxis International 12/1: 1-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