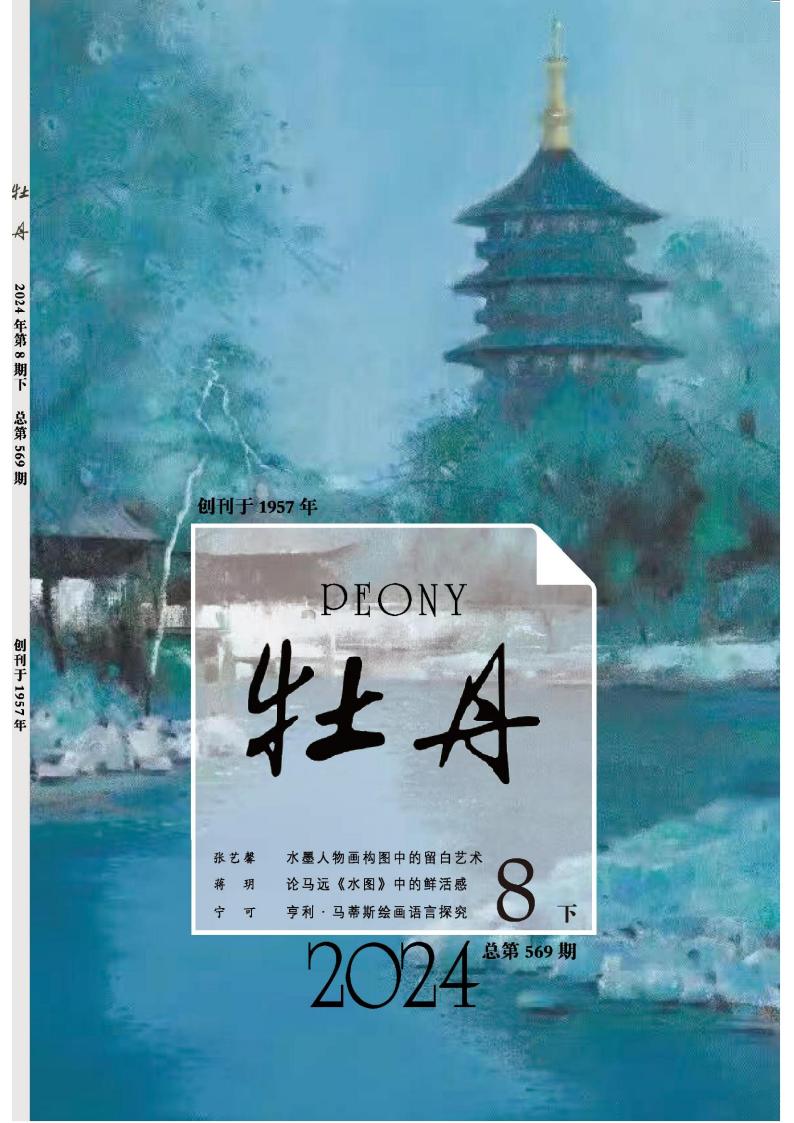抗日時期的國民政府與西北開發
佚名
【提要】本文以翔實、具體的第一手資料為基礎,著重就國民政府開發西北的戰略構想,舉措與實績,以及對西北地區的進行了探討。全文共分三大部分:第一部分旨在九一八事變前后西北地區戰略地位的變化和國民政府開發西北戰略構想的演變,認為整個開發過程經歷了初步醞釀(1928-1931)、著手實施(1931-1937)、積極推進(1937-1945)三個階段。第二部分主要選取水利建設、農業開發、工礦業諸領域,以豐富的事實和數據,展現國民政府從戰時環境和需要出發,所采取的一系列政策、舉措、辦法,以及開發取得的成就。第三部分則從西北地區農業的進步和近代化程度的提高、商貿事業的發展和繁榮、東西部經濟文化交流與合作的擴大,分析了國民政府開發西北活動的影響。論文指出,作為策劃者和組織者的國民政府,為西北開發做出了積極的努力,發揮了相當的作用,其成果不僅為打破日本的經濟封鎖、支持長期抗戰、爭取抗戰勝利做出了貢獻,而且為改變西北的落后面貌奠定了初步的必要的基礎。但國民政府在西北開發中存在著諸多缺陷、不足和,特別是其開發的主旨是直接為戰爭服務的,起決定作用的是軍事上的需要而不是該地區的全面而長遠的發展。因此,隨著抗日戰爭的勝利,國民政府開發西北的熱情遽減,各種開發、建設工作也停頓了下來,最終導致西北地區的社會經濟再次陷入低谷。
【摘 要 題】民國史
【關 鍵 詞】抗日時期/國民政府/西北開發
【 正 文】
任何一個政權,為了維護其統治地位,除了鎮壓反對者的職能外,都不能不執行組織社會經濟文化生活的公共職能。1927年4月成立的南京國民政府(1932年春曾一度移駐洛陽辦公;1937年11月-1946年5月曾遷都重慶)也不例外。20世紀30年代九一八事變后,隨著日本的步步進逼和國防建設的需要,國人開發西北的呼聲日漸高漲,國民政府遂將關注的目光投向比較閉塞的西北地區,開始制定開發西北的政策,并著手實施。全面抗戰爆發后,西北與西南一起成為抗日總后方,開發活動達到了高潮,西北因此而獲得了自近代以來前所未有的發展和進步。而作為此次開發策劃者與組織者的國民政府,在整個西北開發過程中發揮了相當重要的作用。本文擬就抗日時期(1931-1945)國民政府開發西北的戰略構想、舉措與實施、以及對西北地區社會經濟的影響進行探討,期收拋磚引玉之效。
一西北地區所處地位及國民政府開發西北戰略構想的演變
西北是中華民族的發祥地之一,在我國社會文明的開創階段和周秦漢唐時期,曾有過令人艷羨的輝煌。然而,隨著的變遷、經濟重心的東移以及航海事業的發展,東南沿海地區國際交往通道進一步擴大,盛極一時的絲綢之路逐漸成為歷史的遺跡。步入近代,由于西方列強的攻略和歐風美雨的浸染主要來自海路,因而東南沿海成為我國外源后發型近代工商業的匯聚之所和先進生產方式的重心所在。而西北各地,則因交通不便,某些條件惡劣,新的經濟成分極其薄弱。當時,社會上除少數有識之士大聲疾呼,希望國人注意西北邊防外,晚清政府和社會各界則對西北地區很少關顧。民國初年和北洋軍閥統治時期,孫中山先生曾發表《實業計劃》(即《建國方略之二:物質建設》),提出了建設西北鐵路、開發西北資源的一系列設想。但當時的既不具備實現這一宏偉計劃的歷史環境,也缺乏推進它的社會力量和物質條件,致使孫先生的"實業計劃"未能付諸實施。
1927年4月以蔣介石國民黨為代表的國民政府上臺后,在大力推行"武力統一"與"和平統一"政策的同時,也開始逐步關注開發西北、建設西北的問題。事實上,這種關注先后經歷了初步醞釀(1928-1931)、著手實施(1931-1937)、積極推進(1937-1945)三個階段。
1927-1931年,是南京國民政府的創建階段,也是其開發、建設西北的初步醞釀階段。從1928年起,不僅國民政府召開了咨詢性的全國經濟會議和全國財政會議,成立了建設委員會(1928年1月)和全國經濟委員會籌備處(1931年3月),而且國民黨二屆五中全會還通過了《統一財政,確定預算,整頓稅收,并實行經濟政策、財政政策,以植財政基礎而利民生決議案》。與此同時,國民政府也確定了開發西北、建設西北為其要務之一,并相繼派出西北考察團、西北實業考察團等進行實際考察,作為開發西北的依據。1930年,國民政府建設委員會制定了《西北建設計劃》。1931年5月,國民會議第七次大會通過了《開發西北辦理工賑,以謀建設而救災黎案》等。但這一階段由于蔣介石國民黨事實上將主要的人力、物力、財力集中用于剪除異己和圍剿南方的工農紅軍,并未真正把開發、建設西北當作"要務",因而其開發、建設西北的種種計劃和決議只不過是一紙空文,社會影響微乎其微。
1931-1937年,是國民政府由頑固堅持蔣介石"安內攘外"的總國策而最終轉向抗日的階段,也是其開發、建設西北的戰略構想進一步具體化并著手實施階段。從九一八事變東北淪陷,到一二八事變上海直接遭受蹂躪;從偽滿洲國沐猴而冠,到華北事變平津門戶洞開,民族危難日甚一日,局部抗戰時起時伏。朝野上下,嚴厲譴責蔣介石的誤國政策,紛紛要求國民政府積極備戰,加強國防建設,以抵御日本的侵略。與此同時,許多愛國人士如胡應連、王聰之、胡逸民、馬鶴天、郭維屏、李慶lín@①、李維城等都發出了"開發西北"的呼聲,"認為西北是中華民族的出路,要恢復中國版圖,必須以我民族發祥地的西北做大本營,要集中全力來開發西北"。(注:朱銘心:《九一八與西北》,《西北問題》1934年第2卷第1期。)1932年4月,長江通訊社西北考察團主任記者羅靖及華僑團員羅正剛等8人在考察西北告竣后,專門向國民政府行政院呈送報告書,詳細闡述了開發西北的理由、事類、策略及第一步計劃概要。(注: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長江通訊社西北考察團史料兩件》,《民國檔案》2000年第3期。)受各界輿論的影響,國民政府的一批政要人物也發表言論,倡言開發西北的重要性。如國民黨元老邵元沖指出:"以今日之國勢而論,東北則藩蘺盡撤,東南則警耗頻傳,一有非常,動侵堂奧,故持長期奮斗之說,力主建設西北之,以保持民族之生命線……"(注:邵元沖:《西北建設之前提》,《建國月刊》1936年2月第14卷第2期。)1934年,《開發西北》雜志創刊,蔣介石親筆題寫"開發西北",其他如宋子文、孔祥熙、何應欽、于右任等亦有題詞。蔣介石還在西安發表演講說:"我們大家都是黃帝以來圣祖神宗的后裔,祖先既有那樣偉大的聰明智力,那樣偉大的精神氣魄,那樣偉大的事業,難道我們就沒有嗎?"他號召國人要繼承祖先的光榮傳統,為開發西北做出貢獻,并對開發的工作做了具體指示:"蓋各種建設,固貴因地制宜,因時制宜,而一貫之政策與通盤之籌劃,財力要必不可少,此應由中央負責籌劃。"(注:《開發西北》月刊,1934年11月第2卷第5期。)全國經濟委員會常委宋子文在考察蘭州時指出:"西北建設不是一個地方問題,是整個國家問題。現在沿海沿江各省在侵略者的炮火之下,我們應當在中華民族發源地的西北,趕快注重建設。"(注:宋子文:《建設西北》,《中央周報》1934年4月第309期。)又說:"建設西北是我們中華民族的生命線,西北人民所負之責任,不僅是充實本身利益。"(注:宋子文:《西北建設問題》,《中央周報》1934年5月第310期。)這是國民政府中央大員第一次把西北建設提高到國防戰略的高度,把西北開發與國防建設的重要性結合起來。時任國民政府軍政部長的何應欽也發表《開發西北為我國當前要政》的文章,認為"西北為中華民族搖籃,又是中國大陸之屏蔽。從國防考慮,從經濟考慮,從文化考慮,都需開發"。(注:《中央周報》1932年第199期。 )于是"'開發西北'、'建設西北'之聲浪,甚囂塵上,上而當輔諸公,下至關心西北之黎庶,莫不大聲疾呼,細心籌劃。直有對西北之開發,刻不容緩,對西北之建設臾須促成之趨勢"。(注:張繼:《國人宜注意西北問題》,《中央周報》1934年2月第298期。)
面對民族危機的加深和時局的急劇變化,國民政府一方面繼續堅持"安內攘外"的總國策,另一方面,也騰出一部分精力,開始著手國防建設,強調要以西北為中華民族的復興地和生命線,進行重點建設。正如戴季陶赴西北考察時所說:"若就歷史上、政治上、經濟上之地位而言,則建設西北國防,當先借西安為起點,現在中國整個之國防計劃,主力即全集中西北,則建設國防,自當西安始。關中之建設完畢,乃經營蘭州,而以甘肅為起點,完成整個中國國防建設。"(注:戴季陶在西安各界歡迎會上的講話:《中央關于開發西北之計劃》,1932年4月21日。)1932年3月,國民黨四屆二中全會通過決議,決定"以長安為陪都,定名為西京"(注:西安市檔案局、西安市檔案館編:《籌建西京陪都檔案史料選輯》,西北大學出版社1994年版,第5頁。),并隨即成立了以張繼為委員長的西京籌備委員會和以褚民誼為主任的該會駐京辦事處。后經宋子文提議,又由西京籌委會、全國經濟委員會、陜西省政府合組西京市政建設委員會,合力進行西京市政的規劃和建設工作。由于"西京市政建設實為建設西北之起點,建設西北之策源地"(注:西安市檔案局、西安市檔案館編:《籌建西京陪都檔案史料選輯》,第88頁。),因而有關開發西北的決議案也紛紛出臺。如附有開發西北計劃大綱的《開發西北案》、《關于開發西北之各種決議應即速實行案》、《西北國防經濟之建設案》、《擬請提前完成隴海線西蘭段鐵路以利交通而固邊防案》、《促進西北案》等等。這一時期,國民政府內開發西北的言論之層出不窮,開發西北的各種計劃和決議之連篇累牘,形成一種奇特的景觀,這是近代西北開發史上未曾有過的。與此同時,中外人士爭相到西北地區進行考察、采訪、,中央銀行、中國銀行、交通銀行、農民銀行和不少私營商業銀行,以及上海銀行附屬的中國旅行社,爭相到西北地區設立分支機構,擴展業務。由此,國民政府在"開發西北"的高唱聲中轉向了具體的實施和經營。諸如隴海鐵路的向西延展,多條公路的勘測和施工,水利工程的興修,近代工業的創辦等,都是實施西北開發的明證。可以說,從九一八事變到七七事變以前,國民政府的戰略構想是以西北作為未來對外戰爭的戰略基地的。不過在1935年底以后,隨著全國幣制的統一和川、黔、滇等省地方實力派的"中央化",國民政府遂將西南與西北相提并論。蔣介石和龍云談到建立后方根據地時認為:"對倭應以長江以南與平漢線以西地區為主要陣線,而以川黔陜三省為核心,甘滇為后方。"(注:薛光前:《八年對日戰爭之國民政府》,商務印書館1978年版,第59頁。)蔣介石還多次強調四川是"立國根據地"、"民族復興的根據地"。可見西南的戰略地位也在迅速上升。
1937-1945年,是全民族舉國一致抗擊日本侵略的階段,也是國民政府積極推進西北開發和建設的階段。1937年7月7日,日本法西斯發動了旨在滅亡全中國的侵略戰爭。在幾個月的時間內,我國華北、華東的大片領土淪于敵手。11月20日,國民政府正式宣布遷都重慶。從此,以重慶為中心的西南地區的戰略地位日益突出,西北與西南一起成為抗日的大后方,也成為長期戰爭的戰略支撐點。1937年7月25日,日本突然宣布封鎖中國沿海港口;1940年六七月間,日本又迫使法國、英國封鎖了滇越鐵路、越桂公路和滇緬公路;1941年12月太平洋戰爭爆發,香港淪陷,緬甸被占,致使西南國際援華陸路交通線完全繼絕。而西北地區與蘇聯之間的陸空運輸仍暢行無阻,新疆、甘肅、陜西成為國際援華的主要通道。于是西北的戰略地位變得更加重要,開發西北的呼聲再一次高漲起來。為此,國民政府加大了對西北開發的投資力度,并實行政策傾斜。1938年,國民政府經濟部長翁文灝發表談話指出,戰前我國經濟建設分布失調,發展畸形,今后應注意內地建設,"以西南、西北為基礎"。1939年1月,國民黨五屆五中全會通過決議:"今長江南北各省既多數淪為戰區,則今后長期抗戰之堅持不懈,必有賴于西南、西北各省之迅速開發,以為支持抗戰之后方。"(注:李平生:《烽火映方舟--抗戰時期大后方經濟》,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1995年版,第17頁。)1942年為了配合戰時經濟政策,開發西北經濟,國民政府經濟部下令工礦調整處及遷川工廠聯合會,邀集工業界專家及技術人員21人組成西北工業考察團,前往陜西、寧夏、甘肅、青海等省進行實地考察,對當地的自然條件、物產資源及工農業狀況作了實地調查,并撰寫了詳細的考察報告以及開發西北地區工業的詳細計劃,表明了對西北地區經濟開發的重視。
總之,作為抗日的大后方,西北地區地位之重要顯而易見。以民族言,西北各省漢、滿、蒙、回、藏,五族俱全,民情誠樸,吃苦耐勞,勇敢善戰;以物產言,西北的動植五金食用俱全,煤鐵錳硝,皮棉石油,出產尤富,舉辦重工業,取之不盡,用之不竭,足以與暴日作長期抗戰之用。特別是東南海口被封以后,可由新疆另開出路,與歐亞各國聯絡,以獲國際物資的援助。且西北原是中華民族的搖籃地,中華民族文化的發祥地。正如有的論者所說:"我們無論從哪一方面去估計西北,西北在今天實不容再忽視了。它的資源開發,它的國際運輸,它的拓殖增產和它的文化再發揚,都足以補助抗戰根據地西南的不足。"(注:徐旭:《西北建設論》,上海中華書局1943年版。)
二國民政府開發西北的舉措及其實施
抗日時期,由于西北在全國所處地位的變化,國民政府從戰時環境和需要出發,采取了一系列開發西北的具體措施和辦法,取得了多方面的重要成就。以下僅就交通水利、農業開發和近代工業的發展加以論述。
(一)發展交通與水利事業是國民政府開發西北的首要目標
交通既是經濟發展的動脈,又是衡量一個地區經濟發展的尺度。交通便捷,才能談得到政治、經濟和文化的發展。西北資源雖豐,但苦于交通梗塞,以至所有資源都無從開發,這也是近代西北落后的主要原因之一。這種狀況很難適應國防建設的需要。因此,國民政府決定把開發西北的首要目標放在發展交通事業上,使之成為發展西北經濟鏈條上的首要環節,尤其以鐵路建設為重。1928年冬國民政府鐵道部成立后,鑒于隴海鐵路的延展是從海州(連云港)直達西北地區的東西重要干線,乃決定將隴海鐵路(當時通車至靈寶)向西展筑。1929年首先續修靈(寶)潼(關)段,因戰事影響,直至1930年12月通車到潼關東門外。為展筑潼(關)西(安)段,鐵道部于1931年4月設立潼(關)西(安)段工程局,開始勘測施工;1934年12月通至西安;1935年4月,潼西段工程局改組為隴海鐵路西段工程局,繼續承筑西(安)寶(雞)段,并于1937年3月通至寶雞。至此,隴海線寶雞以東至連云港1075公里的鐵路線全線通車。為確保隴海鐵路機車用煤,隴海鐵路局會同陜西省政府于1939年4月動工修建了咸(陽)同(官)鐵路支線,全長138公里,1941年11月竣工通車。另外,為了開發白水煤源,陜西省政府于1937年派工兵修建了渭南至白水輕便鐵路,1939年修成通車。
隴海鐵路的延展和另外兩條輕便鐵道的修筑,大大便利了戰時陜西對外交流,推動了陜西社會經濟的進步。
公路建設因投資少、進展快而被確定為"便利運輸交通之最先急"。七七事變前,國民政府公路建設的主要任務是修筑聯絡公路,使不成系統的各省片段線路互相溝通,以適應戰爭和國內經濟建設的需要。1934年春間,全國經濟委員會組設西(安)蘭(州)工務所,負責修筑西蘭公路,經營近一年,工程初步完成后,1935年1月又在西安設立西北國營公路管理局,專管西北各省公路建設,制訂出西北公路運輸網計劃大綱,并直接主持完成了西蘭、西(安)漢(中)公路。西蘭公路全長753公里,1935年5月1日通車。6月,蔣介石下令限"西漢公路年底通車"。(注: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全國委員會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文史資料選輯》第83輯,文史資料出版社1982年版,第203頁。)該路全長447.6公里,1934年9月開工,1935年12月完工,成為溝通西北地區與西南地區的重要通道。
全面抗戰爆發后,為了打破日本對我國沿海地區的封鎖,打通國際通道,接受盟國的援助和發展對外貿易,國民政府首先在西南抓了中印公路和滇緬公路,在西北則改善了西蘭公路和修建了甘新公路(蘭州-迪化),使之成為貫穿西北地區的國際交通線。甘新公路直接與蘇聯相連,早在20年代已具雛形,1937年底動工修建,經過兩年施工,全長1179公里的甘新公路建成通車,成為開發西北的一條重要公路干線。西蘭公路改造工程于1940年完成,改造后的西蘭公路陰雨天也可行車,是當時西北地區路況最好的公路。其次,國民政府改造和完善了一系列重要公路干線,1936年至1937年整修了華雙路華天段;1938年春整修了甘青公路。還有寧平路、寧蘭路、寧包路、西漢路等也都進行了整修。另外,國民政府在西北還新修了許多公路干線,如華雙公路天雙段,為陜西南部與甘川聯系通道;甘川公路蘭通段,為甘肅入川直通路線;漢白公路為陜南與湖北聯系通道;寶平公路,為隴海鐵路和寶漢、西蘭、寧平公路聯系樞紐;青藏公路玉樹段,全長827公里,系聯結西北與川藏地區的西部通道;此外還有寧(西寧)張公路、夏寧公路、寧陜(陜壩)公路、岷夏公路等。新疆自1935年修筑了迪伊線迪哈公路,該路于1937年7月1日完工通車,是一條重要的國際交通線,抗戰爆發后,大批蘇聯援華物資就是通過這條公路運往中國抗日前線的。1939年5月,新疆又先后興建了額敏-塔城、迪化-焉耆、焉耆-阿克蘇、阿克蘇-喀什和喀什-和闐等公路干線。
除了公路干線外,西北各省都修建了不少省內支線,如陜西從30年代初開始,先后建成了西朝(邑)公路、西zhōu@②(zhì@③)公路、西南(五臺)、西午(子午口)、原(三原)渭(南)、咸榆、渭蒲、渭大(荔)、鳳隴、鳳漢、漢寧(羌)、西荊(界牌關)、綏(德)宋(家川)、fū@④宜(川)等十多條公路。青海先后建成寧民、寧循、寧門、寧互、寧同、寧都、寧貴等公路。寧夏于1933年建成了"三大干線"、"四大支線"。(注:"三大干線"是指寧夏至包頭、蘭州、平涼的三條省際道路;"四大干線"指銀川至鹽城、靈武、預旺和定遠營的四條省內主要線路。秦孝儀:《十年來的中國經濟建設》,臺北國民黨中央黨史委員會1976年版,第7-8頁。)
總之,抗日時期整個西北地區的公路有了成倍甚至成十倍的增加(其中的西蘭、甘新、鳳漢、漢寧、漢白等線由全國經濟委員會直接撥款興筑),最終形成了以蘭州為中心的西北近代公路網和西北各省區的公路網。此外,西北的航空、水運事業也有新的成就,茲不贅述。交通建設的發展為國防建設奠定了基礎,也對西北地區社會經濟發展提供了條件。
西北建設的首要問題是交通,同等重要者即為水利。因為交通即使便利,而農產匱乏,仍不能救濟人民的貧苦。西北向來缺水,頻仍的旱荒如同惡魔威脅著當地人民的生存。為此,國民黨四屆三中全會通過《西北開發案》,其中對西北的水利作了統籌規劃,指出必須設"專門之機關與人材,作精密之考察,通盤之籌劃。凡重要工程,非地方政府力所能任者,由中央辦理,其余重要計劃、簡易工事,皆由其指導督率地方辦理也"。(注:國民黨四屆三中全會通過的《開發西北案》所附《開發西北計劃大綱》,1932年12月19日。)并先后在相關會議上形成了一系列關于興辦水利的決議,如《十年萬井計劃案》、《請撥款興修甘肅省雜大兩渠以利灌溉方案》、《提倡甘肅造林興修水利案》等。1936年全國經濟委員會制訂的《全國水利建設五年計劃大綱》,其中涉及西北水利的就有"完成關中八惠灌溉工程"("八惠"為涇惠、洛惠、渭惠、梅惠、灃惠、灞惠、耀惠、qiān@⑤惠八渠)、"整理綏遠、寧夏、甘肅水渠"等計劃案,以加強對西北水利事業的興辦,西北地區的水利建設掀起高潮。
陜西省的水利在抗日時期發展速度最快,1930-1941年已完成的大型灌溉工程就有涇惠渠、渭惠渠、梅惠渠、織女渠、漢惠渠。其中完成最早且成效最著者當首推由華洋義賑會與陜西省政府合辦的涇惠渠。此渠于1930年冬開工,次年6月完成干渠,開始放水澆地;其他支渠及修補工程,則于1935年春竣事,共費資170萬元,可灌田80余萬畝。渭惠渠興工于1935年3月,完成于1941年,共費資210萬元,可灌田60萬畝。梅惠渠(以首鑿該渠之眉縣縣長而得名)由陜西省建設廳與國民政府經濟部合辦,1936年10月動工,1938年6月完成,計用資21.6萬元;后又改善故道,督開農渠,至1941年已溉田12.2萬畝。織女渠在陜北米脂織女廟對岸,工程始于1937年,1938年底完成,用資11萬元,可灌田1.1萬畝。漢惠渠在陜南,1938年底施工,1941年6月告竣,經費共188萬余元,由陜西省與農本局合籌,可灌田10萬畝。當在進行中的水利工程有洛惠渠、黑惠渠、褒惠渠,而以省府每月撥款2萬元,全國經濟委員會協款辦理(后由經濟部主持)的洛惠渠為最大。經委會并組織涇洛工程局專司其事,于1934年3月開工,1937年底完成大部分工程,后因隧洞流沙等原因而一度中止。(注:關于1931-1941年陜西水利工程情況,綜合自全國經濟委員會《西北建設概況》(1937年8月)、陜西銀行經濟研究室《十年來之陜西經濟》(1942年8月)、趙敏求《躍進中的西北》,新中國文化出版社1940印行,第36-39頁。)所有這些,都為陜西農業發展創造了條件,也為后來西北其他各省水利建設和農牧業生產開了風氣。著名水利專家李儀祉還專門制訂了"陜西水利工程十年計劃綱要"。可惜功成僅半,便積勞成疾而逝。全面抗戰爆發后,由于國民政府的重視和支持,加之一批愛國人士的倡導和投入資金,陜西的水利建設又出現了高潮。1938年國民政府撥款10萬元,陜西省政府出資40萬元,加上華洋義振會和檀香山華僑分別資助的40萬元和100多萬元,又重新規劃了陜西"八大"水利工程。這些水利的受益面積可達300多萬畝。可見抗日時期陜西水利開發的規模和實效在全國是相當引人注目的。
甘肅的水利開發較晚。1934年經委會撥款50萬元,作為水利基金,組織測量隊就洮惠、通惠、永豐、新古各渠開始勘測,至全面抗戰爆發前僅修大型水利工程洮惠渠一項,可灌地5萬畝。1940年11月,時任甘肅省政府主席的谷正倫,聘請原金陵大學農經系教授張心一任省建設廳廳長。張氏主管農田水利建設,主張實行政企分離,多方籌資,實行合資經營開發。由于他的努力,甘肅省政府與中國銀行聯合舉辦了甘肅水利林牧股份有限公司,資本為法幣1000萬元,由省政府承擔300萬元,中國銀行承擔700萬元,1942年增至6000萬元。1945年4月行政院水利委員會亦加入。(注:羅舒群:《民國時期甘肅農林水牧事業開發研究》,載《社會科學》(甘肅)1986年第3期。)該公司的成立,對開發甘肅農田水利起到了重要作用,先后完成了湟惠渠、溥惠渠、永豐渠、永樂渠、靖豐渠,@⑥豐渠等施工任務,繼而又興建了蘭豐、肅豐、登豐等渠,加上其他水利工程共有23處。其中,蘭豐和肅豐兩渠因經費不足于1946年停工,其余21處工程均于1947年完工,計劃收益農田面積35萬畝。1943年1月,甘肅水利農牧公司又公布了河西走廊水利工程的初步計劃,決定修建永登至敦煌17個縣的水利工程,并于武威、張掖、酒泉和敦煌先后成立了34個工作站,負責整理舊渠及測驗水文事宜。到1944年,甘肅省利用庫款辦理的水利工程,"共在河西地區整理舊渠43處,可灌田384853畝"。(注:中華年鑒編輯委員會:《中華年鑒》(上),中華年鑒社1948年版,第1436頁。)
(二)開發西北農業資源是國民政府的一項基本政策和重要措施
近代西北地區的經濟主要還是以農業為支柱,而農業生產卻十分衰敝。西北農業之所以長期滯后,除了兵匪戰亂、苛捐雜稅等因素外,資金短缺,技術落后,自然災害頻繁則是其主要原因。農業的停滯不前制約著整個社會經濟和國家財政,迫使國民政府采取措施挽救經濟。鑒于西北農村生產資金枯竭,高利貸盛行,全國經濟委員會于1933年6月制定了《西北建設實施計劃及進行程序》,提出"救濟西北,當以流通農村為首務"的西北合作事業計劃。于是西北農村合作社很快發展起來。
1934年8月,全國經濟委員會首先會同陜西省政府成立了陜西省農業合作事務局。該局主要以"介紹銀行資金流入農村為原則"。但在銀行尚未投資的情況下,"全國經委會撥款30萬元,陜西省政府撥款40萬元,共70萬元作為貸款基金"(注:全國經濟委員會:《西北建設事業概況》,1937年7月。),先行辦理勸農貸款,指導組織承借農戶的互助社,作為設立合作社之初步。后通過介紹,銀行向農村貸款,作為合作貸款,擴大了貸款渠道。并在咸陽、三原、大荔、武功、鳳翔等關中5個地區成立了辦事處,辦理貸款事宜。據統計,僅這5個地區成立的互助社就有1882個,合作社1688個,申請貸款總額1881741元,已貸合貸390631元,勸貸510587元。同時還在陜北協助中國農業銀行撥款30萬元,辦理了陜北農貸(注:全國經濟委員會:《西北建設事業概況》,1937年7月。),并改組了陜南合作社。截止1936年6月前,經該局介紹的中、交銀行投資者僅關中地區就有11個縣,貸款總額647836元。(注:全國經濟委員會:《西北建設事業概況》,1937年7月。)
全面抗戰開始后,國民政府加大了對農村信用社投資的力度。1937年8月,國民政府頒布《中、中、交、農內地聯合貼放的辦法》,規定農民可以各種糧食和經濟作物產品向四行請求押放。1938年頒發了《戰時合作農貸調整辦法》,嚴令農貸不得停頓,并不得少于歷年放款數額。同年,行政院又通過了擴大農村貸款辦法,頒行《改進地方金融機構辦法綱要》,規定各地方金融機構要通過"農業倉庫之經營"、"農產品之儲押"、"種子、肥料、耕牛、農具之貸款"、"農業票據之承受或貼現"等業務,促使資金流向農村,支持農村經濟發展。1937年6月,國民政府撥款50萬元,作為甘肅農貸專款。同年12月,又續撥100萬元作為甘肅第2期農貸資金。到1938年5月,國民政府再撥款350萬元作為甘肅省第3期農業貸款,農貸的發放區域,普及全省67個縣(局)。到1941年10月,甘肅省農貸發放額達3200余萬元,全省合作社也達6000個。(注:吳文英:《甘肅之合作經營》,《甘肅合作》第18-20期合刊,第23-25頁。)
寧夏和青海的合作社起步較晚。寧夏于1942年底決定成立省合作事業管理處,全面負責推行合作社事業。到1943年,全省除兩個蒙旗外,其余13個縣均已普及,包括縣聯社、鄉鎮社、專營社等共663個社,社員69014人,股金2001899元。歷年發放農業生產貸款總額1500余萬元。(注:羅舒群:《抗日戰爭時期甘寧青三省農村合作運動述略》,《開發研究》1987年第3期。)青海省1940年6月成立合作事業管理處。1943年全省26縣共成立信用社54個,1946年增加到282個,股金18010009元。(注:羅舒群:《抗日戰爭時期甘寧青三省農村合作運動述略》,《開發研究》1987年第3期。)除信用合作社外,西北地區還成立了生產合作社、消費合作社、墾荒合作社、畜牧合作社、水利生產合作社等。農村合作社的廣泛建立,對緩和西北地區農民所受的高利貸剝削、發展農牧業生產等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增加糧食生產"、"增進棉花生產"是國民政府開發西北農業最基本的目的。為此,國民政府把發展西北農業科研、推廣農業技術、獎勵人民種植作為發展農業生產的主要途徑。
1938年秋,甘肅成立了農業改進所,專門負責改進農村畜牧生產技術的工作。這個農業改進機構內設農政、農藝、植物病蟲害、森林、畜牧、獸醫等部門。各專區亦設農業改進所進行技術推廣。經過6年努力,3個優良的小麥品種即"涇陽302"、"武功774"和美國玉米普遍在甘肅扎根。為了普及農業成果,甘肅省政府按行政院農業促進委員會關于建立全國農業推廣機構的計劃和辦法,于1940年11月1日設立了農業推廣處,還配備了農業技術人員,推廣農業科技成果。
棉花為重要的戰略物資,1934年全國經濟委員會會同陜西省建設廳成立棉花改進所,以"選育純良品種,及指導棉農以合理栽培,發展棉戶為之基本工作"。到1937年,美種"斯字棉4號"、"德字棉571號"試種成功,并分別在黃河和長江兩大流域推廣。全面抗戰爆發后,國民政府更加重視陜西棉業,全國經濟委員會在陜西專門設立棉業改良所,以提高棉花產量和質量。國民政府設立西北中央農業實驗所棉作系工作站、農林部糧作繁殖場、農業推廣處棉產改進分處等,對提高陜西及西北的農業科技水平發揮了重要的指導作用。
另外,全國經委會還撥款40萬元,設立西北改良畜牧總場于甘、青兩省之連境,作為改良西北畜牧業的指導中心,并于各省設立繁殖牧場,也對西北畜牧養殖業的發展產生了積極的影響。
(三)發展西北近代工業是國民政府開發西北經濟戰略的重要組成部分
中國近代工業的發展和布局極不平衡,大的工廠基本上集中于沿海各省市,偌大的西北地區則寥若星晨。九一八事變后,隨著國民政府開發西北戰略決策的確定和有關政策的制訂,鐵路、公路的修建,為國外機器的輸入和沿海企業的投資提供了便利,西北的近代工業才開始嶄露頭角。1934-1935年,陜西大華紡織股份有限公司、西安成豐面粉公司、中南火柴廠、西北化學制革廠等企業的成立,標志著西北輕工業的發展有了一定的進步。重工業也從無到有,這除了陜西機器局、西安電廠、新疆兵工廠等由國民政府主辦的國營工業外,商辦機器工業也破土而出。不僅各個行業得到了發展,而且西北各省的近代工業均有一定的進步,特別是過去基本沒有近代機器工業的寧夏、青海等省也開始走上了經濟近代化的道路,如電廠的設立、礦山的較大規模開發等等。
全面抗戰爆發后,國民政府確立了戰時經濟體制,比較重視西北的工業建設,采取了一些扶持后方工業的政策和舉措。首先是支持沿海工廠的內遷。在部分知識分子和愛國工商界人士的建議下,國民政府采取果斷措施把瀕臨戰區的工廠遷往內地,重新建立后方工業基地,作為戰時經濟支柱。1938年8月10日,國民政府行政院第324次會議正式決定工廠內遷,并組成以資源委員會為主辦機關的工廠遷移監督委員會,派出大批人員分赴各地負責組織實施,對于民營廠礦"遷入以后的問題,如廠地問題,機件補充問題,原料問題,技工問題,資金問題等都由政府協助和指導之下,將這些問題次第解決"。(注:高叔康:《十年來之經濟政策》,載譚熙鴻《十年來之中國經濟》上冊,上海中華書局1948年版。)從而使我國歷史上空前規模的工業遷移得以實現。遷入西北的企業主要分布在陜西的西安、寶雞、漢中和甘肅的天水、蘭州等地。到1940年6月底,僅遷入陜西的工廠即有44家。這些內遷企業的到來為戰時西北工業的發展注入了活力,成為西北近代工業的重要組成部分。國民政府在支持工廠內遷的同時,還對后方的民營工礦企業實行獎勵扶持的政策,1938-1939年,國民政府先后頒布了《非常時期礦業獎勵暫行條例》、《經濟部小型工業貸款暫行辦法》、《戰時領辦煤礦辦法》等,取消了戰前頒布的《工業獎勵法》對民營廠礦經營門類的某些限制,擴大了獎勵范圍,降低了呈請獎勵資本額,簡化了申請、批準辦法之程序和手續。這些政策在一定程度上促進了后方工礦業的發展。1942年,僅陜西省登記工廠就有72家,煤礦立案者50余家,土法煉鐵者50余家。
在扶持民營廠礦的同時,國民政府借助國家資本的力量積極發展后方的國營工礦業。尤其把重工業的建設放在首位。1935年11月,國民黨四屆六中全會提出興辦重工業;國民黨五全大會指出:"為從事經濟建設應速完成重工業",重工業建設應由"中央予以指導,令各省分別舉辦"。1935年4月,國防設計委員會易名為"資源委員會",負責指導管理全國礦業及重工業建設。整個抗日時期,國民政府及所屬的資源委員會、工業部、交通部、中央石油公司、各大銀行,加上第二、第八、第十戰區及各省地方政府,都對西北的廠礦建設進行投資,興建了一批石油、煤炭、電力、化學、機械、電器、建材等重工業企業。以石油工業為例,抗戰爆發后沿海口岸陷落,外油無法輸入而西北、西南后方運輸又大多依賴公路,石油需要日益迫切,甚至有"一滴石油一滴血"之說。為此,資源委員會決定開發甘肅玉門和新疆獨山子油礦,1938年7月,成立了甘肅油礦籌備處,并派地質與采礦專家前往玉門老君廟實地勘探,1941年3月正式成立甘肅油礦局,由孫越崎任總經理。該礦鉆井采油均較順利,成為抗戰時期全國石油工業的基地,它的能力、技術水平成為當時我國石油工業水平的一個標志。另外,資源委員會在新疆開采了獨山子油礦。玉門油礦1938年成立后,于同年秋先后鉆井8口,其中兩井深達400多米,探入大油層,產量十分豐富。1939-1945年的7年間,玉門油礦共鉆井61口,原油產量共約7866多萬加侖,煤油511.7萬加侖,柴油71.7萬加侖,此外還有石蠟等副產品。到抗戰結束時,玉門煉油廠已能日煉原油5萬加侖。這些石油產品,在"洋油"來源斷絕的情況下,直接為抗戰服務,不僅保證軍隊運輸,還滿足了后方部分地區經濟發展的需要。新疆石油的開采以獨山子石油廠規模最大。抗戰爆發后,新疆省政府于1939年同蘇聯政府商議,由蘇聯政府出資、出機器和工程技術人員經辦獨山子石油廠。由于采用機器開采生產,日處理石油達150噸,獨山子石油得到了全面開發。1943年,由于盛世才實行反蘇反共政策,蘇決定撤回專家和部分機器,后經國民政府不斷交涉,以170萬美元購得該廠全部機器,由資源委員會經辦,但由于多數機器設備已拆卸待運,該廠生產實際已停止。1942年時,僅資源委員會就以獨資經營或與西北各省政府合資經營等方式在西北創辦的礦山、能源工業就有18個。(注:魏永理:《中國西北近代開發史》,甘肅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39頁。)由此,西北作為重工業基地初具雛形。另外,中國銀行所屬的雍興實業股份有限公司在西北投資的紡織、機械、印刷等工業單位也有15個,資本總額達2403萬元。(注:魏永理:《中國西北近代開發史》,甘肅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39頁。)國營工業的建立,不僅使國有資本在經濟結構中起主導作用,而且有利于改善西北輕重工業比例的不平衡。顯然,西北近代工業的全面發展在一定程度上離不開國民政府的支持與投資。
三國民政府開發西北活動對西北文化的
20世紀三四十年代國民政府開發西北的活動,不僅為持久抗戰奠定了物質基礎,而且對西北地區社會經濟的產生了非常重要的影響。茲舉以下幾個主要方面即可知其全豹。
(一)促進了西北地區農業的進步和近代化程度的提高
抗日時期,由于國民政府制定一系列開發農業的政策,西北農業有了相當的進步。西北地區合作社的建立以及農貸的發放,對促進農業生產起到了積極的作用。如1940年,甘肅農村合作社社員借款4687410元中,用于購買牲畜者占44%;購買種子者占14%;購買農具者占5%,購買、贖回土地者占8%,購買肥料者占2%,購買糧食及其他開支占27%。可以看出,絕大部分貸款都用于農村的生產事業。(注:顧祖德:《五年來甘肅合作事業概況》(上),《甘肅民國日報》1940年7月8日。)同時由于大興農田水利事業、開墾荒地,使西北地區的耕地面積都有所擴大。以陜甘為例,1934年陜甘兩省耕地面積分別為30883000畝和21676000畝,到1946年分別增加到45627000畝和26167000畝。(注:許道夫編:《近代農業生產及貿易統計資料》,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8-9頁表2"各省耕地面積統計"。)隨著國民政府資助棉農擴大生產,推廣優良棉種,以及發展灌溉事業,棉花種植面積和產量不斷提高。1920年陜西棉花種植面積為1283650畝,到1937年增加到4829829畝。1936-1938年,陜西棉花連續3年豐收,皮棉產量分別為1110000市擔、1068000市擔和1055000市擔,是1919年至1948年30年間的最好水平。(注:許道夫編:《中國近代農業生產及貿易統計資料》,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211-212頁表8"主要棉產省區皮棉產量"。)此外由于農業的進步和農業投入的增加,糧食種植面積和產量都有所增加。以陜甘的主要農作物小麥為例,兩省小麥的種植面積分別由1937年13650000畝和8240000畝,增加到1944年的19263000畝和8652000畝;產量也由1937年的9429000市擔和8328000市擔,增加到1944年的33136000市擔和10830000市擔,這是1914年以來30年間的最高產量。(注:轉引自《試論西北近代建設》,《西北大學學報》1994年第4期,第65頁。)陜甘兩省生產的糧食,不僅能滿足自身需要,而且有力地支援了抗戰。
20世紀30年代以前,工業建設在西北幾乎是一片空白,僅有的幾家工廠主要集中在陜甘兩省,且多與軍用有關。進入30年代,隨著國民政府開發西北政策的頒布,隴海鐵路的西延入陜,公路網的初步形成,既便于國外及沿海的機器逐漸輸入,又為工業原料和產品的運輸銷售提供了保障。因此,許多廠礦首先在鐵路、公路沿線建立。不僅當地的企業家開始投資設廠,而且外地的開發商和知識界人士也先后來西北考察或投資建廠。如1932年隴海鐵路管理局組織的由經濟專家、大學教授、新聞記者等40余人參加的陜西實業考察團,對陜西的經濟狀況進行全面考察,并將考察報告編纂成《陜西實業考察》一書(該書約50萬字,1933年10月由上海漢文正楷印書局代印,隴海鐵路管理局發行(注:《陜西地方志通訊》1984年第5期,第28頁。))。再如1935年趙德山將其在徐州的玻璃廠一部分遷到西安,建立襄明玻璃廠;1936年濟南成豐面粉公司設分公司于西安;石家莊大興紗廠和武漢裕華紗廠,集資300萬元,也于同年在西安創辦大華紗廠。從1933年到1937年,陜西先后建立起紡織、面粉、化學、電氣、榨油、機器制造、打包等機器工業。
全面抗戰爆發后,國民政府把西北地區作為抗戰的大后方,對西北開發實行政策傾斜,加大了投資力度;沿海工業內遷,為西北開發提供了先進的機器設備和技術力量;抗戰初期大量公教人員和難民遷入西部,使后方的軍需民用物資日趨緊張,為西北工業的發展提供了廣闊的市場。以上這些因素成為西北近代工業發展的強大推動力,使西北近代工業建設一度出現蓬勃興旺的局面。到1942年,陜、甘、寧、青4省共有工廠839個,資本總額為16917.5萬元,工人32857人,擁有動力151718匹馬力。其中陜西工業發展最為迅速,工廠數增加到385家,工業力量僅次于四川、湖南而位居全國第三。(注:陳真:《中國近代工業史資料》第4輯,北京三聯書店1961年版,第97頁。)到1944年,陜甘兩省各類工廠數已達587家,實繳資本總額48305.6萬元,工人41605人。(注:國民政府經濟部統計處:《后方工業概況統計》,1943年5月出版。)寧夏的工業較為落后,戰時僅建工廠18家。新疆的新式工業也從無到有,共建有工廠44家。(注:陳真:《中國近代工業史資料》第4輯,第88頁。)工業的發展促進了城市化水平的提高,抗日時期西北的西安、寶雞、天水、蘭州、平涼、銀川、西寧、迪化等都發展成為新的工業城市。同時,西北近代工業的發展,也使中國的工業分布發生顯著變化,初步調整了西北地區的工業狀況,中國擁有近代工業的地域有了一定的擴大。
(二)推動了西北地區商業貿易的發展和繁榮
在明清兩代,西北地區曾出現過以從事邊境貿易和省際貿易為特色的著名的"陜西商幫",其活動范圍主要是隴青川黔蒙藏的西部地區,其財勢位居全國十大商幫前列。(注:李剛:《陜西商幫史·前言》,西北大學出版社1997年版。)進入近代,由于官府賦役的苛重,洋貨的打擊,戰爭的浩劫,加之傳統商幫缺乏新的經營理念,以及交通的不暢,西北地區的商業貿易事業日益衰落。20世紀30年代以后,隨著西北戰略地位的提高和國民政府開發、建設西北力度的加大,西北地區的商貿活動呈現出日益繁榮之勢。其主要表現是:第一,商業經營規模的擴大與輸出入商品的增加。據1943年統計,陜西省15個縣共有大小商號13289家;甘肅省全省共有商號2.5萬家,年營業額達28億。(注:魏永理,《中國西北近代開發史》,甘肅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20頁。)因陜西地處西北地區的東部,與豫鄂川晉毗鄰,是西北通往全國各地的重要通道,所以成了各省商品流通的重要集散地。從30年代起,陜西輸出入物資的價值總數不斷增加。據統計,1932年陜西商品輸出輸入總額分別是936.8萬元和1218萬元,到1936年則分別增加到2477萬元和2971萬元;1937年又分別為1561萬元和4842萬元。(注:魏永理,《中國西北近代開發史》,甘肅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63頁。)毋庸諱言,這種多年入超的情況,當然反映了西北地區商品經濟落后性的一面,但商品輸出入總額的增加,又顯示出西北地區商貿規模不斷擴大的趨勢。第二,新型商業貿易組織--股份公司的發展也較為迅速。為適應大規模商業活動的需要,西北地區的商業組織形式也發生了質的飛躍,出現了近代意義上的商業股份有限公司。如蘭州市1945年商業股份公司已有12家,支公司17家,資本總額達8685.74萬元。(注:《蘭州商業公司設立狀況表》,1943年。)新疆有裕新土產公司、省貿易公司,還有民辦的華新公司。寧夏有富寧貿易公司,青海有協和貿易公司和德興海貿易公司等。第三,形成了許多具有重要影響的商業中心。由于商業的繁榮,西北地區的西安、蘭州、銀川、迪化等城市的貿易地位不斷提高,成為戰時后方的貨物集散地和商貿中心。西安是連接中原、西南和西北地區的商貿中心;蘭州是西北交通樞紐,是聯系青海、新疆、寧夏的商貿中心;銀川是連接西北與華北的商貿中心;迪化是戰時西北國際通道的連接中心,也是抗日時期中國對蘇貿易的橋頭堡。1937-1938年夏季,約有6000噸各種物資通過新疆;1938-1941年間,中國經新疆向蘇聯運輸的戰略物資有鎢、錫、汞、銻、鋅、桐油、羊毛、豬鬃、生羊皮等。(注:這些物資的數量分別是:鎢砂14664噸;錫7385噸;汞150噸;銻4075噸;桐油7768噸;羊毛10500噸;豬鬃6340噸;生羊皮1315000張。魏永理,《中國西北近代開發史》,甘肅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09頁。)此外,中國還通過地方貿易從新疆向蘇聯出口了350多萬頭羊,1039萬張羊皮,29413噸羊毛和其他產品。(注:徐萬民:《八年抗戰時期的中蘇貿易》,《近代史》1988年第6期,第203頁。)這些商貿中心的形成和發展,在一定程度上改變了以前中國商貿發展不平衡的狀態。
(三)加強了東西部經濟文化的交流與合作
從30年代起,隨著國民政府開發西北活動的展開,交通狀況的改進,西北與東南、西南各省的聯系大為加強。特別是戰時工業的內遷對近代工業十分薄弱的西北具有極其重大的意義。盡管遷入西北地區的工廠很有限,但這些內遷工廠多系較大的工廠,多系戰前中國工業的精華,它們有較雄厚的設備和技術力量,有較長的辦廠、較豐富的管理經驗、較先進的經營理念和經營方式。所有這些不僅成為帶動西北近代工業發展的酵母和領頭羊,也在一定程度上縮短了東西部經濟發展的差距。與此同時,國民政府開發西北活動的展開促進了西北地區人口的增長和素質的改善,加強了東西部之間的、科技、文化的交流與合作。除了民國十八年(1929年)大饑荒前后西北的人口減少較多外,1935年又逐步回升,全面抗戰爆發后增長很快。統計資料顯示,1931年陜西的人口為897萬余人,1939年即增至1010萬余人;從1928年到1947年,青海的人口從36.8萬人增至134.6萬人;新疆則由255.2萬人,增至404.7萬人。一些城市的人口增長則更為迅速。如西安人口從1936年的15萬人猛增至1945年的28萬人;寶雞在抗戰期間從七八千人猛增至11萬人。(注:以上人口資料綜合自曹占泉:《陜西省志·人口志》,陜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6-7頁;葛劍雄、曹樹基、吳松弟:《簡明中國移民史》,福建人民出版社1993年12月版,第581頁;《陜西省志·商業志》,陜西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43頁;胡煥庸、張善余:《中國人口地理》,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1984年版,第261頁。)這些新增人口,絕大部分是來自東中部地區的難民,也包括一部分內遷的具有較高素質的工商界、文教界、軍政界、科技界、醫衛界人員及其眷屬,他們的到來對于改變西北地區的落后面貌有重要影響。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根據國民政府頒布的《戰區學校處理辦法》和國民黨臨全大會制訂的《戰時各級教育實施方案綱要》和國民政府教育部高教司制訂的《設立臨時大學計劃綱要草案》的精神,平津地區的國立北平大學、國立北平師范大學、國立北洋工學院于1937年9月內遷陜西,極大地促進了陜西乃至西北地區教育事業的發展。這3個著名大學最初遷到西安,合組西安臨時大學,后遷漢中城固,更名為西北聯合大學,當時計有文、理、法商、教育、工、農、醫等6個學院。在此期間,工、農兩學院首先"獨立",教育學院改稱師范學院。不久,聯大工學院與焦作工學院、國立東北大學工學院合并為西北工學院,聯大農學院與西北農林專校合并為西北農學院。1939年8月,西北聯大改稱國立西北大學,師、醫兩學院再行"獨立",聯大師院改組為西北師范學院,聯大醫學院改組為西北醫學院,并轄有一所助產學校。由此,便奠定了陜西高等教育的基本格局和在全國的重要地位。
另外,國民政府開發西北的活動也在一定程度上增進了西北地區各少數民族與內地漢族的相互了解與溝通,消除了某些在宗教信仰、風俗習慣和心理感情上的隔閡,緩和了民族矛盾,改善了民族關系,為西北邊疆的鞏固和進一步開發提供了初步的保證。
綜上所述,在1931-1945年的14年抗日時期,由于西北地區所處戰略地位的變化,開發西北的活動曾幾度掀起高潮。就總體而言,作為策劃者和組織者的國民政府,面對復雜的歷史條件和艱難的戰爭環境,為西北開發做出了積極的努力,其決策和一系列政策基本上也是正確的。這些政策的推行和實施,在不少方面(如交通、水利、農產、工業等)取得了突出的成就,不僅為打破日本的經濟封鎖、支持長期抗戰、爭取抗戰的最后勝利做出了貢獻,而且為改變西北地區極其落后的面貌、促進西北地區社會經濟的發展、調整區域經濟發展不合理的狀態奠定了初步的必要的基礎。筆者認為,對此應予以充分的肯定和實事求是的評價。然而事實又表明,國民黨在很大程度上是一個城市性質的政黨,代表著"城市買辦階級和鄉村豪紳階級的統治"(注:毛澤東:《中國的紅色政權為什么能夠存在》,《毛澤東選集》合訂本,人民出版社1967年版,第47頁。),國民政府也是一個"蹩腳的組織者",其根本弱點是"沒有同人民群眾融為一體,反而高踞在他們頭上"(注:[美]阿·恩·楊格:《1927至1937年中國財政經濟情況》,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1年版,第474頁。),因而在西北開發的過程中存在著諸多缺陷、不足和(如缺乏全盤而切合實際的整體規劃;某些舉措虎頭蛇尾,流于形式;重視工商勝于農業,重視城市勝于鄉村;各級官員尤其是縣級以下官員素質低下,強征強派,貪污中飽,致使一些好的政策反而成了坑害百姓的手段;開發的區域極其有限,基層的動員極其有限;農村的減負半途而廢,治標不治本,農民并未得到實惠等)。因篇幅所限,這些方面將另文專論。有一點應當指出,國民政府在開發西北的過程中雖然對該地區的社會經濟做過一些考慮,但其開發的主旨則是直接為戰爭服務的(前述第一、二階段兼有抗日與"剿共"兩個方面),起決定作用的是軍事上的需要而不是該地區的全面而長遠的發展。這就使西北開發勢必受到戰爭進程的制約。因此,隨著抗日戰爭的勝利,國民政府開發西北的熱情遽減,各種開發、建設西北的活動也停頓了下來,最終導致西北地區的社會經濟再次陷入低谷。
字庫未存字注釋:
@①原字鹿下加吝
@②原字(幸加攵)下加皿
@③原字廠下加至
@④原字鹿加阝
@⑤原字氵加開
@⑥原字氵加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