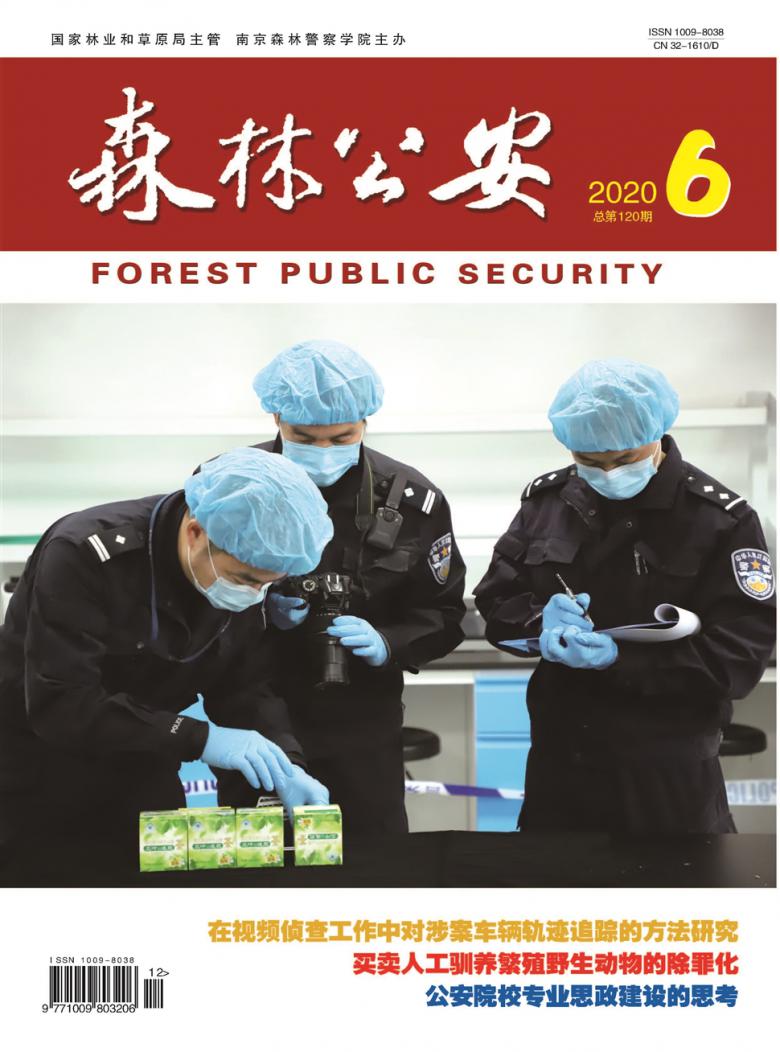關于論憲法上的“宗教”概念——從美國最高法院判例法的發(fā)展切入
陳鵬
【摘要】“宗教”一詞的法律意涵與社會學意涵并不重合。美國聯邦最高法院對憲法中“宗教”概念的認知之擴展契合美國社會宗教多元化的進程,但同時亦帶來一系列問題,包括:超越 “宗教”一詞的語義極限、增加了與禁止國教條款相抵觸的可能性、以及界定“宗教”本身便可能違反禁止確立國教條款。與他國憲法解釋實踐對比可知,美國的經驗雖不具有普適性,但各國多試圖抽象地把握憲法上的“宗教”概念之結構性特征,而非對各教派進行簡單羅列。
【關鍵詞】宗教;信仰;美國憲法;憲法解釋
一、引言
處理與憲法中的宗教自由條款相關的問題,首先需要判斷某種行為的動機是否與“宗教”信仰相關。然而,究竟何為法律意義上的“宗教”?
不論以社會學角度抑或以法學角度觀之,“宗教”的概念本身都充滿了不確定性。法律人生活在此岸世界,擅長的是依據法律規(guī)范對外部行為進行評價,若要其就什么是“宗教”這樣一個涉及人類之精神生活、且遠在彼岸世界的問題作答,無疑相當困難。然而“生活之樹常青”,形形色色的宗教自由之實踐又使得法律人無法回避這一問題。對此,各國的判例及學說不斷予以形塑,其中美國聯邦最高法院之豐富的判例體系頗值得矚目。[[1]]
由于美國憲法第一修正案的宗教條款并未明示“宗教”一詞之含義,因而在解決與憲法第一修正案之宗教條款相關的問題時,美國聯邦最高法院數次遇到如何解釋“宗教”之含義的問題。隨著社會當中宗教多樣性的不斷強化,美國聯邦最高法院對“宗教”之含義的解釋標準在時間向度上經歷了較大的變遷。下文詳述之。
二、20世紀40年代之前的嚴格解釋
在1878年的雷諾茲訴合眾國案(Reynolds v. United States)中,美國最高法院須判斷摩門教所信仰的多配偶制可否使他們免于承擔重婚罪的刑事責任,對此,美國最高法院表示:“‘宗教’一詞在憲法中并未有定義。我們必須通過其它方式確定其含義,我們認為沒有什么比從該條款通過時的歷史當中尋找其含義更為合適。關鍵在于考察何為受保障的宗教自由。”[[2]]在討論了憲法第一修正案制定的歷史背景之后,最高法院認為多配偶制在當時的北歐和西歐都不受歡迎;在摩門教創(chuàng)立之前,多配偶制只在亞洲人和非洲人的生活當中存在;并且按照普通法規(guī)則,第二次婚姻總是無效的,早期英格蘭也將多配偶制視為是對社會的冒犯。[[3]]因而憲法第一修正案當中的宗教自由條款并不保護摩門教所崇奉的多配偶制。
在1890年的戴維斯訴比森案(Davis v. Beason)中,最高法院表示:“‘宗教’一詞涉及一個人對他與造物主之關系的看法,涉及這一關系施加給他的尊崇造物主之存在與特質的義務,以及遵從造物主意志的義務。” [[4]]但由于多配偶制乃“與人類的常識相抵觸”,[[5]]因而不屬于受憲法保護的宗教信條。在同年的另一件關于摩門教多配偶制的案件,即耶穌基督后期圣徒教會訴合眾國(Late Corporation of the Church of Jesus Christ of Latter-Day Saints v. United States)中,最高法院表達了同樣的觀點,即:州可以禁止所有“與人類文明之見解相抵觸”的違法行為,“盡管對這些行為的提倡或踐行披著宗教信條的外衣。” [[6]]
可見,早期最高法院對“宗教”一詞所采取的嚴格解釋遵循了兩條路徑。其一,通過原旨解釋的方式,結合憲法第一修正案制定之時的歷史背景,將“宗教”之概念限定于該修正案通過時的通常理解;其二,將基于某種信仰之動機而做出的“與人類常識相抵觸”的行為排除于宗教自由條款的保護范圍之外,從而否定了這些信仰在憲法上的宗教屬性。盡管這兩種路徑存在差異,但其共同之處在于,認定憲法第一修正案所指涉的“宗教”必須同時具備兩個特性:第一,僅指與神、德性及崇拜相關聯的有神論觀念。[[7]]第二,必須是得到美國主流社會廣泛認同并長期加以尊崇的信仰。[[8]]
以今日之視角省察之,即便某一社會群體共同持守某種信仰,但當基于此種信仰而實施的外部行為有悖于公共利益時,此種信用的宗教屬性雖或能夠得到社會學上的承認,卻可能無法獲得憲法的支持——憲法當中的“宗教”條款不可能保護所有以社會學意義上的宗教為出發(fā)點的行為。就此而言,摩門教所崇奉的多配偶制或許與以活人獻祭一樣,由于違反公共利益而不受保護。但準確地說,這是為自由信仰宗教(free exercise)之權利設定界限,而非否定此種行為的宗教動機,然而早期美國最高法院卻是直接否定此種行為在憲法上的宗教屬性。
三、20世紀40年代至70年代的擴張解釋
美國最高法院的此種認知進路并未得以延續(xù)。在邁入20世紀之前,美國的宗教狀況便已出現了戲劇性的變化,與宗教狀況之變化相伴而生的是倫理觀點的變化。[[9]]到了20世紀中期,最高法院在解釋“宗教”之概念時所采取的嚴格立場逐步被更為寬泛的認知模式所取代。[[10]]
(一)非典型有神論信仰
最高法院解釋的擴張最先體現在非典型的有神論信仰方面。在1944年的一起涉及詐騙的案件,即合眾國訴巴拉德案(United States v. Ballard)中,最高法院確立了這樣的原則:宗教信條真?zhèn)闻c否不應由法院判斷,“法律不知道什么叫做異端邪說,法律并不致力于推動教義,也不確認任何教派。”[[11]]“如果這些教義被付之審判,即由陪審團在審判中認定其真?zhèn)危瑒t任何派別的宗教信仰都可被置于審判之中。一旦承擔事實審查工作的陪審團成員承擔了這一任務,他們便走入了禁區(qū)。”[[12]]然而該案中被告的主張并未得到支持,其原因不在于其信仰具有欺騙性,而是因為被告“明知”其所宣稱的信仰是錯誤的。由此可見,按照最高法院的觀點,在判斷某種信仰是否受第一修正案之宗教自由條款保護時,其關鍵不在于判斷該信仰之真?zhèn)危谟谛磐绞欠耱\地持守該信仰。換言之,對于一種有神論信仰而言,只要該信仰被虔誠持守,該信仰便屬于宗教信仰。
盡管巴拉德案體現了在宗教多樣性面前最高法院的中立態(tài)度,但是該案的判決仍不免招致批評。首先,杰克遜大法官在反對意見中指出了該案中的多數意見所面臨的邏輯上的困境:“政府如何在不能證明某信仰為不真實之信仰的前提下證明信仰者明知該信仰不真實?如果我們將宗教的虔誠性與宗教的真理性割裂開來的話,我們便使爭議游離于按照通常之經驗可提供給我們最可靠答案這一考慮因素之外。”[[13]]此外,有學者提出了這樣的質疑,即:當某種信仰所預測的情況并未發(fā)生之時,是否可以表明信仰者無法一如既往地虔誠持守該信仰?[[14]]但無論如何,最高法院在后續(xù)判例當中仍繼續(xù)沿用了巴拉德案所采取的虔誠性標準。
1981年的托馬斯訴就業(yè)委員會案(Thomas v. Review Bd.)即采取了這一標準。該案中,一名耶證教教徒因其所在的工廠參與軍火武器的生產而辭職,因為該教徒認為他所持守的宗教信仰禁止他從事軍火生產。在申請失業(yè)補償金時,印第安納州就業(yè)保障處認定該耶證教教徒對其所持守的宗教教義之解讀與該教派其他教徒之解讀方式相異,與申請人從事同樣工作的耶證教教徒并不認為該教派禁止從事武器部件的生產。但是申請人認為自己的觀點乃是對耶證教教義的嚴格解讀。具體到此案,最高法院認為法院的職能僅限于判斷行政機關“是否對原告因虔誠持守其信條而終止工作的行為進行了適當的認定。”[[15]]至于“內部的信仰差異(intrafaith differences)”,對于特定的教派追隨者而言“并非異常現象”,“司法程序并未準備解決這些差異與宗教條款之關系的問題……對自由信仰的保障并不限于那些被某教派全體成員所共同信奉的信仰……”“調查……誰所體察到的來自其共同信仰的命令更加正確,不在司法的功能與能力范圍之內。”[[16]]1989年的弗拉基訴就業(yè)保險處案(Frazee v. Department of Employment Security)繼續(xù)維持了該標準。該案中的失業(yè)補償金申請人拒絕接受一份要求在周日上班的工作,因為申請人認為作為一名基督徒,在“主日”工作不符合其教義。伊利諾伊州就業(yè)保障部拒絕為申請人給付失業(yè)補償金,因為申請人拒絕接受工作的原因并非出于某教會、教派或宗派的教義,其信仰完全是“個人的、非強制性的,并且不會致使這份工作變得不適當”。[[17]]然而最高法院認為,盡管申請人并未表明其所隸屬的教派,但這并不能將申請人的信仰排除出“宗教信仰”的范圍之外,因為申請人之信仰的“虔誠性”并不存在可疑之處;最高法院認為托馬斯案在很大程度上已經解決了這一問題,即便申請人恪守的并非特定宗教組織的指令,但只要申請人乃虔誠地持守其信仰,該信仰便應得到保護。[[18]]
(二)倫理信條與“最高之存在”的拓展
盡管巴拉德案的判決拓展了受第一修正案之宗教條款所保護的信仰之范圍,但總體而言,最高法院所拓展開來的“宗教”之領域仍未脫逸出傳統(tǒng)的有神論之領域。在1965年的合眾國訴西格爾案(United States v. Seeger)中,最高法院將“宗教”之概念延伸至雖無“最高之存在(Supreme Being)”但可與有“最高之存在”等而視之的信仰。五年后的威爾什訴合眾國案(Welsh v. United States)亦追隨了西格爾案的判決意見。盡管這兩個判例直接關涉的乃是關于如何解釋《兵役法》(Universal Military Training and Service Act)中的相關條款,而非如何解釋憲法第一修正案中的“宗教”一詞,但由于有學者認為這乃是最高法院唯一兩次試圖界定“宗教”,[[19]]并且可能成為最高法院根據禁止確立國教條款(Establishment Clause)及自由信仰條款(Free Exercise Clause)對“宗教”進行界定的起點,[[20]]因而其重要性不可忽視。
在西格爾案中,《兵役法》規(guī)定:因宗教訓誡及宗教信仰(religious training and belief)之原因而在良心上反對參與任何形式之戰(zhàn)爭的人,可免于在合眾國的武裝力量當中服役。但《兵役法》將“宗教訓誡及宗教信仰”之含義界定為“與最高之存在”相關的個人信仰,其所涉及的義務高于人際間關系所派生出的義務,但不包括本質上屬于政治的、社會學的或哲學上的觀點,亦不包括純粹的個人道德方面的信條。本案的上訴人并不信仰任何與“上帝(God)”相關的宗教,上訴人聲稱他反對戰(zhàn)爭的原因乃是他的“信仰良善本身”,并且“這種宗教信仰純粹植根于倫理”。[[21]]上訴人據此對《兵役法》當中之宗教豁免條款提出合憲性質疑。在判斷上訴人的倫理信仰是否屬于“宗教”時,最高法院認為:國會在立法時采用了“最高之存在”這一措辭,而未采用“上帝”這一措辭,其原因乃是意在將所有宗教包含在內并將本質上屬于政治的、社會學的或哲學上的觀點排除在外。但最高法院隨后提出了認定某種信仰是否“與最高之存在相關”的標準,即只要一項虔誠持守且有意義的信仰在信仰者的生活當中占有一席之地,并且這一席之地可與信仰上帝的正統(tǒng)信仰在信徒生活中的地位相匹配,則這種信仰即屬“與最高之存在相關”。[[22]]
威爾什案進一步發(fā)展了西格爾案所確立的標準。在該案的相對多數意見當中,布萊克大法官表示:在判斷某種信仰是否屬于宗教信仰之時,其關鍵之所在乃是判斷這些信仰在一個人的生活當中是否扮演著與宗教相同的角色。[[23]]通過適用西格爾標準,相對多數意見明確地將倫理與道德納入“宗教”之意旨范圍內。布萊克大法官寫道:
“如果一個人深刻且虔誠持守的信仰就其淵源與內容來說雖屬倫理方面或者道德方面的,但這種信仰卻為他施加了良心上的義務,驅使他在任何時候都避免參與任何形式的戰(zhàn)爭,則這些信仰理所當然與傳統(tǒng)的‘上帝一樣’在他的生活中‘占有一席之地’。”[[24]]
最高法院通過上述兩個判例將“宗教”之概念拓展至無“最高之存在”的信仰。在切莫林斯基(Chemerinsky)看來,對“宗教”之概念進行這樣的擴張解釋有兩點可取之處:第一,許多宗教拒斥最高之存在這一觀念,上述兩個判例使得這些信仰能夠獲得第一修正案的保護;第二,對“宗教”一詞采取的這種擴張解釋使得基于道德之原因而做出的決定可受第一修正案保護,不論做出該決定的深層次原因是宗教方面的或是哲學方面的,這就避免了基于宗教所做出的決定優(yōu)先于基于世俗原因所做之決定,從而避免與禁止確立國教條款相抵觸。[[25]]
(三)純粹無神論
如果說西格爾-威爾什標準通過將倫理與道德納入“最高之存在”這一方式拓展了有神論信仰中“神”的觀念,從而可認為其所涵攝的仍然是處于邊緣地帶的有神論信仰的話,則純粹的無神論信仰是否亦屬于“宗教”?
早在1961年的托加索訴華特金斯案(Torcaso v. Watkins)中,最高法院便以極其模糊的方式嘗試將無神論納入宗教條款之保護范圍。該案中的上訴人被指定為馬里蘭州公證員。根據該州憲法,上訴人必須在就職前宣誓信仰上帝之存在。上訴人不愿作此宣誓,并認為州憲法的這一條款違反了合眾國憲法的第一和第十四修正案。通過援引禁止確立國教條款及相關判例,最高法院裁定馬里蘭州憲法的這一規(guī)定無效,并表示:
“根據憲法,州政府和聯邦政府均不得強迫一個人‘公開聲明他信仰或者不信仰某種宗教,’不得以制定法律或課以義務的方式扶持任何宗教以對抗無信仰者,亦不得因某一宗教信奉上帝之存在便扶持該宗教以對抗那些基于不同信仰而建立起來的宗教。”[[26]]
自此尚無法體察最高法院是否將無神論納入“宗教”之范圍,因為該案之判決乃是建立在政教分離的理念之上;況且某種信仰中不存在“上帝”這一理念并不意味著該信仰中缺少“神”之理念。但是布萊克大法官在多數意見的一個腳注當中卻給出了一個驚人的說明,即“在這個國家中,沒有通常意義上的關于上帝存在之訓示的宗教包括佛教、道教、倫理文化、世俗的人文主義及其它。”[[27]]如果布萊克大法官意在反對政府扶持任何宗教以對抗“無信仰者”的話,則最高法院似乎的確將純粹無神論也納入了“宗教”之范圍。
盡管最高法院在托加索案中認為政府不得優(yōu)待那些包含神之理念的宗教并借此對抗那些不包含該理念的宗教,并且開列了一份無上帝存在之理念的信仰之清單,但最高法院并未解釋為何這些特定的信仰構成了宗教,也未提供一個用以判斷何種信仰可被視作宗教的標準。[[28]]因而盡管有學者認為,自托加索案開始,“宗教”之含義便可自由地將第一修正案的保護延伸至基于任何“道德”信仰而為的行為,[[29]]但是更加適切的理解方式或許應當是:布萊克大法官的腳注僅起到了輔助表達的作用,而非可資援引的先例,否則最高法院便不會在四年后的西格爾案中大費周折。
四、“個人哲學上的選擇”之排除:20世紀70年代的適度限縮
西格爾-威爾什標準雖具有相當程度的積極意義,其不足之處卻也甚為明顯。一方面,在將宗教條款的保護范圍拓展至傳統(tǒng)有神論信仰之外的同時,該標準卻未能為擴張之后的“宗教”之概念提供一個清晰界定。確定某種信仰是否在信仰者生活中占有一席之地的標準是模糊的,審理后續(xù)相關案件的法官必然以自己的判斷代替西格爾-威爾什標準,即便法官表面上可能聲稱自己遵循了這一標準。另一方面,勞倫斯·卻伯(Laurence Tribe)認為這種寬泛的功能性界定在許多場合中是不可接受的。[[30]]在1972年的威斯康辛州訴約德爾案(Wisconsin v. Yoder)中,最高法院的一項表述便提供了一個例證。
在該案中,由于阿米什人崇奉離群索居的生活方式,因而拒絕按照州《強制就學法》的要求支持子女完成一定程度的學校教育。對此,最高法院表示:
“如果阿米什人提出的主張是源自其主觀方面的評價并且排斥多數人所接受的當代世俗價值,即如同梭羅(Thoreau)排斥其所處之時代的社會價值并自我放逐于瓦爾登湖那樣的話,他們的主張便不是立基于宗教之原因。梭羅的選擇是哲學意義上的,并且是個人的而非宗教的,這種信仰并沒有上升到符合宗教條款之要求的高度。” [[31]]
但法院隨后認定阿米什人對生活方式的崇奉不同于梭羅的自我放逐,這種生活方式并非“個人哲學上的選擇”。簡言之,最高法院將對倫理與道德的保護納入宗教信仰自由之保護體系,但拒絕保護“個人哲學上的選擇”。
由于最高法院在西格爾案、威爾什案、托馬斯案和弗拉基案中所承認的“宗教”也具有一定的個人屬性,其與梭羅式信條的差異便不在于此種選擇是否是“個人”性質的,而在于前者并非“哲學”上的選擇,這也符合前述西格爾案中最高法院將“政治的、社會學的或哲學上的觀點”排除在“宗教”范圍之外的立場。然而問題在于:依西格爾-威爾什標準,本與“最高之存在”無涉的“倫理信條”亦受宗教自由條款之保護,那么“哲學”上的選擇何以區(qū)別之?當某種虔誠持守且有意義的“哲學信條”在信仰者的生活當中占有一席之地時,此種信條為何不可與“最高之存在”相類比,從而像“倫理信條”那樣被視作“宗教”?由此,道格拉斯大法官便在約德爾案的反對意見中指出:當多數意見提及了梭羅并且認為梭羅的行為乃純粹個人哲學上的選擇因而不受宗教條款保護時,多數意見所持之觀點便與西格爾案中最高法院的意見相抵觸。[[32]]
將“個人哲學上的選擇”排除出“宗教”之列,反映了最高法院的一種自我校正。最高法院仿佛已經意識到,通過明確地將倫理與道德納入“宗教”之范圍的方式保護宗教的多元化,似乎走得太遠了,因而應加以限制。但由于最高法院仍然承認西格爾-威爾什標準的正確性,故有學者認為,無論最高法院最初的意圖為何,在依照第一修正案所預設的目標處理及理解“宗教”之含義時,西格爾-威爾什標準已經并且仍將對法院產生重要影響。[[33]]
五、是進是退?最高法院的二難邏輯
綜上所述,美國聯邦最高法院對于“宗教”概念的認知經歷了“嚴格——寬泛——適度限縮”三個階段。相比早期將“宗教”概念嚴格限定于傳統(tǒng)的主流有神論信仰而言,20世紀40年代之后,最高法院將其擴張至非典型的有神論信仰、在個人生活中占有一席之地從而可與“最高之存在”相類比的倫理信條,再從中排除純粹的“個人哲學上的選擇”。至于純粹無神論是否屬于憲法上的“宗教”,目前為止還難有定論。但無論如何,相比早期的嚴格解釋而言,最高法院所認定的“宗教”之范圍已然寬泛了許多。然而需要意識到,此種解釋策略是在一種固步自封雖不適宜、革故鼎新亦有不當的二難邏輯狀態(tài)中尋求立足。
一方面,擴張解釋似乎是不可避免的。一如前述,美國最高法院對“宗教”之概念所做的擴張解釋與美國社會中事實上存在的宗教多元化趨勢密不可分。殖民地時期的美國僅有十幾個主要的宗教團體,而20年前美國便已存在超過250個主要的教會,這一數字尚不包括數百個“邊緣”小團體。此種境況的變遷使得最高法院無可避免地修正其對“宗教”的狹隘理解。[34]布倫南大法官(Justice Brennan)便觀察到:“宗教的結構致使我們比我們的先輩更加多樣化。他們所知曉的差異主要存在于新教的不同派別之間。”[35]就此而言,無論憲法文本或憲法判例對毫無異議屬于“宗教”的那些信仰保護到何種程度,都無法應對隨時間推移而產生的五花八門的信仰之挑戰(zhàn)。因而卻伯認為,為實現宗教自由之目標,對“宗教”一詞的界定必然要足夠寬泛,由此方可辨識出信仰之數量與多樣性的增加。[36]
另一方面,如此寬泛地界定“宗教”之含義卻又使最高法院陷入一個三重困境。第一,顯而易見的是,最高法院的擴張解釋致使“宗教”概念與“個人”偏好之間呈現出前所未有的模糊局面。擴張解釋后的“宗教”之概念與通過常識判斷而獲知的“宗教”之概念的距離越來越遠,因而難免面臨這樣的非難:最高法院能否如此牽強地附會憲法文本當中的“宗教”一詞,以至于使其脫離這一概念所能承受的語義之極限?第二,如果自由信仰條款中“宗教”之含義得到擴展,則必然也應對禁止確立國教條款中的“宗教”之含義做擴張解釋。如果對自由信仰條款做擴張解釋的同時,堅持對禁止確立國教條款做限縮解釋的話,則最高法院必然再次面臨源自憲法文本的挑戰(zhàn),即如魯特里奇大法官(Justice Rutledge)所言:“‘宗教’一詞在第一修正案中僅出現過一次。但是這一語詞卻管控著兩個子條款,并且是以相同的方式管控之。它并非具有兩種含義,一種較狹窄以禁止‘確立’國教,而另一種較寬泛以‘保障’自由信仰。”[[37]]但若對“禁止確立國教”當中的“宗教”之概念做擴張解釋的話,則如卻伯所言:“在宗教之形式與概念發(fā)展的同時,國家觸手亦在延伸。”[[38]]如此一來,宗教信仰與世俗國家之功能的交叉與沖突必然增多。此時最高法院非但不能成為糾紛的仲裁人,反而成為糾紛的發(fā)起者,其妥當性必然招致質疑。第三,通過擴張解釋的方式界定“宗教”之概念,是否可以擴大宗教信仰的保護范圍、同時避免與禁止國教條款相抵觸,乃是可疑的。有學者基于以下原因反對最高法院對“宗教”之概念進行直接界定:(1)宗教本身處于流變之中,并不存在所謂的本質;(2)最高法院并無界定何為“宗教”之資格,因為最高法院不免偏頗;(3)由最高法院界定“宗教”之含義將構成對宗教自由的干涉,并且會導致確立國教。[[39]]切莫林斯基亦認為在界定“宗教”方面的任何嘗試都會引發(fā)一個問題,即選擇一種單一的界定方式本身便是在確立國教。[[40]]事實上,上述三個反對理由在邏輯上存在關聯。由于宗教本身不斷處于流變之中,因而最高法院無法準確判斷現有的和未來將會出現的宗教信仰的復雜性,因而最高法院便以其自身對宗教信仰的理解代替了客觀事實;由于最高法院無法客觀地判斷宗教信仰之發(fā)展狀況,因而必然將其所不了解、不理解的信仰排除于宗教之外,從而引發(fā)了干涉宗教自由及確立國教之問題。魏斯(Weiss)一針見血地指出:
“任何對宗教的界定似乎都會侵犯宗教自由,因為這會對現存的和未來的宗教下達指令,指示它們必須是什么。此外,即便為了提升宗教自由,試圖界定宗教的行為也會與‘禁止確立國教’條款相沖突,因為這會將一些宗教排除在外,甚至會確立一種關于宗教的觀念。”[[41]]
因而即便對“宗教”之含義進行擴張解釋,經解釋后,若原本處于最高法院視野范圍之外的信仰進入“宗教”的路徑愈發(fā)狹窄,其解釋的合理性便愈可能受到質疑。
歸根結底,辨識某種行為是否是基于“宗教”動機而非僅基于“個人”之偏好,其本身更接近事實問題而非可憑司法過程予以解決的法律問題。盡管事實認定(fact-finding)乃是法院適用法律以解決爭議的前提,但在判斷某種行為之動機是否具有“宗教”之屬性時,由于法院不可避免地需要引入自身的價值準則,因而法律真實與客觀真實之間的差距便愈加明顯。由此可見,司法活動的有限性致使最高法院注定不具備對此問題做出周全判斷之能力。但正如本文開篇所言,解決憲法當中之宗教問題的第一步便是確定所檢視的行為是否與“宗教”相關,社會現實與案件本身要求最高法院對第一修正案中“宗教”一詞的含義進行解釋。盡管法院所處理的爭議之對象乃是某種具有外在形式的行為,但此種行為密切關聯著行為人的精神世界。當與人類精神生活息息相關且充斥著價值選擇的問題需要通過有限的司法技術予以解決時,最高法院的二難邏輯便無可避免。然而,之所處于困境當中的最高法院仍能保證其對“宗教”之含義進行解釋的有效性,除了應得益于聯邦最高法院的憲法解釋在美國憲政體制當中的權威地位之外,也應歸功于判例法的靈活性及最高法院司法技術的高明。對此,烏斯曼有著極為深刻的洞察:“這些判決都沒有宣告它的支配地位,相反,它們只是對州法院及聯邦下級法院提供了一個寬松的指引。”[[42]]
六、美國經驗的特殊性與各國認知模式的同構性
以比較法角度觀察之,美國聯邦最高法院對“宗教”之概念的認定遠非顛撲不破、放之四海而皆準的真理。下述國家便提供了截然不同的憲法解釋之實踐經驗。
德國憲法法院將自由信仰的權利沿用于不被認為是教會(church)的宗教組織,而怠于觀察諸如信眾人數以及宗教的歷史淵源等外部標準。譬如,在“輸血案”中,憲法法院便認為“宗教自由的行使既不仰賴其組織在數字化層面的規(guī)模,也與其社會關聯性無關。”[[43]]有學者認為,這恰體現了國家在意識形態(tài)與宗教面前的中立,亦體現了各教會(churches)與信條(creeds)間的平等。[[44]]在對“宗教”概念之認知的寬泛程度方面,德國聯邦憲法法院似可與美國聯邦最高法院相比肩,但其在憲法文本上的依據卻不同于美國的情形。依照考馬斯(Donald P. Kommers)教授的考察,在德國的憲政歷史上,主流教會曾一度區(qū)別于少數教派。1848年之前,在公共場合表達宗教觀點的權利只及于前者。而《德國聯邦基本法》第四條則承襲了“法蘭克福憲法”與“魏瑪憲法”的自由主義傾向,其第一款規(guī)定:“宗教或世界觀方面的信仰、良心以及信條之自由不受侵犯。”該條款與《基本法》的禁止歧視條款一道形成了對信仰體系、宗教及世界觀的保護。[[45]]由于該條款不僅保護狹義上的宗教,亦對個人精神自由加以體系化保護,因而寬泛地界定“宗教”之概念對于德國憲法法院而言,其憲法文本上的規(guī)范依據似乎更為充足。
盡管與德國同處歐洲大陸,但在意大利,“宗教”卻曾被限定于傳統(tǒng)上已建立起來的教派。然而,由于法院愈發(fā)傾向于避免直接定義何為宗教,越來越多的教派在法律上得到了承認。“何為宗教”這一問題也被“何為基本的或特定的宗教”、“某種行為是否是特定宗教的一部分”等問題所取代。然而在涉及以宗教的名義請求豁免的場合,法院卻更樂于裁決何為宗教。[[46]]譬如意大利最高法院曾表示,“宗教教派”必須滿足三個條件,即(1)必須是持守某種信仰或教義體系的人的集合,該信仰或教義體系有助于使人在精神上向善,即必須持守某種具有普遍性的信仰;(2)有共同的組織;(3)有特定的名稱,從而可以對其加以識別。[[47]]“精神上向善”之要求似乎排除了那些以離群索居為基本教義的教派(如美國約德爾案中的阿米什教);而“共同的組織”之要求又不似美國聯邦最高法院在西格爾案、威爾什案、托馬斯案及弗拉基案中所接受的認知標準,即不將個別人持守的某種信念(即便此種信念本質上是“向善”的)視作“宗教”。
澳大利亞高等法院則認為:
“‘宗教’最重要的特征之一在于,它是觀念以及/或者行為的集合,這些觀念與實踐關聯著超自然(supernatural)的信仰,此種信仰超越了感知的范圍。如果此種特征不存在的話,便不能說一個人信仰某種‘宗教’。另一個特征是,它是一種關聯著人性、人類在宇宙中的位置以及人與超自然事物之關系的觀念。第三個特征是,它是信徒所接受的觀念,此種觀念要求或鼓勵他們遵循特定的行為標準或行為準則,抑或要求或鼓勵他們參與特定的、具備超自然意義的行為。第四個特征是,不管信徒之間的關系多么松散,也不管他們的信仰與行為有多么大的差異,他們都構成了一個或多個可辨識的群體(identifiable group)。”[[48]]
可見,澳大利亞法院一方面強調宗教的“超自然”屬性,從而排除了純粹的無神論信仰;另一方面則強調宗教的“群體”性,因此與意大利最高法院一樣,澳大利亞高等法院亦不將純粹的個人信念(即便此種信念具有“超自然”性質)視作“宗教”。
日本憲法學界存在兩種對“宗教”的理解方式:廣義的“宗教”是指可被廣泛理解為諸如“確信有超自然的、超人本質(即絕對者、造物主、至高無上的存在等,尤其是神、佛、靈等)的存在,并加以敬畏、崇拜的心情與行為”,狹義的“宗教”是指“擁有某種具備了固有教義體系組織背景的宗教”,實踐中,名古屋高等法院在津市奠基儀式案的二審判決中采取了廣義的理解。[[49]]不難看出,即便是廣義的理解方式,其范圍也遠遠小于美國聯邦最高法院對“宗教”一詞的認知。
可見,“宗教”一詞在憲法解釋之實踐中不具有凌駕于一切社會文化背景之上的普適性。但是至少可以看出,上述各國之解釋實踐具備某種“同構性”,即試圖抽象地把握憲法當中“宗教”之概念的“結構性特征”,而非以明確列舉各教派的方式劃定其范圍,蓋后一種方式不免流于僵化,難以應對社會的變遷與需求。以此觀之,如何在觀照我國具體國情的前提下,高屋建瓴地理解我國憲法文本中的“宗教”一詞,避免以一種“描述性而非本質規(guī)定性”的方式簡單地對各教派加以羅列,[[50]]是需要進一步探討的課題。
【注釋】 [1]王廣輝教授與劉祎博士曾嘗試比較美國聯邦最高法院與我國國務院頒布的《宗教事務條例》、《社會團體登記管理條例》、國務院宗教事務局和民政部聯合頒布的《宗教社會團體登記管理實施辦法》以及民政部頒布的《取締非法民間組織暫行辦法》對憲法中“宗教”一詞之意涵的解釋技術。參見王廣輝、劉祎:《“宗教”一詞在憲法中的意涵——中美憲法解釋技術之比較分析》,載韓大元等主編:《中國憲法學基本范疇與方法:2004-2009》,法律出版社2010年版,第102-119頁。但在筆者看來,解釋技術本身并不是一個本體的問題,若要描摹憲法上“宗教”一詞的規(guī)范意涵,在時間向度上完整地梳理此一概念之解釋的變遷史或許更具意義。本文所嘗試的便是這樣的工作。 [2]Reynolds v. United States, 98 U.S. 145, at 162 (1878). [3]參見同上,第164頁。 [4]Davis v. Beason, 133 U.S. 333, at 342 (1890). [5]同上。 [6]Late Corporation of the Church of Jesus Christ of Latter-Day Saints v. United States, 136 U.S. 1 (1890). [7]See Laurence H. Tribe, American Constitutional Law, 2nd ed. (New York: The Foundation Press, Inc., 1988), p. 1179. [8]See David D. Meyer, “Self-Definition in the Constitution of Faith and Family”, 86 Minn. L. Rev. 791, 811 (2002). [9]參見前引[7],Tribe書,第1179頁。 [10]參見前引[8],Meyer文,第812頁。 [11]United States v. Ballard, 322 U.S. 78, at 86 (1944). [12]同上,第87頁。 [13]同上,第93頁。 [14]See William B. Lockhar (et al.), Constitutional Law: Cases-Comments-Questions, 8th ed., (St. Paul: West Publishing Co. 1996), p. 1127. [15]Thomas v. Review Bd. of the Indiana Employment Security Div., 450 U.S. 707, at 715 (1981). [16]同上,第715頁。 [17]Frazee v. Illinois Dept. of Employment Security, 489 U.S. 829, at 830 (1989). [18]參見同上,第834頁。 [19]See Erwin Chemerinsky, Constitutional Law, 2nd ed., (New York: Aspen Publishers, 2005), p. 1457. [20]參見同上,第1459頁。 [21]United States v. Seeger, 380 U.S. 163, at 166 (1965). [22]參見同上,第165頁。 [23]See Welsh v. United States, 398 U.S. 333, at 339 (1970). [24]同上,第340頁。 [25]參見前引[19],Chemerinsky書,第1459頁。 [26]Torcaso v. Watkins, 367 U.S. 488, at 495 (1961). [27]同上。 [28]See Jeffrey Omar Usman, “Defining Religion: The Struggle to Define Religion under the First Amendment and the Contribution and Insights of Other Disciplines of Study Including Theology, Psychology, Sociology, the Arts, and Anthropology”, 83 N. Dak. L. Rev. 123, 170, (2007). [29]See Lee J. Strang, “The Meaning of ‘Religion’ in the First Amendment”, 40 Duq. L. Rev. 181, 202, (2002). [30]參見前引[7],Tribe書,第1183頁。 [31]See Wisconsin v. Yoder, 406 U.S. 205, at 216 (1972). [32]參見同上,第247頁。 [33]參見前引[28], Usman文,第172頁。 [34]參見前引[7],Tribe書,第1179頁。 [35]Abington School Dist. V. Schempp, 374 U.S. 203, at 240 (1963). [36]參見前引[7],Tribe書,第1181頁。 [37]Everson v. Bd. of Education, 330 U.S. 1, at 32 (1947). [38]前引[7],Tribe文,第1185頁。 [39]參見前引[28],Usman文,第145頁。 [40]參見前引[19],Chemerensky書,第1456頁。 [41]Jonathan Weiss, “Privilege, Posture and Protection: ‘Religion’ in the Law”, 73 Yale L.J. 593, 604 (1964). [42]前引[28],Usman文,第173頁。 [43]32 BVerfGE 98 (1971). [44]See Norman Dorsen (et al.), Comparative Constitutionalism: Cases and Materials, (St. Paul: West Group, 2003), pp. 929-930. [45]See Donald P. Kommers, The Constitutional Jurisprudence of The Federal Republic of Germany, 2nd ed., (Durham and London: Duke University Press, 1997), p. 445. [46]參見前引[44],Dorsen等書,第928頁。 [47]See Acharya Jagdishwaranand Avadhuta v. Commissioner of Police, Calcutta 1 S.C.R. 447, 448 (1984). [48]]Church of the New Faith v Commissioner of Pay-roll Tax (Victoria), 154 CLR 120 (1983). [49]參見[日]蘆部信喜:《憲法》,林來梵等譯,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6年版,第134頁。 [50]以“描述性而非本質規(guī)定性”的方式對憲法上的“宗教”一詞加以定義,從而將我國憲法上的“宗教”限定于佛教、道教、伊斯蘭教、基督教、天主教這五大宗教,是王廣輝教授與劉祎博士的觀點。參見前引[1],王廣輝、劉祎文,第116頁。
生部公報.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