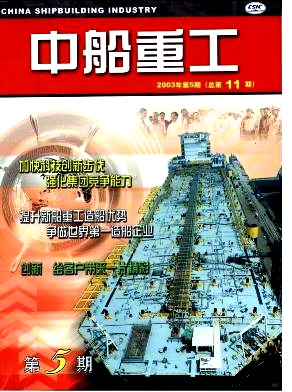“象”模型:易醫會通的交點—兼論中醫學的本質及其未來發展
張其成
摘要:易學與中醫學的會通問題歷來是一個有爭議的問題,本文從一個特定的層面即思維方式的層面探討了這一問題,提出“象”思維是醫易學共同的思維方式,是醫易會通的交點。“象”思維包括“象”思維方法和“象”思維模型,本文認為“象”思維方法是一種模型思維方法,“象”思維模型有卦爻模型、陰陽模型、易數模型、五行模型、干支模型等多級同源、同質、同構的子模型。文章進而探討了“象”思維具有整體性、全息性、功能性、關系性、超形態性、時序性以及重直覺、體悟、程式、循環的特征,指出這一特征正是中醫學理論的本質。中醫學與西醫學的本質差別就是“模型論”與“原型論”的差別,兩者各有優劣。文章還從“象”模型角度提出了“修補”中醫思維方式、促進中醫學術發展的中醫未來觀。
關鍵詞:象;模型;思維方式;中醫學。
綜觀20世紀的易學與醫學研究,可以說走過了一條“之”字形的道路。20世紀初,唐宗海寫成了醫易學專著《醫易通說》(1915年上海千頃堂印本),目的在于“為醫學探源,為易學引緒”,唐氏是最早提出“中西醫匯通”的醫學家,本書從一個特定層面論證了中醫并非不科學,在醫易相關方面著重論述了人身八卦理論及其生理、病理、診斷、治療原理,既是對前代醫易研究的總結,又開創了20世紀醫易研究的新路。近代大醫惲鐵樵是反對“廢醫存藥”、捍衛中醫的主將,主張以中醫本身學說為主加以改革,他在《群經見智錄》中論述了醫與易的關系,認為“《易》理不明,《內經》總不了了”,“《內經》與《易經》則其源同也”。可以說,20世紀前半葉,“醫易同源”、“醫易會通”是醫家的共識。
然而,50年代以后,“醫易”研究趨于低潮,尤其是十年“文革”時期,《易經》和中醫“陰陽五行”都被打入封建迷信的行列,醫易研究成為禁區。
80年代以來,醫易研究逐漸趨熱,到90年代初達到高潮。在短短的十幾年中,研究“醫易”的著作出版了十幾本,①有關“醫易”的專門學術會議開了八九次,②論文竟高達數百篇之多。在醫與易關系如“醫易同源”、“醫源于易”上,大部分研究者是持肯定態度的,也有一些研究者提出相反的意見,認為“醫學理論與《易》無關”。③“《易經》、《易傳》都不是中醫學的直接理論淵源,自《易經》產生后直到隋唐以前,在此長達一千六百多年的時間內,它對醫學幾無影響”。④“將醫理放入《周易》之中,認為醫生必須通曉《周易》,是從明末才開始的思潮,是一部分醫家的認識和主張”。⑤由上述可見兩派在對待隋唐以后“醫易會通”這一點上是一致的,分歧的焦點是在隋唐以前,尤其是《黃帝內經》與《周易》有沒有關系的問題上,肯定派承認兩者有密切關系,《周易》對《內經》有影響;否定派不承認兩者之間有關系。本人是持肯定態度的,并從實踐操作層面、文字載體層面、思維方式層面對《周易》對《內經》作了詳盡的探討⑥,此不重復。近20年的醫易研究應該說取得了不少成績,但也不能不看到不少研究還處在低層面地比附、無根據地猜想、想當然的拔高和低水平地重復之中。對深層面的理論本質、思維方式的研究還遠遠不夠。
本文旨在探討易與醫的共同的思維方式、思維模型,并從中探討中醫學的理論本質及其未來發展方向。
一、“象”思維方法與“象”思維模型
考察《內經》與《周易》在思維方式上是否一致,不但是判斷易學與中醫學有無關系的重要依據,而且是探討易學與中醫學理論本質的必由之路。筆者認為《內經》與《周易》都是采用了“象數思維方式”,因“象數”的“數”實質上也是一種特殊的“象”,因此“象數思維方式” 實質上就是“象”思維方式。
“象”思維方式的特點是:以取象(包括運數)為思維方法,以陰陽“卦象”為思維出發點和思維模型,以具有轉換性能的“象數”、“義理”兩種信息系統為思維的形式和內涵,以外延界限模糊的“象”(或稱“類”)概念對指謂對象及其發展趨勢作動態的、整體的把握和綜合的、多值的判斷。
1. “象”思維方法
所謂“象”思維方法即取象(包括運數)的方法,是《周易》的基本方法。從本質上說,“象”思維方法是一種模型思維方法。中醫采用據“象”歸類、取“象”比類的整體、動態思維方法。所謂“象”指直觀可察的形象,即客觀事物的外在表現。以《周易》為代表的取象思維方法,就是在思維過程中以“象”為工具,以認識、領悟、模擬客體為目的的方法。取“象”是為了歸類或類比,它的理論基礎是視世界萬物為有機的整體。取象比類即將動態屬性、功能關系、行為方式相同相近或相互感應的“象”歸為同類,按照這個原則可以類推世界萬事萬物。
中醫即采用這種方法,有學者稱之為“唯象”的方法。中醫在分析人的生理功能結構時,將人體臟腑、器官、生理部位和情志活動與外界的聲音、顏色、季節、氣候、方位、味道等按功能屬性分門別類地歸屬在一起。《素問 五臟生成篇》:“五臟之象,可以類推。”如心臟,其基本功能是主神明,主血脈,宇宙萬物中的赤色、徵音、火、夏、熱、南方、苦味、七數、羊、黍、熒惑星等均可歸屬于心。五臟均以此類推。這種取象的范圍可不斷擴展,只要功能關系、動態屬性相同,就可無限地類推、類比。如果客體實體與之發生矛盾,那么也只能讓位于功能屬性。中醫有一個“左肝右肺”的命題,歷來爭議很大。肝在人體實體中的位置應該在右邊,這什么說“左肝”呢?其實這是從功能、動態屬性上說的,肝有上升、條達的功能,故與春天、東方等歸為一類,東方即左邊。同時這個方位又是“象”模型的方位。
中醫在對疾病的認識上,也是據象類比的。中醫重“證”不重“病”。將各種病癥表現歸結為“證”。如眩暈欲撲、手足抽搐、震顫等病癥,都具有動搖的特征,與善動的風相同,故可歸為“風證”。中醫“同屬異治,異病同治”的原則,就是根據動態功能之“象”類比為“證”而制定的。因此,有些病的病因癥狀相同,卻分屬不同的“證”;有些病的病因癥狀不同,卻歸為同一“證”。關鍵在于是否有相同的病機,而不是取決于癥狀或病因。例如慢性腹腔、脫肛、子宮下垂這三種不同的疾病,其癥狀(象)不盡相同,發病的原因也不同,但它們的病機(動態功能)都有可能屬于“中氣下陷”,故可歸為同一“證”,都可采用補中益氣湯法治療。
中醫以“象”建構了天人相合相應、人的各部分之間相合相應的理論體系,取象可以不斷擴展,沒有范圍限制。這種“象”已超出了具體的物象、事象,已經從客觀事物的形象中超越出來,而成為功能、關系、動態之“象”。由靜態之“象”到動態之“象”,使得無序的世界有序化,使得人體與宇宙的關系有序化。
所謂運數思維,就是以“數”為思維工具來把握客觀世界。值得一提的是,運數之“數”實質上就是“象”,它并不偏向于定量,而是偏向于定性。《素問·金匱真言論》將五臟中肝、心、脾、肺、腎與八、七、五、九、六相配,這是依五行生成數圖(即后世所謂的“河圖”)中的成數配五臟,木的成數為八,火的成數為七,土的成數為十,金的成數為九,水的成數為六。中醫理論中“五”臟、“六腑”、“十二“經脈、奇經”八“脈、”“十二”經別、“三”陰“三”陽、“五”運“六”氣、“五”輪“八”廓、“六”淫“七”情、“三”部“九”候、“八”綱辨證、“八”法、“四”氣“五”味、“五”腧穴、“八”會穴、靈龜“八”法、飛騰“八”法,等等,均是運數思維的體現,其數字雖帶有量的規定,但主要是為了表性,“數”與其說成“數”不如說成“象”,同時也是為了滿足象數思維模式的需要。在后世的了展中,中醫理論大量吸收了天文、歷法、卦爻的知識和框架,擴大取象范圍。《靈樞·陰陽系日月》將十二經脈與十二月相配,《素問·陰陽別論》:“人有四經十二順(從),四經應四時,十二順(從)應十二月,十二月應十二脈。”楊上善進一步解釋:“四經,謂四時經脈也。十二順,謂六陰爻、六陽爻相順也。肝心肺腎四脈應四時之氣,十二爻應十二月。”《黃帝內經太素·陰陽雜說》在診斷辨證學說中,無論是脈診、舌診、眼診、尺膚診、都有遵循全息的八卦結構規律,依此規律可取象比類。《傷寒論·傷寒例》提出外感病決病法,直接以四時、八節、二十四氣、七十二候觀測外感病,以乾坤陰陽爻的消長取象比類說明一年四時陰陽變化規律及外感病發病規律。而運氣學說、子午流注則是將天文歷法之“象”與人體生理、病理綜合研究的代表,是“天人合一”思想的具體體現。
2、“象”思維模型
“象”思維方法是和“象”思維模型分不開的。 “象”實際上就是一種思維“模型”。所謂“模型”,是人們按照某種特定的目的而對認識對象所作的一種簡化的描述,用物質或思維的形式對原型進行模擬所形成的特定樣態,模型可以分為物質模型與思維模型兩大類。《周易》“象”模型是一種思維模型,而不是物質模型。 “象”模型導源于《周易》經傳及其其他先秦經典,由漢后“易學”總其成。“象”模型是中醫思維所采用的理論模型。作為一種思維范式,“象”模型具有程式化、固定化、符號化的特點。 “象”模型主要有卦爻模型、陰陽模型、易數模型、五行模型、干支模型等。
(1) 卦爻模型:《周易》用卦爻作為思維模型,卦爻最基本的符號是陽爻—和陰爻--,陰陽爻的三次組合構成八卦(23=8),陰陽爻的六次組合構成六十四卦(26=64),六十四卦也可看成是八卦的兩兩相重構成(82=64)。六十四卦是《周易》的基礎模型,這個模型不僅包含六十四卦的卦象符號,而且包括它的排列次序。卦爻辭及《易傳》則可看成是對這個模型的文字解說或內涵闡發。陰陽卦爻既有生成論意義,也有結構論意義,是象數思維的基點。其余六十二卦可看成是乾坤二卦的交合與展開。六十四卦是宇宙生命變化規律的完整的符號系統,也是理想的“象”(符號)模型。
中醫有關生命的藏象模型有多種,其中就有一種是八卦藏象。如《靈樞·九宮八風篇》直接將九宮八卦與臟腑配合,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