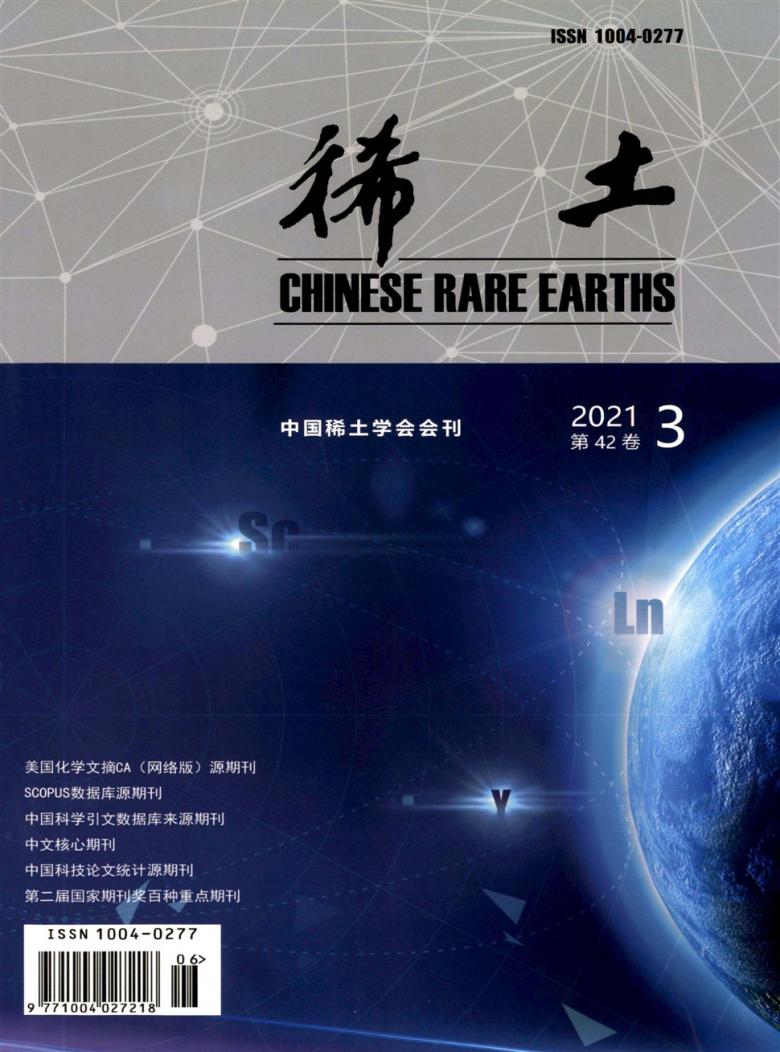論《周易》與中國文化軸心期大轉型(上)
本站會員
提 要:中國文化形態在軸心期發生了第一次大轉型:由神學文化形態轉變為世俗文化形態。這次轉型確立了作為人文主義精華的心學傳統,這是今天現代化的寶貴精神資源;但同時也逐漸失落了作為“第一實體”的個體精神,這是與現代性相悖逆的。這次轉型經過三個階段(西周、春秋、戰國),而《周易》文本正是其經典表征:《易經》觀念是其發端,《左傳》筮例是其發展,《易傳》思想是其完成。唯其如此,《周易》后來成為中國群經之首、百行之源。
關鍵詞:周易;左傳;中國文化;軸心時期;文化轉型
On the Book of Change
And the Great Transformation of Chinese Culture in Axial Period
Abstract: A great transformation from theological type to secular type took place in Axial Period of Chinese culture. The transformation set up ‘mindology’ as humanistic tradition, which is now one of the precious resources for modernization. Nevertheless, it made us lost the inpidual spirits as ‘primary substance’, the consequences of which are contradictory to modernity. The great transformation had undergone three phases, the classical representation of which just was the conditions about the texts of the Book of Change as follows. Its start was the ideas in the Yi Classic (during the Western Zhou Dynasty), its development was the explanation to the milfoil-pination in the Zuo Commentary (during the Spring and Autumn Period), and its completion was the thoughts in the Yi Commentary (during the Warring States). Precisely because these above, the Book of Change became afterwards the leader of all the classics and the resource of all the behaviors.
Key Words: the Book of Change; the Zuo Commentary; Chinese culture; the Axial Period; transformation of culture
眾所周知,中國文化在“軸心時期”、即西周、春秋、戰國時期[1]曾發生過一次大轉型;但是,關于這次轉型與《周易》[2] 之間的關聯、尤其是其現代意義,我們還不是十分清楚,這正是本文試圖探討的問題。
一.作為分析方法的基本觀念
為此,不得不先討論一下作為本文的分析方法的幾個基本觀念,因為我們今天研究《周易》,決不是為了發思古之幽情。在當今時勢下,有兩個問題是我們無法回避的:
《周易》對于我們應對西方文化的逼迫有什么意義?
《周易》對于我們解決中國當下的問題有什么意義?
因此,我們勢必或有意或無意地站在今天的立場上來打量傳統;我們今日關于歷史的傾向性觀念,必將成為我們研究傳統的方法論前提。
1.軸心期與現代性
當西方后現代思潮已經對“現代性”觀念進行深刻反思的時候,我們中國人還未能實現現代化;在這個意義上,我們還不完全屬于“現代人”。我們在太多地失去了自家文化傳統中的可以適應于現代性的“慧根”的同時,也太多地因襲了自家傳統中的悖逆于現代性的“劣根”。怎么辦?徹底拋棄傳統、全盤西化?這顯然是不行的,我曾專門著文對此加以討論,指出中國現代自由主義之所以屢屢失敗,一個重要原因是他們脫離傳統。[3] 那么,如我們所注意到的人們所提出的主張“重建傳統”?然而這里問題在于,傳統不是一成不變的,我們究竟是要重建“后軸心期”的傳統,還是軸心期的傳統、乃至于“前軸心期”的傳統?這就涉及對“軸心期”觀念的評價了。
我們知道,“軸心期”(the Axial Period)是雅斯貝爾斯(Karl Jaspers)提出的重要概念,認為在公元前數百年的時候,人類至今賴以自我意識的世界幾大文化模式(中國、印度、西方)大致同時確立起來,從此,“人類一直靠軸心時期所產生的思考和創造的一切而生存,每一次新的飛躍都回顧這一時期,并被它重燃火焰,……軸心期潛力的蘇醒和對軸心期潛力的回歸,或者說復興,總是提供了精神的動力。”[4] 按照這種思路,我們似乎應該徹底地“回歸”我們的軸心期傳統,或者“復興”軸心期傳統?然而在我看來,雅斯貝爾斯的“軸心期”概念是一種有缺陷的創新觀念。它確實是一種很好的創新觀念,可以相當有說服力地解釋歷史;但它同時是有缺陷的,主要缺陷有二:一是它容易使人將軸心期與前軸心期割裂開來。例如就西方的情況來看,古希臘哲學時代的傳統實際上是此前的某種更古老的傳統的進一步發揚。雅斯貝爾斯自己也說過:“(前軸心期的)古代文化的某些因素進入了軸心期,并成為新開端的組成部分。”[5] 西方的現代性觀念的核心精神不僅可以追溯到軸心期的哲學傳統,而且還可以追溯到前軸心期的神話傳統。二是軸心期觀念并沒有注意到軸心期轉型的負面。其實不論在東方還是在西方,軸心期大轉型的結果都是既建立了某些積極的東西,也失落了某些積極的東西。否則,以西方的情況看,我們就不能理解為什么軸心期大轉型之后出現了中世紀“黑暗時代”,也不能理解為什么后來需要“復興”(renaissance)。中國的情況亦然,作為軸心期大轉型的百家爭鳴,既建立了、也失落了某些積極的東西。所以,我們不僅要回顧軸心期,還要回顧前軸心期。
所謂建立了、同時失落了某種積極的東西,這當然是以現代性作為衡量標準的。那么,何謂“現代性”?這是我們必須首先搞清楚的一個關鍵問題。對此,后現代思想者已有紛紜淆亂的許多說法,因為現代性本身有許多方面的呈現。但在我看來,可以一言以蔽之:現代性的根本是“第一實體”(Primary Substance)觀念,亦即個體精神(Inpidual Spirits)。
在西方精神生活中,這種作為第一實體的個體精神,確實時時處處表現出來,諸如元素、原子、單子、基本粒子、邏輯變元、上帝、主體、個人、公民、法人,等等。它們被認為是基礎的、獨立自足的。按亞里士多德的說法,個體可以被種類所陳述而不陳述種類,因而個體乃是種類的基礎。然后,第一實體組成第二實體:種、類、屬等。這同樣在現代觀念的各個方面體現出來:感知依存于個別感覺,集合依存于個體變元,物種之遺傳與變異依存于生物個體,社會組織依存于成員,市場依存于企業單位,國家依存于公民,等等。現代集合論作為數學與邏輯統一的基礎、從而也是理解“世界的邏輯構造”[6] 的真正基礎,乃是西方第一實體觀念的現代科學表達:集合(set / collective)的基礎乃是元素(elements),此元素可以是低級集合,也可以是個體,但歸根到底是個體,所以集合又叫做“個體域”(domain of inpiduals)。總之,個體乃是存在的根基。[7]
這個重要問題,下文還將論及,這里我想指出的是:中國的現代化,首先是觀念的現代化;而觀念的現代化,核心在于重建第一實體。請注意,我講的是“重建”。我的意思是,中國的前軸心期不僅有過第一實體的觀念,而且這種個體精神雖然在后軸心期的專制時代遭到了削弱,但是從來沒有喪失盡凈,它主要存在于儒家心學文化與道家文化中。這是中國文化傳統的重要基因,是我們的觀念現代化的大本大源。
2.實體與關系
現代西方文化中的第一實體精神是源遠流長的,我們可以追溯到前軸心期荷馬史詩時代、神話時代的眾神生活中。但是,這種第一實體精神的最初自覺的理性表達,則無疑是由軸心期的雅典哲學、尤其是集大成者亞里士多德作出的。如果說西方思維形式在于亞氏的《工具論》,那么更根本的范疇基礎就在于《工具論》當中的《范疇篇》。這個范疇表是什么東西?它就是西方人的心靈結構。假定沒有《范疇篇》“十大范疇”所建構的心靈結構基礎,那么《工具論》乃至于整個西方思想文化的面貌都將是不可設想的。
亞氏列舉了十大范疇:實體,關系,數量,性質,時間,地點,主動,被動,姿勢,狀態。這實際上就是西方人心靈結構中的世界構成。在十大范疇中,最要緊的是實體范疇。他把實體分為兩類:第一實體(primary substance)指個體,而第二實體(secondary substance)指種、類、屬這樣的實體。實體是一切的基礎,而第一實體則是一切實體的基礎。他實際上認為,只有作為第一實體的個體才是真正的實體,因為“實體,從這個詞的最真實、原始而又最明確的意義說,是指既不能被斷言于主體、又不依存于主體的事物”;由于“除第一實體外,一切事物都或者能被斷言于第一實體,或者依存于第一實體;如果第一實體不存在,其他任何事物也都不可能存在”;因此“第一實體之所以更恰當地被稱為實體,是因為它們是其他一切事物的基礎,而一切其他事物或者被斷言于它們,或者依存于它們”。[8]
上文說過,我們曾經也有類似的富于個體精神的實體觀念。這是下文還將涉及的問題;這里我想指出:經過軸心期大轉型,中國文化失落了亞氏范疇那樣的“實體”觀念(我們也有“實體”這個說法,但不是substance的意思)。例如由《周易》哲學所確立起來的作為中國哲學最高范式的“陰陽”,并不被理解為實體范疇,而是被理解為純粹關系范疇。由此,我們談談“關系”范疇。
現代漢語的“關系”也是一個西來的話語,所以這里我得說明,當我們說“陰陽”被理解為一種“純粹關系”的時候,此“關系”并不是西語所說的那種關系(relation)。區別何在?按照亞里士多德《范疇篇》的觀念,關系是由實體、最終是由第一實體決定的:關系就是實體之間的關系,沒有實體,哪來關系?亞氏認為,作為實體,“個別的人或牛并不須要參照某種外在事物就可得到說明。”[9] 這就是亞里士多德關于關系的規定:實體是其前提。這種觀念在西方社會生活中的典型體現,例如“契約”精神:人與人之間、乃至人與神之間的一切關系,歸根到底都是契約關系;締約雙方都是第一實體,契約就是實體之間的一種關系。
但這恰恰不符合中國后軸心期的關系觀念。中國后軸心期的關系觀念之所以“純粹”,就在于它不以實體為前提。它是一種“無實體性前提的純粹關系”。這說起來似乎有些玄乎,其實很好理解:大家試想一下我們的宗法觀念。宗法就是一種純粹的人倫關系,這里,不是作為實體的個體決定了這個關系,而是這個關系決定了個體。——甚至講“決定了個體”也是并不確切的,因為在宗法關系下,作為實體的獨立個體是并不存在的。個體等于零,因為他或她的價值、幸福等等、甚至于他或她的存在本身,統統取決于“宗”這個關系。[10] 即便他或她不存在了,這個關系仍然存在。“宗”就是人倫關系之網,也就是天地萬物之網。宋儒把這種純粹關系稱為“理”。“理”非實體、而且先于實體,故朱熹說:在本體論上,“未有天地之先,畢竟也只是理”;在倫理學上,“未有君臣,已先有君臣之理;未有父子,已先有父子之理”。[11] 這種純粹關系的觀念,顯然缺乏作為第一實體的個體精神的基礎。
3.人與神
中國個體精神的失落,與上帝神的至高無上地位的失落大有關聯。談到中國的前軸心期文化觀念,可將作為“三代”之一的商代的文化觀念作為典型,因為此前的夏代“文獻不足征”,此后的周代則開始已經進入了軸心期轉型。商代文化觀念的一個最突出的特征,是神學觀念。“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后禮”[12],這大概是無須在此作出論證的歷史常識。我這里想要特別加以分析的,是這種神學文化的這樣兩個特征:一是超越性存在者或超越物(Transcendence)的設定,二是超越者(transcender)的個體性(inpiduality)的設定。這兩點是我們理解中國前軸心期文化傳統的關鍵,我們得先從理論上作一番解釋。
“超越”問題是目前的一個熱門話題,但人們對此的理解存在著很大的混亂。按胡塞爾(Emund Husserl)現象學的解釋,超越物是對處于內在意識之外的存在的預設。基督教的上帝、中國商代的帝,都是這種外在超越的設定。這是問題的一個方面,另一方面則是:人似乎天生是追求超越的,所以他總是要設定某種超越存在。人們對胡塞爾的一個極大的誤解,就是以為他是反對一切超越的。其實胡塞爾所反對的只是“外在超越”,因為這種超越的設定會導致“認識論困境”[13];但他訴諸“內在超越”[14],因為普遍的“本質直觀”對于個體的“經驗直觀”來說仍然還是超越的。在這個意義上,先驗的現象學(transcendental phenomenology)可以譯為“超越的現象學”,因為“超越之物”(Transcendence)和“先驗的”(transcendental)其實是同源詞。然而當人在追求超越時,這種超越體驗必定是個體性的(所以胡塞爾也承認,普遍的本質直觀是從個體的經驗直觀入手的)。唯其如此,神學的觀念必然導致個體的觀念。這就是為什么西方哲學的亞里士多德“第一實體”觀念竟然為神學的基督教所接受、又經宗教改革而生長出現代性的個體性觀念的原因所在。
中國商代的神學觀念也是如此,它本質地蘊涵著個體性觀念。固然,對神的設定、宗教儀式的舉行等等,是宗族群體的事情;但對神的體驗,則只能是個體的事情。前一情況孕育著群體精神,它是后來儒家文化、尤其理學的群體關懷的文化基因;而后一情況則孕育著個體精神,它是后來儒家心學、道家文化的個體關懷的文化基因。當人在體驗神或“帝”時,他是單獨地面對那個“絕對的他者”的,他知道這個他者隨時隨地都在關注著自己的言行,他的心靈獨自與這個他者對話。他知道自己的善舉會贏得這個他者的贊許,并因此而產生一種純粹個體性的崇高感。我們在孟子那里看到的那種高揚的個體獨立精神,正是這種崇高感的歷史遺產。可惜的是,中國所固有的這種個體精神后來失落了或被遮蔽了。
二.中國文化的形態及其歷史
為了對《周易》作出準確的歷史定位,我們還須首先討論中國文化形態及其歷史演變的大勢,因為只有以這個參照系為背景,我們才能準確地找到《周易》的歷史坐標。
很明顯的是,中國文化和西方文化的歷史發展過程有一些基本的一致之處:它們都經過三個大階段,中間都經歷了兩次大轉型;這樣,中西文化發展的歷史都可以劃分為五個階段:前軸心期,軸心期(第一次大轉型),中古時代,轉型期(第二次大轉型),現代。
1.前軸心期
前軸心期,在西方是古希臘哲學時代之前,在中國則是春秋戰國乃至西周之前。在這個時代,中西文化之間有許多相似之處,諸如,這是一個神學的時代、神話的時代、詩歌的時代,等等;文獻方面,在西方是《荷馬史詩》,在中國是甲骨卜辭、“書”(虞夏商書)、“詩”[15]。但是同時,中西文化在這個時期又各自呈現著自己的特色,例如在關于神的問題上,西方的“眾神”具有相當獨立的個體精神,而中國的神的等級相對更為森嚴。
中西文化形態盡管后來在軸心期發生了轉型,但軸心時代精神仍承襲了各自在前軸心期所鑄成的基本精神傳統。就中國的情況看,個體精神方面,正如《說苑》所說:“禹曰:堯舜之人皆以堯舜之心為心,今寡人為君也,百姓各以其心為心。”“百姓各以其心為心”,這正是中國前軸心期之個體精神的表現。當然,群體精神也是前軸心期文化精神的另外一個方面。《白虎通·號》說:“古之時未有三綱六紀,民人但知其母,不知其父,……饑即求食,飽即棄余。茹毛飲血,而衣皮葦,于是伏羲……因夫婦,正五行,始定人道。”《新語》說:伏羲時代“民始開悟,知有父子之親,君臣之義,夫婦之道,長幼之序。”可見倫常綱紀作為群體原則也是前軸心期開始奠定的。
中國文化軸心期大轉型的一個重要表現,就是神的地位的降低、人的地位的提高。今天看來,如上所述,前軸心期的人神關系本是一種“健康”的聯系。這是因為人可以兩種方式面對神:一是作為群體族類,一是作為個體自我。在西方現代觀念中,經過文藝復興、宗教改革的洗禮,宗教信仰已成為一件純粹個體性的事務:人可以作為純粹個體,單獨面對神,與神簽約。這與中世紀的觀念是有所不同的,那時人神之間的事務必須由宗教組織教會來代理,而宗教組織所代表的不是個別的人,而是群體的人,因而不是信徒決定了教會,而是教會決定了信徒。但這已是軸心期大轉型之后的事情了。
2.軸心期(第一次大轉型)
前軸心期乃是世界幾大文化形態的醞釀期,而軸心期則是世界幾大文化形態的定型期,如上所說,這種定型原是一種“有因有革”的過程,亦即孔子所說的“損益”的過程。但其共同特征則是哲學理性的覺醒,這個共同特征決定了世界幾大文明傳統的共通性,即它們都有過一個軸心期,那時,哲學理性產生了;但是不同文明傳統之間的這種文化轉型,又有若干不同的特點,正是這種不同,決定了世界幾大文明傳統的文化類型的區分。
中西文化的一個基本區別,在于上述超越觀念經過軸心期大轉型之后的分道揚鑣:西方軸心期轉型導致了文化的更進一步神學化,進入了中世紀基督教神學時代;而中國軸心期轉型則導致了文化的世俗化,進入了中古時代(自秦至清)的儒學時代[16],此時的中國文化雖然保留著許多諸如祭天祈神之類的神學孑遺,但基本上是世俗化的。沒有統一的宗教,皇家宗教活動與儒、道、釋多元并存,這正好表明此時中國人所有的只是古代神學解體以來的宗教“殘片”(借Alasdair MacIntyre語)。《禮記·表記》:“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后禮……周人尊禮尚施,事鬼敬神而遠之,近人而忠焉。”所說的正是這樣一種情況。在前軸心期的商代和軸心期開始的周代之間,這是一個極為重要的分野。有學者甚至于認為:“對于‘天命’,周公其實是不信的。周公對當時的另一輔政大臣召公奭就坦開了他對‘天命’的真實意見:‘天命不易,天難勘,乃其墜命,弗克經歷嗣前人恭明德。’‘天不可信,我道惟寧王德延。’”只不過“在當時宗教思想浸入人心的情勢下,周人又不能不利用“天命”觀念。”[17] 這是頗有見地的看法。
另一方面,如上所說,屬于前軸心期的商代,較之已開始進入軸心期的周代,是更富于個體獨立精神的。據《泰誓》載,武王誓師:“受(紂王)有臣億萬,惟億萬心;予有臣三千,惟一心。”這雖然是聲討紂王之辭,倒是說出了一種事實。軸心期大轉型的另外一個結果,就是這種個體獨立精神的式微。但是,在儒家、道家、墨家思想中仍然保留著個體精神的理念。例如上文提到的,孟子就是儒家中極富于個體獨立精神的人物,這種個體獨立精神傳至現代的儒家,如梁漱溟、張君勱、錢穆、牟宗三、陳寅恪等,也是有目共睹的。墨家主張“兼相愛,交相利”,其前提顯然是承認雙方的個體利益;至于道家的個體精神,那就更不消說了。
3.中古時代
在上述文化形態的轉型中,中國文化發生了巨大的變遷:一方面,神的地位被削弱了,人的地位被提高了;但另一方面,被提高了地位的人不是個體的、作為“第一實體”的人,而是群體的、只作為“類存在”(馬克思語)的人。換句話說,此時的中國人并不是“被解放了的普羅米休斯”,而是雖然擺脫了神的權威、但卻套上了人自己的觀念繩索的束縛。所以,這種轉型的結果具有雙重意義:伴隨著神的地位的降低的,是個體精神的失落;伴隨著人的地位的提高的,是群體精神的強化。在作為絕對實體的神被邊緣化了的同時,作為第一實體的人本身也被邊緣化了。結果例如,道家思想只能作為儒家思想的補充物而獲得存在的價值,至于墨家思想,竟成了“絕學”。
但這并不是說在儒家思想中完全沒有作為第一實體的個體精神,其實,儒家思想存在著內在的緊張。為說明這一點,我們試來分析一下長期充當了儒學正宗的心學。思孟學派創立的心學,經宋明新儒家(尤其是王陽明)、晚明儒家啟蒙運動(尤其是黃宗羲)而至于現代新儒家(尤其是熊十力一系),實際上將外在超越的天命鬼神“懸擱”(epoche)起來了,而將人自身的心性設定為絕對自明的“原初所予”。但是正是這種類似于現象學的“還原”(reduction)蘊涵著內在的張力,那就是“道心”與“人心”、或“天理”與“人欲”的對立設置導致的自我悖逆:可以通過“經驗直觀”達到的人心人欲是個體性的,而只能通過“本質直觀”才能達到的天理道心是非個體性的;但是這種本質直觀活動本身,又只能通過個體行為來體證。這一點在宋明理學中的體現,那就是“本體”與“功夫”的緊張:本體作為非個體性的存在,作為性、作為理,只能通過本質直觀才能領悟;但是這種領悟本身,卻又必須通過個體經驗性的功夫才能完成。這就存在著一個很大的問題:總是非個體性的本體,怎么可能通過總是個體性的功夫來達致?這非常類似胡塞爾對笛卡兒的質疑:個體經驗的“我思”怎么可能到達本質的“存在”?這是不論西方還是中國的先驗哲學存在的一個理論困境。
這種被理解為本質、本體的性、理,實質上乃是對中古專制制度設置的認可,即使之合法化,如黑格爾的“凡是存在的都是合理的”。后來戴震提出的“后儒以理殺人”的批判不是沒有道理的,因為“存天理滅人欲”正是在天理人欲二元對置的基礎上對個體精神的壓抑乃至于扼殺。這是中古精神生活的事實,是我們不能不承認的。但是另一方面,也不能說中古思想文化傳統完全徹底地喪失了個體精神,否則,我們無法解釋這樣的現象:從晚明、明清之際的早期思想啟蒙運動、直到現代新儒學運動,都是富于個體精神的,他們為什么都跟中古儒學、尤其是心學傳統有著密切的內在思想關聯?
4.轉型期(第二次大轉型)
中國思想文化的第二次大轉型是一個橫跨了所謂“近代”“現代”和“當代”的歷史運動,直到今天,我們大家都還身處其中。至少從洋務運動起,這個過程就已開始了,接下來是維新運動、民主革命運動、五四新文化運動……一直到最近的90年代興起的傳統文化熱,其中包括“易經熱”。這當中雖然一直呈現著自由主義西化派和傳統文化派的斗爭,但是人們似乎忽視了一個極為重要的現象,就是:個體精神始終是這個歷史進程的主旋律。即使是被稱為“文化保守主義”的現代新儒家,其實仍然是個體精神及自由、民主精神的闡釋者,只不過他們寄希望于個體精神能從我們的文化傳統中自然生長出來、邏輯地推演出來,而西化派則寄希望于將個體精神簡單地從西方文化中移植過來。所以,在我看來,我們今天必須超越這種兩派對峙、二元對立的格局。我們確實需要“重建”我們曾經固有的個體精神家園,但也同樣確實需要引進西方個體精神的參照。
上述個體精神的張揚導致了另外兩種重要的“精神現象”、另外一種緊張關系:有的人感到中國必須重建宗教神學文化傳統,另外有的人則持相反的立場。感到中國迫切需要宗教神學的,又分兩種情況:一是引進西方宗教、尤其是基督教傳統,這就是目前基督教在中國獲得越來越廣泛的傳播的深層原因;一是把儒學改造為作為宗教的“儒教”,這種企圖早在五四之前便已表現出來,一直延伸到最近還在激烈進行的關于“儒教”問題的大討論。[18] 這種主張的實質,顯然蘊涵著對軸心期世俗化轉型以來、乃至軸心期本身包括《周易》確立的中國文化傳統從根本上的否定。我以為這是不可取的。雖如上文所述,神學本質地蘊涵著個體精神,但是顯然不能反過來說,個體精神必須以宗教神學為基礎。且以西方近代以來的歷史為例,文藝復興顯然同時具有這樣兩個重要特征:一是對神學的批判,一是對個體精神的空前張揚。所以在我看來,無論從學理上、還是從歷史事實上來看,在世俗的人文哲學的基礎上建立現代性的個體性的“第一實體”精神都是可能的,這應該是我們努力的基本方向。
5.現代
這里所說的“現代”其實只是一個文化類型觀念,因為我們中國人還沒有真正進入現代性;如果從歷史時間的角度講,這里的“現代”應該是“未來”。未來中國哲學的方向是個復雜的問題,不是三言兩語能說清楚的,但我認為,核心的一點應該是:重建第一實體;但是,并非回到那種神學的個體精神,而是建立人文的個體精神。這就是說,我們既要重新激活我們前軸心期的個體精神資源,但又不拋棄軸心期以來的世俗的人文精神遺產。因此,我以為我們的任務是:在作為先驗哲學的儒家心學傳統的基礎上,吸收道家思想的積極因素,從而重建個體精神。我個人認為,在這方面,重新闡釋作為中國文化軸心期大轉型的經典文本標志的《周易》,是具有重大意義的。
注釋:
[1] 越來越多的學者確認,西方文化的軸心期是古希臘時代,印度文化的軸心期是佛陀時代,而中國文化的軸心期則是春秋戰國時代。而我認為,中國文化的軸心期大轉型在此前的西周時期就已經開始了。
[2] 關于《周易》的名稱使用并不一致。本文所稱《周易》包括:《周易》古經》(《易經),《周易》大傳(《易傳》)。
[3] 黃玉順:《“自由”的歧路:五四自由主義的兩大脫離》,《學術界》2001年第3期;人大復印資料《中國現代史》2002年第3期。
[4] 雅斯貝爾斯:《歷史的起源和目標》,第14頁,華夏出版社1989。
[5] 雅斯貝爾斯:《歷史的起源和目標》,第13頁。
[6] 這是維也納學派的經典之一、卡爾納普的著作名《世界的邏輯構造》(Der Logische Aufbau der Welt)。
[7] 拙文《儒家心性論作為倫理學基礎是否可能》詳細探討了這個問題,載《恒道》創刊號,鞠曦主編,吉林人民出版社2002。
[8] 亞里士多德:《工具論》,李匡武譯,第12?4頁,廣東人民出版社1984。
[9] 亞里士多德:《工具論》,第28頁。
[10]“宗”原意指祭祖的宗廟,它是宗法關系在觀念、制度、器物層面上的集中體現。
[11] 《朱子語類》卷1、《朱子大全》卷95。
[12]《禮記·表記》。
[13]“認識論困境”是休謨以來的西方哲學面對的一個基本問題:在認識和真理問題上,內在的意識如何能“切合”外在的實在?我常用的一個比喻是:人如何能走出自己的皮膚?
[14] 近年關于“內在超越”已經成為了一個熱門話題,但人們對何為“內在超越”尚無一種真確的認識。
[15]《詩經》的時代與《周易》的有重疊,經歷了春秋前期、西周、乃至“商頌”。同時還有大量未收入《詩經》里的“逸詩”,時代更早,例如拙著《易經古歌考釋》發掘出來的商周之際的歌謠(巴蜀書社1995)。
[16] 這只是從大勢來講,儒學成為了整個中古時代(自漢至清)的主流意識。
[17] 姜廣輝:《論中國文化基因的形成》,原載《國際儒學研究》第6輯。
[18] 近半年來在“孔子2000”網站上開展、并且仍在激烈進行的論戰就是一個突出的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