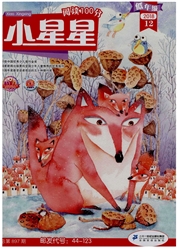關于把脈我國媒體的輿論監督——從“記者黑名單事件”說起
李波
【摘要】媒體的輿論監督被視為繼立法監督、司法監督以及行政監督之外的第四種監督,它是我國憲法和法律賦予媒體的權利,也是每一家有良知的媒體所應具有的基本職業操守。正確地行使媒體的輿論監督權,可以有效地彌補其他三種監督的不足,從而更好地保障民眾的知情權、表達權、監督權。輿論監督既是社會主義民主法治的題中之義,也是公民基本權利,當家作主地位的延伸。然而,近年來,惡意阻撓媒體監督的事件卻屢次曝光。這當中既有當事者民主法治意識淡薄的原因,也有媒體自身報道失實、職業理想偏離等方面的原因。筆者以近日的“記者黑名單事件”為例,以期對我國的媒體輿論監督做一較為全面的“把脈”。
【關鍵詞】媒體;輿論監督;“記者黑名單”
2011年6月13日,由國務院食品安全辦和衛生部共同主辦的“科學認識食品添加劑”座談會,在北京首都大酒店舉行,會議期間,中國健康教育中心、衛生部新聞宣傳中心主任毛群安在講話中說道:“正在打造一個健康的媒體報道平臺,對極個別的媒體記者建立黑名單,以此打擊他們有意誤導人民,傳播一些錯誤的信息的勢頭。”毛群安稱有關食品安全的報道產生的影響是巨大的,給國家的食品工業發展造成負面影響。講話中的“記者黑名單”這一說法立刻引發了民眾的廣泛討論,支持者有之,反對者亦有之。前一派的觀點認為,在針對食品安全的新聞報道中,確實有個別媒體存在報道失實的現象,這不僅誤導了民眾,引發一些不必要的恐慌,而且也直接損害到當事企業的信譽和經濟效益,造成了巨大的負面影響。因此,對這些媒體和記者建立黑名單是完全合理且必要的,能夠達到“懲前毖后”的效果,從而迫使媒體遵守職業道德,杜絕新聞失實。而反對者的聲音則集中為:建立所謂的“記者黑名單”是在有意地封鎖民眾對事件了解的通道,是在打擊正義,維護邪惡,事實上剝奪了民眾的知情權、監督權和表達權。此外,國內的各類媒體對于此事也是紛紛發表評論文章,但觀點不外乎是這兩方面。
筆者通過綜合分析事件的原委以及各大媒體的評論,認為對于“記者黑名單事件”反映出來的我國媒體輿論監督方面的問題可以從以下幾個方面去把握:
媒體的輿論監督是我國憲法和法律賦予媒體的合法權利,任何組織和個人都沒有權利干擾和阻撓媒體合法、正當的輿論監督。1987年,中共十三大正確分析了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歷史趨勢和內在要求,在我國歷史上第一次提出“輿論監督”的新概念,并明確表示:“重大情況讓人民知道,重大問題經人民討論。”且早在1950年4月19日,中共中央就曾專門作出《關于在報紙刊物上展開批評與自我批評的決定》,其中寫道:“在一切公開的場合,在人民群眾中,特別在報紙刊物上展開對于我們工作中的一切錯誤和缺點的批評與自我批評。”1954年7月17日,中共中央在《關于改進報紙工作的決議》中再次強調:“報紙是黨用來開展批評和自我批評的最尖銳的武器。”可見,正視媒體的輿論監督、積極運用媒體指導和監督工作,是我國黨和政府優良的執政傳統。
此外,《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中,涉及媒體活動的就有多條,如第22條規定:“國家發展為人民服務為社會主義服務的文學藝術事業、新聞廣播電視事業、出版社事業、圖書館博物館文化館和其他文化事業,開展群眾性的文化活動。”第35條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有言論、出版、集會、結社、游行、示威的自由。”從以上兩條我們可以清晰地看到,國家對于媒體的正常報道活動是完全支持和保護的。第41條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對于任何國家機關和國家工作人員,有提出批評和建議的權利,對于任何國家機關和國家工作人員的違法失職行為,有向有關國家機關提出申訴、控告或者檢舉的權利,但是不得捏造或者歪曲事實進行誣告陷害。”即公民對于任何國家機關和國家工作人員都有提出批評和建議的權利。這其實就是明文規定了媒體可以進行正當的輿論監督。此外,2008年5月1日起開始施行的《政府信息公開條例》對于政府信息公開的范圍、方式和程序也都有具體細致的規定。這些法律、法規的頒布和施行為媒體的輿論監督提供了可靠的法律依據。“記者黑名單事件”發生以后,國家新聞出版總署有關負責人就曾公開重申:“依照我國的法律和規定,任何組織或者個人不得干擾、阻撓新聞媒體及其新聞記者合法的采訪活動,我國政府從來不允許新聞當事部門、機構建立所謂的記者‘黑名單’!”
由此可見,衛生部此次宣稱的建立“記者黑名單”是毫無依據的。即便是個別媒體在報道食品安全事故時存在虛假成分,但由于衛生部不是法定的媒體監管單位,其建立“記者黑名單”也就沒有法律上的依據。眾所周知,食品安全本來就是一個具有一定專業性質的問題,因此,也就做不到讓每一個記者對其中所涉及的方方面面都能夠像專家那樣做出精準的披露和報道,更何況重大事故的新聞報道本來就是一個需要層層挖掘,不斷深入的過程。當然,在媒體競爭日趨激烈的今天,我們也不排除有個別的新聞記者為了片面追求所謂的“新聞效果”,而故意在報道的過程中添油加醋,造成聳人聽聞的轟動效應。在出現此類情況的時候,相關政府部門最應該做的是最大限度地及時公開信息,讓更多的民眾有從權威渠道了解事實真相的機會,從而讓媒體的失實報道不攻自破。相反,如果在這個“敏感”的時候希望通過“記者黑名單”或者“無可奉告”之類的托詞以期控制事態,無疑是火上澆油,只會更加順應部分民眾的“合理想象”。
輿論監督是保障民眾知情權、監督權、表達權的重要手段,各級政府部門應該做到“善待媒體、善用媒體、善管媒體,充分發揮媒體凝聚力量、推動工作的積極作用”。2010年1月4日,全國宣傳部長會議在北京舉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長春出席會議并講話,他在講話中說道:“要適應時代發展要求,努力提高與媒體打交道的能力,切實做到善待媒體、善用媒體、善管媒體,充分發揮媒體凝聚力量、推動工作的積極作用。”可以說,此次講話為政府部門在與媒體打交道時提供了“行動指南”。曾被譽為“中國第一新聞官”的趙啟正在論及公務員和媒體記者之間的關系,以及雙方應如何溝通時說道:“記者不是部下,不是學生,不是敵人,甚至也不是朋友,而是挑戰者。”“政府和記者之間是接力的關系,政府提供新聞源,記者通過稿件向社會發布新聞,受眾了解新聞后形成輿論。”這應該是他長期與媒體打交道得出的經驗之談。媒體作為立法、司法和行政之外的第四種監督力量,背后是公眾和社會,它并不是代表自己在進行監督,而是一種社會監督、輿論監督、公眾監督。從這些針對政府與媒體交往的觀點可以看出,加強政府工作人員的媒介素養,提高他們與媒體打交道的能力顯得尤為重要。
正當的采訪,是記者的職務行為。記者的采訪權,可以說是憲法規定的公民言論自由權的延伸,實質上是受公眾的委托、為兌現公眾知情權所行使的權利。近年來,國家更是把保障公民的知情權、參與權、表達權、監督權作為基本人權。因此,“善待媒體、善用媒體、善管媒體”,不僅對于提高政府工作人員的執政能力作用巨大,而且也是尊重民意,保障民權的重要渠道。在這方面做得比較成功的有2007年3月海南省政府對“毒香蕉事件”的處理。3月13日,廣州的《信息時報》刊登了一篇題為《廣州香蕉染“蕉癌”瀕臨滅絕》的文章,文章說廣州香蕉大面積感染巴拿馬病毒,幾年內就會滅絕,這種病毒被稱為“香蕉癌癥”。3月21日,《廣州日報》又有一條消息稱“香蕉等十二種水果有毒殘余,有致癌物殘余,成了毒水果”。報道一出,民眾嘩然,海南的香蕉銷量隨之急劇減少,價格猛跌。隨后,海南省政府緊急召開新聞發布會,針對相關情況做出了詳細的解答,并組織權威專家出來辟謠,這一系列做法的目的是要盡量地使各方的損失降到最低,值得其他地方政府在應對此類突發事件時學習和借鑒。雖然此次衛生部門的“記者黑名單”的初衷是要對極個別不負責任的記者進行采訪限制,殊不知其導致的直接后果將是使更多具有良知的記者“人人自危”,因為對于食品安全事故這種千頭萬緒的事情,真相的最終披露本身就有一個較為復雜的過程,在事件尚未徹底澄清之前,記者的報道只能是盡可能地接近真相。如果“接近真相”便被判為“誤導公眾”,那么采訪食品安全的記者們恐怕會無從下筆。如果別的部門也效法建立自己的“記者黑名單”,那么,試問媒體的存在還有什么意義?
因此,“擬對個別誤導公眾的媒體記者建黑名單”的做法是不合適的,這并不僅僅是如何對待記者、對待媒體的問題,也是如何對待公眾知情權、監督權的問題,更是公權力如何對待社會的態度。媒體不僅僅是食品安全信息披露的承擔者,更應該是食品衛生安全的監督者、批評者。盡管有媒體由于各種原因在報道食品安全問題時誤導了公眾,但必須看到,誤導公眾的“誘因”是因為食品安全監管方面出了問題。
媒體工作者在進行輿論監督的時候應該堅持新聞專業主義,遵守職業規范,建立一個客觀公正的輿論監督環境。馬克思有一個著名論斷:“沒有無義務的權利,也沒有無權利的義務。”這說明,任何權利都不是絕對的、不受限制的。無論是宏觀上的權利,還是微觀上的具體權利,都只能活動于一定的界限之內。當我們作為權利享有者行使權利的同時,也應切記自己還是義務的履行者,這樣才能最大意義上獲得自由,這一點,對于從事新聞工作的人來說,尤其值得注意。在行使輿論監督權的時候,同時要履行客觀、公正報道事實的義務,這不僅是法律上的規范,也是新聞職業賦予的道義要求。陳力丹教授曾經講過的“以自律爭自由”其實也就是從這個意義上出發的。
食品安全不僅事關民眾身體健康,而且關乎產品市場走向、企業的切身利益,所以媒體在報道時必須科學客觀,必須把握好分寸,盡量避免出現“誤導公眾”的情況發生。2011年5月有關部門負責人就曾表示,圣元奶粉、皮革奶、牛肉膏等被媒體夸大,食品安全事件所占比例很小。作為一個新聞人,不顧起碼的職業道德發出誤導消費者的報道,不但是對公眾不負責任,對食品企業和生產者更是致命的打擊。對于虛假報道、記者敲詐勒索這些為人所不齒的惡劣行為,從宣傳主管部門到相關司法部門,都有一套制度和機制去管理和約束。2009年4月國家新聞出版總署發布的《關于采取切實措施制止虛假報道的通知》就規定:對經查實采寫虛假、失實報道的記者,要給予警告,并列入不良從業記錄名單,情節嚴重的要吊銷其新聞記者證,五年內不得從事新聞采編工作,情節特別嚴重的,終身不得從事新聞采編工作。對于個別“鋌而走險”的媒體發布的虛假信息,只有政府部門以最及時的速度和最大的限度將事實的真相公之于眾,謊言才會無處遁形。
2011年7月,傳媒大亨默多克旗下的《世界新聞報》終因深陷“竊聽門”而不得不宣布停刊,這家有著168年歷史的老牌星期天報紙是英國最暢銷的小報,曾經的輝煌對照今天的“黯然離場”,令太多的人感到惋惜。究其原因,是因為沒能守住新聞職業道德的底線,為了獲得獨家新聞,而多次發生“竊聽事件”。這也再次向媒體行業敲響了警鐘,公信力是要靠媒體自身在新聞報道的過程中建立和維護的。這就在另一種層面上“倒逼”媒體在以后的工作中加強把關,更加注重消息的真實性,對自己的職業操守負責,也對民眾的知情權、監督權負責。
在我國,輿論監督既是人民言論自由的具體體現,也是人民民主專政實現的形式之一,輿論監督擔負著保障國家公共權力正當行使的職責,因此,媒體作為輿論監督的重要主體,對輿論監督的健康運行負有責無旁貸的義務,并且,政府部門、社會團體以及個人對于媒體的正常報道活動也應該積極支持,不能再出現“記者黑名單”這樣的事件,只有兩方面都遵守好相關法律法規,履行好各自的職業規范,那么一個健康的輿論監督環境才能真正實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