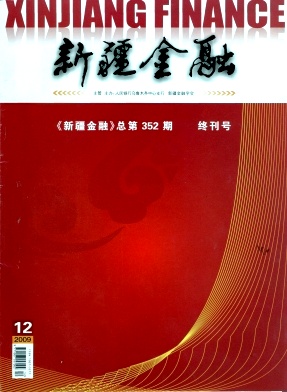關于論“微時代”輿論的畸變形態
李鐵亮
【摘要】在這個以微博作為傳播媒介代表、以短小精練作為文化傳播特征的時代,人們獲取信息、了解事件、參與事件的方式發生了根本性的改變。條件和媒介環境的變更使人們的心理態勢也隨之產生變化,相伴而來的就是輿論形態上的畸變。
【關鍵詞】微博;媒介環境;畸變
網絡——畸變輿論產生的溫床
網絡開始發展的頭幾年,人們給這個時期起了個洋氣的名字,謂之“e時代”,它為世界編織了一張巨大的網,其觸角伸向了世界的每一個角落,“先知”馬歇爾·麥克盧漢預想的“地球村”已成為現實,可是“先知”的預想又怎能快得過科技,如果麥克盧漢今天還健在,他萬萬不會想到他預想到的“地球村”放在今天已過于龐大,網絡高度發達的今天,“微時代”已經悄然到來,有人說,“微時代”即以微博作為傳播媒介代表、以短小精練作為文化傳播特征的時代,“微時代”信息傳播速度更快,傳播的內容更具沖擊力和震撼力。在筆者看來,“e時代”代表了網絡初期,即技術的萌芽期,而“微時代”則是網絡青春期,肆虐而張狂。“微”形容了瞬息萬變的媒介,它代表的是物理上的能力場,把物質的、現實的世界通過媒介的力量虛擬化,與麥克盧漢“地球村”的說法形成比照,把這個世界不斷縮小、縮小、再縮小,最后只剩下了一個微小的用肉眼看不到的質子。
每一個正常思維的人,都有一種感知外界精神的能力,諾埃勒·諾依曼(Noelle-Neumann,E)稱它為人的“準統計器官”(quasistatiscal sense organ)、“統計直覺”(statistical intuition)和“意見器官”等。一個人開始思想、說話或寫作時,都會既清晰又模糊地意識到,有許多觀念包圍著自己。這些觀念的存在形式是多樣的,但有一個共同點,即它們處于“我”以外。在這個意義上,李普曼(Lippmann,W)說:“這些其他人頭腦里的想象,他們自己的情況、他們的需要、意圖和關系等都是他們的輿論。”輿論的形成因不同的社會環境、公眾心理,以及輿論客體的差異,很難給出一個標準化的形成公式,但是輿論總會有一個大致的輪廓概念環繞著它的滋生和成長,那就是社會變動、較大事件的發生刺激意見的出現,特別是與多數人持有的信念相矛盾或與他們的心理期待相契合的事件;意見在社會群體中的相互趨同。然而在網絡“微時代”,輿論形成、傳播的速度已是迅雷之勢,速度的不可思議性有可能使輿論的外體扭曲,傳者的不確定性易使輿論形態產生錯位,從而導致輿論的畸變。
新浪微博、Twitter等微博客的出現,宣告了新的網絡媒介的誕生。140個字的限制,裂變式的傳播方式,傳播終端的便攜式,使得微博特別適宜于承載碎片化的信息,體現社會深層群體的意見和情緒。然而這些看似優勢的特點卻滋生了畸變輿論的形成與成長,產生這種畸變輿論的原因有幾點:一是作為新生媒介,微博把關制度還不完善,致使一些極端言論在其中傳播,特別是社會上一些不法組織以普通草根的名義所發出的具有欺騙性、煽動性的言論。二是傳播信息群體本身就是不同的人群,他們無論是文化素養、家庭背景還是心理成熟度都各有不同,所發信息有時也只是大腦中的一些閃念,這種片面化的信息有時候也能夠引起畸變輿論的迅速傳播。三是面對較大社會變動或者是突發事件所引發的公眾情緒型的輿論。面對突發事件,公眾難免會產生一些負面情緒,諸如焦躁、恐懼、冷漠、抑郁等。這些情緒對待信息的辨識不能夠保持冷靜的思考,導致人們對于主流媒介的不信任,更容易相信深層群體所發出的信息,最后致使輿論的畸變。例如“7·23”動車事件,由于事件的突發性以及主流媒體對事件報道的客觀性,導致許多不實言論在微博中迅速蔓延,事件本身牽扯到生命、出行等人們最為關切的問題,所以導致微博中言論的眾說紛紜,使人們無法辨識信息的真偽,所以只能依據自己的感性因素去追隨一些多數的言論,從而使輿論產生畸變。網絡出現以前,輿論的畸變形態也存在,但那只是社會中傳播速度極慢、影響力極小的留言,而網絡的出現,對社會的重要推動作用是不可否認的,但同時也為畸變的輿論提供了溫床。
輿論的畸變形態對大眾所產生的影響
心理方面的影響。態度是由認知、情感、意向三個因素構成的、比較持久的個人的內在結構,它是外界刺激與個體反應之間的中介因素,反之個體對外界刺激發出反應受其態度所調節。畸變的輿論對個人態度有很大的影響,個人在社會中總是會發生從眾行為,正確的輿論可以給大眾帶來好的影響,能夠團結大眾、鼓舞大眾。然而輿論一旦在網絡中發生畸變,同樣也會影響大眾,但是這種影響卻是負面的,大眾從情感到認知再到意向就會偏離正確的輿論所帶來的好的方面的影響,從而跟從畸變輿論所傳播的信息而慢慢改變自己對事物最初認知的觀念,這種觀念一旦形成,傳播的速度則會呈裂變式,對社會的影響將是極其惡劣。
行為方面的影響。在社會團體的壓力下,個人放棄自己的意見而采取與大多數人一致的行為,這是一種從眾行為。產生從眾行為的原因,是由于實際存在的或頭腦中想象到的社會壓力與團體壓力,使人們產生了符合社會要求與團體要求的行為與信念,個人不僅在信念上改變了原來的觀點,放棄了原有的意見,甚至在行動上表現出來。正確的輿論可以影響人們的行為,同樣,畸變的輿論也可以影響人們的行為。2011年8月4日,倫敦警察懷疑29歲男子馬克·達根非法持有槍械,提前在街道布控攔截。雙方爆發槍戰,據稱達根持未注冊的手槍朝警方射擊,并打傷一名警察,隨后達根身中兩彈死亡。很快社交網站Twitter上出現了討論,其中不乏情緒發泄、謠言與煽動言論,正是由于社交網站上出現的大量的煽動言論助長了人們的憤怒情緒,一些年輕人首先掠奪了城北恩菲爾德等地區的商鋪,隨后便引發了倫敦大面積的騷亂,騷亂甚至波及英國的其他城市。此次事件可謂是典型的由畸變輿論的迅速傳播從而影響個人行為的事件,它就好像從雪山上滾下來的小雪球一樣,速度極快,雪球越變越大,最后形成了猛烈的沖擊力。且不說事情是否就像微博中所傳播的那樣,事實的真相只有當事人知道,即使得到第一手消息的人、第一次在微博上傳播此消息的人對事實也只是一知半解,但是一旦消息在微博中迅速蔓延,那么就會有越來越多的人去相信這個消息,再加上社會的一些深層次的矛盾以及對死者的心理趨同性從而導致信息的飛速傳播,情緒的波動越來越大,人們對于微博中所引發的輿論更是深信不疑,從而最終導致人們在行為上作出行動,引發社會騷亂。
大眾傳播媒介如何減少輿論畸變,正確引導輿論
韋爾伯·施拉姆在他的著作《大眾傳播媒介與社會發展》中說:大眾媒介是社會變革的代言者。它們所能幫助完成的是這一類社會變革,即向新的風俗行為、有時是向新的社會關系的過渡。這一類行為變革的背后,必定存在著觀念、信仰、技術及社會規范的實質性變化。當今社會輿論的產生和發展與大眾傳播媒介的推動作用是息息相關的,在“微時代”的今天同樣是大眾傳播媒介起到重要的作用,那么對于輿論的畸變形態,大眾傳播媒介應該如何去減少、降低它的發生,進而正確引導輿論呢?
大眾傳播媒介應以準確的信息來應對模糊的信息。傳播的過程中之所以會產生虛假的信息、歪曲的信息、過分夸大的信息,從而導致輿論畸變的發生,歸根結底還是因為公眾對外部信息的不確定性,因為不確定,所以會猜測、懷疑、盲目地跟從來自其他方面的信息。從這一點來說大眾傳播媒介就應該為公眾提供準確、真實的一手信息,不斷地消除公眾對外部所獲取信息的不確定性,從根拔除公眾對于錯誤信息的吸收。雖然在“微時代”從某些方面來說微博等網絡傳播媒介所發出的信息要快過傳統媒介所發出的信息,但是絕大多數的群體還是認為傳統媒體所發出的信息比較權威,大多時候還是以來自傳統媒體的信息為參照,所以在網絡信息碎片化不易監管的情況下,傳統媒體更要提高自身的媒介素養,一絲不茍地把關好每一個信息,爭取做到信息的零錯誤,做到不確定性的信息絕不上報,不斷提升公眾對大眾傳統媒介的信任度。
提高網絡媒介的把關作用,降低畸變輿論的影響。網絡是博大精深的,卻又是極其微小的,它的博大精深在于它能夠容納整個世界,它的微小在于它把整個世界都連接在了一起。每天在網絡上傳播的信息數不勝數,要想對這些海量的、碎片化的信息一一把關談何容易,利用再多的人力物力也是不現實的,因為每一個使用網絡的個體都是一個傳播終端,他們可以隨意地在網絡上發表自己的言論和所得的信息。所以只能從網絡中那些主流的、大型的網站來著手,這些網站同時也都有自己的媒體,公眾在網絡上獲取信息也通常都是通過這些網站所發布的信息平臺。所以就需要這些網站以身作則把關好自己向公眾傳播的每一條信息,加強對自己的論壇、貼吧的監管,防止那些煽動性的、不實的信息的流入。微博是最容易引發畸變輿論的平臺,所以傳統媒體以自己的權威性和受眾的信任度的優勢,利用微博強大的傳播功能來正確引導輿論,以真實的、可靠的信息來消除公眾對微博上虛假信息的不確定性,微博的管理層也要加強對微博中傳播的信息的把關。
善用大眾媒介的議程設置功能,提高公眾對外界信息的辨識力。議程設置是大眾媒介的一個重要社會功能。大眾傳播媒介賦予了社會上各種議題不同程度的顯著性方式,影響著公眾矚目的焦點和對社會環境的認知,同時影響著人們對周圍世界事物的認知及重要性的判斷。雖然大眾媒介不能夠決定人們對某一事件的具體看法和意見,但是可以通過提供信息和安排相關的議題來有效地左右人們關注某些事實和意見以及他們議論的先后順序。“微時代”的信息傳播方式可以用兩個關鍵詞來概括,即“快閃式”和“碎片化”,信息內容本身也呈現“新鮮化”,公眾面對這樣的信息其辨識力相對降低,面對那些由虛假信息所致的畸變輿論形態,公眾就會變得毫無抵抗力。就這一點來說,大眾媒介所采取的方式不能只是亡羊補牢式的引導措施,而是通過運用議程設置的方式來改變公眾理解和辨析信息的能力,雖然媒介不能告知受眾如何思考和理解議程之外的事物,但是其已經被告知如何思考和理解議程之內的事物,當大眾媒介這樣做的時候,傳輸給公眾的不單是思考一個事物的方式,而是如何理解這個世界的能力,這種能力使公眾在接受來自外界的信息時能夠加以思考和過濾,排除問題性的信息,吸收可靠的信息。
結語
輿論的主體是公眾,社會的發展依靠公眾,大眾傳播媒介如何正確引導輿論、減少輿論畸變形態的發生,也是在不斷探討的課題,大眾傳播媒介的每一次發展、每一次革新,都會有新的課題擺在大家的面前,面對“微時代”的今天,大眾傳播媒介的發展可謂是一次大的跨越,科技的每一次變革都會以舊事物痛苦的轉變為代價,否則它也不可能去適應新環境所帶來的挑戰。大眾傳播媒介亦是如此,它不能因為網絡的革新導致的輿論的畸變形態去否定其更大的正面影響,而它更應該去考慮自身的因素,加快自身的轉變,以自身的不斷完善來克服這種輿論的畸變形態的發生,從而促進社會的快速發展。
[1]陳力丹.輿論學——輿論導向研究[M].北京: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社,1999.
[2]韋爾伯·施拉姆.大眾傳播媒介與社會發展[M].金燕寧,等,譯.北京:華夏出版社,1990.
[3]馬歇爾·麥克盧漢.人的延伸——媒介通論[M].何道寬,譯.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2.
[4]時蓉華.社會心理學[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
[5]J·赫伯特·阿特休爾.權利的媒介[M].黃煜,裘志康,譯.北京:華夏出版社,19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