試析京派小說的現(xiàn)代意識與中國傳統(tǒng)文化
溫泉
論文關(guān)鍵詞:京派小說現(xiàn)代意識傳統(tǒng)文化
論文摘要:從中國傳統(tǒng)文化角度入手,管窺其與京派小說中現(xiàn)代意識內(nèi)在的多角度聯(lián)系和京派小說現(xiàn)代意識獨特的深層蘊意。他們的現(xiàn)代意識是在吸收中國傳統(tǒng)文化的基礎(chǔ)上,結(jié)合現(xiàn)代心理學(xué)、美學(xué)理論,對傳統(tǒng)進行重新闡釋和運用,從審美角度反思現(xiàn)代性。
任何有意味的“現(xiàn)代”都不可能離開傳統(tǒng)憑空而生,而且最終也將成為傳統(tǒng)。傳統(tǒng)是現(xiàn)代無法掙脫的基因和刻意追求的目標。愛爾蘭作家詹姆斯·喬伊斯的《尤利西斯》是現(xiàn)代主義的經(jīng)典之作和奇書,但作者在運用意識流手法中,采取了與古希臘史詩《奧德賽》情節(jié)相平行的結(jié)構(gòu),使用了不勝枚舉的《圣經(jīng)》和莎士比亞戲劇的典故,雜以理語、歌謠和數(shù)十種語言。同樣,京派小說家也是借中國文學(xué)藝術(shù)傳統(tǒng),向著現(xiàn)代性屈而求伸的一次“對話”,他們的現(xiàn)代意識之所以獨特,從某種程度上看正是對中國傳統(tǒng)文化的轉(zhuǎn)活。
一、中國傳統(tǒng)文化的滋養(yǎng)
京派小說家的現(xiàn)代意識建立在對中國傳統(tǒng)文化的吸收上,這與他們的家學(xué)淵源和身世經(jīng)歷有著深刻的聯(lián)系。
廢名的文化心理、文學(xué)觀念和審美情趣受傳統(tǒng)文化的深層影響,就與他個人獨特的身世經(jīng)歷有著密切的關(guān)系。他出生在禪宗五祖弘忍大師的宏法寶地黃梅縣,距五祖當年秘傳衣缽給慧能的東山只有10余公里。廢名從小隨父多次到過五祖寺,其間的沙灘、石橋、水壩、竹林,還有寺里的小木魚、小喇叭等,都在他童年記憶里留下了深刻的印痕。六歲他就在鄉(xiāng)間私塾誦讀《三字經(jīng)》《百家姓》及古代詩文,深受傳統(tǒng)文化熏染。1922年秋,廢名人北大預(yù)科班。在北大讀書期間,他結(jié)識了胡適、周作人等人。從胡適那里,他開始認識到故鄉(xiāng)黃梅在文化史上的重要價值。廢名師承周作人,而周作人研讀過大量的佛教經(jīng)典并自詡為在家和尚,甚至在北大國文系講授“佛教文化”課程。周作人對于佛教的興趣,在一定程度上啟發(fā)并促進廢名對于禪學(xué)的進一步的自覺。這一切都激活了廢名心中久已潛在的故鄉(xiāng)禪文化影響,使他與禪的因緣更加密切而牢固。廢名的小說在格式的詩化、意境化、意象的古典化等方面都帶有醒目的傳統(tǒng)“胎記”,顯示了他對中國古代文學(xué)傳統(tǒng)的深度回歸和傍依。
凌叔華出生于一個北京的仕宦詩書之門,外曾祖父乃粵中著名畫家。父親凌福彭做過清末翰林,與康有為登同榜進士授一品頂戴,官至順天府尹、直隸部政使。這位達官也工于詞章書畫,加之其母親也粗通文墨,愛讀詩書文章,因此辜鴻銘、齊白石、陳衡悟、姚茫父這樣的文化名人經(jīng)常出人凌府。凌叔華人學(xué)前即由辜鴻銘啟蒙學(xué)英語、背詩詞,又師從慈禧太后的宮廷畫師繆素綺習(xí)畫。這樣的家庭環(huán)境和教育使她的小說中始終充滿著一種古典的氣息。
林徽因也出生于仕宦之家,傳統(tǒng)文化孕育出的溫柔、嫻靜、優(yōu)雅和高貴的氣質(zhì),使她能在創(chuàng)作中將深厚的內(nèi)在修養(yǎng)化為一種濃郁的女性氣質(zhì)和東方傳奇色彩。另外,林徽因從小就接受了完備的英漢語言、文化的熏陶和教育,既深得中國婉約平和風(fēng)格的底蘊,又汲取了西方文化現(xiàn)代性的營養(yǎng),形成蘊藉、含蓄、細膩、寫實兼有熱情的特殊格調(diào)。她始終用一種西方文化的現(xiàn)代意識來審視中國傳統(tǒng)文化中的方方面面,努力構(gòu)建中西文化融合的完美圖景。
沈從文接受的正規(guī)教育僅是小學(xué),巧歲便去當兵,大部分時間輾轉(zhuǎn)于湘西。他的知識、教養(yǎng),既非來自學(xué)校,也非來自家庭,而是來自自然。湘西地處沉水辰河流域,下接洞庭湖,自由浪漫的湘楚精神跨越了千年歲月,像流淌不息的河水永不枯竭,滋育、長養(yǎng)著這塊土地上一代又一代的人。文化、生命與自然一道,獲得了超越時間的永恒。正是湘西這種有著雄強生命氣魄和原始生命強力的生活,以別樣的方式闡釋著中國傳統(tǒng)文化中“和諧”的真諦,也使沈從文以最直觀的感知角度在這種傳統(tǒng)文化的熏陶和浸淫下,彰顯著他那有著現(xiàn)代性的創(chuàng)作意識。與廢名受到禪學(xué)影響不同,沈從文更多地受到一種道家藝術(shù)觀念的影響。沈從文未受過系統(tǒng)教育,未從理性層面接受過道家思想,他對自然的推崇源自生命體驗,卻與老子哲學(xué)暗合。他所推崇的不是現(xiàn)代的科學(xué)理性、人道主義,也不是傳統(tǒng)的儒家倫理,而是一種原始的、未經(jīng)規(guī)范的、一切生命都要遵循的一種法則—自然的律令—生長、繁衍、淘汰。這種體驗和影響,是在大自然潛移默化的熏陶中所養(yǎng)成的一種氣質(zhì)秉賦和從自然中悟得的應(yīng)付人事方面的一種智慧。
有了傳統(tǒng)文化的滲人,京派小說家在審美上更契合傳統(tǒng)文化中的“情志合一”的觀念。京派小說中的許多段落,總讓人聯(lián)想起我國傳統(tǒng)的水墨寫意畫,頗能使人體味出幽邃清遠的境界,從它們的氣韻風(fēng)神中探測到作家的內(nèi)心感受和蘊藉風(fēng)流。如《桃園》中的這段描寫:城垛子,一直排,立刻可以伸起來,故意縮著那么矮,而又使勁的白,是衙門的墻;簇簇的瓦,成了烏云,黑不了青天……這簡直就是中國傳統(tǒng)詩歌中常用的意象聯(lián)結(jié)手法,又是一幅淡抹的水墨畫。京派小說家對宗族社會下的田園生活進行回憶與追懷,雖然離開了時代洶涌澎湃的主潮,卻在美學(xué)上與中國傳統(tǒng)文化中的隱逸詩風(fēng)相銜接,體現(xiàn)了另外一種不同于宏大政治化敘事的詩意風(fēng)格。
二、中國傳統(tǒng)文化的轉(zhuǎn)活
京派小說對傳統(tǒng)文化的吸收并不是機械的,而是借助中國傳統(tǒng)文化的豐富資源,結(jié)合現(xiàn)代心理學(xué)、美學(xué)理論,從現(xiàn)代意義上轉(zhuǎn)活了中國傳統(tǒng)文化的生命,因而獲取了現(xiàn)代情境下永恒的美學(xué)魅力。從某種程度上說,京派小說家看到了現(xiàn)代文化不僅不以傳統(tǒng)文化的錯誤和完全消失為前提,反而可能在新的環(huán)境中通過對傳統(tǒng)的重新闡釋和運用來謀求進步,這就是京派小說的特立獨行的現(xiàn)代意義之所在。
傳統(tǒng)文化作為一種歷史現(xiàn)象,是一種靜態(tài)的凝固物。對傳統(tǒng)文化中的某些成分在當代生活中的意義,以及文化傳統(tǒng)對整個民族文化發(fā)展的支配力的清醒估計,使京派小說家有別于“五四”先賢,而具備了長遠而平實的眼光。于是,在追求自由、感悟生命與直視焦慮上,他們開始了長足的探討與試驗,力圖溝通傳統(tǒng)文化與現(xiàn)代觀念,從而在新的維度和向度上再現(xiàn)自己的現(xiàn)代意識。
從古至今,人們對自由的呼喚從來沒有停止過。《詩經(jīng)》中用“關(guān)關(guān)灘鴻,在河之洲”表現(xiàn)對愛情自由的追求,陶淵明用“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的美麗自然景觀再現(xiàn)對自由的渴望和向往。到了現(xiàn)代社會,京派小說家依然用自然這個傳統(tǒng)意象承載著他們對個體自由的向往與追求。自然意象也是中國傳統(tǒng)文化和文學(xué)中的一種主體意象。如南宋詩人翁卷詩云:“綠遍山原白滿川,子規(guī)聲里雨如煙。鄉(xiāng)村四月閑人少,才了蠶桑又插田。”即使在描寫城市生活時,這種對于自然意象的注重也不時泛上詩人的心頭與筆端:“世味年來薄似紗,誰令騎馬客京華。小樓一夜聽春雨,深巷明朝賣杏花。矮紙斜行閑作草,晴窗細乳戲分茶。素衣莫起風(fēng)塵嘆,猶及清明可到家。”這種在這小樓中聽到的春雨聲和深巷賣花聲等,無一不是大自然生命節(jié)奏與農(nóng)耕文化的特有韻律,詩人于此中“悠然自得”,感到了“盎然天趣”。京派小說中也充斥著各種古典的自然意象,如沈從文的大山、月亮意象,蕭乾的籬下、矮檐意象,蘆焚的廢園、荒村意象,李健吾的山村、陷阱意象,林徽因的市井、胡同意象,等等。一方面它們都是中國傳統(tǒng)文化、文學(xué)中的主體意象,這些意象富于東方特色,都可以在《詩經(jīng)》《楚辭》及唐詩宋詞中找到“遠親”,豐富的意境與鮮活的意象是中國傳統(tǒng)文化、文學(xué)的重要特征;另一方面這些意象又都在京派小說家手中得到了創(chuàng)新與改造,最主要的就是它們與小說的主題相和諧,從而具備了鮮明的時代與地域特征,也寄予了他們獨特的現(xiàn)代意識感知。
對于深受本土文學(xué)、哲學(xué)、美學(xué)思想浸潤的京派小說家來說,中國文化對于他們滲人機理的影響比對西方文化的吸收要深,在對生命的感悟上,他們首先感受到的是中國的儒、釋、道哲學(xué)思想的調(diào)和。廢名的小說主要可以見出佛教禪宗思想的影響,他以一顆虔誠的心、一雙欣賞的眼,去觀照大千世界,捕捉或追求一種超越悲哀、睿智達觀、親自然、樂人生的人生境界,在他的敘述中,生命以一種“體悟”的方式得到了自足的意義。沈從文吸取的則是儒家那種積極人世、修身立人的精神和老莊哲學(xué)中追求相對自由觀念和豁達向上的人生態(tài)度,老莊哲學(xué)中那種強化的自然觀念不僅熏染了他看人論世的心靈品格,還被他引入了對現(xiàn)代中國人生的深刻觀照。尤其是其中樸素的生命意識,更是適應(yīng)了他對普通人命運中個體存在不確定性的感受,從而從審美領(lǐng)域中把握善惡并存、苦樂相生交錯的人生世相,達到對生命價值的了悟。在此基礎(chǔ)上,京派小說家又有了對傳統(tǒng)哲學(xué)的轉(zhuǎn)活,他們拋棄了傳統(tǒng)哲學(xué)中消極的人生態(tài)度,看到生命的本質(zhì)規(guī)定遠不至此,還有其超越性的一面,代表一種存在價值與精神取向。對生命價值意義的探求,已經(jīng)深人到對生命超越性意義的訴求,指向生命的終極存在。 由對國事民虞的關(guān)注而感時憂國,本是我國士大夫知識分子習(xí)以為常的精神傳統(tǒng),由于現(xiàn)代中國種種困賽愈演愈烈,“五四”以降,大凡有些責(zé)任感的作家沒有一個不具備憂患的哀感。京派小說家歷來被認為是“遠離政治”的純文化寫作,然而其小說中對社會種種黑暗面的揭露、對被壓迫被侮辱的弱小者的同情、對自由和個性解放的強力呼喚和追求、對人的精神異化的痛貶等等,無一不聯(lián)系著傳統(tǒng)文化中“哀民生之多艱”的精神內(nèi)核。這些都來自于他們對人的生存狀態(tài)的觀察與思考,對自身生存狀態(tài)的省察與慨慰。他們用藝術(shù)化的態(tài)度和現(xiàn)代人的立場來處置現(xiàn)實人生,這與封建傳統(tǒng)中的那種杜甫、李白式的文學(xué)視閡有著相似的內(nèi)涵,卻又有著現(xiàn)代的焦慮觀照。它標志著個性的覺醒,是在“人”的立場和角度燭照和審視蕓蕓眾生,具備著朗然的現(xiàn)代色彩,也讓傳統(tǒng)中的人文精神與現(xiàn)代的焦慮意識有了更好的調(diào)和與融洽。
京派小說家對傳統(tǒng)文化的轉(zhuǎn)活,是對“五四”精神的深人反應(yīng),也是對“五四”形成中國文化斷裂現(xiàn)狀的反思。他們參與揚棄了傳統(tǒng)文化中負面而不合時宜的部分,同時又用現(xiàn)代的觀念、理論為現(xiàn)代文學(xué)增添了一筆鮮亮的色彩。
三、現(xiàn)代性的反思
京派小說中的現(xiàn)代意識由于其中傳統(tǒng)文化的過多外在表征,而在很長時間里不為研究界所重視。而這種現(xiàn)代意識不僅具有較強的現(xiàn)代性,在某種程度上更有對現(xiàn)代性的反思。
由于現(xiàn)代社會轉(zhuǎn)型的落后性和自身文化傳統(tǒng)的撕扯,中國在奔向現(xiàn)代化的艱難征程上一直存在著對現(xiàn)代性的呼喚與反思相互糾纏的現(xiàn)象,那種實現(xiàn)現(xiàn)代化的急功近利心理與對這一突變進程的猶疑和批判心態(tài)同時并存、相互論爭的事實顯示了本土化的中國特色。一方面,“中國的現(xiàn)代性以激進的方式獲取社會化的形式,以斷裂的跳越方式獲得突變”,這種極端化的前行方式耗空了現(xiàn)代性的宏大規(guī)劃,產(chǎn)生了欲速則不達的后果;另一方面,以傳統(tǒng)為參照建立起的對這種極端化的現(xiàn)代性的實現(xiàn)方式進行的批判性反思,也構(gòu)成了中國現(xiàn)代社會轉(zhuǎn)型的重要景觀,成為建構(gòu)中國特色現(xiàn)代性的重要內(nèi)容。因此,這與吉登斯的“現(xiàn)代性的特征并不是為新事物而接受新事物,而是對整個反思性的認定,當然也包括對反思性自身的反思”觀點相一致。汪暉也認為:“對現(xiàn)代性的質(zhì)疑和批判本身構(gòu)成了中國現(xiàn)代性思想最基本的特征。”
京派小說家不是從思想史的角度來反思現(xiàn)代性,而是從審美的角度完成了自己對現(xiàn)代性的認同和批判。他們的小說以含蓄的筆調(diào)暗示了工業(yè)文明的短處而凸顯了農(nóng)業(yè)文明的生命力因素,張揚了以人為本主體性生命反思,迎合了現(xiàn)代人學(xué)的產(chǎn)生和完善,呼喚著現(xiàn)代生命意識的覺醒。同時,他們又把自己的現(xiàn)代生命思索通過傳統(tǒng)詩學(xué)式的意境、意象手法烘托出來,以一種高度精致化的藝術(shù)審美自覺抵制了那種自稱“現(xiàn)代”卻粗鄙不堪的文學(xué)表達方式。
或許弗洛伊德的一段話有助于我們理解京派小說家的這種“現(xiàn)代性”:“個體的自由不是文明的恩賜……在人類集體中,以渴望自由的形式表現(xiàn)出來的東西是人類對現(xiàn)存不公正的反抗,因此,它可能有助于文明的進一步發(fā)展;它可能與文明一致。但是,它也可能產(chǎn)生于人類原始性格的遺跡中,這種性格還沒有被文明所改造;因此,可能成為敵視文明的基礎(chǔ)。所以,對自由的渴望被轉(zhuǎn)到反對文明的特定形式和要求或者徹底反對文明的方向上。從弗洛伊德的敘述中,我們找到了解讀京派小說創(chuàng)作意圖的鑰匙:既然“個體的自由不是文明的恩賜”,現(xiàn)代“人類原始性格的遺跡”中的自由生命形態(tài)遭到破壞,人性受到異化,他們當然有理由通過批判現(xiàn)代文明來建構(gòu)“健全人性”的希臘小廟。
對傳統(tǒng)文化中“和諧”的審美情趣的繼承,是京派小說中最具有反思意義的表現(xiàn)。因為,與和諧相對的沖突與裂散正是現(xiàn)代性的重要特征之一。這種裂散與沖突可以從兩個方面來理解。一是從表面上看,在現(xiàn)代化的過程中,現(xiàn)代社會的流動性帶來不同的信仰、文化觀念和生活方式等系列的碰撞與沖突,不太可能產(chǎn)生出一種統(tǒng)一的世界觀,而是出現(xiàn)了各種不同的個體化和群體化世界觀的多元競爭和相互排斥的局面。正如亨廷頓在談到當今世界文明的沖突時所說的那樣:“全世界的人在更大程度上依據(jù)文化界線來區(qū)分自己,意味著文化集團之間的沖突越來越重要;文明是最廣泛的文化實體;因此不同文明集團之間的沖突就成為全球政治的中心。”二是從社會內(nèi)部構(gòu)造上看,現(xiàn)代社會結(jié)構(gòu)本身就存在著矛盾和裂隙,隨著現(xiàn)代化的日益深化,這種矛盾與裂隙便更加突出。丹尼爾·貝爾的《資本主義文化矛盾》一書認為,正是當代資本主義社會中經(jīng)濟領(lǐng)域的效益原則、政治領(lǐng)域的平等原則、思想領(lǐng)域的自我表達和自我滿足原則本身以及它們之間的對立與分裂,導(dǎo)致了這個社會的無法避免的巨大的文化矛盾。京派小說家正是在現(xiàn)代文明社會中感到了這種由沖突、裂散所帶來的巨大心理緊張,才祭出了傳統(tǒng)文明中“和諧”這一法寶。
從這個意義上說,京派小說非但像一些研究者認為的那樣是落后的、不合時宜的,反而是對中國最盛行的“現(xiàn)代性”的反思。如果說中國的現(xiàn)代性“是一種知識性的理論附加于在其影響之下產(chǎn)生的對于民族國家的想象,然后變成都市文化對于現(xiàn)代生活的想象”,那么,京派小說家則看到了承載著中國現(xiàn)代性想象的都市中人性的委瑣、現(xiàn)代文明對人性的異化,這使得他們對現(xiàn)代性深感憂懼。于是,他們在對這種現(xiàn)代性進行反思的同時,也重塑了民族國家想象。也許這只是針對現(xiàn)實的以進步理性主義為特征的現(xiàn)代性選擇的一種保留姿態(tài)。
社會主義.jp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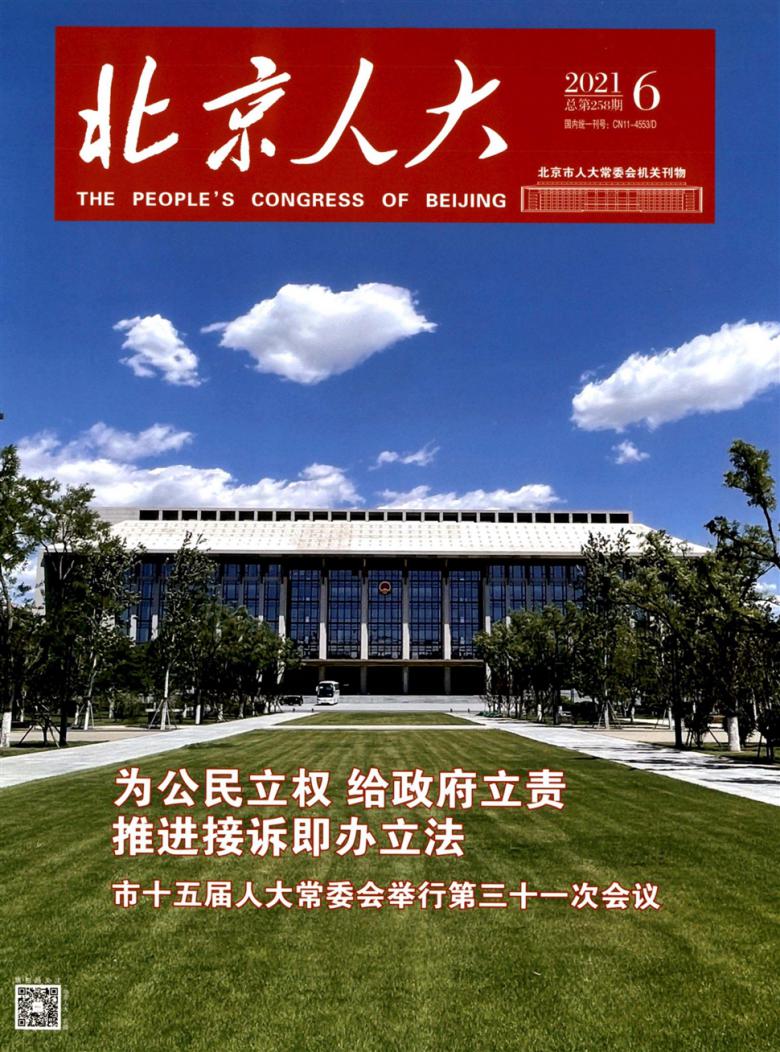

于我們.jpe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