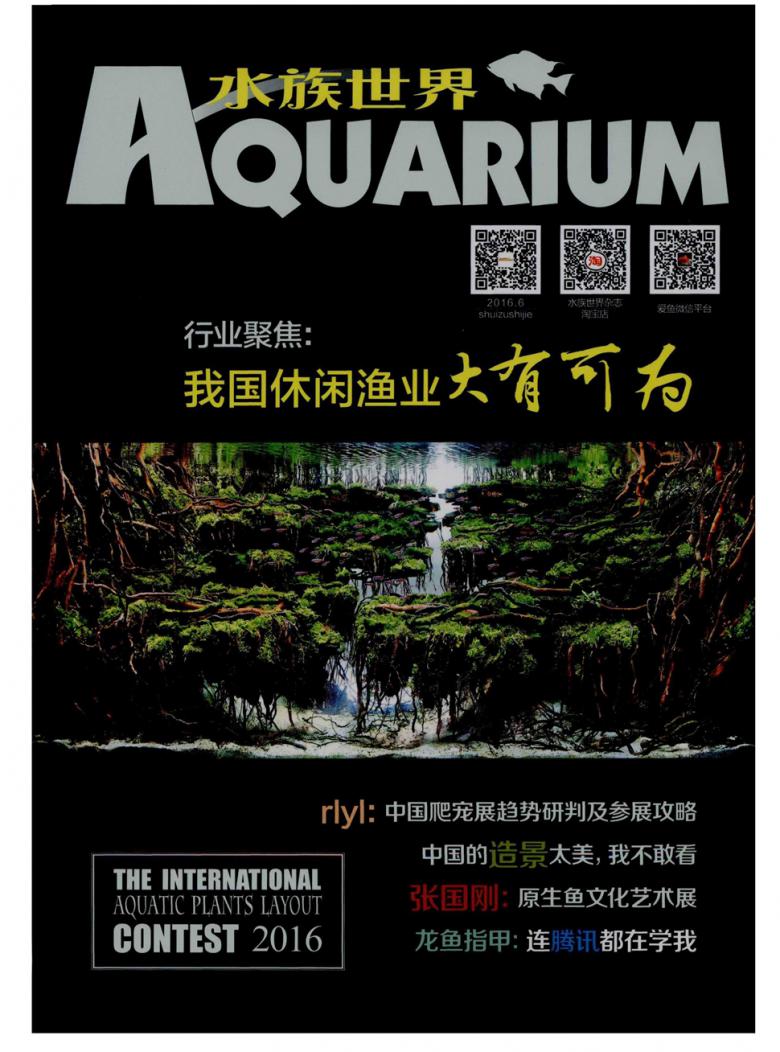淺談中國傳統法律文化的現代化轉型——兼駁傳統文化否定論
李梅
論文關鍵詞:儒家思想;傳統法律文化;現代化轉型
論文摘要:以儒家思想為內核的中國傳統法律文化并非與現代化必然背道而馳。儒家思想在經過清理、改造、轉化之后是能夠與西方市民法文化結合的。中國法律文化現代化應走中西文化結合之路,實現傳統法律文化的現代性轉換,為法治模式的形成培育出適合它成長的文化土壤。
隨著依法治國方略的落實,一系列法律法規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出臺,立法以相當快的速度覆蓋了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已基本形成。但遺憾的是,人們發現對社會關系行使基本職能的仍然是一些傳統的機制,構建起來的法律體系沒有完全融人我們的現實。事實上,早在上個世紀四十年代,曾任民國政府司法顧問的美國法學家龐德就曾告誡中國法律專家不要無限度追求立法層次上的西化,西方法制是有一套功能要件與之配合的。梁治平先生也說道:“因了觀念的不同,一種技術既可能‘物盡其用’,也可能‘形同虛設’。所以歷史上凡割裂兩者,只要技術,全不顧觀念者,沒有不失敗的。”所謂的法律現代化,并不僅僅是法律制度的轉型或法律操作技術的進步,也并非是簡單地向西方國家法律制度認同的過程,在它其間必然蘊含著每個國家在各自的歷史文化視野中的不同價值趨向和模式選擇,也可以說是一個民族在其歷史變遷過程中文明結構的重新塑造川。僅有制度的引進和移植,而缺乏與之相適應的內在條件、社會背景和文化土壤,被引進和移植的制度是很難“存活”的。法律的接受須與中國的內在文化相契合,為此必須對傳統法文化予以準確的定位,處理好本土文化與外來法律資源之間的關系,完成傳統法律文化的創造性轉換。
一、傳統法律文化的定位
中國傳統法律文化以儒家倫理為內核,產生并服務于自然經濟和宗法社會。儒家以“禮”作為基本的社會行為規范,禮的主要功能在于“別貴賤、序尊卑”,漢朝確立儒家的獨尊地位,禮融進了諸子學說中的可取成分,成為“禮教”,并進而成為封建社會統治階級推導立法、司法的原則和理論依據,其要旨即是“三綱”—“君為臣綱,父為子綱,夫為妻綱”,以及由此衍生的“親親”、“尊尊”的政治倫理原理。
“親親”、“尊尊”確立了“尊卑有序、貴賤有別”的宗法等級秩序,使古代法成為等級的、身份的法。“天人合一”的和合倫理,道德教化所產生的“禮讓”則產生厭訟、無訟的傳統。儒家思想為歷代封建統治者發揮至極致,被專制政權所利用,形成所謂的政治文化,成為專制政治的附屬品,喪失了評判、矯正政治現實的功能。有學者由此得出結論,認為“儒家倫理與法治精神格格不人,嚴重阻滯著法治所追求的公平、正義、自由、權利的實現”,甚至認為當前所出現的“道德滑坡、法律松馳、司法腐敗是傳統文化對市場經濟的不適應癥狀”。將當前所出現的社會問題完全歸咎于儒家倫理。恐怕儒家文化背負不了如此之大的罪名。所出現的種種社會問題,誠如費孝通先生所說,舊的制約機制—禮治秩序被打破,新的制約機制未建立。大量權力行使處于真空狀態,法律至上原則落空。這種對儒家文化予以徹底否定的觀點與德國法律社會學家韋伯的理論不謀而合。韋伯認為儒家思想缺乏基督新教的倫理精神,因而不能導致資本主義的發展,而使西方逐步通向現代化道路的“工具理性”則是中國沒有的,這種將儒學與現代化、法治對立起來的觀點從理論上、事實上都是站不住腳的。
從理論上說,即使儒家思想不能孕育出資本主義的大樹,并不能說明它必然與現代化社會絕緣(現代化并不等于西化或資本主義),也不能說明它必然與現代法治精神背道而馳。有事實為證,亞洲四小龍和日本經濟的騰飛就以無可辯駁的事實說明儒家思想與現代化、法治并非水火不容。以新加坡為例,新加坡政府高效廉潔,社會秩序穩定、社會成員文明禮貌。“新加坡在接受西方文明的同時,揚棄了西方文明中可能導致混亂、破壞和諧的一面,轉而從東方文明尤其是儒家思想中發掘出可利用的資源,在西方的科學理性精神中注人了東方的倫理精神和人文內涵。”由此可見,儒家思想并非與現代化必然背道而馳。相反,儒家思想有其積極、合理的因素,儒家思想在經過清理、改造后,能夠轉化為有利的時代精神,達到使傳統與現代,東方文明與西方文明的互動互補。
所謂使儒家文化做創造性的轉化,實際上就是通過對儒學的現代診釋,發掘、弘揚與現代化相協調的思想,批評、避免與現代化相矛盾的思想。
二、儒家文化的現代性意義
在談到傳統儒家文化的現代性意義時,我們先對中西方法文化進行簡單的比較。
西方法文化可以說是一種市民法文化,它把一切人際關系統統視為市民關系,視為契約的產物,這種冷冰冰的契約在帶來平等、權利的同時在一定程度上導致了西方社會人際關系的冷漠、親情的淡漠。追求自由、個性張揚的個人主義在促進社會進步、個人潛質的發揮同時,也帶來貧富懸殊,對環境的破壞和向外擴張的侵略意識,對人權的過分保護,則導致對犯罪的控制力度減弱,司法效率有限甚至低下,犯罪猖撅。
再來看中國傳統的法律文化,如上文所說,傳統法文化是禮治文化,倫理文化,將一切人際關系視為家人,親屬之間的關系。家國一體,天理、國法、人情三者相通。“親親尊尊”是其核心原則。“親親”要求在家族范圍內,人人皆要親其親,長其長,做到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夫義、婦聽,“親親父為首”全體家庭成員以父家長為中心。“尊尊”即要在全社會范圍內尊敬一切應該尊敬的人,君臣、上下、貴賤應倍守名分,一切臣民應以君主為中心,即所謂“尊尊君為首”。 “親親尊尊”的確是對等級秩序的維護,但它也有重視親情、重視家庭的一面,只要將它限制在合理的限度內,不把它發展為“親親得相首匿”、“以親害疏”,“君為臣綱、父為子綱”、“夫為妻綱”它是積極的。“親親尊尊”強調親屬之愛的崇高性、正當性,反對以物欲害親情,主張國家政治應像家庭生活一樣有人情味,主張給人們更多的保護親屬的權利,主張責成人們以更多的敬愛親屬的義務,這種思想在當今物欲橫流的社會,是有其積極意義的。
再來看儒家思想中的“天人合一”觀。“天人合一”講究“和為貴”,不尚爭斗,強調整體的和諧甚于一切,法律的尊嚴服務于“天人合一”的整體利益,認為為自己或他人的公正而斗爭是直接與一種自然的、道德的人生態度相對立。因為這一行為破壞了關于自然和諧的假設,仁慈和謙恭作為處理人際關系的合宜手段,造成了無訴的價值取向和忍讓、屈從、不尚爭斗的民族性,但是同樣的只要不將“天人合一”夸大至極端,而只取其合理的一面或賦予其新的含義,是可取的。“天人合一”將人、自然、社會作為一個整體來看待,保持人與社會、自然的和諧,這對維護社會的統一與穩定,具有不可忽視的內在價值。只要不把“天人合一”解釋為為了和諧而無限度犧牲個人正當權益,不把“仁慈、謙恭”變為無條件的忍讓、曲從,而把它控制在一定的度內,它是合理的,自由是法的目標,和諧、秩序也是法的基木價值。
儒家思想也注重修身養性、道德教化,其目的在于塑造圣人般的理想人格,由“內圣而開外王”,如孟子所言“窮則獨善其身,達者兼濟天下”,但對內在道德過分偏重則走向了泛道德主義的極端。傳統文化中對于人的內在德性的要求是應予積極肯定的,但要防止將道德的作用無限擴大,避免使法律和道德的關系錯位,只要將道德的作用限制在合理的限度內,對德性的要求不是寄望于成圣成賢,而是做一個誠信的人,有獨立品格的人,具備仁義、智慧等良好品性的人,那么儒家的修身養性在法治社會中是有現實意義的。畢竟“徒善不足以為政,徒法不足以自行”,沒有道德力量的支撐,沒有自律的充分保障,法律會成為單純的規范形式而失去生根的基礎。在市場經濟社會中,對利益最大化的追求,意志薄弱者難免利令智昏,注重理想人格塑造的儒學可以作為人們的清醒劑,在一定程度上以獨特的方式對人們行為予以引導、制約,彌補法律調整的不足,實現社會控制手段的互補。
通過對中西法文化的比較,我們可以發現西方市民法文化與中國倫理法文化是各有優缺的。儒家倫理在經過改造、轉化之后,在不犧牲法治的根本價值前提之下,可以矯西方文化之偏,建成“溫馨而理性的法治模式”。中西法文化的結合,應當是中國法律文化的現代化之路。
三、出路
在對待法律文化的態度上,有學者指出“建設法治國家的當務之急是文化改良,回歸‘五四’,完成‘五四’未竟之業’。誠然,五四愛國運動有其歷史意義,但五四時期的知識分子將民族屈辱和國家的落后歸罪于儒家思想,提出“打倒孔家店”,主張全盤西化,但并不如五四先哲預期那樣,全盤西化之路實際上是一條畸型之路,我們摒棄了本身優良的一面,但卻不自覺地保留了壞的一面,我們吸收了西方最表面、最膚淺及最劣質的一面,卻沒有攝收最深層和最優秀的一面,如仿效西方民主選舉形式,卻沒有法治的基礎及其它機制去約束操縱選舉行為。
正如前文所述,西方文化并非十全十美,西方社會如今也面臨著嚴重的社會問題:如槍支泛濫、人格分裂,暴力犯罪、吸毒等,“西方也沒有解決中國問題的‘靈丹妙藥’,因為它自己也陷人深刻的思想貧困之中”。西化之路行不通,除了西方文化也存在缺陷之外,還在于“設計得再完美的體制和程序,如沒有傳統力量的支持,就難以有效運轉,甚至難以為繼”新法制如沒有中國特色,是很難真正在中國有效。中國的傳統法律文化是中國實現法治的根基,輕視或否定自己文化根基是悲慘的事。
我們不能徹底否定自己的文化根基,但也不能走“中體西用”的老路子。“中體西用”不是以科學、理性和發展為標準去評價和取舍外來文化,而是以自己的傳統為參照系,以維護傳統為宗旨來對待外來文化,是狹隘的民族優越感滋生出來的盲目排外心態的表現,是自己政治上和經濟上脆弱無能的表現。“體用論”最終導致的是中國法文化傳統依然故我,新瓶仍然裝著陳酒。
近年來有文化界學者提出“西體中用”的觀點,這并非標新立異,我看倒是頗有借鑒意義的,法治畢竟是在西方文化的背景之下產生的。其實,新加坡實際上也是走的“西體中用”之路,新加坡與日本、韓國不同,“是在沐浴西風法雨洗禮,已經奠定了現代法治的理性基礎,認識了西方‘普世性’文明的缺陷之后,再來尋求和選擇儒家文化的,所處時代和歷史進程不同,使新加坡有條件對博大精深的儒家文化進行‘切片’選擇,取精剔糟,避免了中國、日本和韓國因歷史局限全盤浸潤儒家文化所因襲的重負。而在日本以儒家文化為內在基礎的西化法律體系,在結構和功能上存在深刻矛盾,韓國也由于儒家文化遺產的負面效應,在現代轉型中比新加坡艱難得多,新加坡模式對如何實現儒家文化的現代轉型,如何實現中西文化的會通整合給予我們以極大的啟示。
總之,對以儒家倫理為內核的中國傳統法律文化不能予以徹底否定,它并非全是糟粕謬誤,而是精蕪并存的。在經過清理、改造、轉化之后是能夠與西方文化結合的,通過法文化持續不斷的選擇與整合,促進傳統法律文化的現代型轉換,創造新的法律文化體系,為法治模式的形成培育出適合它成長的文化土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