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重復困境中的敘事反思——在《狂人日記》到《長明燈》之間
羅華
【內(nèi)容提要】 本文以《狂人日記》和《長明燈》為中心,考察在作為文化時間范疇的1918年到1925年,魯迅深陷于文化重復之困境,如何借助于小說敘事進行反思以擺脫這一陰影,從中獲得個人經(jīng)歷的反省。本文的討論從三方面展開:一是知識分子的社會位置與行動策略的轉(zhuǎn)換;二是從觀念性表述到在世俗化生活圖景下的深度追問與思考;三是對知識分子先驅(qū)者不同的命運、抉擇及其意義的認識。本文認為在《狂人日記》和《長明燈》之間不但具有明顯的差異性,而且還存在著動態(tài)的意義空間。
在魯迅小說研究中,《狂人日記》的重要性無庸置疑,“短短五千字,……開啟了一代作家敘述中國、重寫歷史的契機”①。《長明燈》則不但不為學界所看重,還常被簡化為《狂人日記》的一個復本,這樣一種認知結(jié)果,不僅導致《長明燈》被誤讀,而且也遮蔽了在《狂人日記》到《長明燈》之間可能存在的有意味的內(nèi)涵。
《狂人日記》寫于1918年4月,《長明燈》寫于1925年3月,其間相距七年。這七年,如果僅僅從物理的時間去考量,似乎意義不大。但如果同作為文化范疇的時間聯(lián)系起來,問題就產(chǎn)生了。像魯迅這樣的作家,要在七年后再來作一篇似乎類似的小說表達七年前似乎就已經(jīng)表達得相當充分的內(nèi)容,總有其特別的緣由。推想開來,恐怕有兩種可能:一是魯迅陷于文化重復的困境,需要借助于對問題的重新思考擺脫這一陰影;二是在問題反省中個人經(jīng)驗斷裂的敞開,即個人對自身經(jīng)歷和遭遇的反省,這種經(jīng)歷和遭遇是在問題意識的背景上被反身觀照著。這樣一來,《狂人日記》和《長明燈》不但具有明顯的差異性,而且在《狂人日記》到《長明燈》之間還存在著動態(tài)的意義空間。
1918年到1925年,就中國社會狀況而言,仍是處于“城頭變幻大王旗”的混亂之中,黑暗力量的相互沖突和交替構(gòu)成了社會政治關系的主流。就文化環(huán)境而言,新思想與舊傳統(tǒng)的對立實際上也只囿于部分知識分子的圈子中,并未形成廣泛的社會性氛圍,正如魯迅的“鐵屋子”理論所言,沉睡的是多數(shù),清醒的是個別。而作為“中國文化史上一場真正意義上的、大規(guī)模的文化沖突”的新文化運動,雖然給人們提供了一種對傳統(tǒng)文化的全新認識,并開
始了總體性和自救性的理性批判,但也存在著一個致命的弱點——“啟蒙性思索的短促”②,從而導致其對彼時的社會思想和文化思潮影響的有限性,在某種意義上說,其影響力甚至是在多年以后才被人們?nèi)找嬲蔑@的。
這七年,在魯迅生命中卻是一個相當特殊的時間段落,人生的大起大落,最輝煌與最絕望一起呈現(xiàn)。梳理這一時間段落,的確耐人尋味:一方面,魯迅從一個默默無聞的教育部的小官員成為新文化運動的著名人物,事業(yè)的成功不但成就了魯迅用文學啟蒙救國的人生理想,而且?guī)砹藗€人地位的急劇提升,使年已38歲的魯迅從生命的低谷躍至生命的高峰,雖然在這一過程中,其內(nèi)心仍有所懷疑,但那種“夜獨坐錄碑,殊無換歲之感”③的絕望畢竟已被“歷觀國內(nèi)無一佳象,而仆則思想頗變遷,毫不悲觀”④的亢奮所替代,可見魯迅當時精神上的愉悅和滿足。毫無疑問,這是魯迅人生的一大轉(zhuǎn)折,此后世事流變,文學活動不僅是魯迅的生存方式,也是其生命的核心。
但另一方面,魯迅在這一時期又多次遭受精神重創(chuàng)。其中之一是1921年《新青年》同人的疏離、分手,這對魯迅的打擊尤為沉重。魯迅在1922年底所作的《〈吶喊〉自序》中,情不自禁地流露出又一次陷于“寂寞”、“無聊”、“悲哀”中的絕望感。甚至在事隔十年后,這種“荷戟獨彷徨”的悲涼仍未忘懷,1932年,魯迅在《〈自選集〉自序》中,慨嘆當時的情景:
后來《新青年》的團體散掉了,有的高升,有的退隱,有的前進,我又經(jīng)驗了一回同一戰(zhàn)陣中的伙伴還是會這么變化,并且落得一個“作家”的頭銜,依然在沙漠中走來走去,……新的戰(zhàn)友在那里呢?⑤
漸入晚年的魯迅,對于“成了游勇,布不成陣了”的精神狀態(tài)的描述,讓我們不難推想其當年內(nèi)心的巨大創(chuàng)痛。“依然在沙漠中走來走去”的感慨唏噓,既是對當年社會現(xiàn)實和文化氛圍的評價,也是對當年自身處境的評價。
而《寫在〈墳〉后面》的一段話,則是更直接地反思新文化運動:
記得初提倡白話文的時候,是得到各方面劇烈的攻擊的。后來白話漸漸通行了,勢不可遏,有些人便一轉(zhuǎn)而引為自己之功,美其名曰“新文化運動”。又有些人便主張白話不妨作通俗之用;又有些人卻道白話要做得好,仍須看古書。前一類早已二次轉(zhuǎn)舵,又反過來嘲罵“新文化”了;后兩類是不得已的調(diào)和派,只希圖多留幾天僵尸,到現(xiàn)在還不少。⑥
五四新文化運動的起伏,對魯迅而言,又一次強化了他對于歷史經(jīng)驗的悲劇性的重復感與循環(huán)感。事實上,魯迅每一次用進化論觀照現(xiàn)實生活時,結(jié)果卻往往是證實了循環(huán)論的存在。所以,魯迅雖然接受了進化論的思想,并由此獲得一種強有力的精神支柱,但傳統(tǒng)的循環(huán)論觀念像幽靈附體,面對表面上風波迭起,骨子里卻一切照舊的社會現(xiàn)實,不可避免地深陷文化重復之困境,“歷史的演進仿佛不過是一次次的重復、一次次循環(huán)構(gòu)成的,而現(xiàn)實——包括自身所從事的運動——似乎并沒有標示歷史的進步,倒是陷入了荒謬的輪回”⑦。這種深陷文化重復之困境所引發(fā)的內(nèi)心的絕望感,就其強度和深度而言甚至超過S會館時期。本文正是在這一背景下,以《狂人日記》和《長明燈》為中心,討論魯迅在文化重復困境中的敘事反思。
一 從中心到邊緣
《狂人日記》和《長明燈》的確有許多相似之處,比如都表達了對封建傳統(tǒng)的抨擊和否定,都表現(xiàn)了作為個體的知識分子因為自覺承負社會批判和文化批判的職責,而被庸眾視為“異類”,并在與庸眾的尖銳對立中處于被囚禁的地位。
但我所發(fā)現(xiàn)的一個問題是,從《狂人日記》到《長明燈》,狂人和瘋子在文本敘事中“位置”的變化。也就是說,狂人和瘋子雖然同是拒斥封建權力話語系統(tǒng)的“精神界之戰(zhàn)士”,但在文本敘事中表述為從中心向邊緣的位移。
這種變化,就其敘事表征而言,表現(xiàn)在人物言說姿態(tài)和心理狀態(tài)的差異。在《狂人日記》中,魯迅把狂人的十三則日記置于小說的主體性位置,作為一種敘事策略,追求最大限度的現(xiàn)場效果,狂人以居高臨下的姿態(tài)隨心所欲地進行著獨白式的宣言,張揚啟蒙者悲天憫人的情懷和獻身的激情,其極端的言論充分傳達出自我的期待,痛快淋漓的言說幾乎淹沒了庸眾的聲音。甚至面對那些“想害我”的眼光,狂人也極自信地認為“他們怕我”:
……早上小心出門,趙貴翁的眼色便怪:似乎怕我,似乎想害我。……但是小孩子呢?那時候,他們還沒有出世,何以今天也睜著怪眼睛,似乎怕我,似乎想害我。
……我大哥引了一個老頭子,慢慢走來;他滿眼兇光,怕我看出,只是低頭向著地,從眼鏡橫邊暗暗看我。⑧
但是,在《長明燈》中,瘋子已經(jīng)喪失了這一中心地位而趨于邊緣化。其斷斷續(xù)續(xù)的言說已經(jīng)難以構(gòu)成小說的主體,在庸眾的雜語喧囂中,瘋子的“熄掉他罷”、“我放火”只是“一種微細沉實的聲息”。瘋子不但不再是慷慨陳詞的英雄,反而成為被戲弄被審判的對象:
……(瘋子)短的頭發(fā)上粘著兩片稻草葉,那該是孩子暗暗地從背后給他放上去的,因為他們向他頭上一看之后,就都縮了頸子,笑著將舌頭很快地一伸。……
“我想:倒不如姑且將他關起來。”
“那倒也是一個妥當?shù)霓k法。”四爺微微地點一點頭。“妥當!”闊亭說。
“那倒,確是,一個妥當?shù)模k法。”老娃說,“我們,現(xiàn)在,就將他,拖到府上來。府上,就趕快,收拾出,一間屋子來。還,準備著,鎖。”⑨
這一變化意味著什么?在我看來,它意味著魯迅對作為個體的知識分子現(xiàn)實處境和生存狀態(tài)的重新審視,對其價值和作用的重新思考,并將這一審視和思考同對社會文化問題的探索加以結(jié)合。
無論是中國古代的“士為萬民之首”,還是西方近代的“知識分子是社會的良心”,都把知識分子看成社會的棟梁,民眾的導師。“五四”一代人深受這些觀念的薰陶,當他們以居高臨下的態(tài)度發(fā)動新文化運動時,潛意識里難免以救世主自居。魯迅也是如此⑩。況且做“振臂一呼應者云集的英雄”本來就是魯迅的夢想(雖然其多次自認為“決不是一個振臂一呼應者云集的英雄”),只是這夢想的實現(xiàn)一直未有機會,而五四新文化運動在客觀上所營造的時代氛圍,喚醒了那不能忘卻的夢,使魯迅借助于《狂人日記》中的十三則日記完成了書寫英雄的欲望。雖然這“英雄”有些荒誕,如王德威所論,魯迅“讓他的狂人寫下日記,并以其見證古中國的頹廢與恐怖。所有的詩書禮教不過是偽善的門面,所有的倫常綱紀其實是壓迫的借口。一場人吃人的盛宴已經(jīng)開了四千年還散不了席。在死亡的陰影下,狂人不斷地寫著,妄想用文字銘刻他的發(fā)現(xiàn)”11。但狂人畢竟成為魯迅理想中的“作至誠之聲,致吾人于善美剛健者”,“作溫煦之聲,援吾人出于荒寒者”的“精神界之戰(zhàn)士者”,以其“先覺之聲”,“破中國之蕭條”12。
但是,到了20世紀20年代中期,現(xiàn)實生活的接連不斷的教訓,逼著魯迅質(zhì)疑知識分子先驅(qū)者的中心地位,當他以強烈的自我意識來審視現(xiàn)實問題時,就不能不清醒地認識到,政治權力和意識形態(tài)的高壓,使作為個體的知識者以各種方式或自覺或被迫地退至社會邊緣。暴力和壓制,必然地剝奪知識分子先驅(qū)者的言說權,魯迅對這種“言說的無效”的絕望感是如此強烈,甚至說出這樣的話:“我現(xiàn)在愈加相信說話和弄筆的都是不中用的人,無論你說話如何有理,文章如何動人,都是空的。”但是,魯迅接著又說:“然而,世界豈真不過如此而已么?我要反抗,試他一試。”這未一句的“反抗”,魯迅確認為“是與黑暗搗亂”,而非“為了希望光明的到來”13。如何“與黑暗搗亂”?當“言說”不再有效時,行動是否更有意義。就像《過客》中的“過客”,“向前走”是其唯一的動作和目的。因此,在《長明燈》中,處于被定義、被監(jiān)護、被規(guī)定的邊緣化地位的瘋子,以“熄掉他罷”為唯一的目的,以“吹熄”、“我放火”為動作。他很清醒,懷疑一切掩飾、粉飾的話語,拒絕樂觀,知道燈“熄了也還在”,但仍執(zhí)著于行動,“我只能這么姑且辦。我先來這么辦,容易些。我就要吹熄他,自己熄!”小說賦予了人物主體的“動作”實踐以一種絕對的意義,使其成為既是思想者,也是踐行者。
這樣,從《狂人日記》到《長明燈》,不僅表述了個體知識分子從中心到邊緣的位移,同時也是從“思想”到“行動”的轉(zhuǎn)化,亦即魯迅對個體知識者的“知”與“行”的重新審察和重大調(diào)整,不僅追求思想的自由,更強調(diào)主體的動作、實踐的意義。
二 從觀念到世俗
這兩部小說都具有象喻性,《狂人日記》十三則日記,以“吃人”為象征,《長明燈》以“熄燈”為象征。但在敘事的策略上,各各不同。《狂人日記》對社會文化的探索和批判是主觀化、論辯式的,是精神層面的形而上的思辨之直接傳達,小說的敘事完全是“由一先導觀念統(tǒng)帥”14;《長明燈》則把這種探索和批判化為世俗生活圖景,是形而下的敘述,但又不是一般性的敘述,而是通過世俗生活圖景,在人的日常生活的場景與細節(jié)的背后,對人的存在、人性的存在、人與人的關系進行深度追問與思考,把現(xiàn)實的痛苦和黑暗提升到形而上的層面。在我看來,作為一種詩性活動的小說敘事,《長明燈》對生活的表述更感性、情感更復雜、思考更豐富。
我們不妨選擇幾個比較有代表性的問題加以考察。
首先,在魯迅小說中,家族血親關系是魯迅反省人性的一個重要視角,《狂人日記》和《長明燈》也不例外。不過,《狂人日記》中,被狂人認定為“吃人者”的大哥在某種程度上是一個相當概念化、臉譜化的人物,小說對他的描寫無非是“只是冷笑”、“眼光兇狠起來”、“忽然顯出兇相”等等,作為封建禮教、家族制度的功能性符號,簡化而直觀。而《長明燈》中對四爺(瘋子的伯父)的敘述卻復雜得多:
(四爺)捋著上唇的花白的鲇魚須,卻悠悠然,仿佛全不在意模樣。說,“這也是他父親的報應呵。……”
“真是拖累煞人!”四爺將手在桌上輕輕一拍,“這種子孫,真該死呵!唉!”
……“我家的六順,”四爺忽然嚴肅而且悲哀地說,聲音也有些發(fā)抖了。“秋天就要娶親……。你看,他年紀這么大了,單知道發(fā)瘋,不肯成家立業(yè)。舍弟也做了一世人,雖然也不大安分,可是香火總歸是絕不得的……。”
“六順生了兒子,我想第二個就可以過繼給他。——但是別人的兒子,可以白要的么?”
“這一間破屋,和我是不相干;六順也不在乎此。可是,將親生的孩子白白給人,做母親的怕不能就這么松爽罷?”
“我是天天盼望他好起來,”四爺在暫時靜穆之后,這才緩緩地說,“可是他總不好。也不是不好,是他自己不要好。無法可想,就照這一位所說似的關起來,免得害人,出他父親的丑,也許倒反好,倒是對得起他的父親……。”
在我看來,這是魯迅敘述中國家族黑暗和血親關系冷酷的最生動的文字之一,那幸災樂禍的冷漠,陰毒的詛咒、堂皇的借口下包藏著的居心叵測,貪婪和虛偽,無一不表達著人性的陰暗和卑劣。世俗化的敘事是魯迅童年記憶的心理積淀,也是對世俗人情的深刻透視,更是對封建禮教和家族制度下人性異化的文化反思。
其次,世俗生活敘述中對“偽士”的批判性反思。魯迅在《破惡聲論》里,曾提出“偽士”的概念。指出“偽士”的主要特點:一是這類人本身為“無信仰之士人”,既為沒有信仰的知識分子,但又“以他人有信仰為大怪,舉喪師辱國之罪,悉以歸之”,要使出一切手段扼殺別人的信仰,因此常以正統(tǒng)、惟一正確自居,既用“偽信”掩蓋自己的無信仰,又以此來壟斷信仰。二是本質(zhì)上“精神窒塞,惟膚薄之功利是尚,軀殼雖存,靈覺且火”,但又“時勢既遷,活身之術隨變,……摯維新之衣,用蔽其自私之體”15。“偽士”們最慣用的手法是“瞞”和“騙”。因為善于在迎合權勢的同時迎合大眾,在迎合傳統(tǒng)的同時迎合時髦,所以他們在任何時候都能占據(jù)社會文化的主流地位。在某種意義上,“偽士”正是中國社會文化體制的產(chǎn)物16。《狂人日記》和《長明燈》中,與狂人和瘋子形成文化沖突的知識分子正是這樣的“偽士”。從《狂人日記》的大哥、何先生到《長明燈》的三角臉、方頭、闊亭、莊七光、郭老娃、四爺,他們都被魯迅一一加以勾畫。但在《狂人日記》中,魯迅似乎來不及對“偽士”作藝術化的構(gòu)思,因而大哥、何先生的形象顯得過于粗疏。《長明燈》中的“偽士”則傳神入化。比如四爺之類,表面上以真理闡釋者自居,實質(zhì)是要尋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特別是三角臉、方頭、闊亭、莊七光之流,是典型的既迎合權勢又迎合大眾,既迎合傳統(tǒng)又迎合時髦的“偽士”。這些所謂的“以豁達自居的青年人”,不過是以“不拘禁忌地坐在茶館里”為時髦,魯迅不惜筆墨反復描摹他們的世俗畫像:
方頭和闊亭在幾家的大門里穿梭一般出入了一通之后,吉光屯全局頓然擾動了。
闊亭和方頭以守護全屯的勞績,不但第一次走進這一個不易瞻仰的客廳,并且還坐在老娃之下和四爺之上,而且還有茶喝。
面對瘋子的行為,他們儼然是“正統(tǒng)”的維護者,先要“除掉他”,再要“送忤逆”,恐嚇威脅之余,又施以“瞞”利“騙”:
“你還是回去罷!倘不,你的伯伯會打斷你的骨頭!燈么,我替你吹。你過幾天來看就知道。”……
“的確,該死的。”闊亭抬起頭來了,“去年,連各莊就打死一個:這種子孫。大家一齊動手,分不出打第一下的是誰,后來什么事也沒有。”
(方頭說)“我想:倒不如姑且將他關起來。”
在與封建權力者的合謀中,他們是排斥和壓制異己最積極和最陰險者,是“獅子似的兇心,兔子似的怯弱,狐貍似的狡猾”。正如魯迅所論及,“在壞了下去的舊社會里,倘有人懷一點不同的意見,有一點攜貳的心思,是一定要大吃其苦的。而攻擊陷害得最兇的,則是這人的同階級的人物。他們以為這是最可惡的叛逆,比異階級的奴隸造反還可惡,所以一定要除掉他”17。這類“偽士”形象的創(chuàng)造,是魯迅進行敘事反思的重要成果,不僅是對進化論的自覺顛覆,也是在小說敘事中對偽知識分子的有效清理。
其實,“偽士”形象在魯迅其它小說中時有出現(xiàn),如《阿Q正傳》的假洋鬼子、趙秀才等,但都不如《長明燈》中的刻畫更豐富、更深刻。
第三,從《狂人日記》“救救孩子”的呼號,到《長明燈》結(jié)尾孩子們的歌謠,也是一個有意思的變化。關于“救救孩子”,有人認為,它“意味著對含混著地獄和天堂氣味的‘中間物'的否定,這種否定同時包涵了對整個傳統(tǒng)的最徹底的摒棄和對光明未來的最徹底的歡迎”18。也有人認為“這呼聲其實充滿反諷”19,魯迅自己則反思,“現(xiàn)在倘再發(fā)那些四平八穩(wěn)的‘救救孩子'似的議論,連我自己聽去,也覺得空空洞洞了”20,還是魯迅說得徹底,“空洞”。因為只是一種先在的觀念傳達,而且這觀念很容易在文化重復的困境中被不斷追問、受到質(zhì)疑,如何“救”?可能性?可行性?結(jié)果?諸如此類。事實上,我們在《長明燈》里,看到“救救孩子”的呼聲已化為了一群孩子嘲笑瘋子的行動與歌謠:
一 個赤膊孩子擎起他玩弄著的葦子,對他(指瘋子——引者注)瞄準著,將櫻桃似的小口一張,道:“吧!”
這個細節(jié)在小說中幾乎是重復地出現(xiàn)了兩次,除此,小說還不厭其煩地敘述孩子們將瘋子的“我放火”變成“隨口編派的歌”“笑吟吟地”“合唱著”,這樣的敘述顯然意味深長,雖然,孩子們的行為是無目的的,但唯其天然的敵意和凌弱的本性才更可怕,這天真背后的殘忍讓人不寒而栗。這些正在和將要被封建的文化價值觀所同化的孩子們,最終完全可能成為“吉光屯居民”中的一員。這就是社會世俗生活的真實,而這“真實”在小說中的表述,恰恰是魯迅對“救救孩子”的并不樂觀的注釋和反思。
三 從放棄到堅守
對“先驅(qū)者的命運”的思考幾乎貫穿了魯迅的一生。這一思考主要具有兩個指向,一是先驅(qū)者所賴以生存的外在的文化環(huán)境。魯迅早在《文化偏至論》和《摩羅詩力說》中就指出,在“同是者是,獨是者非,以多數(shù)臨天下而暴獨特者”21的社會里,先驅(qū)者“死守真理,以拒庸愚,終獲群敵之謚”22。此后,魯迅又在很多文章里反復地談到先驅(qū)者“要救群眾,而反被群眾所迫害”23的悲劇。因此,知識分子先驅(qū)者是始終處于“以眾虐獨”的文化境遇,承負“獨戰(zhàn)多數(shù)”的歷史宿命。二是先驅(qū)者內(nèi)在的精神世界。也即先驅(qū)者在如此黑暗的文化環(huán)境中能否堅守個人的獨立精神和自由思想,在與封建傳統(tǒng)、政治權力和庸眾意識的曠日持久的絕望反抗中,像曠野里的“過客”,為“永遠探索”的聲音所召喚,永遠在“走”。
應該說,《狂人日記》和《長明燈》亦滲透著魯迅的這一思考。這兩部小說,都有一個共同的意象——囚禁24,即狂人和瘋子處于身體與精神的雙重囚禁之中,這所謂的雙重囚禁,前者是指他們的身體或被囚于祖屋或被囚于社廟,后者是指他們精神上的被敵視被圍剿被撲殺。魯迅有意要把人物置于這一境遇中進行敘述,使小說中的象征性意象不但暗示了知識分子先驅(qū)者的生存狀態(tài),而且使先驅(qū)者對自身命運與結(jié)局的選擇成為某種必然。
我們在這兩部小說中看到了選擇的結(jié)果是不同的。《狂人日記》文言小序所述,狂人的結(jié)局是“已早愈,赴某地候補矣”,通常這被認為是知識分子先驅(qū)者對封建體制的歸附,對政治強權的屈服、對現(xiàn)實生活的調(diào)和與妥協(xié)而導致自我精神的異化。實際上,這也是對作為先驅(qū)者的信仰與責任的“放棄”。這種“放棄”在魯迅此后的小說中以各種不同的方式出現(xiàn),比如《在酒樓上》的呂緯甫是以“做無聊的事”和“敷敷衍衍”表達了“放棄”,而《孤獨者》中的魏連殳則是用以毒攻毒的報復表達了“放棄”。在我看來,文言小序中“至于書名,則本人愈后所題”并非閑話,魯迅特別強調(diào)了“愈后所題”,他要暗示什么?“愈后”的狂人如何評價狂態(tài)時的所言所行、所思所感?是對狂態(tài)的否定,抑或是面對“放棄”的自嘲。不過有一點是肯定的,狂人“放棄”前后的心理過程在小說中是一個空白,如果可以作一想象的話,這過程倒是借助于《在酒樓上》和《孤獨者》進行了補白。
但在《長明燈》里,小說的結(jié)尾是,被囚于社廟的瘋子“一只手扳著木柵,一只手撕著木皮,其間有兩只眼睛閃閃地發(fā)亮”,說著“我放火!”這是一種堅守的姿態(tài),魯迅是把瘋子當作了“不問成敗而要戰(zhàn)斗的人”25,即便失去了行動的自由,仍然堅持思想的獨立,從而把“無路可走”的境遇中的“絕望反抗”作為個體無可逃脫的歷史責任,把義無反顧地執(zhí)著于現(xiàn)實抗爭作為人的生存的內(nèi)在需要。這種持相當明確的堅守姿態(tài)的人物在魯迅的小說中并不多見。魯迅在介紹《彷徨》時曾說:“技術雖然比先前好一些,思路也似乎較無拘束,而戰(zhàn)斗的意氣卻冷了不少。”26我尤其注意到魯迅所謂的“戰(zhàn)斗的意氣卻冷了不少”的自我評價,不管這“戰(zhàn)斗的意氣”是指啟蒙的動機,還是指被“前驅(qū)者”所激發(fā)的熱情,總之,在“冷了不少”的心態(tài)下仍能創(chuàng)造出瘋子這一形象,其意義和價值非同一般。有必要指出的是,在完成《長明燈》后僅隔一天,魯迅就寫了《過客》,最末的一句是:“我只得走。我還是走好罷……。”27再聯(lián)系寫于《長明燈》前后的《在酒樓上》和《孤獨者》的結(jié)尾:“我獨自向著自己的旅館走,寒風和雪片撲在臉上,倒覺得很爽快。”28“我的心地就輕松起來,坦然地在潮濕的石路上走,月光底下。”29這些都與《長明燈》形成了某種呼應,可見魯迅對這一堅守姿態(tài)的不斷強化的心理認同。
值得思考的一個問題是,為什么寫于1918年新文化運動高潮的“吶喊”期的《狂人日記》將狂人送入了放棄信仰,歸順舊體制的行列,而寫于1925年魯迅生命“彷徨”時期的《長明燈》反而出現(xiàn)了不問成敗,堅守信仰的瘋子?如果說,前者在事實性的希望背后是信念式的絕望,那么后者則在事實性的絕望背后卻是信念式的希望,這看起來不合邏輯的生命敘事緣由何在?畢希納認為,每個人都是一個深淵。因而每個人都將面對自己的深淵,不斷泯滅和不斷認可的私人痛楚與經(jīng)驗。事實上,魯迅終其一生都在“常覺得惟‘黑暗與虛無'乃是‘實有'”與“終于不能證實:惟黑暗與虛無乃是實有”之間掙扎。“中國大約太老了,社會上事無大小,都惡劣不堪,像一只黑色的染缸,無論加進什么新東西去,都變成漆黑”,這是魯迅所認定的事實,“可是除了再想法子來改革之外,也再沒有別的路”30,這是魯迅所持有的信念,不過這一信念卻是經(jīng)過了新文化運動的起伏之后,魯迅在文化重復的困境中,通過一種歷史和個人記憶的延展、深化,達到對現(xiàn)實生活和自我生命的直視和清算,并借此獲得有效性的反思的結(jié)果。這一結(jié)果,標示著魯迅在現(xiàn)實生存中自覺到別無選擇之后的人生選擇,從而在重重的矛盾困惑中為自己的人生實踐確定了一種出路,以更為堅定的心態(tài)和執(zhí)著的姿態(tài)直面現(xiàn)實生存。
注釋:
①1119王德威:《當代小說二十家》,第3頁,三聯(lián)書店2006年版。
②劉再復、林崗:《傳統(tǒng)與中國人》,第23、34頁,三聯(lián)書店1988年版。
③《日記》,《魯迅全集》第14卷,第263頁,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年版。
④《書信?致許壽裳》,《魯迅全集》第11卷,第354頁。⑤26《南腔北調(diào)集?〈自選集〉自序》,《魯迅全集》第4卷,第456頁。
⑥《墳?寫在〈墳〉后面》,《魯迅全集》第1卷,第285頁。
⑦18汪暉:《反抗絕望——魯迅及其文學世界》,第27-28頁,第193頁,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
⑧《吶喊?狂人日記》,《魯迅全集》第1卷。下所引均同。⑨《彷徨?長明燈》,《魯迅全集》第2卷。下所引均同。
⑩參見王曉明:《無法直面的人生——魯迅傳》,第93頁,上海文藝出版社1993年版。
1222《墳?摩羅詩力說》,《魯迅全集》第1卷,第100頁,第79頁。
13232530《兩地書》,《魯迅全集》第11卷,第74—79,20,32,20—21頁。
14郜元寶:《魯迅六講》,第109頁,上海三聯(lián)書店2000年版。
15《集外集拾遺補編?破惡聲論》,《魯迅全集》第8卷,第25、28頁。
16參見錢理群:《魯迅作品十五講》,第180頁,北京大學出版社2003年版。
17《〈二心集〉序》,《魯迅全集》第4卷,第191頁。
20《而已集?答有恒先生》,《魯迅全集》第3卷,第456頁。
21《墳?文化偏至論》,《魯迅全集》第1卷,第48頁。
24作為一種對知識分子先驅(qū)者生存境遇和生命體驗的認識,“囚禁”意象不但在魯迅小說中多次出現(xiàn),甚至其為數(shù)極少的新詩中也曾出現(xiàn)。在《新青年》第六卷第四號,魯迅發(fā)表過一首題為《他》的詩,其中有這樣的詩句:“‘知了'不要叫了,/他在房中睡著;/‘知了'叫了,刻刻心頭記著。/太陽去了,‘知了'住了,——還沒有見他,/待打門叫他,——銹鐵鏈子系著。”
27《野草?過客》,《魯迅全集》第2卷,第194頁。
28《彷徨?在酒樓上》,《魯迅全集》第2卷,第34頁。29《彷徨?孤獨者》,《魯迅全集》第2卷,第108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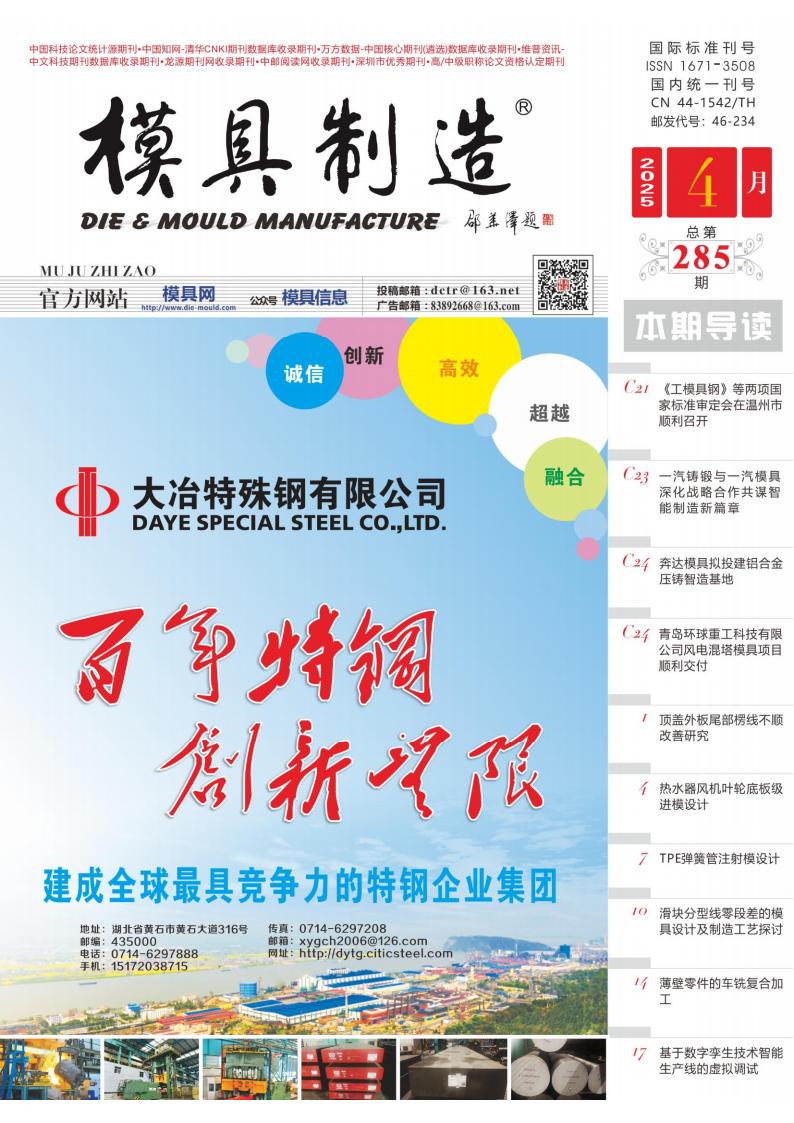


學.jp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