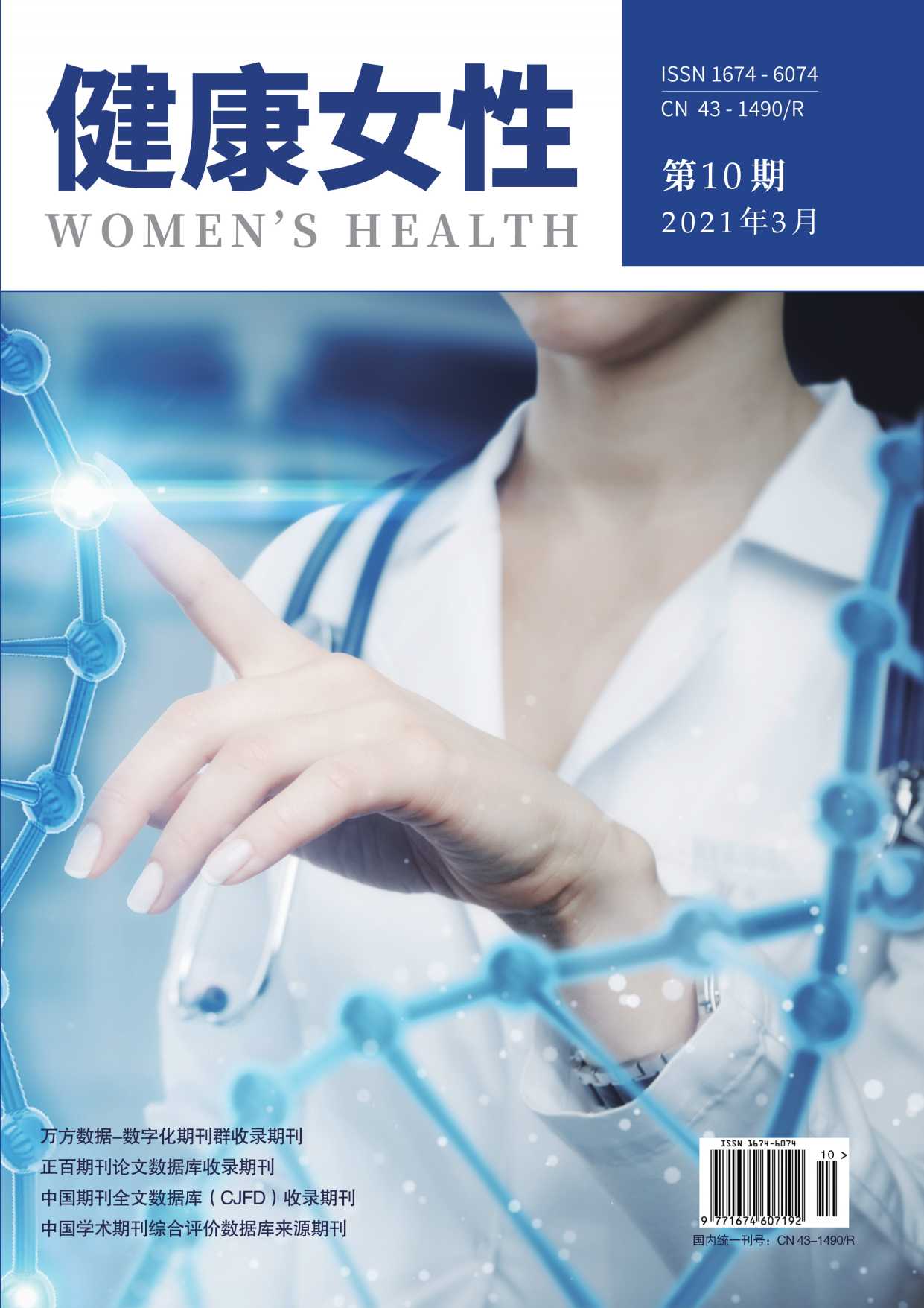管仲的文化治國方略及其當代價值
王華 殷旭輝
摘 要: 管仲相齊40年使齊國成為號令諸侯的霸主。他的文化治國戰略思想是其思想體系中獨特的一方面。管仲強調發展經濟的基礎性作用,把富國和富民有機地結合起來,作為其文化治國思想的物質基礎;其文化治國的戰略思想主要包括三方面的內容:一是通過繼承周文化,從而進入文化主流;二是通過吸納周邊文化,從而促進文化在齊地的融合;在前兩者基礎上塑造獨具魅力的齊文化,成就文化大國的理想,從而構成對經濟和政治的強力支撐。管仲的文化治國思想對于我們今天的社會建制也有著重要的啟示,它告訴我們文化之基礎在于民眾,文化的重塑要體現兼容和開放的精神。
關鍵詞:管仲;文化治國;齊文化 管仲(?—前645),春秋初期齊國著名的政治家。在他擔任齊國宰相期間,在政治、經濟、文化、軍事等領域進行了一系列的改革,使得齊國“通貨積財,富國強兵”[1]2132,建立了“九合諸侯,一匡天下”[1]2131的大業。孔子稱贊管仲的功績:“管仲相桓公,霸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賜。微管仲,吾其被發左衽矣”。[2]梁啟超說管仲是“中國最大之政治家,而亦學術思想界一鉅子也”,說:“其以偉大之政治家而兼為偉大之政治學者,求諸吾國得兩人,于后則有荊公,于前則有管子,此我國足以自豪于世界也。”[3],由此足見管仲的思想和業績所產生的深遠影響。管仲的思想主要見于《管子》一書,該書保存了管仲豐富的政治、經濟、軍事、文化等思想。本文試圖對管仲的文化治國思想進行挖掘,并求得對今天的社會建制的啟示意義。 一、富國富民:管仲文化治國的現實基礎 春秋戰國時期,是我國社會大變革的時期,這一時期奴隸制逐步瓦解,封建制逐步形成。孟軻說:“王者之跡熄而詩亡,詩亡然后《春秋》作”(《孟子?離婁下》),這句話概括地說明了中國社會從西周到春秋的轉變。周王室衰微和諸侯爭霸構成當時政治活動的主要特征。春秋初年,管仲任齊國國相之后,“慎輕重,貴權衡”[1]2132,把經濟建設放到國家建設的首要地位。要在混亂的格局中保全和發展自己,必須首先取得經濟的優先權。國家富裕是長治久安的現實基礎,也是管仲文化治國戰略的物質前提。 富國是治國的根本。管仲說:“錯國于不傾之地,積于不涸之倉,藏于不竭之府。”(《管子?牧民》)強調了發展經濟的基礎性作用。而管仲富國思想的獨到之處在于:他把富國和富民有機地統一了起來。在中國傳統的政治認識中,往往把國家和人民不自覺地對立起來,把國家富裕建立在對老百姓的賦稅和盤剝之上。而管仲把富民作為治國的第一要務,這在先秦諸子中是沒有的。《管子?治國》開篇明義:“凡治國之道,必先富民,民富則易治也,民貧則難治也。”為什么會這樣呢?“民富則安鄉重家,安鄉重家則敬上畏罪,敬上畏罪則易治也。民貧則危鄉輕家,危鄉輕家則敢凌上犯禁,凌上犯禁則難治也。故治國常富,而亂國常貧。是以善為國者,必先富民,然后治之。”又說:“凡有地牧民者,務在四時,守在倉廩。國多財則遠者來,地辟舉則民留處。”(《管子?牧民》)從此出發,管仲強調治國者必須善于與民同利,因為“凡人者,莫不欲利而惡害”。所以,“與天下同利者,天下持久;擅天下之利者,天下謀之。”(《管子?版法解》),“欲為天下者,必重用其國;欲為其國者,必重用其民;欲為其民者,必重盡其力。”(《管子?權修》),只有不斷增強自己的實力,做到民富國強,才有力量與諸侯抗衡。“圣人之所以為圣人者,善分民也。圣人不能分民,則猶百姓也”(《管子?乘馬》)。在管仲執政期間,齊國推行“慈于民,予無財;寬政役,敬百姓”(《管子?小匡》)的政策,盡量做到“靜其民而不擾,佚其民而不勞”(《管子?形勢解》),通過“以天下之財,利天下之人”(《管子?霸言》),使得齊國百姓生活得到保障,政權獲得鞏固和穩定。這不僅促使齊國在經濟上富足殷實,政治上安定秩序,也為管仲文化治國準備了必要的物質基礎。 二、管仲文化治國的具體實踐 “區區之齊在海濱”[1]2132,地理形勢的阻隔使得齊長久以來偏離以中原地區為核心的主流文化。雖然管仲以九合諸侯,“尊王攘夷”之功,使齊國一躍而成為當時的政治中心,但是在文化上仍然相對落后。從文化上來說,齊國屬于東夷的文化圈。管仲大膽提出變革的政治哲學和政治主張,主張用文化理念來統治臣民,順服周邊,這對于文化的挽救和政治的崛起,無疑在歷史上是一大創舉。管仲文化治國的具體舉措如下: 1.繼承周文化——進入文化主流。西周時期的齊國,姜太公實行“因其俗,簡其禮”的基本國策,對原來的夷俗夷禮未作大的改動。到了桓管時期,管仲在齊國推行了一系列文化改革,積極向主流的周文化靠攏,促進了夷夏文化在齊地的融合。“修舊法,擇其善者舉而嚴用之。”(《管子?小匡》)通過整飭、修復文武周公舊法,擇其適合齊國社會實際的部分,創造性地加以運用。主要表現在:其一,創造性地借用周文化中的禮、義文化。管仲認為:“國有四維,一維絕則傾,二維絕則危,三維絕則覆,四維絕則滅。”四維者,“一曰禮,二曰義,三曰廉,四曰恥”(《管子?牧民》)。四維之中,禮、義為先,通過用禮、義來規范人們行為,整飭社會秩序,挽救了處于緊張之中的夷禮、夷俗。其二,吸收了周公“明德慎罰”的思想。管仲認為,德是國家長治久安的要素之一。“錯國于不傾之地者,授有德也。”(《管子?牧民》),在明德的同時,管仲亦主張慎罰。他說:“刑罰不足以畏其意,殺戮不足以服其心。故刑罰繁而意不恐,則令不行矣;殺戮眾而心不服,則上位危矣。”(《管子?牧民》),因而他主張刑罰上要慎重而嚴謹。其三,汲取并發展了重農愛民傳統。管仲認為,統治者應該以民為本,求天下“始于愛民”(《管子?小匡》),“下令于流水之原者,令順民心也。”(《管子?牧民》),管仲又把愛民具體概括為六個方面,即“厚其生”,“輸之以財”,“遺之以利”,“寬其政”,“匡其急”,“振其窮”。并且強調“五谷者,民之司命也。”(《管子?山權數》),從治國的角度上:“明王之務,在于強本事,去無用,然后民可使富。”(《管子?五輔》),又說:“夫富國多粟,生于農。……民事農則田墾,田墾則粟多,粟多則國富。國富者兵強,兵強者戰勝,戰勝者地廣。是以先王知眾民強兵,廣地富國之必生于粟也。”(《管子?治國》)。應該特別指出的是,管仲在繼承周人重農思想的同時,并沒有放棄齊人重視工商業的傳統,而是將二者有機地結合在一起,做到了農、工、商并重。由上可知,管仲期望通過對周文化的繼承,將周人的禮義精神、明德慎罰思想、重農愛民等傳統引入齊國,使齊地的文化邁入主流文化之列,具有更強的生命力,從而對周邊構成了強力的吸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