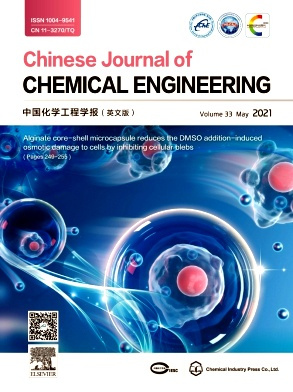后現代的倫理學:論漢斯·約納斯
張旭
一、對傳統倫理學的人類中心主義的批判
約納斯對技術時代倫理的本體論解釋并不是想在現代的各種倫理學之中加入一個所謂的“生態倫理學”或“環境倫理學”的分支,而是要從人的本體論的根基上改變整個倫理學。約納斯認為,無論是亞里士多德的德性論,還是基督教的良心論;不論是康德的義務論,還是密爾的功利主義;不論是羅爾斯的正義論,還是各種道德相對主義,所有這些倫理學無一不是一種人類中心主義的倫理學。約納斯認為這些倫理在本質上都是一種“近距離的倫理”(N?chsten-Ethik)。比如說圣經上說,像愛自己一樣愛你的鄰人,或者你希望別人怎樣待你,你也要怎樣對待別人。或者像康德說,決不要把你的鄰人當成手段,而總是要把他當成目的本身。這些倫理學在本質上是一種主體上或主體間自律或他律的倫理學,是對人與人之間的道德關系提出的規范和約束。無論道德的目標是在于自由,還是在于德性,也無論道德的標準是個人行為的內在準則,還是社會契約的正義和外在規范,這些倫理學的實質都是對人的善與權利的關注。概而言之,“整個傳統的倫理學就是一種人類中心論的倫理”[2](P24)。 人類中心論的倫理學不言而喻的核心就是人或人的社會,倫理學作為一門學科就是研究人的學科。但是,從古至今的各種倫理學在我們的時代已經顯露出它們的貧乏和無能為力,因為它們在技術的無目的性的龐大力量面前束手無策,它們對自然和未來的生命置若罔聞。它們的那些崇高的道德價值隨著技術時代里傳統形而上學的終結和上帝之死而徹底崩潰,與此同時它們卻未能提出一種直面技術時代的道德責任原則。各種人類中心主義倫理學面對技術對地球的統治以及為爭奪這種統治權的斗爭無能為力,這種倫理學的失敗促使約納斯針對傳統倫理學的困境提出了一種“遠距離的倫理”(Ethik der Ferne)。這種“遠的倫理”首先面對的不再是人的精神性的道德困境,而是在技術統治的威脅下人所應當承擔的責任。這種責任無疑是一種道德倫理,但是它的本質是首先對自然的關注的義務(Fürsorgenpflicht für die Natur),而不是首先對人的關切(Sorge für die Menschen)。“遠的倫理”并不只是提供了一個新的范疇,而是意味著敞開了一個新的維度,一個新的價值尺度,所有的古代的和現代的倫理學都將在這一尺度中重新得到檢驗和批判,所有的傳統的倫理學都將在這一維度中被重寫。以前的倫理學與其說是沒有思考到“遠”的維度,毋寧說是在根本上存在著人類中心論的限度。 當然,這一“遠”的維度不同于“遠”的烏托邦。在《責任原理》的最后一章“從烏托邦批判到責任原理”中,約納斯以人的自然的“已經存在”(Schon Da)拒斥了布洛赫空洞的“尚未存在”(Noch-Nicht-Sein)的“希望原理”和“烏托邦精神”。在他看來,布洛赫的“希望原理”仍然只是是一種人類學性質的本體論。[2](P56-376)約納斯所說的“遠”是從現在的人對“已經存在”的自然和“未來”的生命的責任出發的,因此它是一種直面已經存在的人的生存境況的本體論。約納斯將責任原理的絕對命令表述如下:“你的行為必須是行為后果要考慮到承擔起地球上真正的人的生命持續的義務。”其否定形式的表達是:“你的行為必須是行為后果不能破壞地球上人的生命的未來的可能性。”[2](P36) 約納斯的責任倫理是一種考慮到人類行為的后果,甚至很大一部分是不可預測的后果的倫理,他不像基督教的和康德的倫理學那樣訴諸人的行為的良好動機、善良意愿和自由意志等等。在他看來,在倫理學中訴諸人的動機是一種人類中心主義,它將人類從自然以及未來的生命的整體中完全剝離出來,將人類個體的自由和尊嚴視為最高的價值。它的原則是,個人按照正義行事,行動的后果交付給上帝或普遍的道德原則。責任倫則理要求人類充分考慮到技術的權力所帶來的大量的不可預知的全球性的破壞性的后果。責任倫理也不同于效果取向的功利主義倫理學。因為功利主義倫理學雖然是以理性化的、實用的效果甚至是長遠的效果為目標,但是就真正的價值尺度和本體論的基礎而言,它卻是盲目的和虛無的,它的效果是以利益甚至是長遠的利益而非以自然的目的作為評價道德行為的標準。在一個技術文明時代,在福利社會和消費的時代中,功利主義使得人們無法擺脫人類中心主義的利益和需要的邏輯去思考我們人類和地球的生死存亡的問題。 韋伯在人的行動的價值領域區分了責任倫理和信念倫理。在韋伯看來,盡管康德的倫理學是一種理性自律的、形式反思的、可普遍立法的倫理,但仍是一種信念倫理。韋伯的責任倫理認為,在人類的政治行為中,必須從政治義務和行動的后果出發,而不是從善良意愿、良好的動機、偉大的信念等等出發。[3](P30)如果從約納斯的責任倫理來看韋伯的責任倫理,那么韋伯的責任倫理仍然是一種康德式的倫理,一種人類中心的倫理。霍克海默、阿多諾、馬爾庫塞和哈貝馬斯等人對啟蒙辯證法和技術理性的批判同樣陷入一種對技術文明的悲觀主義之中,而缺乏一種規范技術力量的責任倫理。責任倫理的關鍵是我們要對什么負責,即衡量我們行動的后果的標準到底是什么。對于約納斯來說,責任倫理要求行動的后果要對自然的未來和人類的未來負責。
二、責任關系的原型和責任原理的宏觀倫理學
約納斯的責任倫理的絕對命令是要求人對自然承擔責任和義務,因為我們現在所做的一切對時間上未來的人類和空間上遙遠的區域的影響遠比我們所能想像的深刻得多。技術力量的未來的危險已經超出了人們的計算和想像。因此,人對自然和未來的人的責任和義務構成了責任原理的核心。人的責任并不僅僅是為已經做的事情負責,而且還要為未來做的事情負責,承擔自己的義務。約納斯為責任倫理學原則提出了一個生動的原型關系。約納斯說:“所有責任的原型就是對孩子的關系。”[2](P184)這種“父母與孩子的關系”(Eltern-Kind-Beziehung)是一種“不可逆的關系”(ein nicht-reziprokes Verh?ltnis),[2](P176)因為“孩子要求人的庇護是種不可逆的關系。”[2](P192)一個小孩有什么用呢?他不過是個小生命而已。然而,“責任的原初的對象就是孩子。”[2](P234)父母對他的孩子具有不可推卸的義務。在不可逆的關系之中,要求庇護的是弱者,而承擔庇護責任的是有行動能力的強者。相對于人而言,自然和未來的生命就是弱者,尤其在技術統治的強大力量面前,作為弱者的自然和未來的生命更需要我們當代人承擔起自己的責任和義務。在技術文明中,人的力量隨著技術的瘋狂突進而空前地增長,但是人的欲望和需求的增長并沒有同時伴隨著人對弱小者的責任的增長。因技術而強大的人類的責任意識仍然需要啟蒙。人的尊嚴不是體現在他的強大之上,而是體現在他的責任倫理之中,因為“只有人具有責任意識”[2](P185)。 人對自然和未來的生命的倫理責任就在于:“任何行動必須從人類的長遠存在著想,或者任何行動的后果不能對未來的生命造成破壞。”這是對整個人類提出的倫理原理,而不是針對某個個體。現代自由主義的個體倫理學只注重個體的自由、權利與尊嚴,而無力承當集體行動的責任。只有古典哲學和宗教的倫理才針對共同體或集體提出倫理原理和道德律令。自從宗教作為倫理被驅逐出現代世界以來,一種面向未來、面向集體行動和公共領域的“大倫理”再也沒有出現過。現代哲學制造了宏觀倫理學和微觀倫理學以及元倫理學和對象倫理學之間不可彌合的分裂。結果是現代社會缺乏一種能思考人類行為的巨大后果的元倫理學,而那些訴諸個體權利或自由的倫理學卻無力拓展人的道德責任能力。約納斯的對自然和未來的責任倫理再次將道德責任承載者確立在整個人類身上,而不僅僅是理性自律或意志自由的個體上。因為責任原理所基于的“人的自然”(human nature)是處于自然和歷史中的整體的存在,而不是基于人的反思理性、自我意識或良心。約納斯認為,倫理學首先應該追問的是:為什么人根本存在于世界之中?為什么要有保證未來生存的無條件的絕對命令?這一問題不可能在任何一種傳統倫理學中得到回答。這是一個最為本體論的問題,也就是說,這是一個最低限度的根本問題。將人置于倫理的核心的傳統的意識哲學或現代的生存哲學,都追求一種高級目標的倫理,卻在根本上忽視了其最低限度的本體論基礎。這一本體論的基礎就是被整個現代哲學所遺忘了的自然本體論。
三
約納斯的責任倫理是從自然的本體論來界定道德倫理的絕對命令的,這意味著善的概念既要在自然中得以思考,同時也要在未來的時間維度中進行思考。善的概念既不是基于人的權利或社會的契約,也不是按照價值的原則人為地建構起來的,它是植根于自然之中的,因為自然本身就有價值和目的,而且它是人類行為的價值和目的的基礎和源泉。自從康德以來,對事實和價值的區分已經成為了現代思想尤其是現代倫理學的自明的前提。然而這一前提卻是以自然本身沒有目的和價值為前提的。正是現代技術文明的興起才造成了一種二元論的普遍的意見,這種現代性的分裂左右著現代哲學的基本范式。
四
但是,在技術文明時代,讓人類放棄自己的利益和權利而承擔起對自然和人類的未來的義務是何其艱難的一件事,因為技術至上論和技術烏托邦已經深入到現代文明的方方面面了,以至于我們把現代文明稱之為“技術文明”。約納斯認為,在技術的框架之內是根本不可能給出任何克服技術控制人與自然的解決答案的。技術本身不能克服技術的風險和危險。對技術本質的認識以及對技術的警惕是責任倫理首要的任務。技術實用主義者認為技術可以充分考慮到長遠的利益,但是這種辯護實際上何其虛偽和軟弱。[2](P7) 首先,約納斯認為,技術文明的本質就在于技術已經內化成為人自身的需要了。技術不再是一種人所能控制和運用的工具和媒介,而是一種深刻的改變了人與自然的關系的力量。技術就是人的欲望和力量的載體,是人的意志的體現,是人的權力的象征。[8](P43-44)其次,約納斯認為,技術時代的絕對命令是一切皆可利用,一切皆可制造,一切皆可消費。然而,能做的是不是就等于一定要做,是不是應該去做?也就是說,是否凡是技術力量所能做到的都應該去做?在約納斯看來,現代人更多地考慮技術上能否做到,而人對技術說“不”的能力和智慧已經蕩然無存了。再次,技術不僅改造了人類生存的整體的自然,更為重要的是技術重新界定了人的自然(human nature)。人不再被視為智慧的人(homo sapiens)了,人的本質就是勞動的人(homo faber),或者說技術的人。因此,技術已經不再是人自身之外的東西了,而是技術的人的一整套的思維、情感和行為方式。現代人幾乎不能在技術思維之外思考問題,諸如事實與價值的區分、可能與現實的區分等等都已經根深蒂固地扎根在我們時代的自然科學和社會思潮之中。最后,自從培根提出科學技術的新工具以征服自然的近代轉折以來,人們形成了一整套的評價自然和生物以及人的本質的知識,成為整個現代文明技術烏托邦的基礎。[2](P251-255)因此,技術時代的倫理問題首要的就是對技術烏托邦的清醒認識。 技術烏托邦對未來的危險雖然是無法加以確切地計算的,但是它并不因此而不存在。約納斯提出了一種盡可能想像技術在未來的難以預料的巨大危險的“恐懼的啟迪術”(Heuristik der Furcht)。“恐懼的啟迪術”有助于人們在面對技術時代里去測度技術的力量及其威脅,去思索自然和生命的本體論地位和意義。對于約納斯來說,偉大的圣徒施韋澤提出的“敬畏生命”(Ehrfurcht vor dem Leben)是一種最值得尊敬的思想。恐懼技術,敬畏生命,這種技術悲觀主義和自然生命神圣論就是約納斯的責任倫理的基本精神。責任倫理首要針對的就是技術文明本身的危險,那些技術至上論和技術烏托邦的危險,那些使人成為“技術的人”的危險,那些瘋狂地生產一切、制造一切、消費一切、享受一切的危險。責任倫理要對技術本身堅決地說“不”。對于技術文明來說,不僅僅是負責(Verantworten)的問題,而且是給出解決的答案(Antworten zu geben)的問題。約納斯說,在現代科學技術的世界觀和現代哲學的視域之外去思考技術時代人與自然的關系,并使人承擔起對自然和未來的責任和義務,這就是哲學的未來,也是自然和生命的未來。[9](P1-2)
[
[ 1 ] Hans Jonas.Das Prinzip Verantwortung: Versuch einer Ethik Für die technologische Zivilisation[M].Frankfurt/Main,1979. [2]J. C. Wolf.Hans Jonas: Eine naturphilosophische Begründung der Ethik[A].A. Hügli & P. Lübcke.Philosophie im 20. Jahrhundert[M].Reinbek Verlag,1996. [3]Wolfgang Schluchter.Conviction and Responsibility[A].Padadox of Modernity: Culture and Conduct in the Theory of Max Weber [C].trans. by Neil Solomon,California,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96. [4]Hans Jonas.Macht oder Ohnmacht der Subjektivit?t: Das Leib-Seele-Problem im Vorfeld des Prinzips Verantwortung[M].Frankfurt/Main,Insel Verlag,1987. [5]Franz Josef Wetz.Hans Jonas zur Einführumg[M].Hamburg:Junius Verlag,1994.12. [6]Hans Jonas.Dem b?sen Ende n?her.Gespr?ch über das Verh?ltnis des Menschen zur Natur[M].Hrsg. Wolfgang Schneider.Frankfurt/Main,Suhrkamp. 1993. 102. [7]Hans Jonas.Wissenschaft als pers?nliches Erlebnis[M].G?ttingen, Vandenhoeck & Ruprecht Verlag,1987. 19. [8]Hans Jonas.Technik,Medizin und Ethik: Zur Praxis des Prinzips Verantwortung[M].Frankfurt/Main,Insel Verlag..1985. [9]Hans Jonas.Rückschau und Vorschau am Ende des Jarhhunderte[M].Frankfurt/Main,Suhrkamp Verlag,199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