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像中的歷史:“口述歷史”類(lèi)電視節(jié)目探析
蔡騏 謝瑩
關(guān)鍵詞: 口述歷史 電視節(jié)目 個(gè)人化 復(fù)現(xiàn) 重構(gòu)
[摘要]:近年,電視熒屏上興起了多檔“口述歷史”類(lèi)節(jié)目,為歷史題材的電視傳播開(kāi)辟了新路。來(lái)自歷史領(lǐng)域的“口述歷史”,蘊(yùn)含了一種全新的治史理念:以第一人稱的微觀個(gè)人史取代第三人稱的宏觀社會(huì)史;以歷史生動(dòng)、感性的一面取代客觀、精確的史料。這些主張為歷史類(lèi)電視欄目的個(gè)人化、故事化、情感化創(chuàng)作提供了有利的理論依據(jù)。但是在個(gè)人化敘事中,由于記憶的局限、語(yǔ)言的片面、敘述者自我認(rèn)同的需求及鏡頭前的表演欲望往往使得歷史的真正意義被消解,而且,在大眾娛樂(lè)性的需求下,不可靠的史實(shí)還成為電視揭秘、煽情的有利資源。此外,歷史的再現(xiàn)還會(huì)受到社會(huì)語(yǔ)境與媒介生產(chǎn)的制約,節(jié)目的精英定位也將普通人排除在歷史之外。因此,“口述歷史”類(lèi)電視節(jié)目并非簡(jiǎn)單的對(duì)過(guò)去事實(shí)的回顧與描述,本質(zhì)上它是對(duì)過(guò)去的一種復(fù)現(xiàn)與重構(gòu)。 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a new TV genre, “Oral History,” has come into existence. An original concept in the history discipline, oral history represents a new perspective on history. It replaces a macro, objective, and factual approach with a micro, subjective, and narrative approach to historical past; history is narrated in a personalized and vivid fashion by inpidual persons who have experienced the past. The oral history TV genre resorts to the oral history theories and adopts a personalized narrative style in presenting historical events. However, such shows destroy the real meanings of history because of the limited memory and biased language of the narrator who is also influenced by his or her personal identities. In addition, such shows may use false historical facts in order to achieve public entertainment purposes, for example, to arouse certain emotions in their audiences. Finally, factors like social contexts and media production may also affect historical representation. Thus, oral history television shows are not merely recollections or descriptions of what happened in the past; rather, they reconstruct or represent the past.
Key words: Oral History;Television Shows;Personalization;Representation;Reconstruction
口述歷史,原本是一種基本的治史方法,但是近幾年,經(jīng)由各類(lèi)媒體尤其是電視媒體的拓展,“說(shuō)”歷史、“聽(tīng)”歷史這種最古老的歷史傳承方式在熒屏上重新流行起來(lái)。越來(lái)越多的紀(jì)錄片與電視欄目將“口述歷史”作為一種類(lèi)型追求,創(chuàng)造出了許多精彩的節(jié)目,如中央電視臺(tái)的《見(jiàn)證》、《講述》,鳳凰衛(wèi)視的《口述歷史》,湖北衛(wèi)視的《往事》等等。對(duì)于歷史的電視傳播,口述的方式不僅拓展了電視欄目的文本內(nèi)容,也為其提供了一種全新的創(chuàng)作理念。然而由于電視傳播的特殊性,“口述歷史”在影像空間里,并沒(méi)有完成其“最大可能復(fù)原歷史”的初衷,而是成為一種保證收視率的藝術(shù)表現(xiàn)手法,并承擔(dān)了某種特定的意識(shí)形態(tài)功能。本文擬從歷史學(xué)及傳播學(xué)的角度來(lái)解析該類(lèi)節(jié)目建構(gòu)歷史的真相。
影像與口述:史觀變遷下的欄目創(chuàng)新
對(duì)于歷史的呈現(xiàn),主要有書(shū)寫(xiě)史與口述史兩種方式。書(shū)寫(xiě)史由歷史學(xué)家撰寫(xiě),偏向上層或官方的記述,“往往抱有懲惡揚(yáng)善、經(jīng)世致用的目的,希望通過(guò)歷史的書(shū)寫(xiě)來(lái)論證現(xiàn)任政權(quán)、政策的正統(tǒng)性、正確性”,(周新國(guó),2005:121)帶有“帝王史”、“政治史”、“精英史”的特色。口述史則更多地來(lái)自于民眾本身,由活著的人的記憶構(gòu)成,以感知來(lái)認(rèn)識(shí)歷史及其現(xiàn)實(shí)線索,偏重對(duì)日常生活史的關(guān)注,為歷史文本提供豐富的細(xì)節(jié)。盡管人類(lèi)以口耳相傳記事的歷史,遠(yuǎn)遠(yuǎn)長(zhǎng)于其“有史以來(lái)”的歷史。但是,長(zhǎng)期以來(lái),口述史僅僅作為拓展、補(bǔ)充書(shū)寫(xiě)史的方法來(lái)提倡,是書(shū)寫(xiě)史的附屬品。一直進(jìn)入上個(gè)世紀(jì)60年代,隨著史學(xué)的發(fā)展,人們開(kāi)始將其作為促使歷史研究范式更新的新觀念來(lái)主張,口述歷史漸漸成為與大眾親密接觸的顯學(xué)。1988年,美國(guó)歷史學(xué)家海登?懷特在《美國(guó)歷史學(xué)評(píng)論》上發(fā)表《書(shū)寫(xiě)史學(xué)與影視史學(xué)》一文,首次提出了“影視史學(xué)”(Historiophoty)的概念,主張“以影視的方法傳達(dá)歷史以及我們對(duì)歷史的見(jiàn)解”。(Hayden White,1988)這一概念的提出與口述史的蓬勃發(fā)展共同打破了“讀”歷史、“寫(xiě)”歷史的傳統(tǒng)研究模式,成為發(fā)現(xiàn)“新歷史”的新方法,也在某種程度上刺激了影視文本的創(chuàng)作,口述歷史類(lèi)電視節(jié)目成為影視史學(xué)的一個(gè)重要組成部分。
首先,“新史觀”主張以個(gè)人命運(yùn)來(lái)折射社會(huì)歷史,認(rèn)為“能保持下去的惟一具體的歷史,永遠(yuǎn)是那種基于個(gè)人敘述的歷史”,(哈拉爾德?韋爾策,2007:24-25)“個(gè)人性即社會(huì)性,最具個(gè)人性的也就是最非個(gè)人性的”。(郭于華,2008)因此,無(wú)論是影像史學(xué)還是口述歷史都致力于尋找個(gè)人經(jīng)歷和社會(huì)結(jié)構(gòu)的公共議題之間的聯(lián)系,希望透過(guò)微觀的經(jīng)驗(yàn)材料去展示宏觀的社會(huì)歷史,這為電視歷史欄目的創(chuàng)作提供了一條新思路。
我國(guó)以往的歷史影像,尤其是涉及歷史偉人或重大事件的文獻(xiàn)記錄片,創(chuàng)作者大多具有自覺(jué)的政治意識(shí),長(zhǎng)期承擔(dān)重要的宣傳任務(wù),為保證影片的精確性,偏重對(duì)文獻(xiàn)的考證,堆砌文字材料,再輔以相應(yīng)的影像資料,以專(zhuān)家口吻就事論事的進(jìn)行靜態(tài)闡述。可是進(jìn)入信息社會(huì),人們對(duì)社會(huì)生活的觀察、體味方式正在逐漸改變,在感受過(guò)莊嚴(yán)宏大的敘事后,轉(zhuǎn)而歡迎扎扎實(shí)實(shí)的個(gè)案梳理,從小角度切入、感受以往忽略或掩蓋了的鮮活歷史。(胡永芳,2006)在新史觀的啟發(fā)下,影像工作者開(kāi)始在歷史題材中突出“人的主題”,體現(xiàn)歷史的人文關(guān)懷,大膽的將歷史當(dāng)事人或親歷者的口述放在歷史影像五種基本鏡頭畫(huà)面(有關(guān)歷史的影像資料、有關(guān)歷史的文獻(xiàn)資料、當(dāng)事人或親歷者的口述、歷史活動(dòng)的遺址與環(huán)境、專(zhuān)家學(xué)者的訪談評(píng)價(jià))中最突出的位置。因?yàn)闅v史是由一個(gè)個(gè)普通人組成的,只有理解了他們的日常生活、內(nèi)心世界才能理解歷史的主要部分。中央電視臺(tái)《見(jiàn)證?親歷》欄目曾制作了十期《紀(jì)念改革開(kāi)放30周年》的節(jié)目,第十集《生于一九七八》便是由五個(gè)生于1978年的年輕人講述自己這三十年來(lái)的成長(zhǎng)經(jīng)歷,透過(guò)個(gè)人生命歷程的講述來(lái)展現(xiàn)特定群體的生活史、價(jià)值觀及文化心態(tài),繼而挖掘個(gè)體生命與宏觀的社會(huì)背景的相互關(guān)系。借此,“歷史的主要部分本就是這些衣食住行、日常生活的記錄和記述。”(李澤厚,2008:30)的史學(xué)觀點(diǎn)得到驗(yàn)證。
其次,表現(xiàn)個(gè)體故事時(shí)采取第一人稱的自述而非第三人稱的代述,則是口述歷史的最大特色。在它看來(lái),要還原歷史更真實(shí)、更豐富的一面,很大程度上仰仗人們對(duì)自身經(jīng)歷的講述,而不是依靠歷史學(xué)家代為講述。見(jiàn)證以第一人稱“我”敘述只有他本人才有資格說(shuō)的真實(shí)經(jīng)歷,這種獨(dú)特身份為歷史研究提供了一種強(qiáng)烈的真實(shí)效果。因?yàn)椤拔摇辈恢皇且粋€(gè)方便的敘述角度,而且是一個(gè)對(duì)經(jīng)驗(yàn)真實(shí)的承諾和宣稱。寫(xiě)歷史可以是替別人記敘,作見(jiàn)證卻不能由別人代言。“我”給公眾提供的史實(shí),是非常個(gè)人的、在很小經(jīng)驗(yàn)范圍內(nèi)的局部事件,如果當(dāng)事人自己不說(shuō),無(wú)論多少歷史研究可能永遠(yuǎn)都發(fā)現(xiàn)不了的微觀史實(shí)。(徐賁,2008)
口述歷史對(duì)親歷者、見(jiàn)證者身份的強(qiáng)調(diào),與電視傳播的藝術(shù)追求在某種程度上不謀而合。電視傳播的直觀性、形象性決定了影像表現(xiàn)的歷史中,人證、物證的重要性遠(yuǎn)遠(yuǎn)大于文字記述。即使擁有大量的文字資料,倘若無(wú)法找到與其相應(yīng)的影像、人物和事件遺跡,書(shū)面的歷史也很難適合于電視媒體的表現(xiàn)。因此,在歷史類(lèi)電視欄目中,能否找到恰當(dāng)?shù)挠H歷者、見(jiàn)證人,他們是否愿意出鏡接受采訪,有無(wú)歷史物證和影像資料,往往決定某一段落甚至全片的可信性、可看度。鳳凰衛(wèi)視《口述歷史》節(jié)目的制作人張力曾這樣描述他們的創(chuàng)作心態(tài),“即使每一個(gè)人的敘述總會(huì)有意無(wú)意地掩蓋些什么,回避些什么,甚至虛構(gòu)些什么,我們不考證他的話是否屬實(shí),只要他是事件的親歷當(dāng)事人,站出來(lái)表明他的態(tài)度就足夠了。”(郭宇寬,2005)就影像傳播中的口述歷史而言,單單敘述者能存活下來(lái)講述這些故事,已足以引發(fā)觀眾的興趣。
再次,與傳統(tǒng)史學(xué)研究強(qiáng)調(diào)史料的客觀性、精確性、嚴(yán)肅性不同,新史觀承認(rèn)歷史應(yīng)有其感性的一面,諸多形式化的限制會(huì)使歷史脫離真實(shí)語(yǔ)境,失去特定時(shí)空的生活氣息,而影像與口述的結(jié)合則可以彌補(bǔ)這些不足。通過(guò)見(jiàn)證者對(duì)歷史場(chǎng)景及自身感受的描述,讓人們得以回到歷史現(xiàn)場(chǎng),感受歷史氛圍,重構(gòu)出生動(dòng)的歷史畫(huà)面。新的史學(xué)主張為歷史類(lèi)電視欄目的故事化創(chuàng)作提供了有利的理論依據(jù)。
如今電視節(jié)目面臨著越來(lái)越故事化、內(nèi)心化、傳奇化的趨勢(shì)。故事性的強(qiáng)弱和節(jié)目收視率幾乎是成正比的關(guān)系,會(huì)不會(huì)講故事、有沒(méi)有傳奇性情節(jié),是節(jié)目成功的關(guān)鍵。歷史類(lèi)節(jié)目若要在欄目競(jìng)爭(zhēng)中脫穎而出,便不能繼續(xù)以往“解說(shuō)+畫(huà)面”的制作方式,引入口述歷史的模式成為欄目創(chuàng)新的必然之舉。親歷者/見(jiàn)證者“口述”中大量口語(yǔ)的使用以及講述者自我展示的需要,使得口述內(nèi)容常常帶有夸張、荒誕、趣味、情節(jié)化等故事化特征,這為影像傳播帶來(lái)了故事化、傳奇化、情感化的藝術(shù)效果。口述者往往以“說(shuō)來(lái)話長(zhǎng)”、“很久、很久之前”之類(lèi)的句式開(kāi)始,在敘述過(guò)程中,抽象的概念被轉(zhuǎn)為具體現(xiàn)象的表達(dá),有矛盾的沖突,也有情緒的起伏,以此構(gòu)成一個(gè)個(gè)精彩生動(dòng)的故事。
故事的講述過(guò)程也是抒發(fā)情感的過(guò)程,口述的形式同時(shí)也為記錄情境的塑造提供了頗具感染力的情感性畫(huà)面。在口述歷史類(lèi)節(jié)目中,片子從人的視覺(jué)經(jīng)驗(yàn)出發(fā),通過(guò)捕捉、放大敘述者的細(xì)節(jié)行為,記錄與話語(yǔ)敘述同步進(jìn)行的動(dòng)作,還有畫(huà)面色調(diào)的變化、光線的處理以及不同景別的合理搭配,不僅使得局限空間內(nèi)的畫(huà)面視覺(jué)層次感得到了極大的拓展,豐富了視覺(jué)效果,并且讓觀眾感覺(jué)到似乎不是在看電視或其他的電子媒介,而是在與敘述者面對(duì)面,聽(tīng)他/她像一位朋友或長(zhǎng)輩似的向自己講述已經(jīng)塵封多年的往事。敘述者和觀眾之間所形成的對(duì)話關(guān)系、畫(huà)面中口述時(shí)刻的情感流露,聲音元素所發(fā)揮的獨(dú)特魅力能調(diào)動(dòng)觀眾的倫理感情,喚起心理認(rèn)同和情感共鳴,使他們?cè)谟邢薜臅r(shí)間里對(duì)口述片段形成一個(gè)比較豐富、立體的認(rèn)識(shí)。這些都順應(yīng)了電視節(jié)目“好看、好聽(tīng)”的內(nèi)在要求。
盡管歷史見(jiàn)證人的這種個(gè)人化、故事化表達(dá)揭開(kāi)了一些歷史中曾經(jīng)被忽略、被遺忘甚至被有意遮蔽的隱秘地帶,也使許多細(xì)節(jié)還原和凸顯出來(lái),但是既然是個(gè)人敘事,便有它一隅之見(jiàn)的局限性。因此,口述歷史類(lèi)節(jié)目的敘事往往陷入了另一個(gè)悖論,歷史的嚴(yán)肅性被個(gè)體隨意性和盲目性取代,歷史的整體性也被零散的個(gè)體性所模糊。
口述歷史:個(gè)人化的敘事與表演
我們可以看到,口述歷史類(lèi)節(jié)目通過(guò)人物專(zhuān)訪,將一段歷史幾乎完全是由個(gè)人的語(yǔ)言來(lái)傳達(dá)。這讓我們聽(tīng)到了他們?cè)谔囟v史事件中的特殊經(jīng)歷,他們對(duì)自己體驗(yàn)的解釋?zhuān)瑢?duì)當(dāng)時(shí)事件的理解或不理解,讓我們更好地懂得了歷史對(duì)于當(dāng)時(shí)的人們意味著什么,個(gè)人化敘事使得歷史因?yàn)閭€(gè)體生存的多樣性而呈現(xiàn)出無(wú)限的豐富。但敘述中往往有對(duì)已知?dú)v史內(nèi)容的簡(jiǎn)單重復(fù),有對(duì)主要敘述空隙的填補(bǔ),也有個(gè)人的猜測(cè),甚至有道聽(tīng)途說(shuō)或主觀愿望。這就表明,一旦時(shí)過(guò)境遷,即使是親歷者的記憶也不免夾帶了主觀臆斷的成分,歷史以其虛構(gòu)性的想象和帶有敘述者主觀性體驗(yàn)的面貌出現(xiàn),與史實(shí)本身已有距離。從其敘述的歷史表象來(lái)看,倒很符合卡爾?波普爾所說(shuō)的:“不可能有一部‘真正如實(shí)表現(xiàn)過(guò)去’的歷史,只能有各種歷史的解釋?zhuān)覜](méi)有一種解釋是最后的解釋?zhuān)虼嗣恳淮擞袡?quán)利去作出自己的解釋。”(朱立元,1997:39)史實(shí)的不可靠傳達(dá),與個(gè)人化敘述與生俱來(lái)的片面性和局限性分不開(kāi)。
在這類(lèi)訪談節(jié)目中,個(gè)人以語(yǔ)言來(lái)描述記憶。實(shí)際經(jīng)歷往往零亂、復(fù)雜和不明晰,而“講述”或“敘述”則把雜亂無(wú)章的經(jīng)歷條理化和明晰化了。訪談?wù)咴谑稣f(shuō)經(jīng)驗(yàn)的過(guò)程中,會(huì)將復(fù)雜經(jīng)驗(yàn)改變?yōu)榭梢允稣f(shuō),并在時(shí)間序列與因果關(guān)系上成為一個(gè)可以理解的故事。有時(shí)會(huì)前后顛倒、有時(shí)省略自以為不重要的部分,突出對(duì)個(gè)人有意義或有利的地方,或者填補(bǔ)空白或模糊之處。更常見(jiàn)的情況是把個(gè)人記憶與他人記憶混合、交換。這樣做有時(shí)是無(wú)意識(shí)的,有時(shí)則是故意的。(楊祥銀,2004:162)
“無(wú)意識(shí)”,源于受訪人不可能完全跳出事件之外來(lái)觀察、描述該事。每個(gè)親歷者對(duì)歷史的體驗(yàn)與記憶都具有唯一性與特殊性,每個(gè)人的記憶也只是拘囿于自我的個(gè)體選擇與遺忘,因此每個(gè)人的真實(shí)記憶中都帶有本能衍射的混沌與錯(cuò)亂,他對(duì)事實(shí)的理解可能是不準(zhǔn)確的,其價(jià)值判斷可能有一定的歪曲性。
“有意識(shí)”,一方面是因?yàn)閿⑹稣叩谋磉_(dá)與他的自我認(rèn)同需求是聯(lián)系在一起的。敘述者講述話語(yǔ)中所蘊(yùn)含的意義體系提供了他自我認(rèn)同的框架,個(gè)體通過(guò)講故事,使自己的經(jīng)歷變得有意義,獲得一種認(rèn)同感,一種身份。他甚至?xí)谝院蟮臍q月中不斷地復(fù)述過(guò)去發(fā)生之事,根據(jù)社會(huì)環(huán)境的變化不斷地改造他們過(guò)去的親身經(jīng)歷,以便保持個(gè)人經(jīng)歷的完整性和連貫性。
由于人的能動(dòng)性和自覺(jué)性,人們總是在利用文化為自己的存在進(jìn)行注解,同樣,也在利用過(guò)去為自己的存在進(jìn)行辯護(hù)。當(dāng)文化不斷地把歷史推到人類(lèi)的視野中的同時(shí),人們似乎也采用相同的策略來(lái)處理歷史的問(wèn)題,那就是把過(guò)去當(dāng)作一種記憶,當(dāng)作一種有利于當(dāng)下存在的記憶。在口述歷史時(shí),人們總是傾向于解釋過(guò)去,把過(guò)去的事情當(dāng)作有利于自己的資源加以談?wù)摗.?dāng)過(guò)去發(fā)生的事情可能為現(xiàn)存的秩序帶來(lái)不利的影響時(shí),人們通常傾向于利用各種手段來(lái)遺忘過(guò)去。根據(jù)現(xiàn)在的需要來(lái)選擇過(guò)去正是人性的一種體現(xiàn)。這是人的一種趨利避害的本能和在這本能基礎(chǔ)上的文化策略。所以,進(jìn)入記憶的歷史總是要和現(xiàn)實(shí)相聯(lián)系,并且也只有被賦予了現(xiàn)實(shí)的意義之后才成為活生生的歷史。正是在這個(gè)層面上,克羅齊所說(shuō)的“一切歷史都是當(dāng)代史”才有了落腳點(diǎn)。(張偉明,2005)
另一方面則表現(xiàn)在,不管受訪者想怎樣客觀地反映事物的本來(lái)面貌,可是由于受訪者在口述歷史訪談中的主角地位,使得這種敘述帶有明顯的表演性質(zhì)。攝影機(jī)的在場(chǎng),觀眾的想象性關(guān)系更是增加了其表演的欲望。對(duì)于一位一生經(jīng)歷有“歷史價(jià)值”的受訪者而言,他(她)們經(jīng)常能清楚的知道自己的社會(huì)角色(知道自己為何受訪),或采訪者已說(shuō)明他或她的期望。或者,他(她)們揣測(cè)訪問(wèn)者的社會(huì)角色與態(tài)度。如此,“過(guò)去”常被選擇性重建(混合本身記憶,以及與他人共同建立的記憶),來(lái)使某種現(xiàn)實(shí)狀況合理化,或解釋過(guò)去與現(xiàn)在的因果關(guān)系,并同時(shí)滿足訪問(wèn)者的需要。
從上述角度來(lái)看,我們或許可以認(rèn)為,在口述歷史中,“歷史敘事是詞語(yǔ)的構(gòu)造,其內(nèi)容既可以說(shuō)是發(fā)現(xiàn)的,也可以說(shuō)是創(chuàng)作的,而其形式與其說(shuō)是與科學(xué)的共性多,不如說(shuō)是與文學(xué)的共性多。”(趙世瑜,2003)盡管歷史影像中敘述的宗旨已經(jīng)脫離了所謂史實(shí)的真實(shí)性范疇而轉(zhuǎn)向了語(yǔ)言的敘述性游戲,如何理解和思考?xì)v史只是口述者個(gè)性化感悟歷史的自然結(jié)果;但是對(duì)電視而言,不可靠的記憶并不是個(gè)多大的問(wèn)題,反而成為一種有利的資源,它使得歷史與故事、真實(shí)與想象達(dá)成了某種程度的默契與融合。因?yàn)榕c歷史學(xué)家“最大可能地復(fù)原歷史,揭示歷史真相”的目的不同,歷史影像的制作人構(gòu)建歷史陳述的任何一個(gè)步驟都是出于藝術(shù)和倫理考慮,歷史的真?zhèn)我褵o(wú)關(guān)緊要。這便是大眾傳播中歷史建構(gòu)的悖論:歷史要求真相,媒介則需要效果。歷史的嚴(yán)肅性漸漸讓步于傳播的娛樂(lè)性需求,收視率的要求使其口述歷史成為一種表演。
此外,我們不僅要看到個(gè)體視角及認(rèn)知的局限性對(duì)于歷史客觀性的妨礙,同時(shí)也應(yīng)考慮社會(huì)語(yǔ)境及媒體生產(chǎn)對(duì)于歷史再現(xiàn)的制約。控制個(gè)人記憶與忘卻的機(jī)制是什么?口述類(lèi)歷史節(jié)目所描述的歷史敘事到底是對(duì)個(gè)人意義的彰顯還是排除與遮蔽?
歷史生產(chǎn):集體記憶的復(fù)現(xiàn)與重構(gòu)
盡管深知“記憶依次不斷地卷入到非常不同的觀念系統(tǒng)當(dāng)中,已經(jīng)失去了曾經(jīng)擁有的形式和外表。”(莫里斯?哈布瓦赫,2002:82-83)但康納頓仍在《社會(huì)如何記憶》一書(shū)的導(dǎo)論中提到:任何社會(huì)秩序下的參與者必須具有一個(gè)共同的記憶。對(duì)于過(guò)去社會(huì)的記憶在何種程度上有分歧,其成員就在何種程度上不能共享經(jīng)驗(yàn)或者設(shè)想。(保羅?康納頓,2000:3)為此,記憶有了延續(xù)和傳承的內(nèi)在訴求。而實(shí)現(xiàn)這一訴求,保持記憶的完整鮮活,惟一可能的方式是記憶的不斷復(fù)現(xiàn)。復(fù)現(xiàn)總是要依賴于特定的方式和載體的,在信息社會(huì)中,電視傳媒成為建構(gòu)人們集體記憶的重要機(jī)制。依據(jù)哈布瓦赫的集體記憶理論,集體記憶不僅僅是對(duì)過(guò)去事件的回顧和描述,還是對(duì)過(guò)去的重構(gòu)。所以,任何歷史題材的文本都不能被簡(jiǎn)單的視為“客觀史實(shí)”的載體。那么,電視是否在某種社會(huì)意義的掌控下,定義何者是“當(dāng)代或過(guò)去重要的人物或事件?”或者,定義“誰(shuí)是知道過(guò)去真相的人”,而授予他們?cè)忈屵^(guò)去的權(quán)力?借著這樣的口述歷史采訪所得資料,仍然為男性、主要族群、知識(shí)階層、政治權(quán)力掌控者所認(rèn)知的過(guò)去,以合理化某種社會(huì)現(xiàn)實(shí)?(王明珂,1996)針對(duì)口述歷史類(lèi)電視節(jié)目,我們可以從個(gè)人記憶的當(dāng)下性以及節(jié)目制作的現(xiàn)實(shí)需求兩個(gè)方面來(lái)探討節(jié)目對(duì)歷史的重構(gòu)。
首先,在口述歷史類(lèi)的節(jié)目中,受訪者的講述具有明顯的事后再認(rèn)識(shí)的因素。在此,被訪問(wèn)者具有雙重身份:歷史事件的見(jiàn)證者與歷史文本的閱讀者。作為“歷史事件的見(jiàn)證者”的角色,被訪問(wèn)者更接近于歷史對(duì)象的歷史情境,在這個(gè)意義上他是歷史文本的“行動(dòng)作者”,它可以對(duì)歷史對(duì)象的解釋進(jìn)行發(fā)揮,滲透他的主體意識(shí)。同時(shí),被訪問(wèn)者卻還具有另外一種角色——?dú)v史文本的閱讀者。在口述采訪中,被訪問(wèn)者更大程度上擔(dān)任和表現(xiàn)的是其作為歷史文本閱讀者的角色。這兩種角色成分并不是分開(kāi)的,它們同存于被訪者個(gè)體之中。閱讀者角色常常在影響著“歷史事件的見(jiàn)證者”角色的正常發(fā)揮,因?yàn)殚喿x者身處特定的社會(huì)大環(huán)境,必然受其影響,顯示出講述的時(shí)代性。(陳旭清,2006)在鳳凰衛(wèi)視的《口述歷史》節(jié)目中,講述人楊麟表現(xiàn)了以往歷史記載中“心狠手辣、殺人如麻”的“大流氓”杜月笙“精通做人之道、有著一身的俠氣和一顆鮮明的愛(ài)國(guó)心”的一面,這與當(dāng)前對(duì)歷史事件、人物的復(fù)雜性進(jìn)行重新解讀的社會(huì)文化傾向是分不開(kāi)的。因此,雖然被訪問(wèn)者對(duì)于歷史對(duì)象的講述是個(gè)人化的,但不是無(wú)限開(kāi)放的,而是存在集體記憶、社會(huì)語(yǔ)境的制約。個(gè)人“自我的敘事離不開(kāi)自我所屬的地方文化體系,該體系內(nèi)的解釋實(shí)踐自然會(huì)對(duì)自我的敘事產(chǎn)生影響。”(諾曼?K?鄧金,2004:67)正如保羅?湯普森的著作《愛(ài)德華時(shí)代的人》的一位批評(píng)家指出的:“歸根結(jié)底,他那些‘愛(ài)德華時(shí)代的人’活下來(lái)變成了‘喬治時(shí)代的人’,而現(xiàn)在又成為‘伊麗莎白時(shí)代的人’。經(jīng)歷了這些歲月,一些往事在記憶中消失了,或至少關(guān)于這些往事的回憶也會(huì)受到后來(lái)經(jīng)歷的影響。”(約翰?托什,1987)
其次,在節(jié)目制作過(guò)程中,無(wú)論是選題還是嘉賓的選擇都無(wú)不體現(xiàn)出當(dāng)前政治現(xiàn)實(shí)的需要。在英美等國(guó),口述歷史主要被作為一種打破傳統(tǒng)史料來(lái)源局限的有限方法,廣泛地運(yùn)用于諸如經(jīng)濟(jì)史、勞工史、社會(huì)史、政治史、企業(yè)史、部落史、宗教史等研究領(lǐng)域,人們希望歷史研究從此可以避免單一政治史研究的弊端,關(guān)注整個(gè)社會(huì)生活的方方面面。但是,我們所看到的口述歷史類(lèi)電視節(jié)目,其最有意義和可行性的選題,幾乎都是忠于時(shí)代的要求的。那些“在地方上經(jīng)常被人們提及的、并樂(lè)于言說(shuō)的話題,處于集體記憶的高密度區(qū)域”( 陳旭清,2006)的熱點(diǎn)問(wèn)題被反復(fù)提及,如抗戰(zhàn)訪談中關(guān)于艱苦、戰(zhàn)斗的訴說(shuō),文革時(shí)代關(guān)于政治斗爭(zhēng)、知青生活的講述,以及政治領(lǐng)袖、英雄人物的生平往事。而那種年復(fù)一年、日復(fù)一日的日常生活,由于其自然、平淡、習(xí)以為常而往往為人們所不屑一提。
正如哈布瓦赫所指出,“許多社會(huì)活動(dòng)都是為了強(qiáng)調(diào)群體的某些集體記憶,以延續(xù)并鞏固該群體的凝聚。”(莫里斯?哈布瓦赫,2002:70-94)由此出發(fā),能夠加強(qiáng)群體凝聚的集體記憶常常被人們所強(qiáng)調(diào),而那些與群體凝聚無(wú)關(guān)的、或者是不利于群體凝聚的集體記憶,則往往容易被群體所忽略、扭曲,甚至刻意遺忘。任何社會(huì)群體的歷史都是該人群共同體對(duì)特定歷史情境作出選擇性記憶與敘述的結(jié)果,選擇的標(biāo)準(zhǔn)通常就是特定社會(huì)現(xiàn)實(shí)所造成的群體利益需求。當(dāng)外在的利益環(huán)境發(fā)生變遷時(shí),群體通常會(huì)重新調(diào)整記憶中的歷史事實(shí),并且不斷發(fā)現(xiàn)或創(chuàng)造新的集體記憶與歷史敘述,以激發(fā)起群體新的認(rèn)同和凝聚。(王明珂,2006:24-33)鳳凰衛(wèi)視《口述歷史》欄目于2008年10月18日制作了一期《通海大地震揭秘》的節(jié)目,講述了1970年發(fā)生在云南通海的地震由于特殊的歷史背景消息被封鎖、被隱瞞的往事,該事件讓人們聯(lián)想起發(fā)生在2008年5月份的四川大地震,與歷史類(lèi)似事件的對(duì)比,讓人們對(duì)當(dāng)前政府的信息公開(kāi)政策、執(zhí)政能力產(chǎn)生了較大程度的認(rèn)同。正所謂“世界上其實(shí)本來(lái)無(wú)所謂焦點(diǎn)和背景,只是觀看者有了立場(chǎng),有了視角,有了當(dāng)下的興趣,這時(shí)回頭看去,便有了焦點(diǎn)和背景,面前的世界于是有了清晰和模糊的差異。”(葛兆光,2001)
此外,口述歷史還主張,要“自下而上”的研究歷史,歷史的研究對(duì)象不應(yīng)再是充斥以往歷史著作的帝王將相、王公貴族等上層精英,而是普通的民眾及其經(jīng)驗(yàn)與情感。在口述史學(xué)家看來(lái),“來(lái)自社會(huì)底層的不同群體有能力形成自己的亞文化和非政治行為,有能力在他們自認(rèn)為最重要的領(lǐng)域里發(fā)揮決定性的作用。”(陸象淦,1988:220-225)只有大量引進(jìn)來(lái)自下層民眾的口述憑證,才能夠充分認(rèn)識(shí)民眾的歷史作用。保羅?湯普遜評(píng)價(jià)其“意味著歷史重心的轉(zhuǎn)移”、“具有某些激進(jìn)的意涵”。(保爾?湯普遜,2000:6)
但是,口述歷史類(lèi)節(jié)目中的受訪者大多為政治精英和文化精英,無(wú)論是時(shí)間關(guān)系、歷史因果關(guān)系,在敘述歷史的進(jìn)程中,這些必不可少的“歷史轉(zhuǎn)換語(yǔ)”都是精英們掌握的基本話語(yǔ)技術(shù)。正是這些話語(yǔ)技術(shù),使精英和普通民眾區(qū)分開(kāi)來(lái),成為一種新的權(quán)力運(yùn)作方式的基礎(chǔ)。(李猛,1998)上文所提到的《見(jiàn)證?親歷?紀(jì)念改革開(kāi)放三十年之生于一九七八年》這期節(jié)目,盡管采取了以個(gè)人生活史觸摸宏觀歷史的制作模式,但是所選取的五個(gè)講述人,都是主編、主持人、公司經(jīng)理等,并沒(méi)有涉及生于一九七八年的不知名人士。可見(jiàn),普通百姓無(wú)法擁有表達(dá)并傳遞記憶的有效渠道,很難指望他們的經(jīng)歷能夠進(jìn)入影像歷史的話語(yǔ)空間。他們對(duì)歷史的作用是用被概化的“范疇”(比如“人民”、“勞動(dòng)人民”或者“貧農(nóng)”等等)來(lái)計(jì)算的。
節(jié)目之所以挑選某一個(gè)人作為受訪人,盡管牽涉到主事者對(duì)歷史意義的考量,例如能夠填補(bǔ)歷史的空白,或能否解答歷史演變的關(guān)鍵問(wèn)題等,然而更多時(shí)候考慮的卻是,該敘述文本制成之后是供何種消費(fèi)者來(lái)閱讀,而此一消費(fèi)需求能否鼓勵(lì)生產(chǎn)?許多口述歷史類(lèi)節(jié)目的精英定位使得它們并沒(méi)有擺脫傳統(tǒng)的“英雄史觀”的束縛。就算在節(jié)目中我們看到了普通人的講述,那也是為了讓人們了解偉人們的思想、行為如何影響到了普通人的世界觀,而非真正挖掘普通人的生命歷程、文化價(jià)值及心態(tài)如何與宏觀的社會(huì)背景鑲嵌咬合。普通人仍然是證據(jù)不足的存在者,個(gè)體經(jīng)驗(yàn)的意義仍然欠缺著。因?yàn)槿绻麄€(gè)人經(jīng)驗(yàn)只有貼上了某種特殊的歷史標(biāo)簽才有意義,這其實(shí)正是對(duì)個(gè)體經(jīng)驗(yàn)的抹煞。
綜上,口述歷史類(lèi)節(jié)目以私人記憶、民間記憶的方式,憑借其豐富生動(dòng)的敘事藝術(shù),在某種程度上改變“國(guó)家失憶”的局面,(朱大可,2004)其歷史內(nèi)容可能是虛構(gòu)的,其建構(gòu)大眾歷史意識(shí)的社會(huì)影響卻是不容否認(rèn)的事實(shí)。但我們不得不警惕的是,應(yīng)該防止歷史的個(gè)人化敘事走向一種淺薄的消費(fèi)主義思潮,把對(duì)集體記憶的建構(gòu)轉(zhuǎn)化為一場(chǎng)刺激眼球與收視率的大眾文化鬧劇。同時(shí),對(duì)于無(wú)法書(shū)寫(xiě)自己的歷史甚至無(wú)法發(fā)出自己聲音的底層人民,我們的口述節(jié)目更應(yīng)遵循口述史的初衷,力圖為其拓展一方講述的空間,在其中,普通民眾能夠自主地講述他們的經(jīng)歷、感受和歷史評(píng)判。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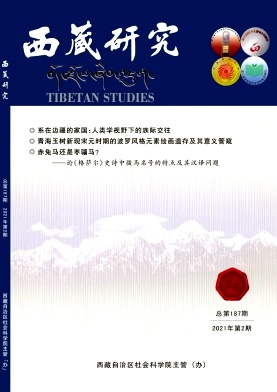
鳴.jpg)
展研究.jpg)
學(xué)院學(xué)報(bào).jpg)

家致富顧問(wèn).jpg)
于我們.jpe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