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個(gè)人解讀”:余秋雨散文“轟動(dòng)效應(yīng)”的表達(dá)秘密
司馬曉雯
無論是褒揚(yáng),還是貶抑,余秋雨散文對(duì)大多數(shù)人都具有無法抗拒的誘惑。僅僅把這一現(xiàn)象歸結(jié)于 “媚俗”或“媚雅”,是講不通的。“媚俗”指的是一種取媚于讀者的寫作態(tài)度。而余秋雨散文具有嚴(yán)肅的內(nèi)容,“秋雨散文(即令是那些怡情悅性的藝術(shù)散文),均不能作為茶余寢后的消遣小品來閱讀。那細(xì)細(xì)密密文字朝你傾瀉的是大氣磅礴的理性思索——那雄健剛直的風(fēng)骨,留給你的不是典麗有余的風(fēng)花雪月,不是自娛自耗的貧血性呻吟,不是八九十年代流行于文壇的小女人小男人斷了脊梁骨的纏綿,它是一種宏大恢廓的文化目標(biāo)的建樹”。而“媚雅”這一說法更是無稽之談,余秋雨不僅是頗有成就的學(xué)者、教授,而且其散文內(nèi)容是嚴(yán)肅的文化,何來“媚雅”之說?這只是表明言者對(duì)通俗語言承載高雅內(nèi)容的不理解而已。 那么余氏散文激起人們閱讀興趣的原因是什么呢? 對(duì)此評(píng)論界眾說紛紜,有的認(rèn)為“主要因了他超群的思辨力和知識(shí)結(jié)構(gòu)。他的思維場(chǎng)中,比一般作家多了學(xué)者深邃的文化感悟力和數(shù)十年積累的史學(xué)功底,又比一般史學(xué)家多了層雄厚的藝術(shù)底蘊(yùn)和天賦的文字表現(xiàn)力;加上他對(duì)哲學(xué)人類學(xué)歷史地理學(xué)的融合,他的作品就具備了‘轟動(dòng)’的條件”,有的認(rèn)為“根本原因在于他突破了傳統(tǒng)散文的創(chuàng)作模式”。而余秋雨自己認(rèn)為“當(dāng)我們放下架子,以一種平等的姿態(tài),以一種較為放寬的形式,表達(dá)我們的思考時(shí),才有可能獲得其他生命的回音”。這段話提示我們,揭示清楚余秋雨“個(gè)人解讀”視角藝術(shù)化表達(dá)問題才是明了其散文引起普遍關(guān)注的鑰匙。 “個(gè)人解讀”這一指稱無疑具有兩重性。“解讀”是一種理性的行為,是運(yùn)用概念、判斷、推理等理性思維要素,采用邏輯推理或?qū)嵶C的方法去分析、解釋自然物理現(xiàn)象和社會(huì)精神現(xiàn)象的方法。通常來講,“解讀”方法多用于學(xué)術(shù)研究,這一方法的運(yùn)用應(yīng)該遵守嚴(yán)謹(jǐn)?shù)膶W(xué)術(shù)規(guī)范和客觀規(guī)律。然而,人是感性和理性兼具的動(dòng)物,許多時(shí)候很難把二者截然分開。從時(shí)代精神來看,中國(guó)的上世紀(jì)80年代末90年代初,文壇散文仍沉迷于國(guó)家民族話語的重復(fù)或者個(gè)人閑適生活的囈語,文學(xué)尤其散文幾乎處于“失語”狀態(tài),在這種時(shí)候,文壇需要呼喚理想,呼喚深刻的思考;應(yīng)該說,這種“時(shí)代需要”與《文化苦旅》甫出時(shí)廣受贊譽(yù)不無關(guān)系。在《文化苦旅》以后的創(chuàng)作中,余秋雨散文一直以個(gè)人獨(dú)立的理性思考為框架。余秋雨散文對(duì)歷史文化現(xiàn)象的理性“解讀”,一度讓許多讀者甚至評(píng)論界產(chǎn)生嚴(yán)重的誤讀,他們隨著自己的閱讀思維定勢(shì),把余秋雨散文當(dāng)成學(xué)術(shù)論文來讀,文學(xué)學(xué)者、文化學(xué)者、歷史學(xué)者一擁而上,指出其中的所謂“硬傷”、“余教授做學(xué)問如此隨意”。筆者之所以在“解讀”之前加了“個(gè)人”,便是因?yàn)樯⑽脑诙鄶?shù)情況下是個(gè)體全部經(jīng)驗(yàn)和精神生命的裸露,是散文家生命意識(shí)和生命觀點(diǎn)的自然流露,也正由于這一點(diǎn),散文作為一種包容性很強(qiáng)的文體才有它存在的價(jià)值,否則,讓想象力和情感豐富的人都去寫詩歌,讓擅長(zhǎng)邏輯思考的人都去寫論文,散文還有誰來寫?余秋雨是一位對(duì)文明、文化有極強(qiáng)感悟力的學(xué)者,同時(shí)也是一位有強(qiáng)烈社會(huì)責(zé)任感和現(xiàn)代意識(shí)的作家,因此他的“個(gè)人”就必然牽扯著厚重的文人觀念、知識(shí)分子意識(shí)。 那么余秋雨與中國(guó)傳統(tǒng)文人一脈相承的對(duì)民族文化、歷史使命、文明傳播的強(qiáng)烈憂患意識(shí)是通過怎樣的藝術(shù)方式表現(xiàn)出來的呢? 首先是對(duì)話式的議論。在文學(xué)批評(píng)領(lǐng)域里,“對(duì)話”這一概念和巴赫金的“復(fù)調(diào)小說”理論是分不開的,它指的是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等作家的小說里,不單是敘述者一個(gè)人在說話,有兩個(gè)聲音在說話。余秋雨散文的“對(duì)話”與巴赫金的“對(duì)話”雖然不完全等同,卻也有相似之處。即與傳統(tǒng)散文比,在余秋雨的散文中我們常常能聽到對(duì)話的聲音:第一是作者與那些“遠(yuǎn)年靈魂”的對(duì)話,似乎他們?cè)缫颜J(rèn)識(shí)、對(duì)坐長(zhǎng)談。余秋雨在探詢古代文化遺跡或文化現(xiàn)象的過程中,著力于剖析歷史個(gè)案——即是他筆下經(jīng)常出現(xiàn)的“遠(yuǎn)年的文化靈魂”。如《陽關(guān)雪》中的王維、《柳侯祠》中的柳宗元、《都江堰》中的李冰、《風(fēng)雨天一閣》中的范欽、《千年庭院》中的朱熹、《蘇東坡突圍》中的蘇東坡等,作者對(duì)這些具有“較為健全的文化人格”的歷史人物并非提到而止,而是盡可能再現(xiàn)歷史情境、探索人物的心路歷程,當(dāng)然這種探索中滲透著作者的傾向性和價(jià)值觀。當(dāng)讀到《蘇東坡突圍》中“成熟是一種明亮而不刺眼的光輝,一種圓潤(rùn)而不膩耳的音響,一種不再需要對(duì)別人察言觀色的從容,一種終于停止向周圍申訴求告的大氣,一種不理會(huì)哄鬧的微笑,一種洗刷了偏激的淡漠,一種無須聲張的厚實(shí),一種并不陡峭的高度……”時(shí),已經(jīng)分不清作者寫的是中年的蘇東坡還是中年的余秋雨了。第二是作者與讀者對(duì)話。無論作者走到哪里,他總是忘不了讀者、面向讀者,在與古人對(duì)話之后,自己便出現(xiàn),通過對(duì)話式的議論向讀者介紹自己的經(jīng)歷和體驗(yàn)。許多歷史散文都是獨(dú)白式的,或是歷史的洪流淹沒了個(gè)人的聲音,或是在個(gè)人獨(dú)斷的聲音中讓歷史成為僵死的客體,余秋雨打破了這種個(gè)人與歷史二元對(duì)立的僵局,通過這兩對(duì)“對(duì)話”行為拓展了文章的空間,也吸引了讀者,讀者不僅能欣賞到別人的交談,還時(shí)刻能感受到自己在歷史時(shí)間和文化空間中的存在,這樣,讀者就不再只是在文本之外觀看作者的炫耀學(xué)識(shí)或是演繹自己的人格魅力,也不再駐足歷史文化之外對(duì)曾經(jīng)的風(fēng)風(fēng)雨雨采取漠然中立的認(rèn)知式態(tài)度,而是被作者邀請(qǐng)進(jìn)去,進(jìn)入文本營(yíng)造的話語空間和歷史文化空間,和作者一道去經(jīng)歷一番文化苦旅。在他那圓熟的語言技巧經(jīng)營(yíng)出的具有魔咒般魅力的文字的感召下,讀者也被帶到了特定的歷史文化場(chǎng)景中,個(gè)人的生命之流與歷史的洪流渾融一片……這樣,又形成了讀者與歷史的對(duì)話。由此我們看到:余秋雨的對(duì)話在兩個(gè)層面展開而形成了多重對(duì)話的格局。在這多重對(duì)話中,余秋雨以自我的敞開博得了歷史的敞亮。
學(xué)院學(xué)報(bào).jpg)
.jpg)
江師范學(xué)院學(xué)報(bào).jp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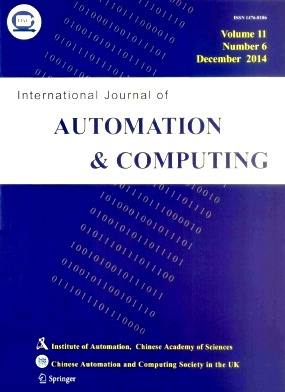

于我們.jpe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