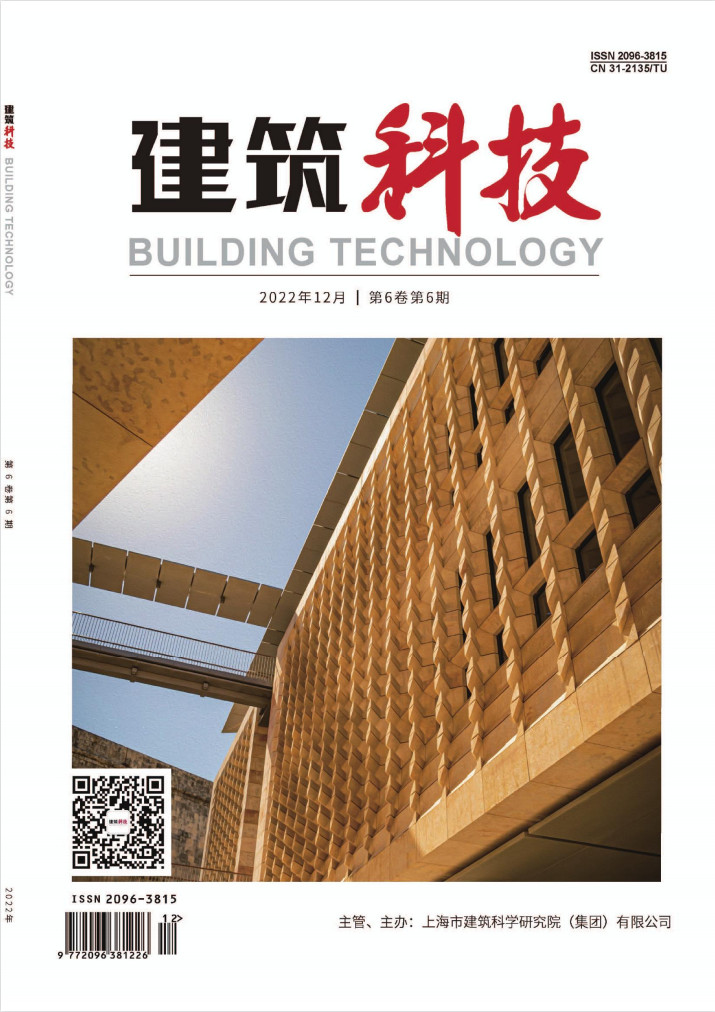淺論文化的批判與歷史的重構——《恥》的流散文學解讀
朱安博
論文關鍵詞:流散文學庫切的《恥》文化批判與重構
論文摘要:在當今全球化語境下,流散文學研究近年來引起了國內外的高度重視。從民族和文化身份的角度來閱讀分析流散文學文本己經成為文化研究中的一個熱門話題。本文以庫切的《恥》為代表從文化視角對流散文學進行深刻的剖析,關注流散的生存狀態來喚醒歷史意識,反思造成這一切的歷史文化根源,并對南非的實際存在狀態做出了歷史和現實批判,并試圖構建新的價值觀念以警醒族人重構文化模式。
在后現代多元文化主義浪潮中,原先處于被忽視的邊緣地位的弱小勢力受到了重視。這種現象反映到諾貝爾文學獎中,便是弱小國家、民族或有多元文化背景的作家受到了格外的重視。考察近20多年來的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我們可以發現一個有趣的現象:80年代以來的獲獎者大多數是后現代主義作家,90年代前幾年是有著雙重民族文化身份的后殖民作家,到了90年代后半期,大部分則是流散作家。通過近幾年流散文學的發表,可以說流散文學在新世紀的世界文學領域已經發揮了舉足輕重的作用。流散文學的一個重大特征就在于它實際上不是“移民文學”這樣簡單化的稱呼所能概括的,它體現了本土與異國之間的一種文化張力:相互對抗又相互滲透,從而體現了全球化時代的一種獨特的文學現象。
2003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是南非作家J. M.庫切(CJ. M. Coetzee, 1940一),瑞典皇家頒獎委員會在其頒獎辭中指出:“在人類反對野蠻愚昧的歷史中,庫切通過寫作表達了對脆弱的個人斗爭經驗的堅定支持。”庫切代表作有《在祖國的心靈中》(In. the Heart of the Country ), ((等待野蠻人))(Waiting for the Barbarians ) ,((邁可爾·K的生命與時代))) ( Li fe and Times o,f Michael K.) ,《恥))(Disgrace)等。本文嘗試通過對庫切這位在21世紀大門口獲獎的流散作家作品《恥》的分析,尋找他的不同的價值取向,以民族和文化身份為切人點來認識流散者在其文學創作中是怎樣作著跨越民族、族裔界限旅行式的思考的。
作為殖民者流亡的庫切對殖民地文化一直保持著清醒而尖銳的認知。面對他的祖國南非,庫切始終在直面現實。他的作品幾乎都有一個共同的主題:描述種族隔離制度造成的悲慘后果及種族制度下個人存在的不自由。他是“南非種族隔離矛盾現實最好的闡釋者之一”。庫切的偉大就在于他對歷史、對未來的洞察力:“他是堅持為人類作證的作家,忠實于人類苦難記憶的作家,也是最富有時代感的作家”。
庫切的所有作品中,長篇小說《恥》具有相當的代表性。在這部書中,庫切用平淡、冷峻的筆調為我們講述了一個發生在新南非的故事,揭示了新舊交替時代發生在南非大地上、發生在各色人種之間的種種問題,對殖民主義在南非對殖民地人民和殖民者本人及其后代所造成的后果表現出深切的憂思和相當的無奈。
故事的主角是開普敦大學的一位教授、浪漫主義詩歌專家盧里。小說一開始就道出了他在老的政治背景和所謂新的政治變革中的生活處境和人生狀態。他每周和一位妓女約會解決基本問題,后來引誘一位女學生。被校方發現后,不愿乞求校方寬恕,最終辭職,帶著恥辱的印跡,前往女兒露西的農場尋求平靜生活。然而,在農場里露西遭三個黑人打劫和強奸。盡管盧里不愿忍受這種恥辱,女兒卻不愿逃避,她寧愿委曲求全,隱居在鄉下的農場上苦心經營著自己的一小片園地,渴望在這片土地上努力拓展一小片生存的空間,想按照自己價值觀中那種理想的活法,為白人過去對黑人的非人道統治贖罪。
故事情節上雖然沒有過于離奇的地方,卻處處充滿了恥辱所帶來的巨大震撼,將南非種族之間的隔膜表現得淋漓盡致。單從書名“恥”來說,“恥”的表現是多方面的:有大學教授每周定時召妓以解決生理需求之恥,有大學教授誘奸女學生進而丟掉教職之恥,有教授女兒“自甘墮落”之恥。透過字里行間,顯然還有一種恥,那就是作者一直不愿直接提及但在他所有的作品中都得到了象征性表達的南非的國家之恥一種族隔離制度。書中之“恥”,不僅僅是一個家庭的個人之“恥”,同時更是南非白人的民族之“恥”。
這一點在“恥”這個貫穿全文的線索上得到了集中的體現。整部小說從“恥”字出發,串連起事件和人物,層次豐富。個人命運和國家歷史緊緊相扣,歷史傳統和個人記憶交相輝映。南非種族隔離制度的歷史記憶仍然深植在人們心中,盡管這種制度作為制度已經成為過去。這種歷史記憶在現實中被一再地血淋淋地展現出來。在小說的全部敘述中,露西的被強暴成為一個觸目的“中心”:露西拒絕向警察告發此事:“我為什么沒有向警察告發這件事?我告訴你,只是你從此不許再提它。原因就是:發生在我身上的事情,完全屬于個人隱私。換個時代,換個地方,人們可能認為這是件與公眾有關的事。可在眼下,在這里,這不是。這是我的私事,是我一個人的事。這里是什么地方?這里是南非。”如果沒有種族隔離的歷史和由于種族隔離造成的不同種族、膚色間的現實仇恨,那么積淀下來的對抗性的文化中就沒有種族主義、民族主義的情緒,一樁強奸案便會面對同一種文化認同下的道德評判。但是,種族隔離的歷史一記憶使得社會道德框架內部產生了對黑人和對白人不同的道德評判標準。
《恥》又具有超越南非社會現實的普遍意義,是一個后殖民世界中人類種族關系的寓言。殖民統治結束后,其危害仍在繼續。小說中沒有直接描述昔日的殖民統治,但從黑人對白人后代的仇恨中便可知道,當年黑人曾遭受白人殖民者何等殘酷的蹂廂。三個黑人的行為既非為滿足生理欲望,也非出于露西個人的原因,而僅僅因為露西是白人,為了發泄仇恨,是對白人殖民者的一種報復行為。三人當中有一個是小孩,如此自幼在心里埋下對白人仇恨的種子的孩子長大了會如何對待白人,是可想而知的!露西的命運則表明,白人殖民統治在南非的受害者不僅僅是黑人,還有他們 自己的后代。在歷史上,白人是以自身所享有的優越感,以教化、拯救、征服而月_高高在上的姿態出現在黑人土地上的,盡管這種越界行為被涂上了冠冕堂皇的色彩,但絲毫不能掩蓋其侵略的本質。露西的被強暴便是這種越界所必付的代價:她成了這一歷史罪責的受害者,白人殖民者的替罪羊。露西選擇“恥辱”地繼續生活在鄉村,表現的是庫切對后殖民時代種族關系的一種認識:發生在她身上的一切只是一種異乎尋常的賠償形式,這筆債務是她作為一名白人不得不償還的,因為她與數十年壓迫黑人的種族隔離制度之間有著一種被動的同謀關系,她要直面過去的罪惡,尋找新的生活模式和希望。庫切提醒人們注意:種族隔離制度雖然已經取消了,但是殖民地的文化中種族對抗的陰毅并沒有完全消除。作為一名真正的公共知識分子,他“要建造自己的權威,以自己的表達方式去呈現死亡和受苦。”他以自己的文本完成了對歷史意識的重建,“召喚聽眾遺忘了的東西”。盡管歷史的積怨和露西無關,歷史的輪回依然沒有逃出這一戲劇性的反諷定律。歷史的罪責必須有人來承擔,即使她是無辜的。這就是她比盧里更能坦然面對這一暴力事件的原因。
殖民主義的代價首先在最為個人的層次上表現出來,露西決心承受任何恥辱,“卻因為所有外在尊嚴的被剝奪而獲得了新的力量”。殖民主義在殖民地所代表的整個西方(歐洲)文明也為此付出了代價:盧里的滿腹經倫、滿口外語(西班牙語、意大利語等)在遇到突發情況(家里遭搶劫、女兒遭強暴)時,什么用場都派不上;他動不動要求得到正義的呼聲如對牛彈琴;在佩特魯斯家的聚會上撞見了施暴嫌疑人,立刻想打電話叫警察這樣典型的西方式反應,顯得那么滑稽可笑,又蒼白無力;作為西方文化教養之人,居然沒想到參加正式聚會應當戴條領帶,如此等等。甚至連西方文明和殖民文化的載體、賦人以某種權勢和力量的英語,在南非這塊大地上也失去了明晰性。語言也是一種文化最外在的品格,當一個人對自己所屬的文化產生懷疑時,便會對語言本身的魅力失去自信。盧里有一段內心獨白就是他這種心境的寫照:“他越來越堅信,英語極不適合用作傳媒來表達南非的事。那一句句拉得長長的英語代碼已經變得十分的凝重,從而失去了明晰性,說者說不清楚,聽者聽不明白。英語像是頭陷在泥潭里的垂死的恐龍,漸漸變得僵硬起來。要是把佩特魯斯的故事硬壓進英語的模子,出來的東西一定是關節僵硬,沒有生氣。”真正有力量的,真正能恰當真實地傳達人在此時此地的思想感情的,仍然是當地的土語。這樣,強行進人非洲(南非)的西方文明從根華到形式都被消解掉了。在這個意義上,庫切等流散作家只是借用了英語這種語言作為文學書寫的載體,但英語所蘊涵的傳統卻為其摒棄。因此,他木僅是身體上的流散者,也是信仰上的流散者。 文化批判不同于政治批判,也不同于道德批判,它是對于文化的梳理、考察、審視和反思。庫切以真實的批判精神和思想的深刻性,無情地揭露和批判了后殖民世界中意識形態對人的奴役以及頹敗停滯的精神狀態,現代人所面臨的問題已經不僅僅是由于勞動產品的異化而引發的政治經濟困難,而更多地是表現為意識形態等文化形態奴役下人們自由自覺意識的喪失。
庫切的《恥;.首先就表現出了意識形態對人的生存狀態的影響。意識形態已經滲透到現代人的性格結構之中,成為人們習以為常的一種生活方式。這種性格結構的形成并不是隨機與偶然的,而是在社會統治層的誘導下生成的,并且潛移默化地滲透到人的生活中去。這一觀點與法蘭克福學派提出的文化批判理論頗有相似之處。法蘭克福學派的成員們認為,“從本質上看意識形態是一種虛假的意識,它具有很大的欺騙性,它是人們生活于其中“的分裂與異化的社會生活的真實寫照,它的主要功能是通過美化現實生活而替現狀辯護,這種辯護的功能不僅僅通過思想宣傳來實現,而且已經通過其他手段內化到人們的心理機制件”。”馬爾庫塞認為“社會控制的現行形式在新的意義上是技術的形式。”技術合理性即是指意識形態把否定思維變成肯定思維,理性沒有了原先所具備的批判和否定意識,喪失了指導人們實現自由的價值判斷。在技術合理性的名義下,人們內心的否定性、批判性和超越性的維度被成功地操縱和壓制了,人成為麻木不仁的“單向度的人”。其實,馬爾庫塞批判現實社會就是要喚醒人們的反抗意識,這種反抗不是指暴力斗爭,而是要人們保持清醒的頭腦,不能喪失人之所以為人的能力—否定和批判,不做單向度的人。
庫切正是運用了形式語言的力量去摧毀異化現實的社會語境。“藝術正是憑借形式超越了既有的現實,在現存現實中反對現存現實。”庫切以否定的辯證法對現代社會進行了病理診斷,提供了批判的靈感和武器,用否定的藝術的形式來拯救衰敗,這是其對當代社會最可貴的現實意義。透過他的文化批判,可以看到他們在歷史批判和現實批判中的自省,對一于南非實際存在狀態的一種異在性、對抗性和超越性,可以看到體現了一種終極關懷的當代人文精神的理想特質。
庫切的《恥》通過個人命運和國家歷史的相互對照中實現的一種凝重的社會歷史感,明確地告訴了我們一個事實-—政治權力的變遷對于根除人類的苦難顯得無能為力。“流散,從一個具有專門意指的、鮮為人知的語匯,現在已經發展成為一種對當代后殖民文化與認同經驗的總體解釋,與全球化相提并論。流散,其實不必是物質性身體的移位。流散是一種深刻的無奈,又或許,流散是一種與母體撕裂的傷痛;但在富有創造性的后殖民理論家那里,流散又是一種特權、一種不可多得的優勢”。庫切等流散作家在生活經驗層面上尋找自我歸宿、在本土文化與西方文化對立中進行文化思索,在異國主流文化中確立文化歸屬這幾個層面上完成文化認同,從而體現有著“文化本位”的特質。
當一種文化秩序窒息了人類的創造性時,需要一種適應新時代要求的文化的建構來顛覆舊有的意識形態,文化批判即是文化重構的前提。文化批判不僅是否定性、消解性的,而且也是建設性、構成性的。庫切批判的目標并不是批判本身,而是為了激發行動的力量,從而使得人們擺脫病態的存在狀態。要實現這一目標有賴于生成一種新的文化模式取代現存的異化的存在模式,也就是文化重構,文化批判的現實意義也就在此。
通過庫切對意識形態壓制人、約束人、奴役人現象的批判,可以看出后殖民地的文化應適應歷史進程而重構出一種新型文化的最佳模式。一種成熟文化模式的創建,必須有價值系統的奠定來支撐。在南非,盡管種族隔離制度已經被取消,但是小說中的人們始終還是處于種族隔離意識的陰影之下,吞食著種族隔離制度造成的悲慘后果。南非要擺脫意識形態的控制,應該正視過去,更好地了解過去。在那片有著殖民歷史的土地上,無論黑人也好白人也好,都是歷史的替罪羊,沒有人是自由的。庫切希望人們通過關注生存狀態而喚醒歷史意識,反思造成這一切的歷史文化根源與歷史的構成方式,從而構建新的價值觀念。
我們今天在閱讀那些流散作家的作品中,往往不難讀到其中隱匿著的矛盾的心理表述:一方面,他們對自己祖國的某些不盡人意之處感到不滿甚至痛恨,希望在異國他鄉找到心靈的寄托;另一方面,由于其本國或本民族的文化根基難以動搖,他們又很難與自己所定居并生活在其中的民族國家的文化和社會習俗相融合,因而不得不在痛苦之余把那些埋藏在心靈深處的記憶召喚出來,使之游離于作品的字里行間。由于有了這種獨特的經歷,這些作家寫出的作品往往既超越本民族固定的傳統模式同時又對這些文化記憶揮之不去,因此出現在他們作品中的描寫往往就是一種有著混雜成分的“第三種經歷,’。正是這種介于二者之間的“第三者”才最有創造力,才最能夠同時引起本民族和定居地的讀者的共鳴。
流散者自覺或被迫地遠離各種各樣的“原初聯系”(家族、土地、傳統關系等),散居在世界各地,經歷了一種“失根”和“漂泊”的狀態,成為無數個體痛切感應到的普遍處境。流散者在他們的文學創作中作著跨越民族、族裔界限旅行式的思考,呈現出情感的多樣化,如渴望、錯位、身份的模糊或喪失、尋求身份認同、靈魂歸宿等等。從流散文學作品中可以看出,流散者反對固化身份,提倡混合身份。他們采取客觀的態度觀察生活在文化移位狀態中的人群,既有同情,又有反諷,抵制了文化上的同化,同時又以跨民族的眼光和文化翻譯的藝術進行新的文化實驗,成為了當代世界文學的一大景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