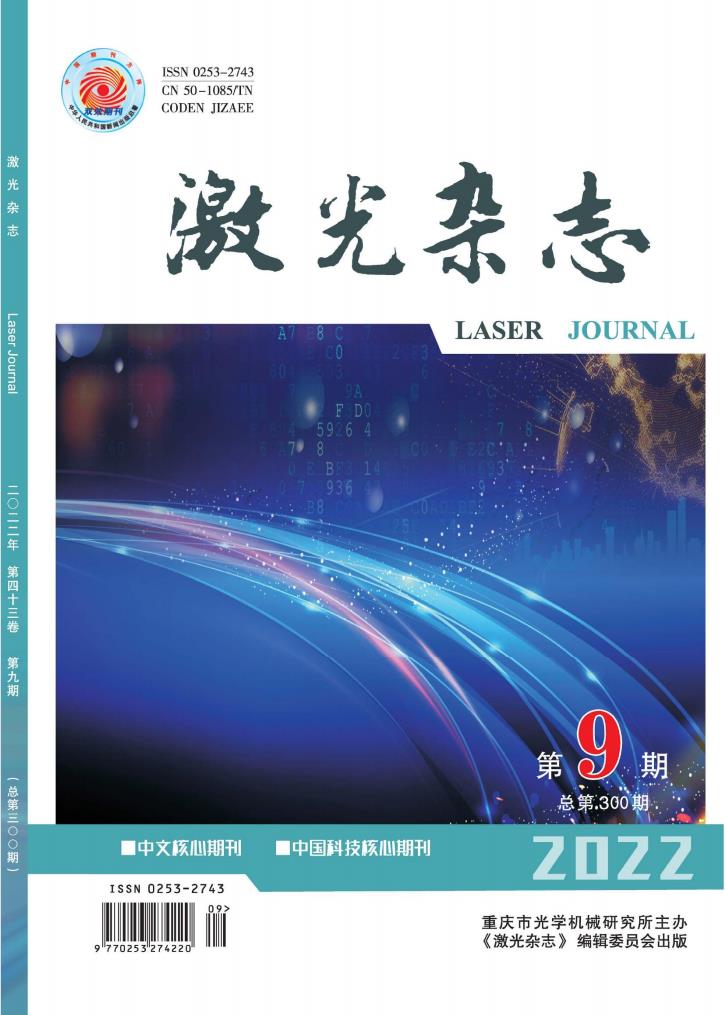試談西方之眼 東方之魂——論中西精神資源對林徽因文學創作的影響
姜煒
論文關鍵詞:林徽因中西精神資源影響
論文摘要:林徽因學貫中西,她深受西方浪漫主義、象征主義、現代主義、人文主義等思潮的影響.同時中國傳統文化中的禮教婚姻觀、儒家的生命本體觀、詩畫意境創作手法也滲入到林徽因的靈魂中。中西兩方面的精神資源在林徽因的文學創作中相互碰撞并融合。本文旨在通過唯美的浪漫與超脫的性靈、含蓄的象征與詩畫的意境、先鋒的現代技巧與傳統的敘事技巧、西方的現代思潮與東方的文人情懷這四個方面的對比闡述.對林徽因的文學創作中受到的中西精神資源進行梳理和分析。
“在現代中國的文化界里。母親也許可以算得上是一位多少帶一些‘文藝復興色彩’的人,即把多方面的知識與才能——文藝和科學的、人文學科和工程技術的、東方和西方的、古代和現代的——匯集于一身,并且不限于通常人們所說的‘修養’,而是在許多領域都能達到一般專業者難以企及的高度。”——梁從誡
林徽因是20世紀上半葉深受新月詩派影響的著名詩人,京派文學的重要代表作家,同時也中國現代建筑學的先驅。林徽因出生在有一定民主氣氛的家庭,追求憲政的父親對她影響甚深.12歲便進入英國教會辦的培華女子中學,開始接觸西方文化。1920年父親林長民攜林徽因游歷歐洲。這年9月林徽因以優異成績考入倫敦St.Mary’sCollege學習。在倫敦,林徽因結識了徐志摩,在理想、信念、文學、氣質等方面深受其影響。而作為建筑家的林徽因.則是在游歷歐洲期間受房東女建筑師影響而立下了攻讀建筑學的志向,在文學的視域之外開拓了其他門類藝術上的造詣。
一、唯美的浪漫與超脫的性靈
文學創作伊始,林徽因與“新月派”詩人保持著聯系,因而她的詩歌創作明顯帶有“新月派”的印記,受到西方浪漫主義和唯美主義的感召。在她的筆下,平常的花草樹木、天光云影,無不具有美的形態和情韻。詩人筆下的自然是一個纖弱、靈巧、幽微的靜謐世界,到處流露出寧靜和諧的氣氛。在這個由自然構成的詩歌世界中。詩人并不是一個單純的風景描繪者,借助自然她抒發了自己對于美的體悟:《雨后天》,她直抒胸臆“我愛這雨后天這平原的青草一片”;《給秋天》里,表現了對秋天來去匆匆的無限留戀和惋惜;《對殘枝》里,對梅花殘落的枝條表示深深的憐愛;在《十一月的小村》里,把山村的濃霧、茅屋、牧童描繪得極富田園詩意。不僅是自然,女性在林徽因筆下也具有獨特的韻致,在詩作《笑》中,林徽因抓住女性美的特征——眼睛、口唇、唇邊的笑渦、卷發,用“艷麗同露珠”“輕軟同花影”等比喻,生動傳神地刻畫了女性美麗的容顏。通過豐富、新奇的想象,詩人用“神的笑,美的笑.水的映影,風的輕歌”,“詩的笑,畫的笑,云的留痕,浪的柔波”來形容“笑”的甜美、柔媚、溫婉,藝術地再現了少女美的面容笑影,風姿神韻。
同時,林徽因追求的“美”也表現為一種對古樸、清遠、靜幽的情趣的向往與追求。中國文化之中的一脈講究除去胸中粘滯,虛心納物、澄心靜虛,去妙悟參會人生,從而達到一種超脫的境界,從莊禪的遁逸哲學到公安競陵派的“獨抒性靈”.從林語堂的“會心之頃”到周作人的“隱逸”,莫不如此。林徽因的作品融人對大自然的贊美的同時,體現了天地萬物莫不相通的生命哲思。林徽因對生命的存在和逝去保持著超然、達觀的“至樂”態度,與莊子“齊生死,等物我”觀念不謀而合。《一首桃花》中桃花“凝露的嬌艷”,“柔勻的吐息”.“生姿的顧盼”,人與自然水乳交融;《中夜鐘聲》和《山中一個夏夜》中輕重緩急的“鐘聲”,蟲鳴交錯的靜寂夜晚,寂寞心境借物言說;《古城春景》、《昆明即景》等詩篇中的景物和人的活動融于一體;小說《模影零篇》中的鐘綠和繡繡也不約而同地選擇在純凈的自然景致下“出走”,生的超脫,死的坦然,“天地與我并生.而萬物與我為一”。林徽因的審美追求的最佳歸宿是歸真返靜.這既順應自然造化的發展過程,完成了人與自然徹底融和:也是調和理想與現實,崇高與平凡之間矛盾最佳方式。
二、西方的現代思潮與東方的文人情懷
林徽因在倫敦游學期間同西方現代主義思潮有過直接碰撞,相較于在傳統文化土壤中成長起來的閨秀作家,林徽因的心態更加開豁,思想更為新潮。首先,林徽因的生命哲學以個體生命為本位,尤其關注社會弱勢群體和邊緣人群的命運遭際,她的幾個短篇如《文珍》、《繡繡》和《吉公》都是關注邊緣個體的生存境遇的,這并非由于作家視野狹窄.而是對于中國傳統文學中對“個”的存在的忽視的一次糾正。其次,在二三十年代封建思想禁錮還相當嚴重的中國.林徽因卻對于愛情的情狀進行了細致的描摹:在《仍然》中是熱烈的謳歌和贊美,在《深夜里聽到樂聲》中是失戀后的哀愁和悵惘,在《情愿》中是時過境遷后的灑脫和豁達。此外,五四新文化運動,受西方現代文化思潮的影響.一大批作家追求個體的解放,也包括性的解放。林徽因的第一篇小說《窘》書寫一個人到中年的知識分子的窘困的性心理以及由此生發的種種人生聯想和感悟,傳遞出作者對個體生命的尊重和理解,性在林徽因的筆下具有了濃濃的人情味,既是展示個體生存困境的一個重要維度,也成為挖掘和反映知識分子心態的一個重要支點。
雖以西方人文主義的視角來審視中國人的生存狀態.林徽因的目光中卻不可避免地透出中國傳統的文人情懷。林徽因曾說“我的教育是舊的,我變不出什么新的人來”,儒家的“仁愛”與“人世”思想與悲天憫人、憂時傷世的精神姿態深深扎根在林徽因的思想土壤中,她打開窗子.走出閨閣.詩作和小說關注生活在大千世界的蕓蕓眾生.體現了一種積極“人世”的人生態度。而與祖國共患難的決心是林徽因對傳統文人知識分子憂患意識的承續.當自己面臨貧病交加的窘迫狀況時,她堅定地拒絕了身在美國的費慰梅夫婦的避難邀約。20世紀30年代的中國正陷于水深火熱的困境中,具有高度人性關懷的林徽因自然對此懷有無限的感觸,詩作《哭三弟恒》雖為悼念在空戰中為國捐軀的三弟林恒而作。但詩人并不僅限于地傾訴個人哀情,而是推及對千萬烈士崇高精神的贊頌。
三、含蓄的象征與詩畫的意境
林徽因登上詩壇時,“新月派”顯示出向現代派象征技法過渡的傾向。西方象征主義鼻祖波德萊爾認為詩人要表達自己的情緒.上乘的方法便是為這情緒尋找一個“客觀對應物”.即“意象”,通過象征性極強的意象烘托氣氛,暗示詩人的精神世界。林徽因的詩歌創作與西方象征主義詩學有某種程度的契合,如《前后》的首段詩節以往返過渡的船、橋上絡繹不絕的足跡、晨昏的交替三個意象.象征時間更迭與延續的綿長不斷.第二節道明一味沉湎于過去的歷史則看不清前路的方向.象征主義手法的運用使這首哲理詩具有多義性與暗示性。“通感”是象征主義者另一常用的表現手段,在象征主義者眼里,“顏色似乎會有溫度,聲音似乎會有形象,冷暖似乎會有力量,氣味似乎會有鋒芒。”《笑》中,詩人時而比喻,時而通感,變本體的“笑”為喻體的“水的映影,風的輕歌”,“云的留痕,浪的柔波”,聽覺的“笑”,在可見的水、云、浪和可感的風的烘托下更加立體可感。 同時.在創作帶有西方現代感的詩歌時,林徽因還是無意識地把古典文學的傳統因子融人了創作中。中國古典詩歌的象征意蘊主要是通過具有近似表征的物象比擬——比興手法而獲得的,被比事物或情感與比喻事物經常同時出現。如《山中一個夏夜》,將深夜對山的燈比喻成“夜的眼”,風的輕柔比喻成“躡著腳”走路,流水聲像“石頭的心,石頭的口在唱”,將山谷夏夜靜謐空幽、平和清靈的氛圍及作者寧靜淡泊的心緒渲染得淋漓盡致。再如《記憶》,作者將它喻為“斷續的曲子”、夜空“一天的星”、梗莖上“兩三朵娉婷,披著情緒的花”、“沉在水底”的“倒影”.把握住了本體與喻體的契合點,將抽象的東西描繪得清晰可感。此外,林徽因的許多詩歌所刻畫的意境,都飽含著深厚悠長的古典韻味,如“當時黃月下共坐天真的青年人情話,相信!那三兩句長短,星子般仍掛秋風里不變”(《山中》),這樣的詩句極易讓人聯想起辛棄疾《清平樂》中有關“明月”“清風”“說豐年”和“七八個星”的描寫,詩人對古典詩詞意境的巧妙化用,使得整首詩傳達出濃厚的古典意蘊。
四、先鋒的現代技巧與傳統的敘事技巧
在中國小說現代性發展歷程中,林徽因的創作雖然不多,卻是具有開拓性的里程碑意義,主要體現在對于現代主義小說創作手法的借鑒。首先是橫斷面特寫法。林徽因沒有拘泥于傳統小說的線性結構,她的六篇小說全部采取具有現代性和開放性的“橫切面”寫法,如《九十九度中》敘寫發生在某一高溫天氣中的五個故事;《窘》截取某一個暑假的幾天時間中維杉對豆蔻少女芝產生的微妙的性心理變化。其次是鏡頭組接法。《九十九度中》包含了14個情節片斷.講述了北平炎熱的一天中40多個人物的生活故事。林徽因在小說中用了好幾種技巧來組織場景的轉換:主題的相關,第二部分是以挑夫渴望喝到冰涼的酸梅湯結束而第三部分以拉車夫的口渴開始,炎熱夏天口渴的主題在這里起了過渡串線的作用:人物位置上的接近.第三部分寫喜燕堂門口車夫楊三與王康的打架連帶引出第四部分喜燕堂中阿淑的喜事:人物心理的聯系。第四部分寫阿淑對被擺布的婚姻不滿,心里幻想著心儀的九哥的關心,而第五片斷則引出逸九懷念著死去的瓊又忽然記起瘦小、不愛說話的阿淑。再次是意識流技法的運用。林徽因的第一篇小說《窘》成功地運用意識流手法來開掘知識分子的潛意識和性心理。作者借助弗洛伊德的理論.試圖從本我與超我的沖突層面來揭示人性中“性欲”被壓抑所帶來的尷尬。維杉在朋友少朗家第一次看到初成少女的芝時,潛意識里產生了性的沖動,北海公園,維杉看到穿著短裙、露著微紅肉色的兩條腿的芝,不禁拉住她的手,這時“本我”沖出了“超我”的束縛。
同時,古典文學底蘊深厚的林徽因也熟練地運用了中國古典小說敘事的手法。《九十九度中》看似結構松散,但時間上寫溽暑的一天,空間上始終沒有離開北平,并采用了首尾圓合的結構,這是典型的中國傳統小說的寫法,形散神聚。此外,林徽因寫人物的性心理波動不像現代派作家用夢幻或心理分析加以表現,而用形體的描繪、色彩的象征,去觸動、掀起人物內心性愛意識的流動。比如寫維杉眼中的芝“是暈紅的肉色從濕的軟白紗里透露出來”.“微紅的肉色和蔥綠的衣裳叫他想起他心愛的一張新派作家的畫”。借鑒意識流手法時,林徽因始終沒有放棄人的情感與表現對象之間的契合這一緯度,所以借鑒西方現代派手法時沒有突破到潛意識非理性的層次,她的現代性是中國式的,保留了中國人特有的審美旨趣,這是真正的吸收后的創造。
林徽因以開闊的西方之眼回望東方,以深沉的東方之魂感悟西方.在中國現代文學史和建筑史均灑下濃墨重彩。她是杰出的建筑家,是中國現代建筑的先驅;她是“新月圣手”.詩作璀璨;她是“京派靈魂”,小說先鋒。她深受西方唯美主義、象征主義、現代主義、人文主義等思潮的影響.同時中國傳統文化中的禮教婚姻觀、儒家的生命本體觀、道家的超脫遁逸、詩畫意境文學創作也滲入到林徽因的靈魂中。中西兩方面的精神資源在林徽因的文學創作中相互碰撞并融合,共同創造了中國現代文學史上不可或缺的詩作和小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