試析人的悲劇性宿命及態(tài)度—曹禺和錢鐘書文學(xué)創(chuàng)作思想比較之一
王麗麗
論文關(guān)鍵詞:悲劇性宿命文學(xué)創(chuàng)作
論文摘要:曹禺與錢鐘書的作品都體現(xiàn)出了人對(duì)于自身的不可知,偶然事件的荒誕性與人的無能為力,以及人的孤獨(dú)感,這樣一些人類生存境況的深刻思索。在對(duì)于人的終極意義指向上,他們同樣投注了遼遠(yuǎn)、容智的目光。這是他們的共同之處。然而,在對(duì)這些深邃命題的思索過程中,二者所體現(xiàn)的情狀和態(tài)度又是不同的。
一、“天外邊”與“圍城”
在曹禺和錢鐘書的作品中共同體現(xiàn)著這樣的思想:在這個(gè)荒誕的世界,人們無論怎樣追求、掙扎也不可能達(dá)到理想的彼岸。這便是曹禺“天邊外”與錢鐘書“圍城”意象所包涵的內(nèi)容。
《雷雨》中的人們陷入一片“情熱”當(dāng)中,都滿懷著想法、企望,最后卻獲到那樣慘烈的結(jié)局。《日出》中可以說從上層階級(jí)到下層階級(jí),沒有一個(gè)能逃脫生活的折磨。同樣的曹禺對(duì)巴金《家》的改編劇中,主人公高覺新發(fā)出了這樣的慨嘆:你要的是你得不到的,你得到的又是你不要的。哦,天哪!《原野》中的仇虎以血性蠻力的生命力掙扎到最后,仍然未達(dá)到那黃金鋪的地方。而那黃金鋪的地方便是他下一步追求的方向。
《圍城》也同樣揭示了人生虛無這樣的主題,展示了現(xiàn)代人的“圍城”般的困境,無論沖進(jìn)逃出都是無謂的,人的努力終究是徒勞的。
錢鐘書和曹禺的作品都深蘊(yùn)著這樣的哲思。他們以生動(dòng)、豐富的文學(xué)形式來傳達(dá)著自己對(duì)于人生、對(duì)于存在的理解與思索。然而他們又井非是抽象、簡(jiǎn)單的去概括、闡釋哲理。他們的作品像磁石般吸引了一代又一代的讀者便是一個(gè)很好的例證。人類永遠(yuǎn)進(jìn)行著無止盡的欲望追求,而到最后發(fā)現(xiàn)實(shí)現(xiàn)的這些欲望追求又不是自己所要達(dá)到的目標(biāo),于是又產(chǎn)生下一輪的追逐,這便是人的悲劇性存在。
二、情狀和態(tài)度
曹禺和錢鐘書在反映他們對(duì)于人無謂、徒勞掙扎的終極意義指向上有很大的一致性。然而他們進(jìn)行思索的過程、狀態(tài)及思考的結(jié)果卻又是相異的。曹禺在惶惑、焦慮的思考中,最后升華為悲憫的情懷來俯視天地間萬物生靈:錢鐘書以其睿智的目光透徹洞明人世真相后,以絕望的姿態(tài)達(dá)到孤傲的超越。
曹禺在探討人的生存境遇時(shí)充滿了一種強(qiáng)大的、不可排解的惶惑、焦灼的情緒。他在告白《雷雨》的創(chuàng)作動(dòng)因時(shí),說到“自己不斷來苦惱著自己,這些年我不曉得‘寧?kù)o’是什么,我從不能在我的生活里找出個(gè)頭緒”。“……我覺得宇宙似乎縮成昏黑的一團(tuán),壓得我喘不出一口,”以上的自我告白以及作品中所體現(xiàn)出的“郁熱”氛圍和強(qiáng)烈的矛盾沖突都可以看出曹禺在對(duì)宇宙人生和對(duì)人自身的困惑、探索中所產(chǎn)生的惶惑和焦灼。人生、生命的謎團(tuán)是以如此強(qiáng)大的吸力將他重重包圍,可以看得出他是如何心急如焚,如何自我折磨般地想叩問出其中的究竟,這便是曹禺在探討人類生存境遇時(shí)的一種情態(tài)。
然而,對(duì)于錢鐘書來說更體現(xiàn)出一種淡遠(yuǎn)的姿態(tài)。“在錢鐘書的作品中,諷刺、幽默、喜劇的笑是同時(shí)并存的,諷刺中滲透著幽默,幽默中蘊(yùn)藏著諷刺,其喜劇意識(shí)極為強(qiáng)烈、突出,堪為典范。可以說曹禺與錢鐘書所思考的思想命題都是遼遠(yuǎn)、嚴(yán)肅、深沉的,但從材料可以看出兩人在思考過程中所表現(xiàn)出來的狀態(tài)卻是不盡相同的。曹禺的女兒萬方曾說:“痛苦是他的天性”。而在《錢鐘書傳》楊絳的父親在見到錢鐘書時(shí)曾問楊絳鐘書總是那樣快樂嗎?錢鐘書正是具有一種開闊的胸襟、爽朗的氣質(zhì)。正如他說:“一個(gè)真有幽默的人別有會(huì)心,欣然獨(dú)笑,冷然微笑,替沉悶的人生透一口氣。”如果說曹禺與錢鐘書兩人在對(duì)人生、宇宙的思考洞悉中,都看到了現(xiàn)實(shí)與理想的沖突,都看到了人生悲劇性的真理,那么曹禺在現(xiàn)實(shí)與真理的逼迫下,恰如一頭被殘酷真相圍困的獸,而錢鐘書在人生到處圍城般的境地,想要通過笑,替“沉悶的人生透一口氣”。這正是錢鐘書悲劇意識(shí)中的喜劇氣氛。這也是錢與曹兩者表現(xiàn)出來的心境上的不同。 曹禺在探索人的悲劇性命運(yùn)后,從而滋生出對(duì)世界萬物一種普遍的悲憫、關(guān)懷,用悲憫的目光理解、撫慰人世這一切的痛苦和無奈,以及人的崇高和卑微,善與惡,美與丑。同時(shí)也以這種認(rèn)識(shí)來緩解、沖淡作者內(nèi)心洶涌的焦慮與不平靜。
然而對(duì)錢鐘書而言,更似乎是一種絕望之后達(dá)到了超越,這可以由評(píng)論者對(duì)錢的作品評(píng)價(jià)有所應(yīng)證,也可以從其本人所說的處世態(tài)度略見一斑。夏至清說到《圍城》時(shí),提到它的“喜劇氣氛和悲劇意識(shí)”。錢鐘書曾說自己的處世態(tài)度是;“目光放遠(yuǎn),萬事皆悲;目光放近,則應(yīng)樂觀,以求振作。”從這可以看到錢鐘書洞悉人情世事后,面對(duì)人生的姿態(tài)。
可以說曹禺和錢鐘書都看到了“目光放遠(yuǎn),萬事皆悲”的人類生存境遇。然而,其間兩人的情狀又是不同的,一人焦灼,一人冷靜。正因?yàn)閮烧卟煌那闋睿谧髌分校茇云渖畛翝饬业那楦胸炞⒃诿總€(gè)人物的身上,以其內(nèi)在燃燒、凝聚的急切焦灼的心理體驗(yàn)飛揚(yáng)出創(chuàng)造、不羈的想象力,熔鑄成凝結(jié)著現(xiàn)實(shí)與超現(xiàn)實(shí)的戲劇意象與戲劇情境。而錢鐘書以其對(duì)人生、人世睿智的心領(lǐng)神會(huì);以其寬廣的知識(shí),敏靈的思想;以其機(jī)趣、幽默的風(fēng)格道盡人生悲喜,人世滄桑。其開闊的胸襟,爽朗的氣度形成了一種冷靜的悲氣氛,
以上所述,便是曹禺和錢鐘書兩者的不同之處。然而兩人對(duì)于人的悲劇性存在有如此深刻認(rèn)識(shí)之后,是否便導(dǎo)向消沉、絕望的境地?汪暉曾說過“希望一絕望的二分法在中國(guó)現(xiàn)代作家的藝術(shù)世界中幾乎是一個(gè)永恒不變的模式:或者為希望而欣喜、奮斗,或者因絕望而頹喪、消沉,或者在無可奈何的情境中添加光明的尾巴—極度的悲觀與輕率的樂觀在二十年代的文學(xué)中尤為明顯”,可以說曹禺與錢鐘書克服了輕率的樂觀,然而他們也沒陷入輕率的悲觀。這在曹禺的《日出》、《原野》、《北京人》等的結(jié)局中都能看到。錢鐘書的《圍城》中方鴻漸也還是自里又生希望,像濕柴雖點(diǎn)不著火,而開始冒煙,似乎一切會(huì)有辦法”。(他也是要走的,去重慶。這里的“走”,已經(jīng)不是一種簡(jiǎn)單的樂觀狀態(tài),這里的走不是作者會(huì)想象走之后一切都會(huì)好起來,前途會(huì)由黑暗而轉(zhuǎn)向光明。而走正如汪暉在評(píng)價(jià)魯迅時(shí)所言的“作為一種現(xiàn)實(shí)的行為,‘走’表達(dá)的只能是實(shí)踐人生的方式,同時(shí)也是面對(duì)現(xiàn)實(shí)的執(zhí)著態(tài)度”。他們的悲觀絕望是深刻、深沉的,因而他們不可能復(fù)而轉(zhuǎn)成一種簡(jiǎn)單、輕率的樂觀:然而他們依然用人物未停的腳步來表達(dá)著一種透徹洞悉之后的執(zhí)著,沒有指明前面的方向,只有“走”下去這樣的信念與行動(dòng)。當(dāng)對(duì)于絕對(duì)和終極的價(jià)值都持可疑的、表面的、相對(duì)的看法時(shí);當(dāng)對(duì)自我及人本身有所懷疑、否定時(shí),自我的生命意義僅僅存在于對(duì)自我的認(rèn)識(shí)、選擇和反抗之中。如果說魯迅的對(duì)絕望的深刻體驗(yàn)達(dá)到了超越絕望,反抗絕望的思想、哲學(xué)高度,那么曹禺和錢鐘書也同樣是在中國(guó)現(xiàn)代文學(xué)史上為數(shù)不多的幾個(gè)能在人類生存境遇的這樣高深的命題上有所探索的人,而且他們同樣在獲得悲劇性真理的面前依然不曾萎縮,而以絕望之后更堅(jiān)定、更清醒、更現(xiàn)實(shí)、更超越的目光注視著現(xiàn)在與未來。這是他們的偉大之處,也是他們異中有同的地方。
代大學(xué)教育.jpg)
裝備.jpg)

.jp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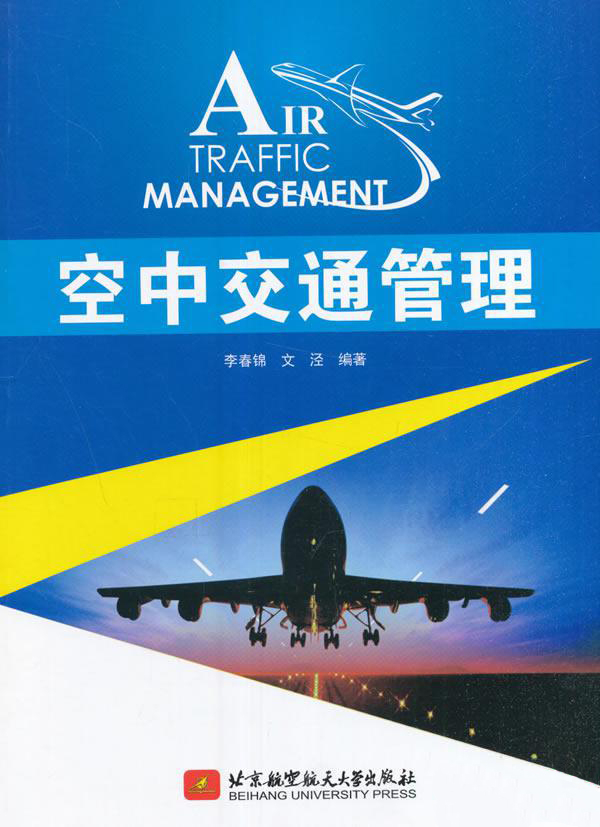
于我們.jpe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