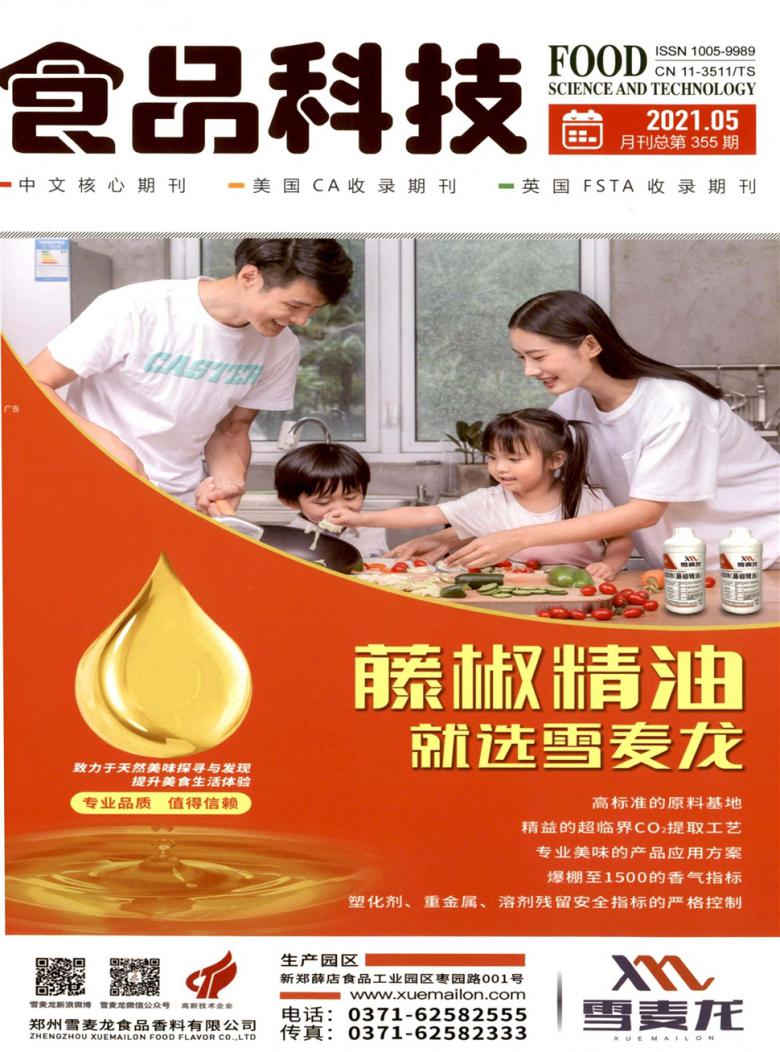淺談人性透視與文化批判:魯迅、錢鐘書小說主題之比較
趙慶超
論文關鍵詞:魯迅錢鐘書現代小說人性透視文化批判
論文摘要:魯迅和錢鐘書的小說在人性透視和文化批判上都顯示出鮮明的獨特性和深刻性,他們的小說均以苛刻的標準過濾傳統和現代視域中的人生百相,由表及里地揭示人的生存和精神困境,其清醒的批判意識與深刻的反思精神能夠提升文學彰顯人性和世界的審美品格。
魯迅和錢鐘書分屬于不同的現代文學史階段,其各自創作的小說數量都不是太多,但所呈現的思想意識、文化觀念、審美意蘊和生命體驗卻是同時代作家所無法比擬的。敏銳的人生體驗和豐富的學養積淀為他們提供了觀察世界、表現人生的獨特視角,這種厚積而薄發的創作范式是他們的小說成為經典之作的重要原因。筆者試從對比分析的角度研究兩人小說在人性透視和文化批判方面的異同性,并試圖揭示造成這些異同表現的時代文化癥候和文學啟示。
一、對傳統文化劣根性的反思和批判
魯迅和錢鐘書以一種苛刻的眼光過濾現實與歷史、本土與異域的復雜文化現象,在冷靜的審視中揭示集體無意識的文化惰性對個體生命的無情吞噬和有意遮蔽的歷史真相,發掘沐浴在自由之光中的現代人深陷新的人生困境的深層原因,指出部分不自知的人們沉醉于黑暗大澤而不掙扎、不覺醒的劣根習性和悲劇命運。兩人都在小說中揭示傳統文化麻醉人、毒害人的負面作用,批判經過幾千年積淀而占據國民精神高地的文化劣根性。這種積習深重的傳統思維定勢被國民奉為圭臬,以極大的排他性對相異的精神向度進行擠壓與吞噬,對異己分子的精神與肉體進行雙重虐殺。對于這種在傳統的溫床上滋生出來的惰性文化因子,魯迅和錢鐘書都進行形象的刻畫和毫不留情的批判,并指出它們滋生的社會文化根源。不管是魯迅小說中的閏土、阿Q、孔乙己、祥林嫂等鄉間底層人物形象,還是錢鐘書筆下的方逐翁、董斜川、愛默的公公與父親等遺老形象,都拖著長長的傳統文化暗影,他們或愚昧不堪,或頑固不化,或狡詐蠻橫,或老實無用,或忍辱負重,或自欺欺人,在“看”與“被看”的人生舞臺上既拒絕給予別人以幸福與安慰,又被人賞鑒著自己的悲歡與苦欣,小心地維護和修補著“老例”。對他們身上頑固不化的國民劣根性,魯迅和錢鐘書都進行毫不留情的批判,并從文化的視角去深挖導致精神劣根滋生的傳統溫床,或“哀其不幸,怒其不爭”地刻畫他們愚昧麻木的生存現狀和精神風貌,或在喜劇式的嘲諷中戳穿他們虛偽、迂腐的真實面目,或在不動聲色的冷靜觀照中昭示他們固守過時的人生信條而不自知反而認為其放之四海而皆準的錯位意識和時代幻覺,從而使人性批判在文化層面上達到旁人難以觸及的深度和廣度。
在展示和批判國民劣根性的同時.魯迅和錢鐘書所創設的文學場域卻有著重大的差異。魯迅在其小說中描繪一個老中國的鄉土世界,這個世界仿佛與時間的流逝無關,幾乎封閉式地保存著傳統的生存狀態,自給自足地繁衍生息。魯迅以“挖祖墳”、“清舊帳”的徹底性集中批判了傳統陰魂不散的鄉土世界里國民的愚昧、麻木或狡詐的生命本相,他們好像擺脫不了歷史輪回的宿命,在現實的時空中重復著歷史的生存之夢,時光的流逝只不過為其增加好奇的談資和消遣的話題,而隨后消融在古老歷史記憶的圖像里。在這片傳統觀念根深蒂固的鄉土世界里,傳統意識對現代精神的警覺是自發的、不約而同的,吉光屯的闊亭們對想要滅燈的瘋子是那樣的恐懼與殘忍,大哥與趙貴翁們對狂人的戒備連眼神都是相像的。這種吃人的真相只不過是傳統老例的一種延伸,“四千文明古國古”的舊賬上記載著如此類似的把戲,既有血淋淋的肉體殘害,也有陰森冷酷的精神虐殺。魯迅直指國人積習深重的心靈暗影,批判他們身上遺留已久的主奴根性、面子膨脹、精神勝利法等劣根習性,以求喚起沉睡的人們,擺脫傳統暗夜的束縛,走上決絕的新生之路。錢鐘書的小說主要展示現代背景下的傳統城鎮生活,他讓生活在城鎮里的遺老們在嬉笑怒罵中粉墨登場,不管是方鴻漸的父親方逐翁,還是愛默的公公和父親,還是“同光體”詩人董斜川,都在現代城鎮里過著豐衣足食的生活,他們堅持傳統宗法社會的人生信條,做著現代社會里落伍的遺民之夢。方逐翁迂腐守舊得像家中的那座祖傳老鐘一樣跟不上時代的步伐,卻抱守著古老迂腐的傳統信條并時時炫耀它們的高明。在現代社會背景下,這些遺老們或以歷史守舊的眼光衡量事物,或以傳統的守舊心理定位自我,成為現代社會中別樣的類群,與魯迅老中國土地上的人們形成鮮明的對照與互補。在這種對照互補中,魯迅和錢鐘書的小說對傳統文化劣根性的反思顯示出深廣的文化通透感,以現代人的眼光對傳統群體進行冷靜觀照,使得兩人的批判具有豐富的文化意味,蘊含著鮮明的主體精神。
二、透視和質疑現代文明的種種假象
魯迅和錢鐘書是現代社會的啟蒙者,但他們對現代文明的關注并不是盲目地只唱贊歌,而是以苛刻的眼光去發現新的壓迫、新的不平等、新的精神奴役和創傷,從而揭示現代人物的精神困境和生存危機。兩人既批判傳統思維定勢對現代人性萌芽的扼殺與圍攻,也指出現代精神枝條的稚嫩與脆弱。兩人都不回避現實世界的矛盾和悖論,在冷靜的審視中直面和揭示現實世界的不完美、不全面,處處存在人類自造或他設的陷阱,批判不自知的人類的浪漫主義、樂觀主義和英雄主義的天真和自戀癖,戳穿現代文明外衣下的種種人生和生活的假象。他們在小說中并不是一味地批判,而是在解構的同時也微微透露些許生命的亮色,暗示通向美好未來世界的諸種可能性,如《狂人日記》里的孩子、《藥》里夏瑜墳上的花圈、《在酒樓上》和《孤獨者》里坦然走路的“我”,以及《圍城》中的唐曉芙等都暗示了對令人窒息的現實人生的突圍力量。這些事物或人物身上既有對難以驅除的歷史陰影的清理,又有對新的生命征程的踏入與邁進,象征著現實世界中蘊含理想色彩的審美內容,它們可能會蒙上新的污垢,在新的起點中可能會遇上新的歧路,但畢竟預示了通向未知世界的可能性。但也應該指出,兩人由于過于關注對歷史與現實的文化批判和人性剖析,認識到傳統社會向現代轉型的漫長,感到重建理想未來的艱難,所以其小說主要進行的是對歷史傳統與現實人生的清理和反省,而沒有致力于描繪未來世界的理想圖景。
魯迅所揭示和批判的現實世界多是過去時間的一種延伸,由于現實世界中不斷襲來的精神暗箭和感受現實世界時層層淤積的心靈創傷,由于童年世界里的陰郁記憶下意識地不斷涌現,由于發現現實與歷史之間總是驚人的相似甚至仿佛完全疊加在一起,魯迅常把現實作為歷史悲劇的循環影像,現實并沒有標示時代的進步與發展,而仿佛陷入荒謬的輪回之中,所以魯迅對現實同樣不滿并執著地予以批判。《藥》表現革命者與群眾之間的雙向隔膜,《肥皂》、《高老夫子》諷刺了偽知識分子好色、獵奇的虛偽本性,《兄弟》揭示現代知識分子潛意識中的陰暗、自私心理,《在酒樓上》、《孤獨者》寫出知識分子在追求個性解放道路上的軟弱與偏激,《傷逝》寫出現代愛情在遭受舊有綱常倫理的圍攻和現代人格不能承受之輕的困境下而走向寂滅的真相。另外,魯迅還深刻地揭示所謂的一些“新”的名目其實不過是舊的把戲的排演,骨子里散發出演過無數遍的舊戲的氣味。《阿Q正傳》里假洋鬼子們的革命只不過是在玩一種投機的把戲,而革命后的縣城掌權者沒變,只不過換了一下稱謂而已;《離婚》中的愛姑看起來是一個擺脫封建淑女品性、追求女性獨立的新人形象,但她的追求只不過是被封建夫權所拋棄之后想依附而不可得的女性悲劇;《風波》中被剪去辮子的七斤不僅沒感到進入民國時代的輕松與喜悅,反而因張勛復辟而在趙七爺的威嚇下感到自己末日的降臨。正如汪暉所指出的那樣:“魯迅抑制不住地將被壓抑在記憶里的東西當作眼下的事情來體驗,以至現實與歷史不再有明確的界線,面前的人與事似乎不過是一段早該逝去而偏偏不能逝去的過去而已。”
錢鐘書對現實的解構和批判更為底,他的小說不僅僅是把現實看作是傳統的延續,而是從人類根性的基點上對現實世界中人們難以改變的精神缺陷進行揭示和批判。在《圍城》中,他幾乎解構了一切合目的性的結局和世俗的進步,方鴻漸既沒有花好月圓、良辰美景般的婚戀結局,也沒有出人頭地報效祖國的事業成功,雖然他曾求學于中西文化,有著較為廣博的人生視野,但仍身陷歸國后的灰色生活之流而不能自拔,最終成為一個無根飄浮的現代人。小說中的其他“新儒林”人物也基本如此,他們常常浪漫地懷舊,這種虛幻的懷舊為他們的現在爭回了一些面子,精神勝利似的填補了現實的虛空、無聊和不能逃脫的困境。汪處厚常向人們吹噓自己戰爭中失落在南京房子里的無數古玩,陸子瀟不斷描述戰前兩三個女人搶著嫁他的盛況,李梅亭也在腦海里建構了一所被日本人燒掉的上海閘北的洋房,連方鴻漸也把淪陷區的故鄉老宅在意念里放大了好幾倍而到處吹噓自己家曾經如何富有……。現代人自欺欺人的劣根性成為他們身陷現實泥淖的重要原因,他們既不能正視現實,也不能認識自我,因此常常造成現實與自我的錯位。《人·獸·鬼》暗示出現代人由于不自知而常常事與愿違的現象,虛榮心得到極大滿足的愛默在聽到丈夫另有新歡的消息后馬上露出了女人軟弱可憐的本相,而作為丈夫的李建侯在婚外情滿足之后的心境也像火車上看到的向后退的黃土那樣干枯憔悴;渴望婚外情的曼倩在和丈夫的表弟天健切切實實發生了肉體關系之后,卻感到超出希望的失望……。不管是錢鐘書把現代人看作孤島上的人、圍城內外的進城者或出城者,還是比喻為鳥籠內外的鳥、想吃葡萄的猴子等等,都顯示他對現代人生困境的獨到發現。不管社會如何進步發展,現代人仍然會被新的問題和矛盾所困擾,人性的劣根也會像猴子尾巴一樣總有露出來的時候,這種發現劣根性并使其形象地展示出來進行批判的意向寓指整個人類的生存困境,具有普泛性的文化色彩。 不管是以民族現實為考察基點,還是著眼于人類根性的揭示,魯迅和錢鐘書的小說都通過對個體形象的塑造深入到集體無意識的文化心理層面,對現代文明進行冷峻的透視和質疑。兩人都有著寬廣的理論視野,但他們的小說并沒有因此抽象化和教條化,而是在審美層面上包蘊著對生命個體的終極思考,他們的小說在現代生命哲學的高度擴充了對現實生活的審美展現力度,加深了對人性世界的認識與揭示。
三、風格形成原因和啟示探析
在2O世紀二、三十年代。魯迅最關注的不是對整個人類生存困境的焦慮,而是弱小民族的生存危機問題,是中華民族的自救、自新問題。作為一個現實感和憂患意識非常強烈的作家,魯迅思考問題的起點還是以對國民性的考察為基點,以救國、立國的愿望為緣起。他考察了近代以來器物救國、制度救國的發展歷程,但避免了它們的狹隘性和急進功利性,注重精神啟蒙和反思性的文化批判。因此,這種啟蒙主義意圖進入創作實踐的建構過程之后,那種救國、立國的民族主義觀念在很大程度上已退居幕后,而關于人的本能欲望和生命力的現實思考和文化批判則被置于小說主題的前臺,構成他審視社會和人生的文化視點。雖然他的小說畫面和人物語言都帶有鮮明的中國作風和中國氣派,但這種深廣的文化批判卻暗合整個人類的靈魂世界,阿Q形象接受的世界性影響已說明了這一點。這種最初在民族傳統的思考基點上展開的人性和文化批判具有更為深廣的文化內涵。錢鐘書是在民族救亡運動進入高潮的年代進行小說創作的,但炮火連天、風起云涌的戰爭氛圍并沒有影響他的小說創作,他冷靜地避開政治意味日益加重的時代主潮,在戰爭的縫隙里找到安放心靈的寧靜書齋,進行中西文化的冷靜觀照和深刻剖析,揭露長期被忽視的人類“根性”,揭示現代人的生存困境。這種文化觀照的通透性其實在某種意義上是魯迅的文化批判的延續,只不過魯迅把批判與揭示的重點放到傳統與歷史上,而錢鐘書的重點則是現代文明與現代文化。但不管怎樣,他們的文化批判都抓住了人的最深層次的“根”,即精神和靈魂的更新與蛻變,這是人們擺脫奴隸時代向“第三樣時代”邁進的最重要、最根本的一步,只有作為個體的人的精神面貌和靈魂痼疾發生根本改變,真正的“人國”才會出現。所以說,他們在小說中所進行的文化祛魅(消除文化負面性的影響)和人性透視是深刻而必要的。
魯迅和錢鐘書小說中深刻的文化批判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現代性的神話,顯示了現代性自身的悖論性特征,提供了反思現代性的文化視角。兩人在小說中肯定現代制度和現代精神,看到時代進步、科技發展的重大作用——孕育了現代文明、現代精神。不管是夏瑜的革命行為,還是方鴻漸的求學西洋,都是現代文明和現代思想影響、推動的結果。同時,他們又在小說中描繪現代文明和現代社會產生的新的陷阱及其對個體生命造成的新的束縛和壓迫。呂緯甫、子君和魏連殳無法遠行,成了“折翅鳥”,方鴻漸、曼倩、愛默也身陷難以逃脫的現代圍城.成為失樂園里無家可歸的游子。因此,兩人的小說在諷刺和刻畫傳統文化“吃人”本質的同時,也揭示進步理性觀念和現代科技文明所帶來的人的新的異化、拜物化、工具化狀態。這種懷疑一切、批判一切的通透認識反映兩人認識世界的深度和廣度,它是在宏觀把握歷史與現實、傳統與現代的基礎上帶著豐富的體驗作出的清醒反省,這對喪失獨立立場、膺服某種理論或夢想的知識分子是一種參照。不管是革命化的歷史敘事,還是欲望化的情欲敘事,還有粗鄙化的物質敘事,都試圖取消人文知識分子精英階層賴以存在的價值前提——獨立的人格、自由的思想、自覺的理性批判精神,獻身或依附到某一思想或潮流中,無條件地服從于某一種社會思潮或文化觀念,不是用理性批判的眼光去審視它們,不關注它們的歷史過程性和有限性缺失,而是為之制造大量終極性的結論。魯迅和錢鐘書的文化批判顯示著長久的生命力,它告別了現代文化的幼稚病,沒有把批判指向絕望的虛無主義,而是在對世界的不滿足中暗示生命前行的諸種可能性,在韌性的文化批判中暗含著人文主義的溫情關懷,在感悟世界的大徹大悟中深味人間的悲涼與無奈,從向內與向外的雙重視點來尋找深層的文化癥結,從而確立徹底的文化批判姿態,這種永不滿足的探尋和求索顯示著現代知識分子的有機性。魯迅和錢鐘書的文化批判為我們提供了尋找或拯救自我心靈的參照,那是一種對自我和社會的深層文化意識的自覺把握與沉省,一種既不自大亦不自輕的清醒冷靜的主體意識,一種雖悲觀卻不徹底絕望的人生觀照情懷。
魯迅和錢鐘書被稱為學者型的作家或作家型的學者,他們的小說所進行的人性和文化批判,既與其敏銳的文學感知力密不可分,也與自身的文化素養和思想穿透力密切相關。他們都注重知識與社會生活的連接與融合,不管是對國民劣根性的批判,還是對無毛兩足動物基本根性的刻畫,都與他們宏闊的文化觀照視野相關聯,作家與學者的雙重身份使得他們具備厚積而薄發的創作優勢,正是這種嚴肅的藝術創作態度與深厚的文化素養相結合,才使得他們的作品具有較高的思想藝術品位。不管是什么時代的文學,都應該具備發人深省的內涵、暗示真相的啟悟和通向高遠境界的審美導引力,這樣的作品才會成為經典性的厚重之作,魯迅和錢鐘書小說中深廣的人性和文化批判精神可為之提供豐富的借鑒和啟示。
總之,魯迅和錢鐘書的小說都在理性審視世界的基礎上,對人的生存和精神困境進行深刻揭示,都從形象的層面上升到寓言或哲理的層面,形成對世界和人性的特殊體驗和認識,完成從形而下向形而上層面的拓深和升華,這也是它們具有長久生命力的深層原因。在整個2O世紀中國文學中,具有這種品格的文學作品本來就不多,有的還長期被排擠到文學主流話語的邊緣。在這個意義上說,繼承和深化魯迅和錢鐘書小說中的這種人性和文化批判精神,彰顯和提升這種深邃的文學品格,對新世紀中國文學的發展無疑是一個富于啟示性的話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