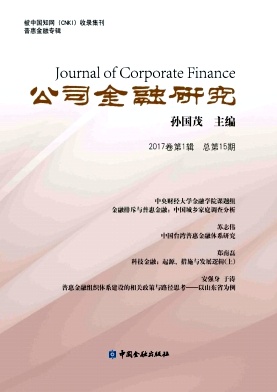現代漢語與中國美學史寫作
張法
一、現代漢語:中國美學史研究中被忽略的因素
“中國美學史”這一詞匯在中國20世紀前期才零星地出現,20世紀80年代才成為一個學術常用詞。中國美學史是怎樣的一門學問呢?它是一門古代的學問,因為它的研究對象是中國古代與美學相關聯的資料;它更是一門現代的學問,因為它是以現代學科體系中美學這一學科的結構方式去組織古代的資料,用現代漢語去談論古代的資料。這樣,中國美學史的研究,從消極的方面說,受三個方面的因素制約;從積極的方面說,由三個因素所推動。這三個因素就是:研究中國美學史的目的;中國美學史得以被研究的材料;進行中國美學史研究的語言工具。
中國古代沒有一部美學史而我們要總結一部美學史出來,這是中國現代性的要求。中國的現代化包括著學術體系的現代化,這就是按照世界主流學術的規范重建中國的現代學術。在這一學術重建中,美學史,西方有,我們也要有。這一目的決定了研究中國美學史的性質,從美學學科的角度去尋找古代材料而呈現古代美學。從中國美學史一定要呈現出古代本有的性質來說,這是一種“還原”的工作。“客觀還原”是學術研究的一個基本理念,但這一“還原”是受建立中國美學史這一學科以完善現代學術體系這一目的影響的,從這一角度看,客觀還原就表現為一種現代建構。古代文化已具有如是的美學材料,但古代文化沒有呈現為現在所呈現著的中國美學史的形態,因為中國古代的學術體系不須這樣,現代中國非得把這些材料組合成中國美學生,因為中國的現代學術體系要求這樣。在這一意義上,可以說,中國美學史的研究活動是用還原的形式去建構一種中國美學史。因此,也可以說,中國美學史的研究活動,是一種古今對話,這場對話不是一個純粹的還原古代,也不是一個純粹的以古證今,而是在古今的對話中“建立現代中國學術的自我”。這種“立我”的活動,一方面用今天的眼光去看古代,發現古代本有(但用古代學術體系去看又看不見)的美學資源,這同時也是把古代資源納入今天的學術體系。另方面用古代的資源來重視現代美學,讓現代美學在一種差異中發現自己的問題,從而克服自己的問題而達到一種更大的普遍性。因此,中國美學史的研究活動,不僅是怎樣還原古代,更是怎樣建構現代。這一包含著還原和建構兩重基質于一體的中國美學史研究,從這兩個內含矛盾和張力而又必須并置在一起的主詞,就可以體會出其進行中的巨大困難。這一巨大困難已經多多少少地為研究者們所體會。但在體會中國美學史研究的巨大困難中,一個非常重要的問題被忽略了,這就是現代漢語在中國美學史研究活動中的巨大作用。
在中國美學史的研究中,無論是還原還是建構,不但有一個目的性的為完善中國現代學術體系的主體,還有一個還原和建構的工具——現代漢語。中國美學史的研究是用現代漢語進行的。任何一種古代美學思想,無論你是意在還原還是意在建構,你都必須用現代漢語去解釋。舉例說吧,“形神”是一個古代美學概念,在中國美學史的寫作中,不可能說,形神者形神也,而是說,“形神”就是形式與內容,“形”是形式,“神”是內容,“以形寫神”,就是通過形式去表現內容。為什么要這樣解釋呢?因為古代用形神這一概念去講解的關于審美對象或藝術作品問題,在現代漢語中是用形式內容這一對概念去言說,把形神翻譯成形式與內容,我們對什么是形神就理解了,古代與今天的對接就成功了,古代的思想就被納入到了現代的話語體系之中,為我們所理解也為我們所運用。但是,形神既等同又不等同于形式與內容,說等同,是因為二者都是在講審美對象或藝術作品的結構,說不等同,在于中國古代是以人體學作為示范學科,運用于各個領域,因此,藝術作品的結構用人體的形神來把握更得其神髓,呈出了審美對象或藝術作品的生動氣韻。現代漢語的形式與內容概念源于西方,西方文化以物理學為示范學科,可以實驗的物體成為研究的榜樣,因此,審美對象或藝術作品用內容形式概念來把握更得其本質,顯出了審美對象或藝術作品的學理氣質。這樣,用現代漢語去研究和言說中國美學史,往往是獲得了古今相通的一面,而遮蔽了古今不相等的一面。因此,對現代漢語的認識,成了中國美學史研究中的一個重要問題。
二、現代漢語與中國學術語匯
中國現代性進程中具有決定性意義的事件之一,就是新文化運動以現代漢語取代古代漢語成為中國文化的主要的和普遍性的語言。現代漢語從語言來源上說,來自:1.凝結在白話文本中的宋代以來的白話演進,2.現代中國的大眾口語,3.西方語言參照。白話與口語建立在現場語音交流的基礎上,為了現場聽清,以單音節詞為主的書面漢語演為以雙音節為主的說書白話和日常口語。西方語言受科學明晰性影響,以嚴格的語法和標點來使語言明晰化。白話、口語、西方語法和標點,是形成現代漢語的三大因素。現代漢語形成的五四時代,一種全盤西化、力爭上游的思想成為主流,其精神核心是西方近代思想模式,其要義是明晰性和確定性。現代漢語的語言三個來源都凝聚在這一西方近代思維模式上。其基本精神就是如何通過把古代漢語的單音詞變為現代漢語的雙音詞時,把古代中國思想的活躍而靈動的動態特征改造為現代漢語的確定而明晰的靜態特征。正是現代漢語把中國古代型的氣的宇宙改變為西方近代型的機器宇宙,把中國古代思維改造成了具有西方近代思維特點的中國現代思維。
就現代漢語的語言整體來說,經過近百年的寫作,已經證明其能夠熟練地表達政治、經濟、文化、宇宙、人生的方方面面,而且很容易與時俱進。但就其學術語匯來說,從20世紀前期定型的學術術語群,特別是一個學科的核心術語,有更大的凝固性。而學術語匯的更新是現代思想更新的質的尺度。因此,思考現代漢語中學術術語的性質,成為思考中國學術性質的一個重要方面。在中國現代學術術語群中,哲學概念具有學術的普遍性,從中可以從普遍性的方面顯出中國學術的一般特質,美學術語具有專門性,但仍可以從具體學科層面顯出普遍的學術問題。這里我們先選幾個具有普遍性的哲學的基本語匯來看看現代漢語是如何改變中國思維的。
“事物”是中國現代哲學的關于宇宙構成的既作為本體又能運用于現象的最基本的概念,就是西方近代哲學中泛指一切存在的“物”(thing),物是靜態,可以讓你仔細觀察詳細分析的。但在古代漢語里,事物是“事”與“物”兩個東西,“物”類似于現代漢語的事物,是靜態的,“事”類似于現代漢語的事件(event),是動態的,難于定位觀察的,正在運動過程中的,無法預料其結果的。現代漢語把事與物放到一塊,正是(巧妙地運用古代漢語語法中偏義復詞的原理)用靜態的“物”吃掉了動態的“事”。在“事物”一詞中,“事”的含義沒有了,只剩下“物”的含義。
“變化”是建立在辯證法基礎上的中國現代哲學關于世界運動的基本概念。古代漢語中“變”是可看見可計算的變,“化”是看不見不可計算的變。“變”重在強調變化的可見結果,一物變成了它物,“化”重在指出決定變化的內在不可計算的決定性力量(“如氣化萬物”)。現代漢語的“變化”,對應于西方的change,用“變”消滅了“化”,把世界上的一切變化都納入了科學的可觀測可把握的意義系統之中,而把包括中國哲學在內的世界哲學中的一個更具有形而上意蘊的“化”取消了。
“規律”是建立在“科學世界觀”上的一個關于宇宙本體的最根本的概念。“規”與“律”在古代漢語中部是屬于講得清楚的、可以明白遵守和運用的,雖然也重要,但畢竟是較表面和較淺層的東西。中國宇宙最根本的東西——“道”——是“道可道,非常道”,是可意得而難以言詮,可神會而難以形求的。一旦用“規律”作為宇宙的根本的概念表述,實際上就成了如存在主義對古典哲學的批判那樣,關于“道”(存在)的表述和規定在,而“道”(存在)卻不在。如果說,“事物”和“變化”一類重要概念是運用偏義復詞原理,以一個詞消解和改變另一個詞的方式建立了內含西方近代明晰精神的中國現代哲學概念,那么“規律”一類詞則是用一個明晰的概念去遮蔽和逐除原有的根本概念,而建立內含西方近代明晰精神的中國現代哲學概念。
從以上三例,可以體會到,中國現代哲學和現代文化在理論創立期,從深層背景上,是建立在西方近代文化的價值體系和思維體系上的。隨著中國現代性的演進和世界文化的轉潮,包括中國哲學在內的現代文化的理論建設,還沒有從其創立當初的根本概念上得到重視。在全球現代化的過程中,可以看到兩個相反相成的過程,非西方文化通過對自身傳統的批判,以適應著由西方文化主導的世界化的現代性文化,西方文化不斷地批判著自近代以來的西方中心論,不斷地走向與各非西方文化的匯通。這兩方面的溝通越深入,各大文化在深層中的同一性一面會從更高的層面上顯示出來。比如,隨西方現代社會興起的古典油畫是最具西方獨特性的,而在西方現代文化波及全球時出現的西方現代繪畫,其繪畫原則就具有了與各文化相匯通的性質。同樣,現代物理學與東方古代思想,現代西方哲學與東方思維的相通性一面也呈現出來。回到哲學的基本概念上,在西方現代哲學中,靜態的“物”(thing事物)的根本性意義遭到否定,而動態的“事”(event事件)的根本性得到了高揚。維特根斯坦說:世界不是“物(thing)”的集合體,而是“事(event)”的集合體。定義的絕對權威受到否定,而宇宙本體的不可定義性得到了高揚。海德格爾說,一旦你要給“存在”下定義,那么其得到的只能是一個“存在者”,結果是關于“存在”的規定在,而“存在”本身卻不在。[1] (P592-601)
這三個哲學概念已經突出了中國學術演進在新世紀遇上的主要困難,下面再從中國美學史的術語揭示這種困難。
三、中國美學史用現代漢語表達的困難
從現代哲學這樣一門現代學科概念;立論,可以看到現代漢語在建立中如何與古代漢語斷裂;從中國美學史這樣一門講述古代的學科的主要概念為視點,可以呈現出在古今的斷裂中,古代的學術語匯何以難于進入現代漢語的學術語匯里。一方面,古代的材料必須要用現代漢語解釋才為現代人所理解,另一方面現代漢語的解釋在使現代人理解中國美學史的主要概念的同時,又往往錯解和誤解了這些概念的根本內涵,正因為這一錯解和誤解,以至古代漢語的學術語匯無法進入現代漢語的學術語匯之中。仍然舉三個中國美學的主要概念。
“氣”是中國文化的主要概念,也是中國美學的主要概念。文學上是“文以氣為主”[2] (P136),繪畫六法以“氣韻生動”為第一,書法上要“梭梭凜凜,常有生氣”[2] (P211),音樂上,要“冷冷然滿弦皆生氣氤氳”。[3] (P178)怎樣理解“氣”呢?哲學上,張岱年的《中國哲學史大綱》,任繼愈主編的《中國哲學史》,張立文發表的《中國哲學范疇發展史》,都把“氣”解釋為“物質”。這樣解釋,是與世界主流文化接軌了,但是失去了中國哲學的特點。在世界文化中,所有文化都把宇宙看成一種生命,只有古希臘人把宇宙歸結為物質,正是從這里,產生了被愛因斯坦稱為決定西方文化兩大基本的東西:形式邏輯和實驗科學。雖然一切非西方文化都把宇宙歸于生命,但其他文化都認為這一生命是神,只有中國文化把宇宙的生命看成“氣”,中國文化的宇宙就是一個氣的宇宙。氣,無法翻譯,它既在空中,又在地上,還在人體的體內,也在人的精神中,它是構成宇宙萬物的本質性的東西。荀子說:“水火有氣而無生,草木有生無知,禽獸有知而無義,人有氣有生有知亦且有義,故最為天下貫也。”[4] (P127)雖然水火、草木、禽獸、人有種種差別,但都有氣是一樣的。莊子說:“通天下一氣”[5] (P599),講的就是水火、草木、禽獸、人之間的共同性,這就是萬物都具生命性。《西游記》里孫悟空是石頭變的,為什么石頭能變成猴子呢?就是在于石與猴在氣這一生命性的共通性。西方文化中就不會有這一變化,因為對西方文化來說,石屬非生命的礦物,猴屬生命的動物,沒有相互轉化的同一性。在中國文化中,宇宙的根本是具有生命性的氣,藝術作品的根本也是具有生命性的氣,因此,氣韻生動是中國美學貫串到一切藝術作品中最根本的東西。在西方文化中最基本的是物質,生命體都被看作以物質實體為基礎生長出來的,是可以進行還原,放到實驗室里進行分析的,藝術作品當然也是一種可以進行分析的物質實體。
從西方近代文化精神而來的現代漢語面對中國美學的藝術作品中的氣,一旦要進行解說,就顯得困難重重,如李澤厚、劉綱紀《中國美學史》用了17頁來解釋謝赫的“氣韻生動”,但仍然沒有說得很清楚。(注:該書在旁征博引后進行的好幾次歸納中,雖然不能說沒有說出一些東西,但很難說它說清楚了什么東西。例如:“‘氣韻’作為一個美學范疇,就是與人的個性,氣質相關的生命的律動和個體的才情、智慧、精神的美兩者的統一,它呈現為一個訴之于直感的形象,處處顯出生命的律動,同時又滲透著一種內在精神的美,十分接近于音樂。”見李澤厚、劉綱紀:《中國美學史》第二卷(下),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7年版,第831頁。)從20世紀80年代以來數百本的美學理論和文學概論都不把氣韻生動這一中國美學最主要的概念引入其概念體系里,可見這里的講不清楚,在于兩套觀念體系的沖突。現代的美學理論和文學概論只能講清藝術作品中的與氣相關的“內容”,但卻不知道把氣放在內容的何處。關于這一觀念體系的沖突,我們放到后面講。
“神、骨、肉”這一組概念,可以說是氣的展開,也是氣韻生動的具體載體。氣是宇宙的生命,氣具體化在人體上就是神。氣是人體的基本,神是人體的統帥,就人體的核心層而言,氣、神、意、情屬于同一層面。人“含無一(氣)以為質,稟陰陽以立性、體五行而著行。”[6](P1)從整體而言,人體的基本層面可用神、骨、肉去把握。在中國文化中,藝術作品也是一個生命體,從而神、骨、肉也是藝術作品的基本結構。劉勰論文章“以情志為神明,事義為骨髓,辭采為肌膚,宮商為聲氣。”[2](P208)王國維論詞“(溫)飛卿之詞,句秀也;(韋)端己之詞,骨秀也;李后主之詞,神秀也。”[7](P16)這是從神、骨、肉(具體到詩上詞為“句”)結構把握。蘇軾說:“書必有神、氣、骨、肉、血。”[3](P41)謝赫的繪畫六法,氣韻生動、骨法用筆、應物象形、結營位置、隨類附彩,包含了氣、韻、骨、形、色。中國人體,從最簡說,是氣;概括點,是形神;基本一點,是神、骨、肉;具體全面些,是神、精、筋、骨、氣、色、儀、容、顏……用這套結構來講藝術作品,對古人來說得心應手。轉釋為現代美學語言,前面已經講了,形神可以釋為形式與內容,但一到神、骨、肉,就不好辦了。特別是以中國人體學為基礎的“骨”在以物質觀和分析法為基礎的西方美學范式里,找不到自己的位置。《文心雕龍》中“風骨”一篇,傷透了現代學者的腦筋,有人說,“骨”是內容,有人說“骨”是形式。由于“骨”的含義模糊,以至對“風骨”的解釋五花八門,出現了20多種說法。對“骨”產生歧義的根本在于中國古代的人體學范式與以西方近代精神為基礎的物質觀范式之間的沖突。現代漢語的學術語匯在建立于全盤西化和全盤蘇化時代造成的古今漢語在學術詞匯上的斷裂,使之在解釋中國古代美學面臨的困境,在“骨”上充分地體現了出來,“骨”在現代美學中找不到一個現代漢語來對應。
“意境”是中國美學的一個非常重要的概念,如果說神、骨、肉偏重于從結構談藝術作品,那么意境則是從審美特征談藝術作品。意境一詞既難于翻譯成西文,也難于翻譯成現代漢語。它雖然包含形式于其中,但形式只是它最淺的一層;它雖然包含形象于其中,但它更強調的是超越形象的象外之象;它雖然包含主題于其中,但主題對它強調的意外之意來說太膚淺;它有內容,但內容一詞所包含的可言說性在它的超以象外和言不盡意中顯得不合適。于是人們用“在有限中包含無限”,“于有限中表現無限”之類的語言來解說意境,這基本上讓我們可以理解到意境一詞的意思了,但是“有限”、“無限”這樣的詞匯又把意境網進了一種西方哲學結構之中,失去了意境本來的蘊含,也失去了意境的中國意味。最主要的是,意境一詞對接不出現代的美學原理和藝術原理的術語體系之中。由西方近代主客二分和實驗分析而來現代漢語學術語匯對解釋意境上遇上了最大的困難。意境包含著兩個基本方面,一是境不是客觀之景,而是客觀之景進入主體知覺中形成的境,境是主客觀的統一,如果把“境”看成是藝術作品中的形象,那么,這形象是主客觀的合一。意境不是形象就在于,作為形象的境包含著意,而這意既有可以從境(形象)中直接看到之意(如主題一類的東西),更在于不能直接把握而可以體會到的景外之景、象外之象、意外之意,味外之味、韻外之致。意境的這一根本特征不能像對待“物”一樣進行還原式的分析,而只能對之以心靈來體悟。因此,意境難于與任何一個西方語言和現代漢語的學術語匯進行對接,因此也難于邏輯嚴密地進入現代美學原理和藝術原理的語匯體系之中。
正因為以“氣”、“神、骨、肉”、“意境”等為代表的中國古代美學語匯,把以現代漢語為基礎的學術語匯的局限暴露了出來,讓我們重新思考中國文化在新世紀的思想建設和文化建設問題。
四、中國美學史的寫作與現代漢語學術語匯的更新
中國現代學術的建立和發展,經過了三個時期,一是從嚴復的體系性介紹西方,梁啟超領導的人文學科的全面革命到五四的全盤西化,建立了以西方近代精神為核心、以現代漢語為載體的中國現代學術語匯的主要精神和基本框架。二是從十月革命后前蘇聯與西方爭奪世界史的主導權,西方和前蘇聯文化在中國的競爭,到共和國成立,融西方古典傳統/俄國民主主義/蘇聯斯大林主義為一體的前蘇聯文化全面占領中國學術,與中國型馬克思主義的出現,完成了現代漢語學術語匯的全面轉型,并在共和國前期擴展到人文社會學科的一切方面。三是共和國的改革開放期,中國學術重新與作為世界主流文化的西方學術接軌。如果說,頭兩個時期,中國學術主要建立在西方近代精神之上(前蘇聯文化也是生長于西方近代精神之上,從培根、笛卡爾、康德到黑格爾、馬克思,到列寧、斯大林),那么,第三時期中國學術卻主要學習西方現代學術(從存在主義到精神分析、結構主義)和后現代學術(從加達默爾、阿多諾、后期維特根斯坦到德里達、福科、德勒茲,到利奧塔、波德里亞、詹姆遜)。西方現代和后現代思想與近代思想既有延續發展的一面,也有對立斷裂的一面。因此,以西方近代精神為基礎建立起來的現代漢語學術語匯,面對西方現代和后現代學術語匯,在對話和對接上,遇上了很大的困難,以現代和后現代為代表的20世紀西方學術思想的基本語匯,從20世紀80年代起,潮水般地進入中國學界,20多年過去了,卻仍然沒有進入現代漢語學術語匯的主流之中。根本原因之一,就在于西方近代學術與現代和后現代學術之間本有的對立和斷裂。
從17世紀西方文化向全球擴張,把本來分散的世界史帶進一個統一的世界史以來,西方文化分為三段,17世紀至19世紀末是近代,西方列強向外擴張直至把世界瓜分完畢。19世紀末至20世紀60年代是現代,西方列強之間的斗爭和帝國主義與被殖民民族之間的斗爭錯綜復雜,形成了以西方和前蘇聯為代表的兩極對立世界。從20世紀60年代到今,是后現代,從以電視和互聯網為主體的電子傳媒在社會中主導地位,消費社會的形成,大眾文化的普遍化,跨國資本的全球流動到兩極世界的消失,形成了全球化的新潮。近代西方思想,以牛頓、達爾文、黑格爾、基督教神學為代表,伴隨西方文化的全球擴張,具有堅定的西方價值優越觀,有清晰的西方/非西方二元對立世界等級圖式,堅定地認為西方是先進的、文明的、科學的、理性的、民主的,而非西方是落后的、野蠻的、愚昧的、迷信的、專制的,西方的擴張與殖民,就是給廣大的非西方文化帶去先進、文明、科學、理性、民主。正是因為以西方中心主義價值觀為指導,西方近代思想與非西方思想出現巨大的差距,顯現為尖銳的矛盾和對立。
西方與非西方經過三百年的斗爭與交流,西方人改變了自己的看法,形成了西方現代思想,它以愛因斯坦的現代物理學、海德格爾的存在主義、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列維·斯特勞斯的結構主義和現代神學為代表,運用一種存在/存在者、無意識/意識、表層現象、深層結構的本體/現象的復雜結構思維方式,這種方式更尊重各現象的復雜性和特殊性,西方文化的表現是一種現象,各非西方文化也是一種現象,從現象層面看,西方與非西方是平面的,沒有價值高下之分。然而在現代西方思想中,各種現象后面又有一個共同的本體,而這個統一的本體是通過西方思想而思考出來的,為西方思想所定義,又最與西方思想相通的,是為西方人首先把握和運用的,并在西方思想中得到最好的表達。從而這個本體實際上還是一個西方的本體,因而西方文化的價值在本體論上仍然是高于非西方價值的。盡管這樣,西方現代思想與非西方思想有了一種更多的相通性,比如,與近代思想相關的西方古典繪畫,是完全與非西方思想不同的焦點透視,而與現代西方思想一致的現代繪畫,則走到了與各非西方繪畫相通的平面構圖、平面造型、平面色彩上來了。在新一輪的信息全球化(電視與互聯網普及)、經濟全球化(資本跨國流動)、文化全球化(大眾文化全球傳播)的背景中出現的后現代思想,以德里達和福柯的后結構主義、后期維特根斯坦的語言游戲理論、阿多諾反同一性的否定辯證法、加達默爾否定原意的解釋學、利奧塔反大一統的宏偉敘事以及后殖民主義等為代表,徹底解構了存在一個本體論意義上的中心觀念。這時,西方文化與非西方文化才不僅在現象上是價值平等的,在本體論也是價值平等的。這樣后現代思維為全球對話和不同文化的溝通奠定了一個價值論平等和平等對話的基礎。
從西方文化三段來看,可以知道西方近代與各非西方文化距離最大,對立最強,西方現代和后現代與非西方文化距離稍近,對立較弱。自20世紀80年代中國接受西方現代和后現代以來,古代中國與西方現代與后現代的相似不斷地呈現出來:海德格爾與老子,德里達與莊子,格式塔美學的力的樣式與中國美學的氣韻生動,現代派藝術與八大山人的藝術……而現代漢語的學術語匯正是在中國與西方相遇的初期(即西方近代與古代中國的巨大距離時期)建立起來的。從而這一學術語匯在全球化的背景中,在共和國的改革開放時期,既遇上了解釋西方現代和后現代的困難,又遇上了解釋中國古代的困難,而且隨著形勢的發展,將還會遇到解釋其他世界文化(如印度文化、伊斯蘭文化等)的困難。因此,解決這一困難,不但是現代漢語學術語匯自我更新的需要,也是一個偉大的民族重新認識傳統的需要,更是中華民族在全球化的形勢下與世界各文化溝通的需要。在這一現實語境下,中國美學史的寫作,將成為推動現代漢語學術語匯更新的活動。美學是一門跨學科的學問,它關聯到哲學、藝術、人體、心理、社會、自然諸多學科,從而中國美學史的寫作,將把現代漢語學術語匯與古代學術語匯種種矛盾呈現出來,把這些矛盾與現代漢語在解釋西方現代和后現代學術碰上的矛盾結合起來,就會產生一種學術合力,而讓人全面思考現代漢語學術語匯的更新之路。從某種意義上說,中國學術的更新,其關結點、瓶頸處,是現代漢語學術語匯的更新。
[1]孫周興.海德格爾選集:上[M].上海:上海三聯書店,1996.
[2]北京大學哲學系美學室.中國美學史資料選編:上[Z].北京:中華書局,1980.
[3]北京大學哲學系美學室.中國美學史資料選編:下[Z].北京:中華書局,1980.
[4]北京大學《荀子》注釋組.荀子新注[M].北京:中華書局,1979.
[5]陳鼓應.莊子今注今釋[M].北京:中華書局,1983.
[6]劉紹.人物志[M].西寧:青海人民出版社,1978.
[7]王國維.人間詞話[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