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一首宋詞的英譯看文學翻譯中“信”與“美”的悖論
卓艷芬
摘要:本文從接受美學的角度對一首宋詞《鵲橋仙》的不同英譯本進行比較分析,探討中國詩詞翻譯中存在的“信”與“美”的悖論,認為評判譯文是否成功應以接受對象的期待視野和審美取向為前提。
關鍵詞:接受理論;文學翻譯;“信”與“美”
一、引言
中國古詩詞是中國傳統文學寶庫中一顆璀璨的明珠,其獨具魅力的格律形式和瑰麗華美的文采風流亦使之成為世界文學之林中的奇株異葩。人們或為其“落花無言,人淡如菊”的空靈雅致的風韻而吟詠回味,或因其“一洗萬古凡馬空”的曠達雄渾的氣象而擊節贊嘆,這些千古吟誦的詩詞凝聚著中國文字的獨特意象,沉淀著厚重的中國文化的神秘氣韻。故而許多人感嘆,譯中國古詩詞之難,難于上青天。的確,古詩詞翻譯至少在兩個方面存在著比其他翻譯更大的挑戰:語言形式即格律的忠實再現,和文化神韻的美感傳遞。中國古詩詞的“詩為樂心,聲為樂體”、平仄相輔、韻律整齊的語言形式構成了特有的外在美,而用字精煉,講究用典,又使其蘊涵著幽深綺麗的內在美。
由于英漢兩種語言在句子、詞形、聲音和表達方式上的截然不同,以及文化背景上的巨大差異,譯者便不可避免地陷入了中國古詩詞翻譯的悖論——“信”和“美”的痛苦抉擇中。信,指忠實于詩詞的語言形式,試圖在翻譯中用英語詩歌中的韻律來對應中國古詩詞的格律,“如用揚抑格來表示平仄,用重讀音節與中國的古詩詞中的字數相對,用強調韻的密度來對應中國古詩詞中的韻等等”。(王守義:《論中國古詩詞英譯》)“美”,則是指在譯文中傳遞詩詞中只可意會不可言傳的獨特美感和神韻,使譯語讀者得以領略和欣賞。一直以來,譯學界對中國古詩詞的翻譯見仁見智,但也無非是在“信”與“美”這兩個命題之間徘徊:是寧信而不美?抑或為求“神似”,而放棄形式?還是在信與美之間尋找一個同心圓?筆者認為,中國古詩詞的英譯要擺脫這種進退兩難的悖論,必須首先明確翻譯古詩詞的意義和目的是為了介紹和傳播中國的文學和文化,既然翻譯本身就是一個閱讀和再創造的過程,而譯者由于先在認知,審美情趣和期待視野的各自差異,對同一文本的翻譯必然不盡相同。因而,對中國古詩詞的英譯不妨拋棄“信”和“美”這些無謂的爭論,因為這些抽象的概念不可能有一個絕對的標準。只要在譯語讀者可接受的限度內,譯出受本國文化限制的古詩詞的意象,神韻和美感,那么這個譯文便不失為一個成功的范例。本文擬從接受美學的角度,對一首宋詞的不同英譯為例進行分析和探討。
二、接受理論與文學翻譯
翻譯由于對象、手段、要求等的不同,而有種種不同的分類。文學翻譯則是其中最無定性、最變幻莫測、最難把握的一種。因為它面對的是變異無窮的文學文本。它的手段與形式屬于語言范疇,但追求的是文學作品的美學價值。西方文論中接受美學理論把文學文本從決定性和自足性的牢籠里解放出來,而將接受理論的主要觀點與研究方法引入文學翻譯研究則構成了對原來的文學翻譯標準的反駁。以西德康斯坦茨學派為中心的文學接受理論認為,作品的意義不是一個現成的完整地存在于文本之中有待于批評家去尋找的東西,而是具有無限的開放性和多樣性。文本未閱讀時,包含著許多“意義空白”和“未定性”,讀者在閱讀過程中發揮想象并加以補充,使之“具體化”,從而發掘文本的意義。因而讀者對作品的意義起著決定性的作用。作品的意義因讀者不同“具體化”而有所不同,不可能對某一文本的理解確定最后的限界。因而,文學的接受可分為“垂直接受”和“水平接受”。垂直是指從歷史延續的縱向角度考察讀者接受作品的情況;水平是指同一時代的不同讀者橫向接受作品的情況。但突出讀者的決定作用并不意味著在接受過程中絲毫不受作品的制約,他們提出“呼喚結構”,即作品中的空白呼吁讀者去完成作品的未盡之意,它一方面是讀者的再創造,一方面規定了讀者的理解不能逾越作品本身包含的潛在含義。接受理論否定了文本的封閉性,文本不是給讀者唯一不變的意義,而是為讀者提供多種意義的可能性,它不再是限制理解,而是語言解放,是觀念上的革命。翻譯是一種特殊的語言交流活動,譯者身兼兩職,既是讀者又是信息傳遞者,而且,首先是一個讀者。在文學翻譯過程中,譯者首先進行的是一種文學閱讀,并且是一種比一般閱讀更積極的、更加具有參與沖動的、主體意識更加活躍的特殊閱讀,即批評性閱讀。譯者的譯本則是他閱讀后經過語言轉換固化了的文學閱讀,是讀者接受的凝固形式。
如果從接受理論的視角來看文學翻譯的話,譯者作為讀者所面對的則是一個開放而未定的文本,文本意義的具體化與譯者自身的審美體驗或期待視野密切相關,每個讀者都會把自己獨特的“能力模式”帶入閱讀過程,用不同的方式去填補文本的“空白點”。因此,對同一文本各自所獲得的美學價值也就不同。譯者所處的特殊地位使他不能停留在審美的意境中,還必須進一步將各自的審美感受用譯語表達出來,于是同一個作品便理所當然地出現內涵不盡一致的譯本了。按照這樣的觀點,我們看到,文學翻譯中,變化不僅僅發生在語言層面,更重要的是,它是滲透了譯者對于原文本一切文化、藝術、歷史等種種文學內容的理解、接受與闡釋。任何文本都永遠不可能被徹底完成,文本內涵也因譯者的不同而被不同的完成。
三、文學翻譯中的“信”與“美”
從某種意義上來說,文學翻譯本身就是一種創造性的語言藝術。我國翻譯界歷來強調“信”,自嚴復、魯迅以來,“信”一直是翻譯的標準之一,然而關于“信”的理解卻并不一致,眾說紛紜。而文學翻譯既然是一門藝術,“美”自然是不能或缺的。于是,如何才能做到“信而美”成了譯界的難題。而筆者認為,從接受理論的觀點出發,所謂“信而美”的譯文正如烏托邦一樣是不可能的,下面讓我們從一首宋詞的不同英譯來進行分析。
鵲橋仙
秦觀
纖云弄巧,飛星傳恨,銀漢迢迢暗度。
金風玉露一相逢,便勝卻人間無數。
柔情似水,佳期如夢,忍顧鵲橋歸路!
兩情若是久長時,又豈在朝朝暮暮!
秦觀的這首詞以清麗細膩的筆觸,歌詠牛郎織女純潔真摯的愛情故事,境界幽深,纏綿悱惻,令人吟詠再三而回味無窮,可謂千古絕唱。下面將四種不同的英譯抄錄如下,以進行分析比較。
Que Qiao Xian
Clouds have their peculiar flair and skill;
They can change their size and shape, as they will.
Stars have qualities more wonderful still;
The hopes of their fellows,they can fulfill,
In those celestial regions,high above,
As links for one star to appproach her love.
They help “Lassie” to cross the Milky Way,
To see her “ Laddie” once a year, this day.
Their love is like heavenly dew for gods to drink.
To the human level,it would never sink.
One rendezvous between them is of more worth-
Than countless such as we have on this,our earth.
Their love is constant, as water is, in its flow.
The lover’s meeting is short, as sweet dreams go.
How she bears the sight of Magpie Bridge without a tear.
Which marks their separation for another year!
ince their affection is something that endure,
Must they bill and coo as daily renewer?
——張德鑫 譯
Que Qiao Xian
The fleecy clouds affect patterns delicate;
The flying stars communicate their grief e’er so deep,
Crossing the expansive Milky Way they meet
Alas! That single meet amid celestial winds and dews
Surpasses countless meets on earth;
Sweet tenderness overflows their hearts,
Short rendezvous passes like a dream
Mournfully she contemplates her homeward way
Across the magpie-bridge!
Yet if two hearts are ever steadfast,
Though parted, they are together
Night and day!
——黃宏荃 譯
Lines for the Que Qiao Xian Melody
These transparent clouds so delicate and beautiful
The milky way so luminous a star vanishes in it
That falling star which caries regret like a messenger
For the cowherd and the woman at the loom
Altair and vega
Those lovers who can meet only once in a year
But for them this is more wonderful
Than the countless times
Lovers in this world meet
They are joined for one long perfected moment
They merge into each other like slow running waters
Their happy loving is the kindliest of dreams
Oh they have to know the sadness of looking back
As they depart on their separate ways
Traveling over the bridge of birds
But because what they feel shines in them forever
It surely does not distress them
Each day and each night they cannot be together
——王守義 / 約翰·諾弗爾 譯
Tune:“ Immmortal at the Magpie Bridge”
Clouds float like works of art;
Stars shoot with grief at heart.
Across the Milky Way the Cowherd meets the Maid
When Autumn’s Golden wind embraces Dew of Jades,
All the love scenes on earth,however many, fade
Their tender love flows like a stream;
This happy date seems but a dream.
Can they bear a separate homeward way?
If love between both sides can last for aye,
Why need they stay together night and day?
——許淵沖 譯
詞是中國特有的文學體裁。宋人作詞擇調,不光選擇調聲,更要顧及調名。當然詞調多數具有通用性,在內容和題材上并沒有太嚴格的限制。但有些詞調,“按其制調造曲的本意和習慣用法,用調時不能背離。”鵲橋仙這個詞調一般用于節序,主要是詠七夕,這幾乎是約定俗成的。從對詞調的翻譯來看,只有許淵沖先生的翻譯將這個詞調的含義譯了出來,其他三首翻譯都只是用漢語拼音把鵲橋仙這個極具中國傳統文化內涵的詞調名直譯了過去。這種譯法似乎過于籠統。如不對這個詞調名進行解釋的話,那么不熟悉中國文化背景的譯文讀者會如讀天書,不知所云。
這首詞一開頭前三句便描繪了一幅七夕的美景。“纖云弄巧”,天上纖細的云彩飄曳多姿,色彩紛呈,可以想見織女的編織技巧是多么高明和精巧。“飛星傳恨”,天空劃過一道閃亮的光輝,從東到西越過半個天空,又消失在冥冥的黑暗里。這一顆明亮的流星,仿佛又是一位報訊的多情使者,為牛郎織女傳送著離愁別恨。“銀漢迢迢暗渡”,七夕的歡會之期,通過它的流光,帶出了牛女雙星通過鵲橋,渡過銀河,作一年一度的聚合了。對這三句的翻譯,可以說四位譯者的版本大相徑庭。張的譯文在很大程度上已經與原詞偏離了,他把織女星譯成了“Lassie”,英文里是“少女”的意思,而牛郎則譯為“Laddie”,“少年”的意思。原詞里關于牛郎織女的神話愛情故事在譯文里消失無蹤了。其他三個譯本的譯文的意思都跟原文大致相近,只是許淵沖的譯文更近似于英語詩體,在押韻和音步等方面下了一番工夫。而黃宏荃與王守義的譯文則近乎于散體(free verse)。此外,盡管原詞沒有出現牛郎星和織女星這兩個詞,除了黃的譯文之外,其他三個版本都把這兩個詞給譯出來了。如許淵沖的譯文是“coward”和“maid”,而王守義 / 約翰·諾弗爾則譯為“Altair and vega”,并在此前作了解釋-“the cowherd and the woman at the loom”。可見譯者在翻譯的時候考慮到了譯語讀者的文化限制和接受的限度,試圖在譯文中通過不同的方式來傳遞原詞的文化底蘊。但是仔細的分析之后,會發現所有的譯文似乎都有對原文不忠之嫌,因為原詞中并無牛郎織女幾個字出現。何謂“信”?如果不對原詞所蘊藏的文化內涵進行解釋,以致譯文讀者不明所以然,那么這樣的譯文似乎也無“信”可言了。所以在文學翻譯中一個“信”字可大有文章在。 “金風玉露一相逢,便勝卻人間無數。”這兩句可謂是上闋的點睛之筆,大意是牛郎織女在美好秋夜的匆匆一晤,其深切情愛卻勝過人間無數朝夕相伴的戀人。“金風玉露”四字充分體現了中國文字的不可言傳的美感,既點明了七夕之期,又烘托出二星愛情的純潔美好。在對這兩句詞的處理上,各個譯者采取了不同的策略。許譯幾乎是字對字的直譯,固然“信”也,卻有“寧信而不順”之嫌,這對于不知“金風玉露”為何意的譯語讀者而言,可能會丈二金剛摸不著頭腦,引起文化誤讀了。張譯和黃譯相似,把“金風玉露”譯成了“Heavenly dews”和“celestial winds and dews”,與原詞的含義已相去甚遠了。而王譯則把這四個字的翻譯省去,避而不譯,只把原詞的大致內涵譯了出來。相比較而言,似乎王譯更為明智和容易為譯文讀者所接受。在詩詞翻譯中,與其受制于原文的語言形式和文化負荷,一味追求“信”而拋離原文導致不順不美且為譯語讀者難以接受的譯文,不如適當地作些割舍,以準確傳達原文意思為主要目標。
下片開頭寫雙星的一段短暫的歡會。“柔情似水”,形容雙方感情深沉廣大,浩渺無際;“佳期如夢”,這一歡會又是似真如幻,并且是非常短暫的;“忍顧鵲橋歸路”,不能不分手了。一個“忍”字,如怨如慕,如泣如訴,寫出了多少依戀,多少悵惘!“兩情若是久長時,又豈在朝朝暮暮!”詞尾的一聲感嘆,把這纏綿的意象升華了,把一往情深的愛戀抒發得酣暢淋漓,令人蕩氣回腸。從四個譯本的翻譯看,不同譯者對原詞的的內容,情感和文化內涵等種種不同認識、接受與闡釋,使他們的譯文呈現出了迥然相異的風格。如果從所謂“信”和“美”的角度去評價,很難說誰的譯文更忠實,或更具有美感。
四、結語
我國的傳統譯論受傳統的美學文論的影響,從本文出發,一味追求譯作文本與原文文本的全方位契合,實際上是一種幻想。從傳統的“信、達、雅”,到“神似”和“化境”,“直譯與意譯”,再到奈達的“動態對等”、“等值反應”等等,可以說已成為一種公認的文學翻譯標準,盡管表達不盡一致,但都旨在通過原語文本與譯語文本的比較,最終達到最大限度的理想的譯文這一目的,并以此來評判翻譯結果的好與壞,是與非。文學翻譯,尤其是詩歌翻譯,更是強調譯文再現原文的“形美、音美、意美”,然而從對上面的幾種譯文的分析和比較,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沒有一個譯本是十全十美的。因為“信”和“美”都只是相對而言的,從不同的角度去分析便會有不同的標準。
正如尤金·奈達(1993:5)所指出的:“翻譯中最不可思議的矛盾是從沒有十全十美或永恒不變的譯文,因為語言和文化都在不斷地變化著。”既然如此,任何譯文所展現的都是在一定歷史時期或階段的語言和文化制約下的對原文文本的詮釋和再現。而譯者對文本的闡釋并沒有一個固定不變的準則,對于文本的解釋和爭論可以無休止地進行下去。因而,所謂對原文的“信”“和”“美”,早已轉化成了不同譯者對譯文與各自所理解和認識的原文相對照的主觀的“信”與“美”,并沒有一個客觀存在的正確與否的標準。于是乎誰信誰美的爭論似乎已無任何的實質意義,異人異譯的現象由來已久,譯文實際上是不同譯者以原文為模本而獨創的作品,認識到這一點,才能真正走出文學翻譯中的“信”與“美”相悖的怪圈。
[1]Eugene A.Nida.1983.Language,culture,and Translating[M]. Shanghai:Shanghai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2]馬以鑫.接受美學新論[M].上海:學林出版社,1995.
[3]特里·伊格爾頓,王逢振 譯.當代西方文學理論[M].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8.
[4]王守義 約翰·諾弗爾.唐詩宋詞英譯[M].黑龍江人民出版社,1989.
[5]許淵沖.唐宋詞一百首[M].中國對外翻譯出版公司,1991.
[6]吳熊和.唐宋詞通論[M].浙江古籍出版社,1989.
[7]姚念賡,范岳.英漢翻譯論稿[M].遼寧大學出版社,1987.
[8]朱云奇.朝圣者的靈魂[M].外語教學與教育出版社,1994.
[9]張德鑫.中國古典文學概觀[M].北京語言學院出版社,199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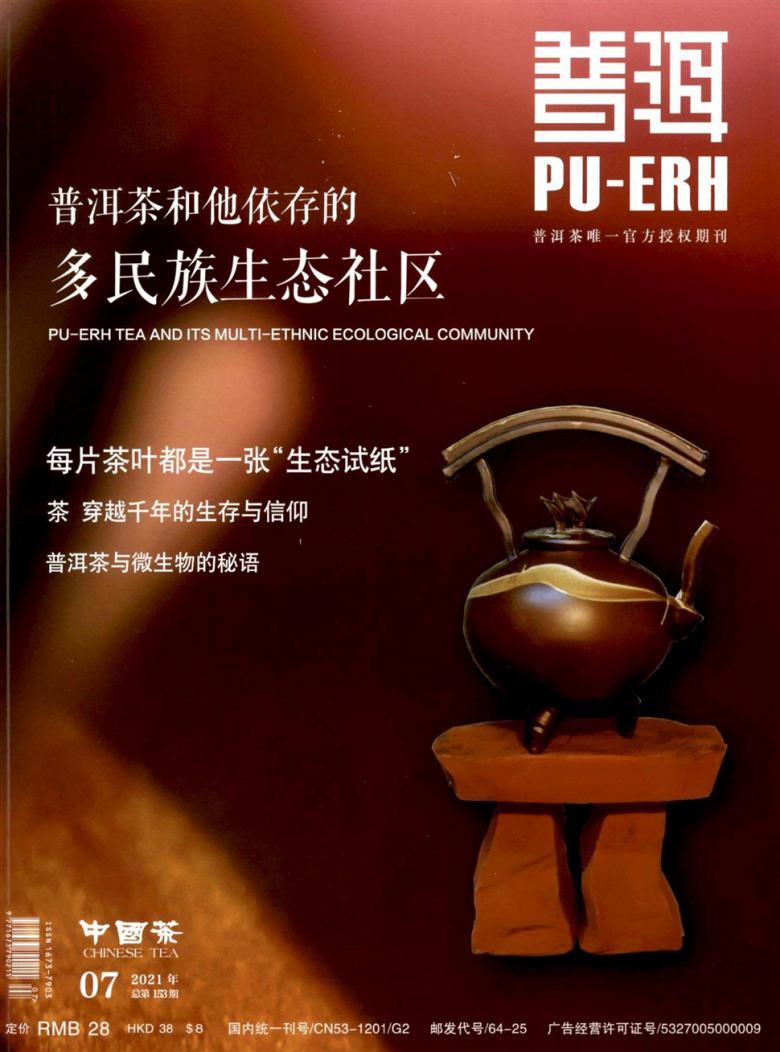

.jp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