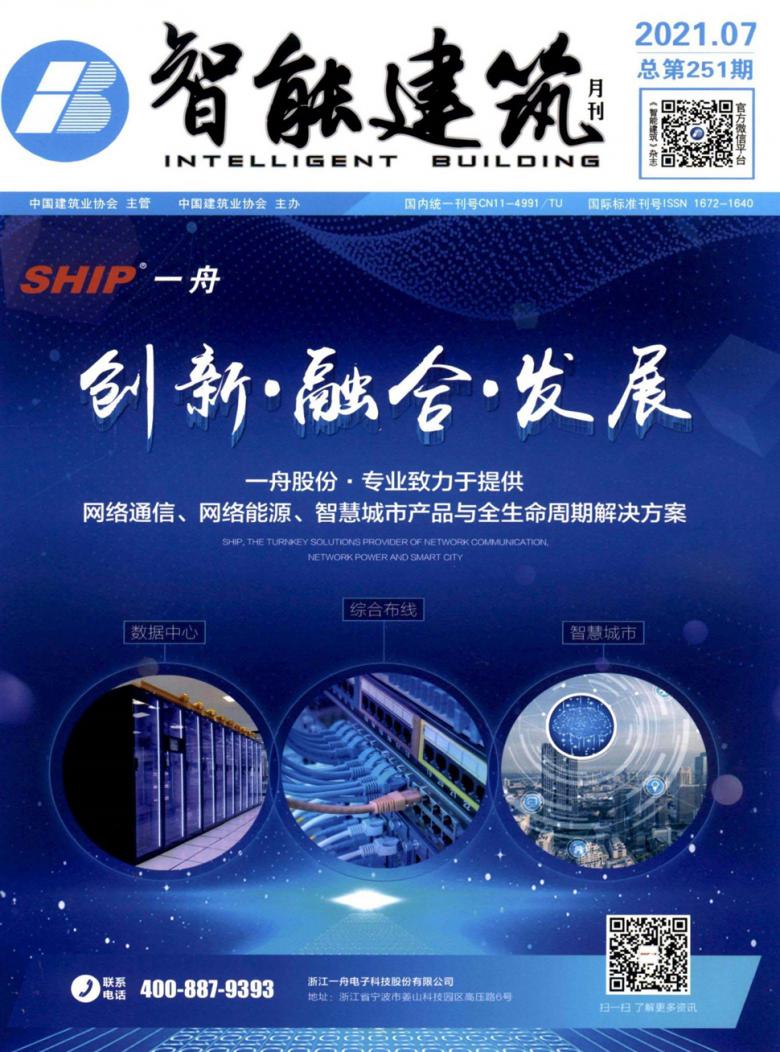魏源對老子的真詮——《老子本義》讀釋蠡析
李素平
一、概述
1、生平簡介
魏源,原名遠達,字良圖,又字墨生、漢士,號默深,法名承貫。湖南邵陽人,生于公元一七九四年(清乾隆五十九年),卒于一八五七年(清咸豐七年)。
一八0八年(嘉慶十三年),考取秀才。一八二二年(道光二年)考中舉人后,受江蘇布政史賀長齡聘,編輯《皇朝經世文編》。一八二六年會試落地。一八四一年,在兩江總督裕謙幕府中參謀。鴉片戰爭失敗,憤而寫成《圣武記》。一八四四年,中了進士,分發到江蘇高郵州作知州。一八四六年(道光二十六年),他在林則徐《四洲通》的基礎上編纂作成《海國圖志》。一八五三年(咸豐三年)太平天國克復南京時,他在高郵以知州身份辦團練,抵抗之。一八五四年以“坐遲誤驛”被劾去職。后來回興化老家,皈依佛門,專治佛學。一八五七年死于杭州。終年六十四歲。
魏源一生著述甚豐,在經學、佛教、諸子學上均有論述。
2、關于《老子本義》著述時間的爭議
有學者認為《老子本義》二卷是魏源一八二三年至一八二四年之間所作。”[1]
黃麗鏞、許冠三關于魏源《老子本義》成書年代有過較長時間的爭論。黃麗鏞認為《老子本義》成書年代最晚不會遲于嘉慶二十五年(一八二○年),即為魏源二十六歲前所作。許冠三堅持認為《魏源年譜》之一八四O年說,即魏源四十六歲所作。理由是懷疑今傳本《老子本義》是否為‘嘉慶二十五年奉母東下錄于舟中’之原本?他分析“今傳本《老子本義》非但經過增訂,而且增訂之痕跡相當明白。大致是《本義》上、下篇之撰述最早,其次是《論老子》四章,最后才有《序》。《論老子》優,而上、下篇劣。”[2]
筆者基本同意許冠三先生認為《老子本義》上、下篇之撰述最早,其次是《論老子》四章,書成之后作《序》,也同意他對作品優劣的分析結論,但不同意其一八四O年之說。
筆者以為魏源的《老子本義》研讀注釋大致是一八四四年到一八五五年期間,即五十歲至六十歲之間,為官高郵期間主要從事注釋,被革職回老家皈依佛門之前乃修改增訂上下篇,并著成《論老子》四章。因為:
(1) 通觀《老子本義》,就能發現魏源前后思想的矛盾、不一貫,有些章節評注資料豐富、詳細,有些則相當簡單,如第十二章。魏源最先動筆的是考證《史記·老子列傳》及收集《附錄》的資料,其次是作《老子本義》上、下篇的注釋,在此基礎上他把握了《老子》思想的基本脈絡,遂寫就了《論老子》1——4章,集中闡述了他對《老子》以及老學研究的看法,可以認為是一鼓作氣完成的,最后是《老子本義序》。魏源在當時是以“好時務者”而著稱,作為今文經學一員干將,在儒家經典里苦苦尋找治國方略,結果發現:“內圣外王之學,闇而不明,百家又往而不返,五谷荑稗,同歸無成,悲夫!知以不忍不敢為學,則仁義之實行其間焉可也。”[3]他的學術重點由經學轉向子學,釋老為救世之書,顯然,魏源有拿《老子》為經世致用服務的目的。
(2) 魏源早年關注“公羊春秋”,是清朝今文經學的一員大將,直言“五帝不沿禮,三王不襲樂”[4],他主要精力用于研究儒家經典,試圖用“經世致用”思想來改變清朝江河日下的局勢,但科舉會試的失敗,鴉片戰爭清朝的失敗,個人仕途的坎坷,都動搖并銷蝕了他“慷慨論天下事”的雄心壯志。他清醒地向清王朝提出警告:“大不相齊即至喪天下”。然而在當時的環境之中他找不到別的更有用、實效的思想工具來達抵踐履“經世致用”這一理想,遂思量用道、佛來互補,思以“救世”,同時“救己”之“心灰意冷”,這只能是他中、晚年目睹“世風日下”,經歷坎坷之后才可能做的事情。[5]
(3) 魏源在《老子本義序》里反復提示、警告統治者“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亂。如遇大寒暑、大疾苦之后,則惟診治調息以養復其元,而未可施以肥濃朘削之劑”;“當天下生民大災患、大痌瘝之時”當則“約法三章,盡革苛政酷刑,不擾獄市,不更法令”;“況人主窮于道者乎?下奪民力,故荊棘生,上違天時,故有兇年”等,顯系有的放矢。魏源所處的時代正是清王朝由盛而衰、內憂外患相逼而來的時代,那時內有白蓮教、太平天國、小刀會、邊疆少數民族反滿等農民、邊民的起義運動;外有外敵入侵,帝國主義列強的堅船利炮轟開了清王朝閉關鎖國的大門。對一個飽讀經書,憂國憂民,思想敏銳的士大夫來說,他必定在痛苦悲憤中對許多東西進行反思,能說出“圣人經世之書,而《老子》救世書也”,可見反思之深刻。而對一個熱血沸騰、慷慨激昂的年輕人(指黃、鐘的說法)來說,恐怕難以做到。
(4) 文筆風格來看,《老子本義》顯然不及《海國圖志》、《圣武記》、《古微堂集》、《古微堂詩集》、《書古微》、《默觚》、《孫子集注》這些文章辛辣、犀利,血氣方剛,盡管筆鋒尚顯銳利,但畢竟顯得無奈、滄桑、落寞多了。尤其是《論老子》四章有極為成熟老練的閱歷隱含其中。
(5) 《老子本義》上、下篇中出現援釋喻老的情況,據說,魏源“潛心禪理,博覽經藏”乃是道光八年(一八二八)的事情,晚年皈依佛門,這期間,并未終止對禪理的窮究。這說明,在他尚未對佛、道兩家有明確、深刻認識之前,自以為佛、道兩家有合,《老子本義》上下篇里出現援釋喻老,等細究之后,就非常明確地在《論老子》和《序》里否定二家合。這也說明《老子本義》并非一時之作,亦非青年所作。
(6)魏源在《孫子集注序》里說老子是一部兵書:“《老子》其言兵之書乎?‘天下莫柔弱于水,而攻堅強者莫之能先’吾于斯見兵之形。……故夫經之《易》也、子之《老》也、兵家之《孫》也,其道皆冒萬有,其心皆照宇宙,其術皆合天人、綜常變者也。”[6] 按照《清史列傳·魏源傳》所排書籍例目,《孫子集注》在《老子本義》后面。有資料認為,《孫子集注》在《海國圖志》(一八四二)年之前。筆者以為是作于鴉片戰爭之前的一、二年里,大約是在作裕謙幕僚時寫的。可惜此書已佚,只存《孫子集注序》一篇。他說:“夫非知《易》與《老》之旨者,孰與言乎?”顯然,認為《易》與《老子》都是“言兵之書”。《孫子》則言兵以通于道,可看作是魏源“《老子》一書是救世之書”這一觀點的前奏。
《老子本義》此書的刊行據說是在魏源去世之后的光緒四年(一八七八),對此,黃、許二人均沒有異議。筆者亦認可此說。
以上僅為個人之蠡見,未經嚴格考證,我以為關于《老子本義》寫作時間及刊行時間這一問題不是研究魏源老學思想的關鍵所在。所以只是粗略釋讀,期望史學考證專家專門考證。
3、《老子本義》的分章不同于通行本
魏源對老學史上的分章進行了一番評述:
《河上公注》不見《漢·志》,隋始有之,唐劉知幾即斥其妄,所分八十一章,與嚴君平《道德指歸》所分七十二章,王弼舊本所分七十九章,皆大同小異。[7]
魏源基本接受了的吳澄分章,其《老子本義》在分章上與吳澄完全一樣。沒有稱呼《道德經》,而直稱《老子》。分為六十八章,上篇三十二章,下篇三十六章。將通行本第一章列為篇首語,這一點與吳澄一樣。所以說,魏源在分章上沒有多大新意。不同的地方在于他對有些章節的斷句上有吳澄不一樣。由此也引發了他對老子思想的闡述上與吳澄之間的不同[8][9]。
4、《老子本義》的解釋手法
魏源注釋《老子》的方法亦與河上公、嚴君平有所不同,以上二本直接表述自家的理解,未曾引述別家。魏源則采用“類比”的手法,除夾句校字外,分章引述前人如王弼、韓非、呂惠卿、陳懿典、吳澄、蘇轍、焦竑、李嘉謨、李贄等人的注說,引述之后加以“案語”詮以己意補綴。需要指出的是魏源在義理闡發上根本沒有采納嚴遵、河上公的任何言辭,只是在原文斷句、字詞辨析上部分采用了他們的意見。顯然,在辨別歧義方面,魏源盡量回避養生、虛無之解讀。
二、 魏源擬還原一個被歷史曲解的老子
魏源在《老子本義》里指責老學史上無一人得老子之真,因此魏源他要還原一個被歷史曲解的本真老子。這說明魏源在研究子學時秉持諸子經典與儒家經典應予以同等真詮這一立場,也說明在對經典解釋的問題上魏源有自己的認知解讀準則的。
魏源堅持對老子進行詮釋時應持以“真”的標準,否則“遂至萬事蠱廢”,“王綱解紐,萬事瓦裂”。他認為解《老子》得真與不得真,具有重大的現實意義:
老氏書賅古今,通上下。上焉者羲皇、關尹治之以明道;中焉者良、參、文、景治之以濟世;下焉者明太祖誦“民不畏死”而心滅,宋太祖聞“佳兵不祥”之戒而動色是也。儒者自益亦然,深見深,淺見淺。余不能有得于道而使氣焉,故貪其對治而三復也。[10]
老子一書“賅古今,通上下”,顯然是在高度評價老子,認為老子思想融古博今,通貫上下幾千年。至少有三個歷史階段說明《老子》具有治理國家、管理社會的功能或者說理解老子有三種境界。“上焉者羲皇、關尹治之以明道”,“上”即魏源所津津樂道的太古社會,民風淳樸,人們無憂無慮、生活閑適,安定和樂。亦可以將上解釋為最高的境界、檔次:羲皇(即伏羲氏)、關尹鉆研老子思想以求昭彰大道――“明道”。“中焉者良、參、文、景治之以濟世”,“中”從朝代講可以說是指漢朝社會了。或謂魏源認為老子思想的次一個境界為“濟世”,張良、曹參、文、景之采用黃老學說,清靜無為而治,遂取得天下安定,修養生息。“下焉者明太祖誦‘民不畏死’而心滅,宋太祖聞‘佳兵不祥’之戒而動色是也。”“下”可謂是指明朝、宋朝了。或謂再下一個境界為“勸世”。這要看《大明太祖高皇帝御注道德真經》里所云:“朕……見本經云民不畏死,奈何以死而懼之?當是時天下初定,民頑吏弊,雖朝有十人而棄市,暮有百人而仍為之。如此者,豈不應經之所云?胗乃罷極刑而囚役之,不逾年而朕心滅。”[11]據《宋史·太祖本紀》記載:宋太祖趙匡胤在閱讀《老子》之后,對攻伐江南后主李煜的十萬將士戒告曰:“城陷之日,慎無殺戮。”趙匡胤在位“務農興學,慎罰薄斂,與世休息,迄于丕平。治定功成,制禮作樂。”[12]
魏源在《老子本義》中尚有:“《老子》之書,上之可以明道,中之可以治身,推之可以治人”的說法,可謂是上述思想的繼續表達。顯然,在魏源看來,《老子》一書在上下幾千年、各個朝代均起過不同的歷史作用,這些作用都是有利于人類社會長遠發展的,有利于生命的維護和天下的穩定。在魏源的解老思想中,認為解釋老子最高的境界為“明道”是毋庸置疑的了,其次為“濟世、治國”,再次為“治身、治人”。所以,《老子本義》雖然沒有直接提出諸如河工、鹽政、漕政、幣制等改革措施,也沒有提及“師夷”等對策,但它同樣是魏源經世致用主張的論壇,這與他研治今文經學,闡發微言大義的做法如出一轍,有異曲同工之效。
魏源指出老學史研究中的一種現象:“后世之述《老子》者,如韓非有《喻老》、《解老》,則是以刑名為道德,王雱、呂惠卿諸家皆以莊解老,蘇子由、焦竑、李贄諸家又動以釋家之意解老,無一人得其真。”[13]
這么強硬的否定態度,不禁令我們對魏源的《老子本義》刮目相看。我們不禁要問:魏源究竟得到《老子》什么“真傳”?抑或說魏源挖掘、抓住了正確解釋《老子》思想的什么真諦?
魏源對自己的解老自視甚高:“著其是,舍其是,原其本,析其歧,庶竊比于述而好古者。”他將老子之說未能在現世發揮應有的歷史作用,歸結為諸子解讀丟棄本根臆說曲解,為此進行激烈批評:
《解老》自韓非下千百家,老子不復生,誰定之?彼皆執其一言而閡諸五千言者也。取予翕辟,何與無為清靜?芻狗萬物,何與慈救慈衛?玄牝久視,何與后身外身?泥其一而誣其全,則五千言如耳目口鼻之不能相通。夫不得言之宗、事之君,而徒尋聲逐景于其末,豈易知易行,而卒莫之知且行以至于今泯泯也。[14]
這口氣儼然宣布魏源是真正證悟老子本義了。那么,我們要問,魏源解老求“真”的標準是什么呢?
魏源所謂的“真”是“本原”、“自身”的意思,魏源認為解老的標準必須得“言有宗、事有君”,也就是說他堅持對經典詮釋恪守“本真(即忠實性)”標準。魏源說的很明白,他認為得《老子》之“真”就在于把握老子思想不但能治理天下,尤其在社會危亡之際能“救世”。言外之意,指望僧侶、道士從老子中解讀出“救世”的思想是不可能的。從魏源釋老的這一思路來看,顯然魏源意識到解釋者對經典解讀的不同在于其具體歷史環境所限制。他之所以發出如此不客氣的批評,就在于他認為不“忠實”于老子的本意,臆說妄度的解釋會對社會造成極大危害,這是歷史事實。釋《老子》為救世之書,顯然魏源有致力于拿《老子》為經世致用服務的目的,其釋老的本意亦可歸結於斯。
魏源對當時的政風有深刻的體驗:“鄙夫胸中,除富貴而外不知國計民生為何事,除私黨而外不知人才為何物。所陳諸上者,無非膚瑣不急之談,紛飾潤色之事。以宴安鴆毒為培元氣,以養癰貽患為守舊章,以緘默固寵為保明哲,人主被其熏陶漸摩,亦潛化于痿痹不仁而莫之覺。豈知久之又久,無職不曠,無事不蠱,其害且在強藩、女禍、外戚、宦寺、權奸之上,其人則方托老成文學,光鋪升平,攻之無可攻,刺之無可刺,使天下不陰受其害而已不與其責焉。古之庸醫殺人,今之庸醫,不能生人,亦不敢殺人,不問寒、熱、虛、實、內傷、外感,概予溫補和解之劑,致人于不生不死之間,而病日深日痼。故鄙夫之害治也,猶鄉愿之害德也,圣人不惡小人而惡鄙夫鄉愿,豈不深哉!”[15]他反復研討《老子》,在他看來《老子》能對挽救衰敗的清王室、革除官吏“鄙夫”弄虛作假、貪生怕死、侈糜富貴、粉飾太平、結黨營私、因循守舊等弊端,除祛“人心之寐患”和“人才之虛患”等弊端有用。他說:“圣人經世之書,而老子救世書也。使生成周比戶可封之時,則亦默爾已矣。”[16]這就是說,儒家經典是講治理社會的,而《老子》是在社會危難時期起挽救作用的。在《老子本義》中多次說:
《老子》救世之書也。[17]
老子著書,明道救時。[18]
老子見學術日歧,滯有溺跡,思以真常不弊之道救之。[19]
此老子憫時救世之心也。[20]
魏源理想的救世,就是“遂以太古之治矯末世之弊”。[21]魏源認為,在老子看來最初的社會是太古社會,那時的政治叫做太古之治,是最為理想的政治狀態。但人類社會卻不能永遠保持那種美好的社會政治,必然要向不好的社會政治轉變,這就是魏源所說的必然要遞相嬗變,而且越變越不好,到了最糟糕的時候,就叫做末世:
氣化遞嬗,如寒暑然。太古之不能不唐虞三代,唐虞三代之不能不后世。一家高曾祖父,子姓有不能同,故忠質文皆遞以救弊,而弊極則將復返其初。[22]
魏源借用氣化遞嬗,就好比寒暑變更,來說明老子生活的時代已經不再是太古之世了,他已經看不到太古之治了,就連次一等的唐虞三代,他也只能通過歷史的記載來了解了,而且太古、三代、后世的遞相更替都是無法逆轉的。所謂的“夏尚忠、商尚質、周尚文”,在魏源看來只不過是遞以救弊。老子實際面臨的乃是“弊極”的“后世”:“末世小人多而君子少,人以獨善之難為也,而不知秉彝之不改也。”[23]
如果沒有太古及唐虞三代的美好政治加以對比,也許人們對于面臨的惡劣的政治和社會還不會那么反感和厭惡。因此,老子在這種“弊極”的“后世”之社會里,對于現實的不滿就促成了他的深刻思索。魏源分析老子著書立說的動機:“吏隱靜觀,深疾末世用禮之失,疾之甚則思古益篤,思之篤則求之益深。懷德抱道,白首而后著書,其意不返斯世于太古淳樸不止也。”[24] 魏源認為老子著書的目的,是要用他的思想主張來救世。所謂救世,是因為世道已經變得充滿弊端,完全與太古自然淳樸之風氣相違背。魏源認為老子通過退隱觀察,深深憎惡“末世用禮之失”,(需要注意的是魏源在這里并沒有說老子反對“禮”,而是說老子看到“用禮之失”,意思是說對“禮”的運用偏頗、失當)。但老子并沒有徹底失去信心,相反世道之亂,反倒激發出老子的信心和力量來,“疾之甚則思古益篤,思之篤則求之益深。懷德抱道,白首而后著書,其意不返斯世于太古淳樸不止也。”[25]社會愈是動蕩不己,老子愈是痛心疾首,愈是憎恨、厭惡末世之亂,其思古之情愈是深厚,愈是思古之情深厚,其追求的信心、力量愈是深刻、堅定,于是老子不顧自己年老白發,奮筆疾書,他要向世人闡明“真常不變之道”,教人懂得事理,世道再變,弊端再多,即使混亂不堪,但是,總有一種“真常不變之道”永恒存在,并且這種“道”與人類始終共存下去。
魏源認為《老子》能救世最有說服力的證據就是西漢初年運用黃老之學取得天下大治的歷史事實。他說:
夫治始黃帝,成于堯,備于三代,殲于秦,迨漢氣運再造,民脫水火,登衽席,亦不啻太古矣。則曹參、文、景,斫雕為樸,網漏吞舟,而天下化之。蓋毒庯乎秦,酷劑峻攻乎項,一旦清涼和解之,漸進飲食而勿藥自愈。蓋病因藥發者,則不藥亦得中醫,與至人無病之說,勢易而道同也。孰謂末世與太古如夢覺不相入乎?[26]
秦湯方燠,九州為爐,故漢初曹參、蓋公沐之清風而清靜以治。若乃席豐履豫,泰久包荒,萬幾業脞于上,百慝養癰于下,乃不厲精圖志以使民無事,而但以清談清靜為無事,有不轉多事者乎?皇春帝夏,王秋伯冬,氣化日禪,歲犧黃復生,不能返于太古之淳。是以堯步舜趨、禹馳湯驟,世愈降則愈勞。況欲以過門不入、日昃不食之世,反諸標枝野鹿,其不為西晉幾希?[27]
曹、參、文、景之治,給了魏源一個信心:這就是即使到了“弊極”的末世,只要正確解釋、運用《老子》的思想,也能改變衰敗、壞亂的世道。問題在于如何正確解釋、運用?魏源認為:“文、景、曹參之學,豈深于嵇、阮、王、何乎?而西漢、西晉、燕、趙焉。則晉人以莊為老,而漢人以老為老也。”[28]在魏源看來,文、景、曹、參之學,并不深奧玄義,但他們能解決現實問題,原因在于他們掌握了老子本真的思想,即他們解釋老子的路數是正確的,即學術應為治術服務。
魏源認為“晉人以莊為老”,學走了樣子。而“漢人以老為老”,是真正學到家了,遂把江山社稷整治的很好。魏源對諸子之學老子反而學走了樣子進行了評述:
老氏徒惟關尹具體而微,無得而稱焉。傳之列御寇、揚朱、莊周,為虛無之學,為為我之學,為放曠之學。列子虛無,釋氏近之,然性沖恉邃,未嘗貴我賤物,自高詆圣,誣愚自是,固亦無惡天下。揚朱而刑名宗之,莊周而晉人宗之。入主出奴,罔外二派。夫楊子為我,宗無為也,莊子放蕩,宗自然也。[29]
魏源認為老子之后,其后人依據對其學說的不同理解分化為列子的“虛無之學”、揚朱的“為我之學”、莊子的“放曠之學”。這可否看做是魏源對老學流派的一種解釋呢?從魏源對列子、揚朱、莊子等諸子的批評來看,似乎可作此解釋。魏源認為揚朱為解老之一派即“刑名”派所尊崇,莊周則為晉朝清虛玄談人士所尊仰,共同特征是“入主出奴”,顯然為“罔外二派”。這是否也可以認為是一種解釋呢?還有,魏源明確指出揚朱和莊周這二派,即學術走向各執一端:揚朱將無為發揮,為為我之學;莊周將自然發揮,為放曠之學。這二派成為老學史上的經典派別。
魏源認為老子的其他學生列子、揚朱、莊周,學《老子》皆走了樣子,與老子原義相去甚遠。而且,魏源指出他們幾個曲解老子就在于各自抓住了老子思想中的一點而各走極端:“楊子為我,宗無為也;莊子放蕩,宗自然也”。魏源指斥這種極端簡直就是有“惡天下”。魏源是受儒家正統思想訓練出來的人,他對揚朱的“貴我賤物,自高詆圣,誣愚自是”這種看法可能來自孟子,從行文能看出魏源對揚朱甚為鄙厭。
魏源顯然秉持傳統說法,認為列子虛無。他對列子的虛無之評價還是中肯的,認為列子的思想與“釋氏近之”,基本把握住列子思想的主旨。魏源在《老子本義序》中就很明確地說到:“其實開佛老之先者,莫如列子,故張湛《列子注敘》曰御寇宗旨與佛經為近,不獨西方至人皆不言而自化、無為而自治一章而已。要之《列子注》莫善于張湛。”魏源認為列子“固亦無惡天下。”由此可見,魏源評價一種學說的標準主要看它對社會的效果如何。這也就不難理解魏源解老的出發點――從社會功效來解釋老子為救世之書。在魏源看來由于列子思想接近佛教,故而對社會危害不大,而揚朱、莊周都對歷史影響很大,故而亦造成不小的“惡”影響。魏源將揚朱視作老聃的弟子,這是一種解釋,因為學術界還有其他不同的解釋。
魏源認為老子的學生中只有關尹基本上把握住其老師的思想實質。其特征為“具體而微,無得而稱。”對此特征魏源并沒有作詳細闡釋。
魏源認為諸子曲解《老子》的一個主要原因是對“無為之道”的走失:
無為之道,必自無欲始也。諸子不能無欲,而第慕其無為,于是陰靜堅忍,適以深其機而濟其欲。列子致柔矣,而不知無之不離乎有也。故莊、列離用以為體,而體非其體。申、韓、鬼谷、范蠡離體以為用,而用非其用。[30]
魏源認為,老子之道,無欲是體,無為是用。諸子動輒飚行“無為”,卻無不求無欲之體之心。于是,假借無欲實現濟欲、可欲。魏源指出:
后人以急功利之心,求無欲之體不可得,而徒得其相反之機,以乘其心之過不及,欲不偏不弊,得乎?老子兢兢乎不敢先人,不忍傷人,而學者徒得其過高過激,樂其易簡直捷,而內實決裂以從己,則所見之乖謬使然也。《莊子·天下篇》自命天人,而處真人至人之上。韓非《解老》,而又斥恬澹之學、恍惚之言為無用之教,豈斤斤守老氏學者哉?[31]
不能無欲,在于有“急功利之心”。這里,魏源其實是對“無欲”作了詮釋,無欲不是指沒有欲望,不要欲望,而是指不能有“急功近利之心”,即不能過分追求功利欲望,只要滿足正常且正當的需求欲望就可以了,所謂澹泊、恬淡即是。魏源認為“求無欲之體不可得”的那些有“急功利之心”之后人,在“急功利之心”的驅使下,最終將老子的“無為”思想推向極端。
魏源為老子所謂“過高過激”找到一個理由:
《老子》專述《皇墳》以上。夫相去太遠者,則勢常若相反,故論常過高,乃其學固然,非故激而出于此也。[32]
因為《老子》專門論述三皇之《墳書》以上,由于時代相去太遠,則必然地出現其論述與當前的形勢相反的情況,因而其論調不可避免地出現過高,并不是故意偏激所導致的。而后世解釋老子者,多只就《老子》的字面意思去玩弄,如看到《老子》書中有“絕仁棄義”的字眼,便說老子之道不關心社會,于是便加以引申、演繹開去以至歧義,或者走上莊子那種“徜徉玩世,薄勢利遂訶帝王,厭禮法則盜圣人”的道路,或者產生魏晉名士那種“意糠秕一切,拱手不事事”的偏激,或者導致申韓刑名家的“萬物一付諸法”的極端。
魏源分析到:
老子言絕仁棄義,而不忍不敢,意未嘗不行其間。莊周乃以徜徉玩世,薄勢利遂訶帝王,厭禮法則盜圣人。至于魏晉之士,其無欲又不及周,且不知無為治天下者果如何也,意糠秕一切,拱手不事事而治乎?卒之王綱解紐,而萬事瓦裂。刑名者流,因欲督責行之,萬物一付諸法,而己得清靜而治。于是不禁己欲而禁人之欲,不勇于不敢而勇于敢,不忍于不忍而忍于忍,煦煦孑孑之仁義退,而涼薄之道德進,豈盡老子道乎?豈盡老子非道乎?[33]
魏源提出統治者應當減輕老百姓的賦稅勞役,應當節制自己的貪欲,才是真正的行仁義,也才能真正達到、實現老子之道。
通過以上分析,魏源基本否定了歷代諸子對《老子》不得其真的解讀,在魏源看來,《老子》根本不是什么為個人的退隱避世而作,相反,它發泄了對充滿弊病的現實社會的不滿,是要對有種種弊端的現實社會進行改造——反動,是要對處于朦朧不覺、蒙昧不醒的世人進行挽救,是對圣人式政治家出現而改變世界的期望。
魏源分析老子著書立說的動機就是為了“救世”,魏源認為自己是真正理解了老子。“孔子寧儉毋奢,為禮之本,欲以忠質救文勝。是老子淳樸忠信之教,不可謂非其時,而啟西漢先機也”[34]。魏源認為孔子的思想是想以“忠質救文勝”,這與老子的“淳樸忠信之教”在本質上是一致的。既然孔子的思想得到人們的推崇,老子的思想也不能是不合時宜的。魏源認為,從歷史的發展看,老子的思想對于西漢的無為而治正是起了“啟先機”的作用。
魏源分析老子著書立說的動機就是為了“救世”,魏源認為自己是真正理解了老子。
魏源著《老子本義》是帶著歷史使命感的——“風氣日開,智慧日出,方見東海之民,猶西海之民。”[35]魏源從“無為”、“無欲”為老子之道的體用入手,將自己的“救世”期望與設想順利地帶入他的釋老中,并得出《老子》乃救世之書的結論。魏源的釋讀是有意義的,具有積極的教育價值。因為從這種理解中映照、體現出魏源從儒家的“君子自強不息”之立場釋老的特征:
萬事莫不有本,眾人與圣人皆何所本乎?……曰:以天為本,以天為歸。皇帝、堯、舜、文王、箕子、周公、仲尼、傅說,其生也自上天,其死也反上天。其生也教民,語必稱天,歸其所本,反其所自生,取舍於此。大本本天,大歸歸天,天故為眾言極。[36]
讓這種釋讀出來的精神熏陶、改造、教育、感化自己并勖勉、感動、同化他人,這是對經典詮釋的有意義的價值所在吧。這也正是魏源著述《老子本義》的本意所在。
[1] 鐘肇鵬《魏源評傳》,見《中國近代著名思想家評傳》下冊, 主編 辛冠潔等 齊魯書社 1982年
[2] 見《中華文史論叢》1980年四輯及1982年四輯
[3] 《老子本義·論老子四》
[4] 《圣武記》卷七,《雍正西南夷改流記》
[5] 《中華文史論叢》一九八二年四輯
[6] 歷史上,許多著名人物如蘇轍、王夫之、章太炎乃至毛澤東,都曾將《老子》視作一部兵書。然而,將《老子》視作兵書并且予以系統論述的,則只有唐朝的王真一人。他著有《道德經論兵要義述》。
[7] 《論老子》四
魏源這里所指《河上公注》、嚴遵的《老子指歸》、王弼的《老子注》,被稱為《老子》三大古本。《河上公注》在《漢書·藝文志》未見記載,《隋書·經籍志》開始有明確記載,唐宋以來對此多有爭論,劉知幾疑為偽著。帛書老子甲乙本的現出,應是最古的寫本。依據帛書勘校,發現《河上本》“訛誤尤多,不僅非漢人所寫,而且晚于王弼。”(參閱高明《帛書老子校注》中華書局1996年版)
王弼的《老子注》自李唐以來,逐漸逾越河上公本而占上風,學人一般以王弼本作為通行本。該本分為上、下二篇,上篇即道經,下篇即德經。不過,版本甚多,就章節劃分存有爭議。有說八十一章的(《道藏提要》謂:“劉歆<七略>謂劉定向著《老子》為”二篇八十一章。上經第一,三十七章,下經第四十四章。”今觀此本亦上經三十七章,下經四十四章,猶存古式。)也有另外說法,魏源持王弼舊本上下二篇七十九章之說。樓宇烈認為明朝正統年間《道藏》流傳下來的張志向本,可能有兩種。
[8] 〔元〕吳澄,其《道德真經注》為六十八章的分法,他說:“老氏書,字多誤,合數十家校其同異。”“荘君平所傳,七十二章,諸家所傳,八十一章,然有不當分而分者,實為六十八章云。上篇三十二章,二千三百六十六字。下篇三十六章,二千九百二十六字。總之五千二百九十二字。”見《道德玄經原旨序》見《道藏》十二冊第725頁。
《四庫提要》謂其“大抵以意為之,不必於古有所考。”
《道藏提要》謂其“澄學出象山,以尊德性為主,其《老子注》亦多以性理釋之。”
[9] 《道藏》十二冊第820頁
[10] 《論老子》之二
[11] 《道藏》十一冊第699頁。
[12] 《二十五史·宋史》
[13] 《老子本義序》
[14] 《論老子》之一
[15] 《默觚下·治篇十一》
[16] 《論老子之二》
[17] 《老子本義》第二章
[18] 《老子本義》第五十七章
[19] 《老子本義》篇首
[20] 《老子本義》第六十一章
[21] 《老子本義》第二章
[22] 《論老子》之二
[23] 《默觚·學篇二》
[24] 《論老子》之二
[25] 《論老子》之二
[26] 《論老子》之二
[27] 《默觚·治篇二》
[28] 《論老子》之一
[29] 《論老子》四章
[30] 《論老子》 一章
[31] 《論老子》 之三
[32] 《 論老子》之二
[33] 《論老子》之三
[34] 《論老子》之二
[35] 《海國圖志·議戰》
[36] 《默觚·學篇一》
參考書:
1:《魏源集》 中華書局1976年
2:《中國近代著名思想家評傳》上、下 主編 辛冠潔等 齊魯書社 1982年
3:《魏源年譜》王家儉 臺灣中央研究員近代史研究所1967年版
4:《魏源年譜》 黃麗鏞 湖南人民出版社 1985年
5:《魏源對西方的認識及其海防思想》王家儉 臺北精華印書館 1963年。
6:《魏源研究》陳耀南 乾惕書屋 1979年。
7:《清代通史》蕭一山 商務印書館 1927年 上 中 下
8:《三松堂全集》1——5卷馮友蘭 河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
9:《中國學術史講話》楊東莼 北新書局 1932年
10:《道藏提要》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1995年
11:《中國老學史》熊鐵基 馬良懷 劉韶軍 福建人民出版社 1997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