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來(lái)《三國(guó)演義》中曹操形象研究的回顧與思考
紀(jì)德君
【內(nèi)容提要】 20世紀(jì)以來(lái),關(guān)于《三國(guó)演義》中曹操形象的研究,大體經(jīng)歷了三個(gè)階段。其研究?jī)?nèi)容,主要涉及曹操形象的審美認(rèn)識(shí)價(jià)值、“為曹操翻案”,以及《三國(guó)演義》的不同版本中曹操形象的差異等;近20年來(lái),研究者則主要運(yùn)用新的理論視角來(lái)透視、解讀曹操形象,這有效地拓展了曹操形象研究的審美空間。不過(guò),回顧百年來(lái)的曹操形象研究,雖然取得了不俗的成就,但也由此引發(fā)了一些耐人深思的問(wèn)題。 【關(guān)鍵詞】 《三國(guó)演義》/曹操形象/研究回顧/存在問(wèn)題
曹操形象是《三國(guó)演義》研究的重要課題之一。關(guān)于這一課題的研究,如從上個(gè)世紀(jì)初算起,迄今已歷百年。百年來(lái),研究者曾就曹操形象的審美認(rèn)識(shí)價(jià)值、“為曹操翻案”,以及《三國(guó)演義》的不同版本中曹操形象的差異等問(wèn)題,展開(kāi)過(guò)比較熱烈的討論,發(fā)表了許多頗有價(jià)值的研究成果。今天,重新梳理這些研究成果,不僅有助于加深對(duì)《三國(guó)演義》中的曹操與歷史人物曹操的理解和認(rèn)識(shí),有助于推動(dòng)《三國(guó)演義》研究的進(jìn)一步開(kāi)展,而且對(duì)于如何正確地研究、評(píng)價(jià)歷史小說(shuō)中的人物形象等,也是不乏啟迪意義的。
一、20世紀(jì)初至新中國(guó)成立前的曹操形象研究 這一時(shí)期的《三國(guó)演義》研究逐漸經(jīng)歷了從古典形態(tài)向現(xiàn)代形態(tài)的轉(zhuǎn)型,這種轉(zhuǎn)型涉及了文學(xué)觀念、思維方式、研究方法,以及表述方式等諸多方面;表現(xiàn)在對(duì)曹操形象的研究上,學(xué)者們雖承傳統(tǒng)批評(píng)之余緒,尚不脫比經(jīng)附史式的道德評(píng)點(diǎn)模式,但已開(kāi)始嘗試運(yùn)用西方的美學(xué)理論來(lái)分析、評(píng)價(jià)曹操等人物形象。例如,冥飛的《古今小說(shuō)評(píng)林》即以現(xiàn)實(shí)主義的美學(xué)原則為依據(jù),指出《三國(guó)演義》“極力尊崇關(guān)云長(zhǎng),然寫來(lái)不免有剛愎自用之失;寫孔明亦是極力推崇,然借風(fēng)、乞壽、袖占八卦、羽扇一揮回風(fēng)返火等事,適成為踏罡步斗之道士,殊與賢相身份不合矣。……綜觀全書,倒是曹操寫的最好。蓋奸雄之為物,實(shí)在是曠世而不一見(jiàn)者。劉先主奸而不雄,孫伯符雄而不奸,兼之者獨(dú)一曹操耳。……書中寫曹操,有使人愛(ài)慕處,如刺董卓、贖文姬等事是也;有使人痛恨處,如殺董妃、弒伏后等事是也;有使人佩服處,如哭郭嘉、祭典韋,以愧勵(lì)眾謀士及眾將,借督糧官之頭,以止軍人之謗等事是也。又曹操之機(jī)警處、狠毒處、變?cè)p處,均有過(guò)人者;即其豪邁處、風(fēng)雅處,亦非常人所能及者。蓋煮酒論英雄及橫槊賦詩(shī)等事,皆其獨(dú)有千古者也”。[1](P132)這段評(píng)論就通過(guò)關(guān)云長(zhǎng)、孔明與曹操形象塑造的得失比較,較為具體地揭示了曹操形象的真實(shí)性、典型性和復(fù)雜性,給人以耳目一新的感受。 胡適也指出《三國(guó)演義》并沒(méi)有將曹操簡(jiǎn)單化:“平心而論,《三國(guó)演義》之褒劉而貶曹,不過(guò)是承習(xí)鑿齒、朱熹的議論,替他推波助瀾,并非獨(dú)抒己見(jiàn)。況此書于曹孟德,亦非一味丑詆。如白門樓殺呂布一段,寫曹操人品實(shí)高于劉備百倍。此外寫曹操用人之明,御將之能,皆遠(yuǎn)過(guò)于劉備、諸葛亮”。[2]魯迅則指出《三國(guó)演義》的缺點(diǎn)之一是將人物簡(jiǎn)單化、絕對(duì)化了,它“寫好的人,簡(jiǎn)直一點(diǎn)壞處都沒(méi)有;而寫不好的人,又是一點(diǎn)好處都沒(méi)有。其實(shí)這在事實(shí)上是不對(duì)的,因?yàn)橐粋€(gè)人不能事事全好,也不能事事全壞。譬如曹操他在政治上也有他的好處;而劉備、關(guān)羽等,也不能說(shuō)毫無(wú)可議,但是作者并不管它,只是任主觀方面寫去,往往成為出乎情理之外的人。”不過(guò),魯迅又指出,從客觀效果上講,“作者所表現(xiàn)的和作者所想象的,不能一致。如他要寫曹操的奸,而結(jié)果倒好象是豪爽多智”。[3]顯然,魯迅也是基于現(xiàn)實(shí)主義的美學(xué)思想,以真實(shí)性、典型性等審美標(biāo)準(zhǔn)來(lái)評(píng)論曹操等人物形象,才作出這些精辟的論斷的。 而李辰東則針對(duì)胡適《三國(guó)演義序》對(duì)《三國(guó)演義》所作的否定性評(píng)價(jià),圍繞著人物塑造,以曹操等為例,通過(guò)《三國(guó)演義》與《三國(guó)志》的比較,指出作者在塑造人物時(shí)采用了歪曲、改正、選擇、增加、夸張、捏造、附會(huì)史實(shí)等多種手法,并沒(méi)有“拘守歷史的故事太嚴(yán)”,“想象力太少,創(chuàng)造力薄弱”,當(dāng)然也不是“搜羅一切竹頭木屑,破爛銅鐵,不肯遺漏一點(diǎn)”。此外,李氏還探討了羅貫中改塑歷史人物性格的動(dòng)因,指出作者是站在平民的立場(chǎng)上來(lái)寫作的,“他的同情心當(dāng)然也放在平民身上,于是平民建立的帝國(guó)自然成了正統(tǒng),而貴族出身的曹操孫權(quán)必然成了奸賊”。[4]這些評(píng)論無(wú)疑是切合實(shí)際的,也較富有啟發(fā)性。
二、新中國(guó)成立后至70年代的曹操形象研究 建國(guó)以后,《三國(guó)演義》的研究,則比較側(cè)重于探討作品的思想內(nèi)涵。學(xué)者們多以馬克思主義文藝?yán)碚摓橹笇?dǎo),致力于探討作品中對(duì)人民有認(rèn)識(shí)和教育意義的東西,而分析和評(píng)價(jià)曹操形象,也是旨在發(fā)掘其所包含的思想意蘊(yùn)和認(rèn)識(shí)價(jià)值。例如,顧學(xué)頡即認(rèn)為,《三國(guó)演義》中的曹操是一個(gè)“有權(quán)謀,多機(jī)變的“奸雄”,他多疑善忌,口是心非,奸詐兇殘,損人利己,集中地表現(xiàn)了反動(dòng)統(tǒng)治階級(jí)欺詐殘暴的特性。[5]陳涌亦認(rèn)為,曹操在《三國(guó)演義》中被成功地表現(xiàn)為一個(gè)有著無(wú)窮的貪欲和權(quán)勢(shì)欲的封建階級(jí)的陰謀家和野心家,他是一個(gè)在文學(xué)上不朽的否定典型,可以歸入世界文學(xué)中最成功的典型人物的行列。[6]周立波則進(jìn)一步指出,雖然“曹操在羅貫中眼里是個(gè)否定的典型。他在許多篇章里,把曹操寫成了一個(gè)偏狹、自私、兇狠和毒辣的暴君”,但是“曹操的才略,在小說(shuō)里,還是特別鮮亮地顯露出來(lái)了”。[7]顧肇倉(cāng)(即顧學(xué)頡)還特別強(qiáng)調(diào)了曹操形象具有的認(rèn)識(shí)價(jià)值:“作者把這些統(tǒng)治階級(jí)的罪惡,形象地、概括地集中在曹操這個(gè)人物身上,把他塑造成為一個(gè)統(tǒng)治階級(jí)的化身,以便更明顯更有力地揭露和鞭笞他們;以便人民更清楚地認(rèn)識(shí)和憎恨他們。人民在曹操這個(gè)典型人物的身上,認(rèn)識(shí)了統(tǒng)治者的重要方面”。[8]這樣的分析、評(píng)論,可以說(shuō)代表了當(dāng)時(shí)學(xué)術(shù)界對(duì)于曹操形象研究的主要思路和價(jià)值取向;盡管在今天看來(lái)這一研究思路和取向未免狹隘了,研究模式也較為單一(主要是社會(huì)政治批評(píng)模式),但是它們對(duì)于正確地把握曹操形象的精神實(shí)質(zhì),還是非常必要的,也是富有成效的。 到了1959年春天,學(xué)術(shù)界就如何評(píng)價(jià)曹操,還展開(kāi)了熱烈的爭(zhēng)鳴。爭(zhēng)鳴是由郭沫若借新編歷史劇《蔡文姬》和新編京劇《赤壁之戰(zhàn)》為曹操翻案引起的。1959年1月25日,郭沫若在《光明日?qǐng)?bào)》發(fā)表了《談蔡文姬的胡茄十八拍》,稱曹操是民族英雄,但是“自《三國(guó)演義》風(fēng)行以后,差不多連三歲的小孩子都把曹操當(dāng)成壞人,當(dāng)成一個(gè)粉臉的奸臣,實(shí)在是歷史上的一大歪曲。”1959年2月19日,翦伯贊也在《光明日?qǐng)?bào)》發(fā)表了《應(yīng)該替曹操恢復(fù)名譽(yù)》一文,認(rèn)為《三國(guó)演義》作者在否定曹操的過(guò)程中可以說(shuō)盡了文學(xué)的能事,“他知道曹操并不如他所說(shuō)的那樣壞,那樣愚蠢無(wú)能,但是為了宣傳封建正統(tǒng)主義的歷史觀,他就肆意地歪曲歷史,貶斥曹操。他不僅把三國(guó)的歷史寫成了滑稽劇,而且還讓后來(lái)的人把他寫的滑稽劇當(dāng)作三國(guó)的歷史”。1959年3月23日,郭沫若又在《人民日?qǐng)?bào)》發(fā)表了《替曹操翻案》,承認(rèn)《三國(guó)演義》是一部好書,但認(rèn)為“它所反映的是封建意識(shí),我們更沒(méi)有辦法來(lái)否認(rèn)。藝術(shù)真實(shí)性和歷史真實(shí)性是不能夠判然分開(kāi)的,我們所要求的藝術(shù)真實(shí)性是要在歷史真實(shí)性的基礎(chǔ)上而加以發(fā)揚(yáng)。羅貫中寫《三國(guó)演義》時(shí),他是根據(jù)封建意識(shí)來(lái)評(píng)價(jià)三國(guó)人物,在他并不是存心歪曲,而是根據(jù)他所見(jiàn)到的歷史真實(shí)性來(lái)加以形象化的。但在今天,我們的意識(shí)不同了,真是‘蕭瑟秋風(fēng)今又是,換了人間’了!羅貫中所見(jiàn)到的歷史真實(shí)性成了問(wèn)題,因而《三國(guó)演義》的藝術(shù)真實(shí)性也就失掉了基礎(chǔ)”。 引人注意的是,郭文之中引用的“蕭瑟秋風(fēng)今又是,換了人間”的詩(shī)句,乃本自于毛澤東《浪淘沙·北戴河》詞的下片:“往事越千年,魏武揮鞭,東臨碣石有遺篇。蕭瑟秋風(fēng)今又是,換了人間!”該詞對(duì)曹操的文治武功顯然是肯定的。實(shí)際上,早在郭沫若、翦伯贊為曹操翻案之前,毛澤東于1954年就已說(shuō)過(guò):“曹操是個(gè)了不起的政治家、軍事家,也是個(gè)了不起的詩(shī)人”,“說(shuō)曹操是白臉奸臣,那是封建正統(tǒng)觀念所制造的冤案,還有那些反動(dòng)士族,他們是封建文化的壟斷者,他們寫東西就是維護(hù)封建正統(tǒng)。這個(gè)案要翻。”[9]1958年11月,毛澤東在武漢召開(kāi)的座談會(huì)上還指出《三國(guó)演義》與《三國(guó)志》對(duì)曹操的評(píng)價(jià)不同,前者是把曹操當(dāng)作奸臣來(lái)描寫的,而后者則把曹操當(dāng)作正面的歷史人物來(lái)記述,說(shuō)曹操是“非常之人”和“超世之杰”。可是因?yàn)榍罢咄ㄋ住⑸鷦?dòng),加上舊有的三國(guó)戲多是以《三國(guó)演義》為藍(lán)本編造的,所以曹操在舊戲舞臺(tái)上就是一個(gè)白臉奸臣。“說(shuō)曹操是奸臣,那是封建正統(tǒng)觀念制造的冤案”,“現(xiàn)在我們要給曹操翻案,我們黨是講真理的黨,凡是錯(cuò)案,十年、二十年要翻,一千年、二千年也要翻”。[10](P145)由此可見(jiàn),郭、翦為曹操翻案,與毛澤東欣賞曹操并要求為曹操翻案是有著直接關(guān)系的。 不過(guò),對(duì)于郭、翦二老的意見(jiàn),當(dāng)即就有不少學(xué)者表示異議。劉知漸即認(rèn)為羅氏并未完全歪曲歷史上的曹操,“歷史人物的曹操,本來(lái)就是一個(gè)殘暴的、自私自利的極端利己主義者,陳壽《三國(guó)志》沒(méi)有替他掩飾;裴松之《三國(guó)志注》所引用的材料,也沒(méi)有替他掩飾;魏晉以至北宋的‘帝魏寇蜀’派論者都沒(méi)有替他掩飾”。因之,民間藝人在平話和戲曲中就根據(jù)一些歷史事實(shí),按照“撫我則后,虐我則仇”的觀點(diǎn)把曹操的殘暴、陰險(xiǎn)、狡詐加以夸張,以表達(dá)人民對(duì)暴君的憎惡,而羅貫中則“吸取了平話和戲曲的藝術(shù)養(yǎng)料,參考了更多的歷史素材,寫出了曹操的軍事才能,寫出了這位極端利己主義者心靈深處的丑惡本質(zhì),更典型更集中地暴露了統(tǒng)治階級(jí)中所謂‘雄才大略’的英雄的真實(shí)面貌”。[11]李希凡也指出:“對(duì)于替歷史人物曹操翻案,我沒(méi)有什么意見(jiàn),作為一名杰出的封建統(tǒng)治者,曹操在三國(guó)時(shí)代確實(shí)起了歷史上的進(jìn)步作用,應(yīng)該使人們認(rèn)清曹操在歷史上的真面目。但是,對(duì)于把作為文學(xué)形象的曹操和歷史人物的曹操?gòu)街钡氐韧饋?lái),以至擴(kuò)展到全盤否定《三國(guó)演義》……我是不能同意的。”因?yàn)椋膶W(xué)作品的歷史真實(shí),“并非指的是歷史事實(shí)的內(nèi)容,它是更為廣泛地包括著作者本人生活時(shí)代的歷史內(nèi)容”,《三國(guó)演義》中的曹操固然與歷史人物曹操不大一致,“卻并不違背他所處環(huán)境的真實(shí),在這一形象里,作者進(jìn)行了廣泛的概括,集中了封建階級(jí)政治家的多方面的品質(zhì)特點(diǎn)……。為曹操翻案的同志,盡可以為歷史人物的曹操翻案,卻不可能為《三國(guó)演義》里這個(gè)反映了、概括了封建政治家多方面品質(zhì)特點(diǎn)的作為藝術(shù)形象的曹操翻案。因?yàn)樗呀?jīng)不是那個(gè)真實(shí)的歷史人物,而是一個(gè)具有廣泛代表性、概括性的藝術(shù)典型了。”[12]袁世碩也認(rèn)為替曹操翻案,“這就把作為歷史人物的曹操的評(píng)價(jià)問(wèn)題和作為藝術(shù)形象的曹操的評(píng)價(jià)問(wèn)題,完全混為一談了”,“對(duì)于三國(guó)時(shí)代的曹操,應(yīng)該還他以完整的本來(lái)的面目。但是,《三國(guó)演義》中的曹操,卻有著另外的意義和價(jià)值。它是曹操那一類的人物——封建時(shí)代的統(tǒng)治者、政治家的品質(zhì)和精神面貌的特定側(cè)面的更概括、更集中、更本質(zhì)、更典型的藝術(shù)反映”。因此,肯定歷史人物曹操在歷史上的進(jìn)步作用,就不一定非打倒《三國(guó)演義》不可。[13]另外,蘇興也指出:“歷史真實(shí)不等于史實(shí),站在史學(xué)家立場(chǎng)指責(zé)藝術(shù)作品違反史實(shí),這本身就不科學(xué)”,“《三國(guó)志通俗演義》中的曹操是封建社會(huì)政治家的一種典型,典型化程度之所以高,是羅貫中藝術(shù)的筆鋒創(chuàng)造的,一方面這曹操不是歷史上的曹操,一方面正因?yàn)樗皇菤v史上的曹操,才使得他成為封建社會(huì)政治家即剝削階級(jí)陰謀家、野心家(奸雄)中具有最大代表性的藝術(shù)典型。”[14] 這場(chǎng)關(guān)于如何評(píng)價(jià)曹操的爭(zhēng)鳴,不僅有助于全面、正確地認(rèn)識(shí)、評(píng)價(jià)歷史人物,而且也促使許多學(xué)者對(duì)《三國(guó)演義》的材料來(lái)源、曹操形象的塑造,以及歷史真實(shí)與藝術(shù)真實(shí)的關(guān)系等問(wèn)題進(jìn)行了有益的探討。引人思索的是,郭沫若一生寫過(guò)多本歷史劇,曾主張以“失事求是”為歷史文學(xué)的創(chuàng)作原則,因此誰(shuí)會(huì)真的相信他竟連歷史與小說(shuō)的區(qū)別都分不清呢?看來(lái)他當(dāng)時(shí)為曹操翻案確有上述所言的非學(xué)術(shù)因素的影響;同時(shí),恐怕也是基于現(xiàn)實(shí)的考慮,即《三國(guó)演義》在過(guò)去人民生活中的影響的確是太大了,而一般讀者又多習(xí)慣于以讀史的眼光來(lái)讀《三國(guó)演義》,認(rèn)為歷史上的曹操就像小說(shuō)中所寫的那樣,因此要使人們正確地認(rèn)識(shí)歷史上的曹操,就必須向人們指出《三國(guó)演義》中的曹操是對(duì)歷史上的曹操的歪曲,應(yīng)該恢復(fù)歷史上的曹操的本來(lái)面目。當(dāng)然,“翻案”也與郭沫若所持的“藝術(shù)真實(shí)須得跟歷史真實(shí)合拍的原則”有關(guān)。20年后,有人在對(duì)這場(chǎng)“翻案”進(jìn)行總結(jié)時(shí)即指出其局限性:“其一,客觀上沒(méi)有劃清史學(xué)與非史學(xué)的界限”,“其二,郭老等人給歷史文學(xué)定下了一個(gè)藝術(shù)真實(shí)須得跟歷史真實(shí)合拍的原則”,并以此來(lái)苛求《三國(guó)演義》,這給《三國(guó)演義》研究帶來(lái)了一定的消極的影響。[15] “文化大革命”中,在極“左”思潮的煽惑下,《三國(guó)演義》和其他古典文學(xué)作品統(tǒng)統(tǒng)被當(dāng)作封建主義的“四舊”打入冷宮。1974年,“四人幫”為了篡黨奪權(quán),大搞所謂“評(píng)法批儒”,《三國(guó)演義》又被指責(zé)為有明顯的尊儒反法的思想而再遭厄運(yùn)。報(bào)刊上發(fā)表的近30篇文章,幾乎異口同聲地誣指《三國(guó)演義》有一條儒法斗爭(zhēng)的線索貫穿著,《三國(guó)演義》之所以丑化、攻擊、誹謗曹操,而僅僅在于曹操是個(gè)法家,等等。這些文章肆意歪曲《三國(guó)演義》,把曹操形象研究納入了“四人幫”儒法斗爭(zhēng)的軌道,致使《三國(guó)演義》研究特別是其中的曹操形象研究被引向了歧途。
三、20世紀(jì)80年代以來(lái)的曹操形象研究 十年動(dòng)亂過(guò)后,學(xué)術(shù)界為了清理“評(píng)法批儒”所造成的混亂,又重新探討了對(duì)曹操形象的評(píng)價(jià)問(wèn)題。一些論者繼續(xù)就50年代后期為曹操“翻案”的問(wèn)題展開(kāi)了一些討論;有的論者則發(fā)現(xiàn)了《三國(guó)演義》的不同版本中對(duì)曹操形象的處理是有所不同的,還有的論者則運(yùn)用了新的理論視角對(duì)曹操形象加以詮釋,都提出了不少富有啟迪性的新見(jiàn)解。 (一)關(guān)于為曹操“翻案”的問(wèn)題
四、百年來(lái)曹操形象研究引發(fā)的幾點(diǎn)思考 回顧百年來(lái)的曹操形象研究,雖然取得了如上所述的頗為不俗的成就,但也由此引發(fā)了一些耐人深思的問(wèn)題,這些問(wèn)題有的已在上文略作評(píng)議,有的則不易置評(píng)。簡(jiǎn)言之: 其一,用現(xiàn)實(shí)主義的美學(xué)標(biāo)準(zhǔn),諸如真實(shí)性、典型性等,來(lái)評(píng)價(jià)《三國(guó)演義》中的曹操等人物,是否完全適當(dāng)?20世紀(jì)80年中后期,曾有不少學(xué)者圍繞《三國(guó)演義》中的人物是不是“類型化典型”發(fā)生過(guò)爭(zhēng)議。雖然他們的學(xué)術(shù)觀點(diǎn)不同,但運(yùn)用的基本上是西方現(xiàn)實(shí)主義的典型理論。既然如此,我們就有必要追問(wèn)一下,《三國(guó)演義》是不是運(yùn)用現(xiàn)實(shí)主義創(chuàng)作方法創(chuàng)作出來(lái)的;如果不是,那么又怎能簡(jiǎn)單地運(yùn)用典型理論來(lái)評(píng)騭《三國(guó)演義》中的人物呢? 其二,評(píng)價(jià)歷史小說(shuō)中的人物與其他類型小說(shuō)中的人物,是否應(yīng)有所區(qū)別?曾有學(xué)者用“熊貓是熊,但必須像貓”來(lái)譬喻《三國(guó)演義》的藝術(shù)特質(zhì),其意思是說(shuō),歷史小說(shuō)是小說(shuō),但必須與歷史相像。據(jù)此,歷史小說(shuō)中的人物雖然是藝術(shù)形象,但也必須與歷史人物相像。替曹操翻案的學(xué)者,其主要依據(jù)就是,《三國(guó)演義》中的曹操與歷史人物曹操不大相符。而反對(duì)翻案的學(xué)者,則強(qiáng)調(diào)歷史與小說(shuō)的區(qū)別,認(rèn)為歷史小說(shuō)有權(quán)利對(duì)歷史人物進(jìn)行藝術(shù)變形;可這樣也就產(chǎn)生了這種變形是否應(yīng)該有個(gè)“度”的問(wèn)題,以及歷史小說(shuō)中的人物與其他類型小說(shuō)中的人物是否應(yīng)有所區(qū)別的問(wèn)題,若有區(qū)別,那么評(píng)價(jià)標(biāo)準(zhǔn)是否也應(yīng)有所不同? 其三,歷史小說(shuō)人物塑造的歷史真實(shí)與藝術(shù)真實(shí)問(wèn)題。什么是歷史真實(shí)?歷史真實(shí)與歷史事實(shí)是什么關(guān)系?什么是藝術(shù)真實(shí)?它與歷史真實(shí)、歷史事實(shí)的關(guān)系又是怎樣的?歷史真實(shí)與藝術(shù)真實(shí)這一理論命題的提出,對(duì)于研究《三國(guó)演義》以及其他歷史小說(shuō)的指導(dǎo)意義究竟何在?這恐怕不是只言片語(yǔ)能夠說(shuō)清楚的問(wèn)題。按照郭沫若的觀點(diǎn),古代歷史小說(shuō)家羅貫中是根據(jù)他所理解的歷史真實(shí)去塑造曹操形象的,但是以今天的意識(shí)、眼光來(lái)看,也就是以我們今天所理解的歷史真實(shí)來(lái)衡量羅貫中所理解的歷史真實(shí),那么羅貫中的歷史真實(shí)就成了問(wèn)題,因而他創(chuàng)造的藝術(shù)真實(shí)也就失去了基礎(chǔ)。如果照他這樣以今例古,那么所有古代歷史小說(shuō)中的人物和故事,都是不符合今天的歷史真實(shí)和藝術(shù)真實(shí)標(biāo)準(zhǔn)的,因而都是可以翻案的,只要我們想給誰(shuí)翻案,就可以給誰(shuí)翻案。如此這般,豈不是有些荒謬、滑稽了嗎? 其四,“兩種版本,兩個(gè)曹操”研究方法的科學(xué)性問(wèn)題。筆者曾看到一篇題為《明反曹,暗反劉》的文章,論者羅列了《三國(guó)演義》中某些客觀上似乎可以反映劉備虛偽、狡詐的細(xì)枝末節(jié),通過(guò)深文周納的分析后,指出羅貫中并不真心“擁劉”,他的骨子里是“反劉”的,他認(rèn)真地揭示了劉備的偽詐和殘忍。這種看法似乎并不符合羅貫中的主觀創(chuàng)作意圖,也不符合絕大多數(shù)讀者的閱讀感受。究其原因,就在于論者人為地割裂了人物與文本主旨、情節(jié)、環(huán)境、語(yǔ)境,以及其他人物等多重的具體關(guān)系,孤立地分析人物的言行,以至于主觀臆斷,用矛盾的次要方面掩蓋矛盾的主要方面,從而得出以偏概全的結(jié)論。這種情況是否也存在于“兩種版本,兩個(gè)曹操”的研究方法中?這是值得思考的。 其五,建國(guó)以后至六七十年代,研究者多喜歡用階級(jí)論、人性論等觀點(diǎn)來(lái)定性、評(píng)價(jià)曹操形象,這種理論、方法的合理性和局限性表現(xiàn)在哪里?這個(gè)問(wèn)題實(shí)際上牽涉到對(duì)50~70年代國(guó)內(nèi)古代小說(shuō)研究成果的客觀、公正的評(píng)價(jià)問(wèn)題,因而也是值得我們認(rèn)真加以反思的。 以上這些問(wèn)題,無(wú)疑多是令人困惑的學(xué)術(shù)難題,雖然并不易解決,不過(guò)列舉出來(lái),對(duì)于促進(jìn)、深化《三國(guó)演義》乃至其他歷史小說(shuō)中的人物研究,應(yīng)該是不無(wú)裨益的。
【
.jpg)
技術(shù)學(xué)院學(xué)報(bào).jp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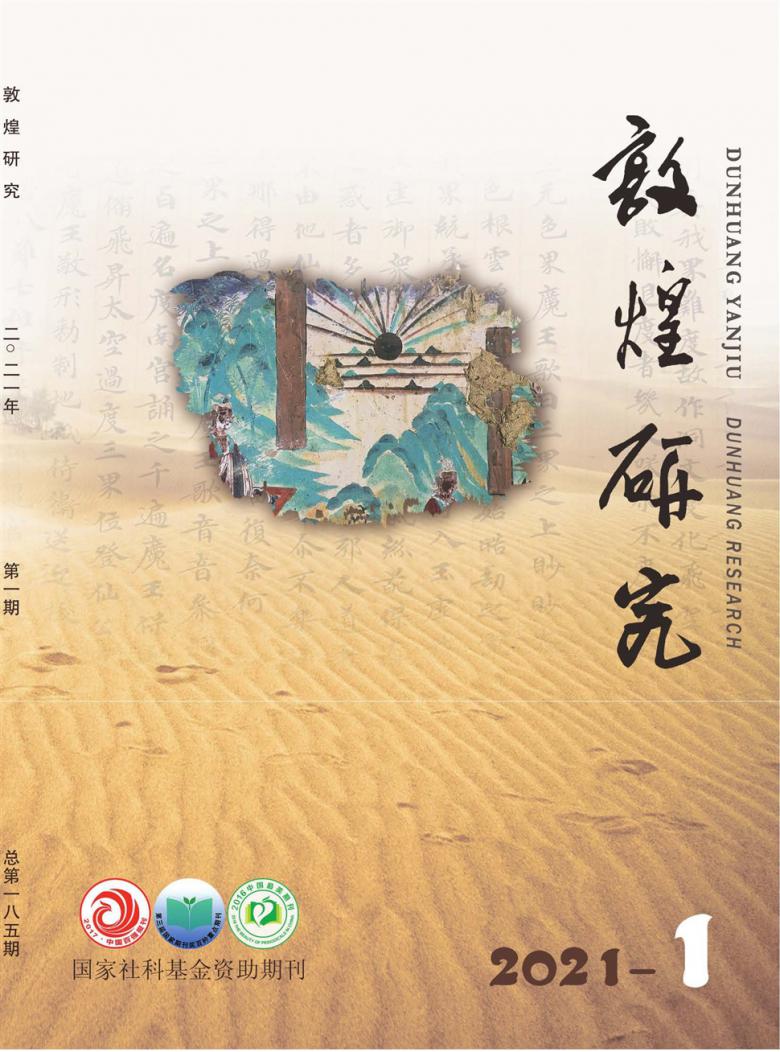
.jpg)
際流行病學(xué)傳染病學(xué).jpg)
報(bào).jpg)
于我們.jpeg)